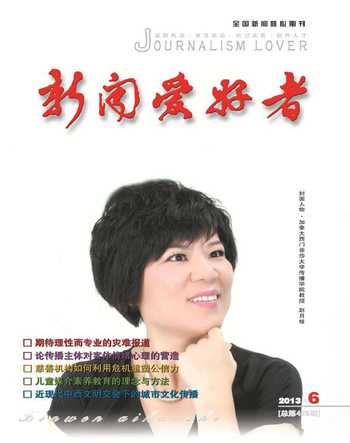论真人秀节目《我是歌手》的成功之道
2013-04-29王超然
王超然
【摘要】《我是歌手》节目作为近年来中国真人秀节目的佳作,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从受众心理、明星现象、节目手法和内涵角度,分析了节目的成功要素,希望对同类节目起到借鉴作用。
【关键词】电视真人秀;湖南卫视;明星;受众;纪实手法;精英文化;大众文化
《我是歌手》源自韩国MBC电视台大红大紫的同名节目,作为湖南卫视精心打造的年度大作,其从今年1月18日正式登陆湖南卫视,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就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收视狂潮,一直霸占同时段的收视冠军,成了街头巷尾人们热议的话题,甚至有学者高呼“真人秀节目的又一个暖春来了”。俗话说没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我是歌手》节目第一季以成功者姿态华丽落下大幕的时候,很有必要对其成功背后值得借鉴的原因加以剖析和探讨。
一、节目创新:变则通,通则久
2000年6月,中国广东电视台《生存大挑战》节目的开播,让中国观众首次领略到了“真人秀”这种全球炙手可热的电视节目的魅力。[1]如今,真人秀节目在我国已经走过了13个年头,泛滥的真人秀节目给观众带来不可避免的审美疲劳。中国电视界和中国观众急需一个全新的节目,用变化迎来一个柳暗花明的春天,因此《我是歌手》栏目呼之欲出。
(一)节目形式:明星成为参赛者。明星作为特殊的视觉符号,长期以来被各种电视节目所运用,旨在博取观众眼球,吸引该明星背后的特定观众。“崇拜明星能给崇拜者带来极大的情感心理满足。明星迷恋是一种抚慰空洞心灵的方式,它同样也是对真实身份与社会角色的寻求。”[2]尤其是在选秀节目中,明星常常以评审的角色出现,对参赛的“草根阶层”的舞台表演和竞技水平加以点评。该种节目的泛滥使得观众已经对这种缺乏创新的节目形式产生了“免疫力”,导致预计传播效果大打折扣。因此为了引爆收视热点,有些节目故意设置明星评审与参赛者的矛盾冲突,并用明星嘉宾的出格言行制造噱头或是恶意炒作。明星本身的人格魅力和美学价值被掩盖了,而成为满足受众“审丑心理”的“丑角”。
《我是歌手》节目打破常态,把明星归还给舞台,极力彰显明星自身的艺术魅力和美学价值,还原正常的明星与观众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顺应了后现代社会的去中心化,消解权威的趋势,艺术家、明星、名人、权威专家……本来是高高在上的,但在‘真人秀中他们也自然地降低到普通参赛者、普通观众的地位。”[3]183这种改变既满足了观众对明星符号的渴望和期待,又使得观众完成了由习以为常的仰视视角向充满交流感的平视视角的转变。
(二)考核方式:观众独揽“生杀权”。赋予观众决定选手去留的权利,作为吸引观众注意力、调动观众参与性的方法在很多娱乐类节目中都已被广泛采用。但往往观众并不是唯一决定选手去留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观众只是作为配角依附于现场评委的选择。而《我是歌手》节目第一次把这种权利毫无保留地交给了观众。在《我是歌手》节目中,500名来自5个不同年龄段的大众评审是决定歌手淘汰与否的最终也是唯一的“审判者”。而专业乐评人和媒体人的点评只是以幕后采访的形式出现,他们既不能直接投票又不能左右现场观众的喜好。这就使得原本掌握在或绝大部分掌握在专家评委手中的权利,第一次完完全全地下放到普通观众手中。权利移交的背后是对观众选择权和个人喜好的最大程度的尊重。“观众在电视传播过程中的主人翁地位,决定了他们具有主动参与的可能性,选择适当的方式参与电视传播活动成为不少观众的心愿和行动。”[4]20赋予观众权利,充分调动观众的参与性,观众不再只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成为集传者和接受者于一身的重要传播环节,并在心理上获得极大的满足感。“明星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有意无意地去迎合大多数追星族的欲望期待,成为受众欲望投射的对象。”[2]这种全新的互动和反馈方式,极大满足了受众的审美需要和个性偏好,使栏目更好地与受众相贴合。
(三)节目内容:保持观众新鲜感。“观众的收视动机建立在人类基本需要的基础之上,电视节目是为了适应观众的各种心理需求而设置的。”[4]13追求新鲜事物是人的本性,对于电视媒体来说,新鲜感是吸引观众收看、打开市场、维持观众收看、培养栏目忠诚度和收视习惯的不二法门,保持节目的新鲜度是维系栏目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是歌手》采用两回合淘汰制,每回合皆由500名大众评审投票决定歌手名次,两回合票数累计产生最终排名,得票数最低的一位将离开舞台。与以往其他同类型的真人秀节目不同的是,《我是歌手》节目没有因为淘汰制的存在而减少参赛的明星人数,而是由另一位新晋歌手填补空缺,新任明星的不断出现也将稳定吸引其追随者加入收视群体。这样的比赛规则,有效避免了观众的审美疲劳,不同的明星以及其本身所呈现的不同演绎风格和美学特征会给栏目带来新鲜的视听效果,也将牢牢抓住观众的注意力。由于复活赛的存在,栏目将明星淘汰所带来的特定观众,尤其是该明星粉丝流失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与此同时,《我是歌手》注重节目内容的不断变化。“转盘选歌”增加了节目的悬念感,“齐秦专场”更是在规定的曲目中展现歌手的唱功,这些不定时加入的新鲜元素给予了节目新的看点,满足了观众求新求变的心理诉求。
二、元素融合:取长补短之道
随着电视娱乐节目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电视视听艺术和娱乐元素被加入到节目中以期满足日益挑剔的观众,从而使得节目的娱乐效果极大提高,收视爆点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多的节目希望通过丰富的表现手法和娱乐元素满足各类特定受众的独特需求,使之紧紧抓住忠实观众的同时吸引更多的游离性受众,弥补原本单一手法带来的诸多缺陷和制约,扬长避短、精益求精,带给节目以新的生命力。
(一)纪实手法和戏剧悬念的“联姻”。从真人秀节目诞生之初,关于它和纪录片之间的界定和区分就一直饱受争议。真人秀节目作为一种娱乐节目类型,充分借用了纪录片的纪实手法,尤其是在野外生存类和室内生活类的节目中,摄像机如同人的眼睛,会全景展现节目参与者的比赛历程,从客观冷静的旁观者角度满足观众“窥视”的心理诉求。但是在通常的选秀节目中,纪录片式的纪实手法如同可有可无的“调味品”,其重要的艺术价值长期得不到重视。《我是歌手》栏目打破常规,对纪实手法的运用在选秀节目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从明星驶抵开始进行全程跟踪拍摄,包括后场、彩排直至上台表演的一举一动都在摄像机的监控之下,使得观众得以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到明星台前幕后的言谈举止,极大满足了受众对明星的窥视和崇拜心理。更为重要的是,《我是歌手》节目加入了大量赛前和赛后的类似独白的采访,面对镜头的明星褪去环绕一身的光环,走下遥不可及的神坛,如同面对面般与观众进行交流,其中也不乏真情流露的时刻,产生了极强的带入感。真实是真人秀节目的命门,尤其是对于以“真情”为节目立足点的《我是歌手》来说,其对纪实手法的重视给观众带来了尤为强烈的真实感,使观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心理体验。
制造悬念作为戏剧创作最常用的基本手法,通过引起观众持续性的期待心理和紧张心情,从而激发并维持观众的兴趣,产生引人入胜的戏剧化效果。《我是歌手》每期首回合竞演都会邀请新的明星歌手参与,其候场、准备、排演的整个过程对观众是开放的,而对于同台比赛的其他歌手却是保密的。这种建立在观众对事态发展有所了解的状态下而产生的期待心理被称作“期望式悬念”。除此之外,由于节目采用末位淘汰制,因此每期节目结尾处公布结果的过程也成为最大悬念揭晓的时刻。观众被压抑已久的期待以及对自我心理评价和最终结果的对照全部积聚在此处获得释放。节目通过大量的参赛者面部特写镜头不断强化紧张感,并且在揭晓结果时故意延宕增加了观众的期待心理。“当真人秀赋予观众决定选手去留的权利时,它既更牢固地锁定了观众的注意力,同时也进一步增加了故事结局的变数,戏剧性更为强烈。”[3]184节目完全由大众评审决定参赛者的去留,其本身就有极强的悬念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悬念的制造与栏目强化使用的纪实手法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由于节目中贯穿始末的纪实手法,为悬念的制造奠定了真实可感、极富感染力的环境土壤。从表情的特写镜头到独白式的心理披露,无一不加深了整个过程的悬念感。
(二)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交融。大众文化作为电视文化的主流长期占据电视的统治地位,并不断压缩精英文化的生存空间。在夹缝中苦苦挣扎的精英文化正在不断衰落,大众文化逐渐成为一切娱乐化节目的制作样本和范式。越来越多的娱乐节目成为简单的复制品,在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精英文化所体现的终极关怀和批判精神备受冷落。《我是歌手》作为大众文化产品,自然也具有商业化和娱乐化的属性,并且与现代观众的世俗心理和文化品位相契合,“从而满足大众群体的精神愉悦,并不断取悦大众群体平庸的日常生活和消闲时光”[5]5。
但是“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不是绝然对立的,大众文化(至少可以说有一部分大众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会成为‘高雅的大众文化,或者‘精英的大众文化”[5]111。《我是歌手》节目与其他大众文化产品相比,其本身就吸取并涵盖了精英文化的某些核心要素。“这种文化不但具有严肃高雅的趣味,而且具有一种强烈参与社会重大问题的责任感和反思批判性”[6],社会责任感和反思批判性作为精英文化内核的体现也同样被《我是歌手》节目所容纳。在第八期节目中,歌手辛晓琪为了缅怀不幸遇难的小皓博,临时把参赛曲目改为《亲爱的小孩》,并身着素衣含泪演唱,这正是精英文化所倡导的社会参与和终极关怀。此外,《我是歌手》自觉担负起传播不同类型的音乐形式以及改变业界浮躁风气的责任。在节目中民歌、摇滚、电子乐、蓝调、爵士等风格迥异的音乐形式都被搬上舞台,并重新焕发出光彩,而且通过乐评人专业中肯的点评和总结引领指导观众。与此同时,《我是歌手》栏目以真情为本,通过歌手现场演唱的方式,用真诚和质朴的表演体现了精英文化的高雅品位,传递着真善美的价值追求。这也是对传统的类似节目中无厘头的低俗噱头和不断触及文化底线的恶意炒作的摒弃和批判。
(三)代际因素的混搭。不同受众有不同的诉求,整合弥补受众群体的差异,找到不同受众群体间的共同之处,从而实现受众规模的最大化,是电视栏目扩大社会影响力、实现节目的传播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关键。“传统的电视综艺节目大都以某一年龄段或者拥有某一具体需求、爱好的受众群体为目标受众,受众面相对狭窄,节目内容局限度较高。”[7]而《我是歌手》成功将年代因素融入节目中去,充分满足受众的怀旧心理,延展了整个栏目的收视群体。首先,参赛的明星歌手既有出道20年以上的齐秦、黄绮珊、黄贯中等人,又有出道10多年的羽·泉、彭佳慧,以及出道6年的尚雯婕和7年的杨宗纬,可谓老中青三代歌手齐聚。“演艺明星显然具备了弥合不同受众群体需求差异的天然素质,能够在节目中担当起吸引不同层面观众眼球的任务”[3]99,不同年代的歌手作为一种年代标志,很容易勾起观众的青春记忆和怀旧心理,并在情感上和认知上与有着相同背景的观众形成共鸣和互动。电视观众可能只是因为对一首歌、一个明星产生的认可,最终会上升为对节目的认可,从而对节目本身产生依赖性。其次新生代歌手可以唱老歌,而新歌也可以被中老生代的歌手演绎,这种明星与歌曲年代的脱离与混搭,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舞台时空,使得不同年代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也为节目增添了更多的娱乐性。此外通过经典歌曲的现代化改编,又使得经典和流行相得益彰,不同的代际元素在不同年代的受众群体间有效贯通,激发了受众群体间的文化认同与归属感,产生了强烈的文化共鸣,使节目吸引了更广泛的受众。
《我是歌手》节目中来自5个不同年龄层面的大众评审,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栏目对不同受众群体的极大包容性。与以往选秀节目只针对青少年受众群体有很大的不同,该节目通过引入年代因素,从而使不同年龄层次的观众的兴趣得到了迎合和满足,并将两代人甚至三代人锁定在电视机前,改变了长期以来国内电视娱乐节目受众过于单一的问题。《我是歌手》通过“代际因素”的叠加,使得老、中、青三代人可以在相同的时空获得彼此不同的心理体验,共同找到契合彼此内心感受、实现内心愉悦的收视点。不同年代的情感和触动融合在一起,充分实现了代际之间感情的传递和沟通。受众群体的扩大和黏性的增强,强化了不同受众群体在群体传播和人际传播中的巨大作用,并借助新型媒介使得节目的影响力呈现倍增式扩散的态势,使得受众群体在数量和层级上得到扩大和延展。
《我是歌手》自开播以来在收视率上的一路高歌猛进以及在社会上引起的广泛共鸣,并不是昙花一现的偶然现象。只有创新才能保持节目旺盛的活力和持久的生命力,也只有真诚才能在打动观众的同时紧紧地抓住他们的心。《我是歌手》无论是在节目内容还是节目形式上都处处展现着新颖的变化以及远远超出同类电视节目的立意与制作水准。在国内电视节目大量同质化和低俗化的今天,众多电视节目都把视线转向了国外的电视荧屏,对他国的同类电视节目或照搬或改造,以期在国内的电视竞争中获取一席之地。《我是歌手》作为“舶来品”在国内市场所获得的成功是不言而喻的,而其中的节目创新和元素融合的手法值得中国电视人好好地体会和思考。
参考文献:
[1]端木凡昌.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发展困境及对策[J].新闻爱好者,2012(6上).
[2]蒋宁平.根源、功能与动力——传播心理视角下的明星崇拜现象[J].学术论坛,2009(12).
[3]莫林虎.电视文化导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4]刘建鸣.电视受众收视规律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5]吴世彩.大众文化的和谐价值[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6]荣耀军.当代中国电视文化研究〓多维话语系统的竞争与共生[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136.
[7]冯丹阳,毛东东.代际元素在电视综艺节目中的传播效果——以深圳卫视《年代秀》节目为例[J].新闻爱好者,2012(12).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