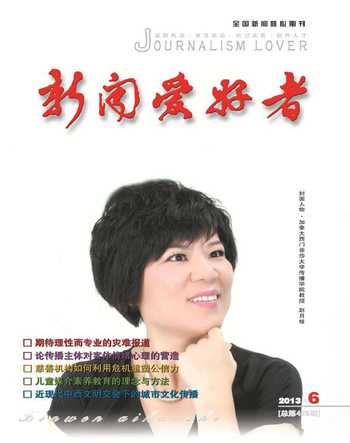天下风云一报人
2013-04-29李彬
李彬
距今三十载的1983年,一位美国记者一再努力,终获中国政府同意,在古稀之年踏访红军长征路,并以一部轰动世界的新闻名作,成就了斯诺及其《西行漫记》后的又一里程碑。这位记者就是知名美国新闻界、驰誉天下新闻人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1908-1993),而那部名作就是《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索尔兹伯里的《长征》,既为人们触摸一段传奇历史提供了鲜活的感觉,也为新时期的中国记者采写新闻、讲述故事展现了新颖的范本。仅看其中的小标题,就足以引发读者的好奇与兴致:《月光下的行军》《“赤匪”的兴起》《担架上的“阴谋”》《魔毯(草地)》《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
作为一代名记者,索尔兹伯里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以合众国际社记者的身份活跃于欧美,二战期间,深入前线,采访苏联,发出《列宁格勒被困九百天》等传世报道。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他又出任《纽约时报》常驻莫斯科记者,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时,他还参加了苏方举行的欢迎宴会。他一生获得的荣誉与头衔包括普利策新闻奖、纽约时报副总编辑、全美作家协会主席等。
1938年,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问世,30岁的索尔兹伯里同千万欧美读者包括罗斯福总统一起先睹为快,从此他就对中国、对长征心向往之,对斯诺钦佩有加。不久,他便在欧洲相遇了这位崇敬的同行:
我见到斯诺是在二次大战期间。这时我俩都是战地记者,恰巧都在苏联采访关于苏联红军作战的消息。我们一起上前线,报道苏联红军如何击退希特勒的部队,如何把他们从苏联的领土上清除出去。斯诺和我自然常常谈到中国……我同斯诺的多次交谈,加深了我对长征的兴趣。[1]
在闻名世界的《西行漫记》里,斯诺曾预言:总有一天,有人会写出一部关于长征这一惊心动魄远征的“全部史诗”。只是他不可能想到,这一心愿由索尔兹伯里实现了。早在斯诺去世、尼克松访华的1972年,索尔兹伯里就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了采写长征的请求。过了11年,当中国大使馆打来电话,同意他的计划时,他欣喜不已地喊道:“我简直不能想象,这世上还有什么比长征更绝妙更刺激的事情!”[2]
于是,1984年,红军长征50周年之际,索尔兹伯里从江西的于都河畔出发,沿着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的行军路线乘车行进,途中也涉足了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部分地区,历时72天,到达了长征的落脚点——陕北的吴起镇。一路上,陪伴他的除了妻子夏洛特,还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长秦兴汉将军,外交部译员、一位老红军的后代张援远——《长征》中译本的译者之一,美国外交官、“中国通”谢伟思——当年在延安就曾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交往深厚,为此在“麦卡锡时代”还同斯诺等一同遭到政治迫害。
时隔20年,张援远想起那次“长征”还不胜感慨:“那是一个真正的老人团呀”,“老头儿那年75岁,他的朋友谢伟思74岁。妻子夏洛特再有两星期就70岁!索尔兹伯里还有心脏病,身上还带着心脏起搏器呢”。张援远回忆说,索尔兹伯里“这老头儿,可不得了”:
拒绝了各地政府提供的小轿车,只坐面包车或吉普车。虽然坐这种车对人的腰、腿、背都是一种“考验”,但好处是坐的人多,可以随时在车上开咨询会、座谈会。因为道路十分颠簸,“老爷子”只能在车上记个梗概。他的笔记本上又是文字又是符号又是数字还有莫名其妙的涂鸦,简直就像“天书”。尽管各地政府对这位“老外”都极为照顾,但因为那时条件限制,也常常会有许多让这几个外国人感到不方便的地方。没有更洁净的水,一瓶水传来传去,几个人对着嘴喝……面对着漫长崎岖的路途,疲惫困乏的身体有时真感到难以支撑。每到这时,索尔兹伯里那种当战地记者锤炼出的意志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就会显露出来。
“这老头儿还真有点‘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的精神。他一路上总是对我们说,中国红军男女完全靠徒步走下来的,我们呢?又有吉普车又有面包车,还有指挥车开道,已经很不错了。”张援远还记得索尔兹伯里在路上不止一次地对他说过:“只有亲身走过这段路程的人才能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出长征中的战斗和艰难困苦——特别是过雪山和草地!”
索尔兹伯里真正开始“战斗”的时间是晚上。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伴着窗外的山风和虫鸣,索尔兹伯里那台在苏德战场就用的旧式打字机便噼噼啪啪响起来。他细细整理着白天的记录,小本上的一切数字符号草图此时都变成了流畅的文字,就连沿途所见的风俗风景也一一写了进去。陪同他的中方人员——军博馆长秦兴汉和翻译张援远歇息了,谢伟思睡了,连妻子夏洛特也进入了梦乡,只有索尔兹伯里和他的打字机还在工作。[2]
由于玩儿命工作,走到西昌时,索尔兹伯里的心脏病犯了,险些丧命,人们赶快用飞机送他去成都抢救,才算化险为夷。回到北京后,他又采访了多位红军将领,包括李先念、肖克、杨成武、肖华、程子华、李一氓、姬鹏飞等,以及几十位红军老战士、老船工、老赤卫队员等。然后,带着几箱资料、图片、照片和笔记本返回美国。1985年,书稿杀青。由于邓小平发话,允许外国人用自己的眼光看待中国革命,于是让他意外的是,中国有关部门除了校正人名地名等外,未对敏感章节增删任何内容。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如同古希腊的特洛伊战争激发了诗人荷马的灵感,创作了两部英雄史诗《伊里亚特》与《奥德赛》,中国的万里长征不仅激发了诗人的喷薄诗情,留下脍炙人口的史诗华章——铁流两万五千里、不到长城非好汉、“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长征组歌》……同时更吸引了新闻人与文化人,书写了各领风骚的名篇佳作,其中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如今最为著名。
作品开篇就先声夺人:“每一场革命都有自身的传奇。”美国革命的传奇,是独立战争最困难的冬天,华盛顿将军与爱国者们在“福吉谷”陷入险境,“度过了那次严峻考验之后,乔治·华盛顿和他的战士们踏上了胜利的征途”。与此相似,“法国革命摧毁了巴士底狱。对俄国革命来说则是攻占彼得格勒的冬宫。当时巴士底狱中仅关押着七名囚徒,而布尔什维克进入冬宫则易如反掌。因为冬宫只有一些年轻人和妇女在守卫。但是这些都无关紧要。它们都成了革命的象征”[3]。
而在索尔兹伯里看来,“1934年中国革命的长征却不是什么象征,而是考验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3]。这是他为长征及其作品定的基调或主题,嘈嘈切切错杂弹的缤纷叙事均由此展开。基调或主题尽管恢弘壮伟,但笔法却娓娓道来,朴素,生动,引人入胜。《长征》给读者的阅读体验以及鲜明印象,首先当数惟妙惟肖的人物故事以及富有历史感的细节。尤其刚刚走出格式化、程式化的年代,如此活灵活现的文字怎不令人耳目一新:
她还记得在吉安第一次参加战斗,在一个小屋里度过的一夜。小屋里亮着一盏没有灯罩的电灯。她从来没有见过电灯,也不知道怎么关灯。最后她拿起步枪,举起来用刺刀捅破了灯泡。这杆带刺刀的枪比她还高几英寸呢。
博古在长征开始时是二十六岁。从十八岁至二十二岁,他在莫斯科呆了四年。长驻莫斯科领导博古他们的王明也只有二十八岁。洛甫当时是三十四岁,算是较为年长的了。
长沙师范学校大门的石头上刻着“实事求是”。这是“徐老(徐特立)”的手迹。毛泽东后来把这一格言当作他政治哲学的基础。
危秀英是个黄花闺女,曾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她记得当她和一位年青战士一起蹚水过河时,引起了那位战士的惊慌。她的黑裙子一直卷到臀部,这位战士喊道:“你受伤了吗?”她意识到,他看到了她的月经排血。他不知道妇女还来月经。在这方面许多战士与他一样无知。
当晚,毛和李先念谈了一次话。毛问李三十军有多少人(李以前指挥第九军,此时指挥第三十军)。李说有两万多。毛问他多大了。李说二十五六。
张国焘一度曾走到周恩来面前说:“你们有多少人?”周天生是位外交家,反问道:“你们有多少人?”张说:“我们有十万。”周回答说:“我们有三万。”周的夸张程度比张的要大得多。
(过草地时)在后卫部队前面的红军指挥部的人们患了可怕的腹泻和痢疾。粗糙的整颗的谷粒和麦粒通过肠道排泄出来时带着血污。面临着饥饿威胁的后卫部队,挑拣着这些谷粒,就像麻雀从马粪中捡燕麦粒一样,他们把谷粒洗净煮沸后就狼吞虎咽地吃下去。
高岗担任了刘志丹的政委。他能力很强,但正如一位中国人所说,他有“乱搞女人”的坏名声。刘志丹对此当然不能容忍,对高岗行为放荡不羁的问题,有一次刘曾提出要处决他。
他(邓小平)打牌争输赢,但不赌钱。输者得钻桌子,邓输的时候,牌友们总是说:“你可以免了。”他总是说:“不,我要钻,这是我们打牌的规矩。”然后,他就钻了起来。由于他的身材矮小,钻桌子对他来说比较容易。[4]
…………
故事,故事,故事!细节,细节,细节!引语,引语,引语!此类西方记者的新闻笔法,如今我们无不习以为常,并已融入中国的新闻实践。我在《新闻记者》撰文《读“天珠”,谈新闻》,所谈清华新闻研究生刘鉴强的《天珠——藏人传奇》(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年)即为一例。熟悉斯诺的《西行漫记》以及《翻身》(韩丁)、《中国的惊雷》(白修德)、《中国震撼世界》(贝尔登)、《震撼世界的十天》(里德)、《光荣与梦想》(曼彻斯特)、《普利策新闻奖》(特稿卷)等作品的人,对这路新闻笔法更不陌生。出自欧美记者的新闻名作,都有类似的特征与风格——注重细节、讲究叙事、栩栩如生的情景、个性鲜明的引语……
虽然过了30年,我对坐在暨南大学图书馆,读着《光荣与梦想》的印象依然深刻难忘,但觉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改革开放初,广州领风气之先,女孩子长发飘飘,走起路来娉娉婷婷。于是,看到曼彻斯特描绘当年美国大学校园风景的一个细节,不由莞尔:由于长发披肩,每个女生从后面看上去都像美女。
再以贝尔登记述解放战争的新闻经典《中国震撼世界》为例,有段描写华北平原的文字,读来同样生动形象,历历在目:
要想对华北平原的地形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只需在地上放一个大写的A字,A字的左腿代表平汉铁路,右腿代表津浦铁路,中间一横代表陇海铁路。A字的顶点是蒋介石的华北集团军的司令部所在地北平;左边底端是他在华中的供应基地汉口;右边底端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所在地南京。
A字上端的三角形可以代表华北平原的中心地带,自从一九三八年以来,共产党就在这个地区与日本人作战。
黄河像一条泥鳅,从群山西面游出来,沿着A字中间的横杠,忽上忽下,蜿蜒穿越过中原,滋养着中华半壁江山。
而贝尔登对中国革命性质及其原因的分析,更是举重若轻,鞭辟入里:
法国大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实现平等和民主,近代德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实现统一,俄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曾是土地革命。中国革命的任务则是同时解决这三种问题。中国必须争取民族独立,因为它仍然处于受外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地位;中国必须争取民主,因为它仍然处于专制统治之下;中国必须开展土地革命,因为它仍然被封建地权所束缚。
至于美国记者科林斯与法国记者拉皮埃尔合写的《巴黎烧了吗》,看起来简直就像一部惊险小说,环环相扣,扣人心弦。而如此传神的“深度报道”,没有一丝一毫虚构,“事事有根据,人人有下落,句句有出处”(董乐山),每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都无不有根有据,都由采访调查所得,让人叹服。同样不得不叹服的是,《西行漫记》《第三帝国的兴亡》《美国新闻史》《巴黎烧了吗》等佳作佳译,都出自同一位新华社的新闻人和文化人——董乐山。他在译介这些名作之余所著的《译余废墨》,同范敬宜的《敬宜笔记》一样,均属“大手笔,小文章”。巧的是,董乐山与范敬宜还是圣约翰大学的校友。
无论受到此类笔法多少熏染,反正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非虚构”作品,包括新闻报道显然日益灵动,千姿百态,如新华社的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作品《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中国青年报》“冰点”的开篇之作《北京最后的粪桶》、《北京日报》的《赤脚医生——二十世纪中国的温暖记忆》、中央电视台的《皮里村蹲点日记》以及黄济人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沙场》、张正隆的《雪白血红》……即使学术著述《苦难辉煌》,风格章法都颇有《光荣与梦想》的韵味。其间,王树增的非虚构“三部曲”《朝鲜战争》《长征》《解放战争》尤为典型。以书写长征而论,斯诺自是先驱,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再上层楼,而王树增的《长征》堪称又一高峰。中央电视台曾邀请王树增在《百家讲坛》开讲长征,果然名不虚传。
或是所见略同的巧合,或是灵机一动的启发,就在索尔兹伯里踏访长征的1984年,《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也走上长征路。不同的是,他完全靠两条腿一步一步“丈量”了万里长征路,而且严格按照红一方面军的路线和日程行进。所以,他成为第一位名副其实重走长征路的记者。每到一地,他都将当日见闻写成新闻,发回报社。于是,从1984年10月16日到1985年10月19日,读者每天都能在邓小平题写报名的《经济日报》上,读到这组系列报道——《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仿佛随他过湘江、渡赤水、攀上娄山关、跨越大渡河,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如他后来回忆道:
1935年1月7日夜里两点,红军打开了遵义城门。50年后的1985年1月7日我也必须在同一时辰进城门。在提前到达城门口的1个小时58分的大雨天气中,我脱下雨衣用棍子一撑当帐篷,搬了砖头垒起了“办公桌”,在忽明忽暗的烛光下写完稿子,用明码电报发回北京。
犹记一年冬天,我在清华主持“名记者研究”课程,邀请各路名家来给新闻学子传道授业,上课时间是晚上7点20分。邀请罗开富那天的下班时分,京城突然纷纷扬扬卷下一场大雪,冰天雪地,交通瘫痪,许多人辗转跋涉,午夜或凌晨才到家。时任经济日报常务副总编辑的罗开富,5点许离开报社,赶来清华,结果也陷在路上,寸步难行。一两个小时中,我一边安顿学生,一边不时同他联系。眼看天气越来越糟糕,觉得今晚课程恐怕够呛,便建议他打道回府,以后再说。而他不肯轻易罢休:长征路都走过了,这点儿困难算什么,今天就是爬也要爬到清华!走过长征路的人,确有一种精气神儿,当然最后还是劝他折回了。
继1985年《长征》问世,索尔兹伯里又在1988年出版了《变革时代》,中译本题为《天下风云一报人——索尔兹伯里采访回忆录》。在“卷头语”里,他提到自己敬佩的三位同行:以报道十月革命著称的约翰·里德、同中国革命息息相关的埃德加·斯诺、涉足古巴革命的《纽约时报》记者赫伯特·马修斯。他还说道,中国是他“儿时及今心中之麦加”。拙著《传播学引论》从1993年第一版到2013年第三版,一直引用书中记述的一段里根逸事,以说明“拟态环境”的影响。
有一次里根接受记者采访,当谈到美国的种族问题时信口说道:“我们美国真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地方!你们记不记得就在珍珠港事件后的一天,罗斯福总统一道命令就取消了美军中的种族隔离?”记者一听不对头,美军中的种族隔离是到二战结束后,杜鲁门当政时才取消的嘛,为此还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里根对记者的反驳并不介意,又耐心解释说:“怎么不是,你忘了吗?当时珍珠港一艘军舰上有位黑人厨师,当全舰官兵都打光时,他抱起一挺机枪对空扫射,结果击落一架零式战斗机。于是,第二天罗斯福就下令取消美军中的种族隔离。”听里根这么一说,记者才算明白是怎么回事:“总统记得一点也不错,但那不是事实,而是一部电影里的情节。”[5]
距今二十载的1993年,一代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别了一生钟爱的新闻工作。按照其生前嘱托,那台伴随他半个世纪,从苏德战场到万里长征的老式打字机留给了儿子;那个随身携带踏访长征路的心脏起搏器送给了中国。当年5月,当张援远把这件遗物转交中国军事博物馆时,在场许多人眼圈都红了。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斯人已逝,长征魅力永恒:
(长征)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我想,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被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6]
参考文献:
[1]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M].过家鼎,程镇球,张援远,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中文版自序”第1页.
[2]秦晓鹰.索尔兹伯里和他的《长征》故事——访外交部翻译室主任张援远[N].中国财经报,2004-10-23.
[3]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M].过家鼎,程镇球,张援远,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1.
[4]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M].过家鼎,程镇球,张援远,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33,80,86,91,279,282,312,337,400.
[5]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天下风云一报人——索尔兹伯里采访回忆录[M].粟旺,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0:309.
[6]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M].过家鼎,程镇球,张援远,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中文版自序”第4页.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过家鼎、程镇球、张援远等译,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王树增:《长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