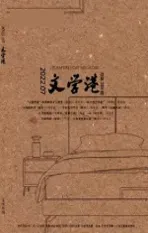在乡卫生院的日子(三题)
2013-04-29干亚群
干亚群
医生不是在吗
第一天,我第一次坐门诊。一间十平方米的门诊室里有二张合并起来的桌子,旁边摆放着两把木凳,那是为来看病的人准备的。过去了二十分钟,除了我自己的座位,其他还是空荡荡的。隔壁是内科,不时有凳子移来移去的声音,还夹杂些其他,有打招呼的,也有询问的,拖着当地浓重的口音。
我突然有些无聊起来,翻翻医学书,但目光时时从书上游离,期待有人来。在县级人民医院实习了一年,给患者开过不少方子,做过一些手术。如今身边没有来自带教老师或严厉或温和的目光,开好的处方不必在自己签名上划一条斜线,添上老师的名字。已被人称作医生了,那个称呼虚空着,需要一个一个的方子来填充。
门口闪了一下人影,随即有两个人嘀嘀咕咕的声音。很快,两人的声音消失了,脚步声却在走廊里响起。难道她们没看到我?我走过去把门往后推了推,继续回到座位上。一会儿,有一位年约三十多岁的女人站在门口,环视一周后,目光从钱医生的座位上移到我这儿,但又很快瞟了过去,自言自语地说,阿姐不在。说完转身离去。又一会儿,有两位中年妇女走进来,一个朝里面的检查室张望,一个问我,秀娣在不在。秀娣是我对面的同事。我称她钱医生。我回答说,她今天休息。那个人上上下下地打量了我一番,欲言又止。这时,又进来一个妇女。她一口就说,医生不在呀。说完,她似乎有些不甘心,伸长脖子朝里面瞅了瞅。刚才张望过的一个女的说,确实不在。三个人像商量好似的,一个个走出了门诊室。
不一会儿,后面响起她们此起彼伏的喊声,那是在叫钱医生。她们一个叫秀娣,一个喊秀娣姐。钱医生把家安在医院里,即使休息也住在医院。钱医生风风火火马上赶来。她还在走廊里时,就听见她有些抱怨,今天我休息。旁边有人小心翼翼地说,医生不在嘛。钱医生闻此言不好再说什么。她一进门,看见我正坐在桌前,不由得提高声音,“医生不是在吗?”钱医生说,“这可是从卫校毕业的,人家是正儿八经的医生。”这几个人脸上疑疑惑惑,不知是谁低声说:“还是个娃娃嘛。”
那年我从卫校毕业,分配到离家有百里远的一家乡镇卫生院。在医院的第一个月过了十九岁的生日。那时的我看上去像一个高中生,而且她们一听口音知道不是本地人,不免有些生疏,甚至怀疑会不会看病。妇产科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科室,每年有二百多个产妇建立产检卡。妇产科的医生数算最多了,有两个半医生,说半个是因为有个医生还兼着牙科,白天上牙科班,只有轮到夜班时才值妇产科班。我去的时候当地还有农村接生婆在家接生的现象。整个卫生院连我在内才十四个人,而我是第一个从卫校毕业的助产士。
医院里的医务人员除我是外乡人外,都是本地人。大家有乡缘、地缘的关系在里面,有的还有亲缘,他们不会叫你医生,而称你哥或姐,再大一点的就是叔与婶。倘如有几个病人进来,他们就各自喊自己想找的医生看病,有喊姐的,有喊哥,也有喊叔的。稍怠慢些,他们就站在院子里开始责怪起来,称呼里缺少了尊为姐与哥的亲切。那些个被人称为姐哥的同事,一边笑呵呵地应着,一边赶紧坐到门诊室里。
同事叫我“小干”,于是他们也叫我“小干”。刚开始我很不习惯,似乎自己被人淡化了医生的角色。更让人接受不了的有一次有一位产妇的母亲等我忙好产科的事后,一个劲地称我“小娘”。我听了不高兴了。“小娘”一词在我老家是老人骂小孩不懂事的意思。后来同事向我解释这是当地的一种方言,是母亲跟女儿间的称呼。接下来还遇到一些因为语言上的差异而引起的误会,因为我的方言与当地村民的方言相差很大,再说那时还不习惯用普通话,所以有好几次造成诊治上的困难。好在都有同事在一旁周旋与解释,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半年后我基本适应了他们的语言,而且还会说当地的方言。
密密的针眼
夜间,我听见掌钉的皮鞋声,特别是冬天,像是钉子在凿冰面的声音。
隔壁住的是一位外科医生。我刚到医院那会儿,他刚上班不久。同事告诉我,他得了肝硬化,还患上了杜冷丁依赖症。他的脸色看上去黄黄的,还带点硬涩,懂医的都知道这表明肝脏有问题。因为这个病,他上班很不稳定。
他有一双旧皮鞋,上面的皮皱巴巴的,还开了几处口子。鞋头往上翘着,很僵硬。走起路来,踢踏踢踏。鞋底的鞋钉有好几枚。他那时虽然带着病,但还保持着一个中年男人的形象,走路很挺,脚步沉稳。晚上我们值班两个人,一个妇产科,另一个是全科。如果晚饭后楼梯里传来踢里踏拉的声音,肯定是他。他有个习惯,平时用过晚饭后就不再下楼,窝在宿舍里看电视。遇上值班,不管有没有病人,他必定下楼去办公室坐一会儿,什么也不做,就是一个人捧着茶杯,若有所思地靠在椅子上。一个小时后,楼梯里再次响起他的踢踏声,然后从我的窗前一直响到我隔壁。
有一段时间,他常常是白天休息,晚上9点后起来烧东西吃。一会儿是高压锅“丝丝丝”的声音,一会儿是下油锅噼哩啪啦的声音,再一会儿是拿碗抽筷子丁零当啷的声音,这样会持续一个小时以上。
我一般11点后睡,睡前照例要去一下水龙头边洗漱一番。水斗装在他宿舍门口,于是不免要与他碰见。有时他会主动叫你一声,还会问你要不要吃点;有时干脆一点反应也没有,顾自低着头吃烧出来的食物。他弄出那么多声音,其实烧的无非是一些从老家带来的土豆、芋艿、玉米等五谷杂粮。
这位黄医生后来病情越来越严重,皮鞋已穿不成了。脚上的水肿已很明显,即使穿着袜,也能看到里面一层亮光,那是皮下组织积水的表现。他穿上了他母亲做的布鞋,黑面白底,鞋帮那儿还镶了一层白色。他母亲是村里的一位妇女主任,长得很精干的模样。平时隔一段日子就能见到她,或是为村里计划生育的事,或给他一家送菜送米。鞋子的底纳得特别厚,上面的针线眼密密麻麻,真不知他母亲是怎样纳出来的,就是用顶针顶着也难以穿过去。医院里没有了踢踏声,静的时候可以听出外面有几只鸟在叫。
他的步伐看起来不太稳了,有好几次我看到他有些踉踉跄跄。他扶着楼梯的栏杆,一步一步地下来,眼睛紧紧地盯着台阶。但还不允许别人搀他,同事只好装着没看到。他的脚步变得轻轻重重,有时还会停止很长时间,那是他在歇息。那双布鞋先是被他穿着走,一段时间后被他拖着走,息列索落,一只鞋子朝左斜,另一只朝右斜。
有一天,我听见久违的皮鞋声。我欣喜,黄医生的病好转了?可是,隔了一天,他又穿上了布鞋。他一定是想穿上那双皮鞋的。
他的杜冷丁的剂量远远超过了以前的剂量。以前他打杜冷丁自己打,后来不得已来到注射室打。我给他抽药水的时候,他在一旁看得非常仔细,还一再关照我把药水抽干净。等我抽好药水,他还会拿起被抽光的药瓶再看一下,事后他会不好意思地跟我笑笑,但每次都会这样检查一下。那些针眼让他的肌肉变得很硬,针打下去并不是很利索,如果用力不到位,针尖一不小心就会弯过去。有时他会自己帮着找位置,我顺着他指的地方打下去。他一边跟我说推慢点,一边又让我把药水推净了再拔出来。
杜冷丁是一种被管制的药,黄医生是通过很努力每月才要来几支。如果要不到时,他会变得很暴躁,烟抽得很凶,有时还会摔东西,稀里哗啦,砰……准是他在摔盘子。半晌,医院上面的宿舍里传来一阵“索索索”,他妻子抹着眼泪在扫地上的碎片。他妻子也是我们医院的职工,是一名出纳。她性情温和,长得很漂亮,尽管他们俩说不上恩爱,但也没见过大吵大闹,尤其她丈夫得了这种病后,她曾想方设法为丈夫去购买针剂,哪怕高价也不在乎。她流眼泪,我知道家里又少了几只盘子。
我并不清楚黄医生患上杜冷丁依赖症多长时间了,但一看到他密密的针眼,知道他至少五年以上。这位外科医生最后还是没有熬过肝硬化,吐了很多血。他过世后的几天里,我不敢去水斗倒水。
晚上,我竟然期待走廊里传来踢踏踢踏的皮鞋声。有时,真的会响起,我却恐惧起来,因为,他已去世。
大门口的喊声
我最怕的是大门口突然传来喊声。
晚上值班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值班室里静静地看书,四周静得连叶子落下来都能听到。医院的大门在晚上九点后关上。门口有一盏灯,从夜色降临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工作。白色的灯光把大门照得雪亮,让灯光外面的夜色更加黑暗。
突然传来“突突”的声音,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不由自主地朝大门口望去。如果“突突”声渐渐远了,我才继续集中精力到书上。最让人害怕的是一边响起“突突”声,一边有人在大门口喊“叔”。一听到这喊声,哪怕不值班的,只要在医院里谁都会奔下来。
拖拉机在当时农村还是一种比较奢侈的工具,不是一般人家可以拥有的。不过,每个村子里总有那么几辆。拖拉机农忙时是农耕用具,闲时用作交通工具,每逢市日集镇上停着不少拖拉机,与周围的自行车、手拉车相比,显得很有气派。尤其是主人,戴上满是油污的手套,拿出发动杆,在车头使劲一摇,“突突突”后,跳上驾驶室,一手抓住方向盘,一手摆弄下面的排挡,然后左旋右转,志得意满地奔驶在马路上,弄出一路的声音后开出集镇。
一般病人不会坐拖拉机到医院里来,除非是两种人,一是喝农药的,二是产妇。如果是产妇,肯定叫“姨”或“姐”,声音响亮,镇定而透着喜气,待拖拉机进了大门才冲着院子叫喊。产妇一般半夜三更来医院的比较多,那时我正熟睡中。但只要大门口有人喊“姨”时,我不用门卫阿婆来叫自己早就醒来了,似乎随时在等待一样。哪怕外面天寒地冻,马上一骨碌地爬起来,利索地穿好衣服奔下来。
喊“叔”的,肯定是喝农药的。声音里焦躁不安,甚至是声嘶力竭。人还没到门口,那喊声早就急着奔过来。
那时农村喝农药的特别多,大年三十都有。多是夫妻吵架引起的,而服毒者大部分是女人。村里如有人服农药,左邻右舍都便奔过来,有拖拉机的立马开来,往里面扔几把稻草,以最快速度开到医院。全院所有的人投入抢救,输液、吸氧、洗胃,各司其职。这时亲属陆续赶到,娘家人自然数落起男人来,男人的亲属也跟着责怪,尽管听得出那责怪声里没有真责怪。男人在一旁早已哭哭啼啼起来,央求我们一定要把他的女人抢救过来。大部分女的听到自己男人在边上又是认错又是哭啼,会非常配合我们的抢救,能自己喝水尽量自己喝,然后再呕吐出来。但性子刚烈的,我们只能插管子洗胃。等病人情况稳定后,全部转送到市人民医院,因此绝大部分都能抢救过来。也有个别其实只为了吓唬男人,只喝了一点点,然后假装昏迷过去,当看到男人悔恨不已向自己赔不是时,心里早已原谅了他。所以当我们要插管子时,自己马上一骨碌地爬起来,主动告诉我们喝了多少。
这些喝农药的,其实就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并不是家里真的过不下去。农村的男人都有大男人主义,对自己的老婆爱在心里,但面子上却一定要摆出男人的霸气,一点都不肯让步。有一次,一个女的让男人去买酱油等着烧菜,结果男人久去不回。她到小店去找,发现男人正在那儿玩牌。女人的气一下子上来了,数落了他几句。男人觉得自己的面子没了,便当着别人的面打了她一下。女人回到家里一时想不开,抓起床底下的甲胺磷往嘴里倒。这时男人自觉刚才有些过分,回家准备认错,看到老婆喝农药了,一下子瘫倒在地上。幸亏家里的老人及时呼救,赶忙用拖拉机送来。由于抢救及时,再加上喝得不多,这命才保了下来。因为这件事,这个村的妇女地位倒得到了加强。男人实在害怕女的往嘴里倒农药。
有时大门口不仅有喊声,而且还有人拍打着大门,混乱的拍门声和惊恐的喊声,一下子惊醒值班医生,慌乱地穿上白大褂,一边是啪啪开灯的声音,一边杂乱的脚步声和病人的呻吟声从大门口涌进来。肯定又是外伤病人。寂静的卫生院一下子变得有些零乱,有商量转院的,有声讨肇事的,也有抚慰病人的。半小时后,急救车在雪白的灯光下飞驰而去。大门再次被掩上。
一晃五年,好像一株树苗,适应了乡村的土壤,一天,我被移植进了城里。似乎我收获了满脑子乡村医院的声音。慢慢地,声音在减弱。可是,偶尔,听到车声、喊声,我会想到乡村夜晚的声音,那突然闯入乡村夜晚的声音,那突然闯入医院的声音,背后却经过了慢慢地慢慢地接受,只不过,到了一定时候,突然喊出来——临近生与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