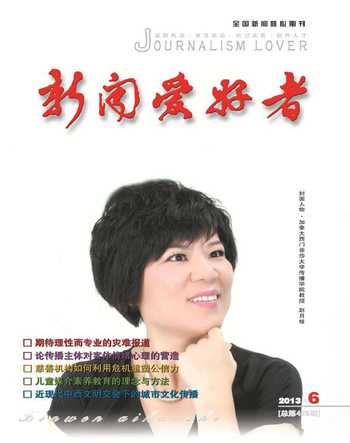保护电子和网络媒介影响下的童年
2013-04-29李凌凌陈楠
李凌凌 陈楠
【摘要】科技进步使当代社会处于急速变化之中,生活节奏加快和工作场所变动导致亲子相处时间缩短,关系疏离,电子媒介成为陪伴儿童成长的“精神保姆”。媒介文化研究者波兹曼曾提出,“童年”的产生归功于印刷媒介的出现,而“电视侵蚀了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如今,以卫星电视、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等构成的全新媒介环境正对儿童社会化构成新的影响与挑战。本文从分析印刷媒介对儿童的影响入手,着重探讨电子和网络媒介对儿童世界的侵蚀,在此基础上,讨论家庭、学校和媒介工作者应该如何为保护儿童的童年做出努力。
【关键词】儿童;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社会化
印刷媒介促进“儿童”概念的诞生
尼尔·波兹曼认为,如果我们把“儿童”认为是一类特殊的人,需要特殊形式的抚育和保护,并相信他们在本质上与成人不同,那么大量的事实可以证明“儿童”的存在还不到400年的历史。[1]162伴随着印刷术的发明,阅读成为一种将成人与儿童分割成两个不同阶层的技能,成人可以将自己的世界与儿童分离开来,并通过教育使儿童逐步获得探知成人世界内容的能力,“儿童”这一概念才得以产生。然而随着电子媒介的产生,儿童通过电子媒介“看”这个世界,阅读文字的障碍被突破,成人与儿童之间获得信息的“不对等”界限逐渐模糊,“儿童”这一概念也逐渐消逝。
印刷媒介的出现,改变了儿童成长的方式,不能阅读的儿童与能阅读的成人之间产生了分化,一个人必须具备读写能力,才能完全接触社会知识。儿童如果不通过读写训练,就被隔绝在大部分的“成人世界”之外,无法窥探其中的秘密。当阅读成为成人享受教育之后获得的特权时,控制“儿童不宜”的信息就轻而易举了。成人通过管控学校教育,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分阶段地让他们了解成人世界的知识,避免儿童过早地暴露在成人社会中,并通过对阅读书目的把关和过滤,将包含着性、权力、金钱、暴力、凶杀、死亡、犯罪、仇恨等隐秘或负面内容的书籍与儿童隔离,从而在儿童心目中构建起一个相对纯净的信息环境,阻止他们过早地知晓成人的秘密,尽量延长他们的童真,保留他们对于世界的信心。
在印刷媒介时代,儿童和成人之间的不对称性还体现在性情上。儿童天性好动、活泼,兴趣广泛,注意力容易转移。而成年人,即有阅读能力的人,通过进入印刷品所营造的抽象符号的世界,逐渐改造了冲动的天性。审慎正式的书面表达方式促进了逻辑思维的发展。而逻辑思维也和儿童从感觉出发的思维方式格格不入。由此,对性情的控制力成为儿童和成人之间的又一种差距。
电子和网络媒介对童年的侵蚀
运用电子技术及数字技术进行信息传播的电子和网络媒介,给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带来了新的变革。同时,这种高度感官化、情境化的传播方式也拆除了儿童和成人之间的信息樊篱,把儿童曝光在一个完全成人化的世界中,从而导致“童年的消逝”。
电子和网络媒介消弭了儿童和成人之间的界限。和书本相比,电视媒介作为一种视觉媒介,拆除了儿童探知成人世界秘密的门槛。电视以影像为代码来展示世界,其符号形式直接诉诸感官,不需要抽象的逻辑思考就能理解和接受,儿童只要学会使用遥控器,按下按钮,就可以在不同的频道之间转换,在没有节目分级制的情况下,儿童直接进入了成人的世界。
随着科技的发展,台式机、笔记本、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等网络终端逐步普及。电脑和手机因其便携、具有强大的多媒体功能和良好的人机交互性能而备受儿童的喜爱。通过自然地点击和触摸,儿童几乎无师自通地进入了成人的世界,所有社会性的话题,都可能暴露在儿童的认知世界里。
从本质上说,电视传播是一种单向的信息推送,而以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网络终端是一种双向媒体,其互动体验要远超电视。另外,电视机通常放在公共起居室里,观看电视是一种全家人共同参与的集体活动,家长可以在观看时为儿童进行必要的节目选择和指导。但电脑和手机因其屏幕较小,其使用是一种更加私人的行为,当儿童通过这些网络终端与其他网民互动时,他们可能被暴露于一些恶意的传播活动中。在西方,恋童癖者通过电脑向儿童发送色情图片进而引诱儿童参与色情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犯罪方式。在中国,约会见网友成为导致少女离家出走乃至遭受性侵害的重要因素。网络色情、网络游戏、网络聊天和约会网友成为儿童网络活动中常见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数字化时代的“原住民”,儿童比作为“数字移民”的父辈在电脑和网络世界中更加如鱼得水。越来越多的父辈感受到,既无法将儿童隔绝在网络世界之外,又对他们的网络使用忧心忡忡,在指导儿童的网络使用上常感到力不从心。
从电视的单向传播到网络的双向传播,使用者的卷入程度加剧,主动性得到提升。但儿童因其能力限制,只能对电脑实行鼠标式参与而非键盘式参与,参与水平较低,缺乏批评性使用的意识和能力,因而难以避免受到媒体的操控。
电子和网络媒介占据了儿童的大量时间和空间。现代生活导致成年人的生活压力加大,生活节奏加快,亲子相处时间缩短,在中国农村,更有超过5800万儿童成为常年和父母分离的留守儿童。[2]电视和电脑由此成为陪伴未成年人成长的“精神保姆”。电视“打开就看”的傻瓜式信息提供模式和五彩缤纷的内容,使儿童几乎不需要任何付出就能得到感官的满足和精神的愉悦,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电视内容的巨大影响。而从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到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儿童的参与方式从点击发展到触摸,参与门槛更低,更符合儿童探索世界的天性。吸引儿童深度参与以获利的商业模式驱动着网络游戏等内容的不断升级,导致不少儿童长期沉迷其中,消耗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并由此形成对网络生活的依赖和对现实世界的疏离。长此以往,儿童将丧失追求更高形式精神满足的动力,越来越多的儿童会舍弃户外活动,宅在家里与电视、网络为伴。而户外活动所提供的体育和社交,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电子和网络媒介侵蚀了儿童的学习方式。声情并茂的电视节目和网络游戏如同一场视听盛宴,其呈现信息的方式倾向于感官而非逻辑,恰好契合儿童的思维水平,其强烈的现场感和冲击力令儿童快速兴奋,相比之下,阅读成为一项沉闷的、需要高度自觉调动注意力的活动。儿童本能的趋易避难造成他们沉迷于电视和网络之中,远离阅读。而电子和网络媒介碎片化的、诉诸感官的信息易造成儿童注意力的分散,逻辑思维发展延后,从而进一步降低了他们的阅读兴趣,使他们丧失学习的自主性,在感官享乐的沉迷中失去自我,心甘情愿地被媒介控制和操纵。
借助于搜索引擎,网络终端几乎可以提供世界上一切问题的答案,许多儿童已经养成“万事问百度”的习惯。这种直接得到答案的方法使儿童跳过了艰苦的思考过程,减弱了他们探索未知世界的乐趣,不利于儿童思考习惯的培养和逻辑思维的养成。
在帮助儿童认知世界方面,电子和网络媒介也并非全能,它基本上只能提供视觉与听觉上的感受,而无法提供味觉、嗅觉、触觉等方面的感受和认知,沉迷电子和网络世界的儿童因而处于麦克卢汉所说的“感官不平衡”状态,损害了人的全面健康发展。
电子和网络媒介的负面内容造成儿童丧失童真,善于模仿。相对于印刷媒介,电子和网络媒介是一种敞开大门的媒介。具体的画面和解说,使儿童和成年人具备同样的权利去感受电子媒介提供的内容,家庭和学校对儿童的信息控制权被稀释,成人社会刻意在儿童面前规避的秘密被透明化了,儿童与成人一样成为电子媒介所呈现的社会信息的受众。儿童由于身心发育的不完善,对媒介的内容甄别和选择的能力不足,过早地接触到性、金钱、犯罪、毒品等影像,常常导致儿童成为这些影像的模仿者与受害者。
过早地接触成人世界的话题,导致儿童和成人在行为举止、语言习惯、处世态度和需求欲望上,甚至身体和外表上,越来越难以分辨了。[1]166政治上意识形态的教化和洗脑,经济上商业利益的垄断和操纵,文化娱乐的表面化和肤浅化,社会认知的成人化和庸俗化等,正在造就一批过早丧失了童真,急于跻身成人世界、善用成人世界游戏规则的“小大人”。而童真乃是想象力与创造力之源泉,丧失了童真的“小大人”,长大后擅长的往往只是低层次的模仿与“山寨”,难以产生超越前辈的创造性贡献。
电子与网络媒介影响下儿童童年的保护
在电子和网络媒介的侵蚀之下,童年的消逝似乎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一个不可逆的现象。但是,童年是人一生的摇篮,童年时期的发展对人的一生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儿童具有极强的可塑性,是“未成形的成人”,在童年时期的不恰当教育,可能造成他们将来失去一个成熟的成年。面对电子和网络媒介冲击下童年的缩短或者消逝,我们应该如何保卫儿童的童年?
儿童自身是保存童年的一股力量。儿童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儿童天真可爱、充满活力,拥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世界的兴趣,这些儿童的天性会成为保卫童年免遭成人世界污染的一股力量。2011年5月,“五道杠”蹿红媒体,一个“2岁开始看央视《新闻联播》,7岁开始每天读《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13岁担任中国少先队武汉市副总队长”、佩戴着“五道杠”的少年引发了人们的诸多争议。但在随后媒体的报道中,一张同班同学对“五道杠”鄙视不屑的表情被媒体再次聚焦。对早早进入成人世界、按照成人世界游戏规则说话行事的主人公和媒体的爆炒,这种来自同伴的不认可就是儿童自发保卫童年和童真的一股力量。
在尼尔·波兹曼的书里,作者向我们引用了他的一些从小学到中学的学生读者提出的异议,他们认为“大多数孩子看电视节目,知道那不是真的……我不认为一个10岁的孩子看了成人节目,就不再是儿童了”,这些意见让人们意识到,儿童自身是保存童年的一股力量,一股道德力量,儿童不仅懂得他们与成人不同的价值所在,还关心二者需要有个界限,如果这一界限被模糊,那么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就会随之丧失。[1]160
成人世界应该为保护童年做出努力。家庭、学校、大众媒体是儿童获得社会化教育的重要途径。作为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家庭和学校理应做出努力,成为监督和制衡媒介传播、保护孩子童年的主要力量。
家长应努力寻找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增加亲子互动和户外活动的时间,在读书、思考和讨论方面为儿童做出榜样。当家长在自然界中让孩子亲身感受到花朵的芬芳,触碰花朵柔软的花瓣,通过问答传授给孩子相关的知识并引导孩子进一步思考和探索时,孩子会得到电子和网络媒介所无法提供的心理和情感满足。与此同时,家长应随时了解孩子的兴趣,和孩子一起接触并使用媒介,从而规范和指导孩子的媒介使用行为。
学校应开设媒介素养教育方面的课程,指导孩子主动地、批判性地、建设性地使用媒介。改变儿童在媒介接触中的被动角色,加强其主体性。比如让儿童在教师指导下自办报纸、杂志、网站和制作电视节目,通过加强主体性,帮助儿童找到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学会自己管理、控制和约束自己。网络时代,学校这一传统的教育场所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学生可以凭借网络资源轻而易举地获得与教师同样的知识库存,教师们在印刷时代凭借一本学生无法获得的教学参考书就可以维持教学活动的优势一去不复返,因此更明智的选择应是与学生建立一种“学习共同体”,通过互动式的教学方式共同去探寻未知的世界。
媒介工作者应当怀着敬畏和爱为孩子工作。儿童节目的一个难题就是内容的生产者基本上都是成人,他们按照自己对于儿童的设想来为儿童制作节目,因此供给和需求的脱节在所难免。媒介应通过加强受众调查来发现孩子的真正需求,制作适合儿童身心发展阶段的电视节目和网络内容,在满足儿童需求的同时不忘对儿童的价值引导和品位提升。在必要的时候对电视和网络内容分级,建立起儿童和“儿童不宜”内容之间的防火墙,呵护孩子的童真和童年。
媒介工具本身和媒介传播的内容构成了媒介影响社会的双重因素。媒介的技术特征(口头传播、书面传播、电子传播等)决定着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比例、信道特征与容量,而媒介的社会特征(媒介的立场、风格、传播内容及其选择标准等)则决定着人们的社会视野和社会认知。电子和网络媒介所创造的符号世界构成了当代儿童成长的主要拟态环境,在儿童认识世界、建立规范、培养共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何发挥媒介对儿童社会化进程的积极影响,减少其负面效应,是家庭、学校、媒体和社会长期面临的课题。
[本文为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村留守儿童媒介使用与媒介素养教育研究”(12CXW027)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R].2011.
(李凌凌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陈楠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