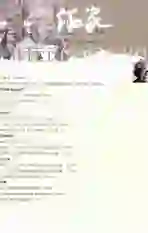洞悉与悲悯
2013-04-29刘威韵
摘要 杜甫写于长安十年的《秋雨叹三首》,起自“秋雨”,落笔于“叹”,借写长安深秋的淫雨,委婉地讽刺了时事,并抒发对自然、人生、国家黎民的种种忧思,蕴涵了诗人洞察、体恤万物的睿智眼光和脉脉温情,体现了杜诗的悲悯情怀。
关键词:秋雨 忧患 讽刺 洞悉 悲悯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杜甫的长安十年是其创作心态发生变化的重要时期,亦是其现实主义诗风形成与成熟的关键阶段。文学史上的许多诗人都经历过类似的阶段,但杜甫却转变得更为典型和彻底,他由轻狂热烈到潦倒愤懑的生命轨迹,恰与唐王朝极盛而衰的国运取得了共鸣,这种共鸣带来的是更为广阔的视野,与其内心缘于深切了解而产生的深切同情,共同形成了杜诗独一无二的悲悯精神。
写于长安十年的《秋雨叹三首》,全诗无一字是“悯”,却处处流露出诗人悲悯的目光。观其诗题,始自一“秋”字生感,而终落于“叹”,宛如露水沿着枯叶的茎脉缓缓而下,而后在一声清响中坠落,简洁而别致。“秋”是传统文学里一段重要的时光,它将不同时代、不同性情的文人聚集到同一个情境里,进行一种超越时空的、集体化的缅悼。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春日的繁华已经远逝,冬日的晦暗和死亡则隐藏在落叶华美的葬礼背后,随时有可能到来。人们被迫直面生命的终结。他们或者努力抓住旧日辉煌的遗物,落叶秋菊;或者追怀亲人和情人的温暖,幻想遥遥无期的重逢;或者哀叹生命的短暂与个人的衰老。而杜甫使“秋”成为一个时代的空气,一则有关唐王朝命运的预言。他赋予季节以社会化的象征意义,即王朝的“秋气”。“雨”在古典诗词中常常扮演着双面角色。有时它作为充沛、滋润、丰盈的源泉,承载惊喜和赞叹,于是有大量的喜雨之作;有时却又作为沾染和玷污勾起无尽的烦忧,此诗显然旨在后者。诗人着力表现了连日淫雨强大的破坏力。作为唐王朝国都的长安,它的繁华却如此脆弱,不堪一击,仿佛宣纸上的图画,在雨水的不断冲击下,渐趋模糊泥烂。“叹”不同于悲秋、伤秋、惊秋,它没有那么用力,看似平稳的情绪里蕴含着难以言说的痛苦,更多的是无奈和忧怅。由一个“叹”字引领而去,“叹”中滋味亦有多重,家愁命舛、民忧国苦一层层漫溢而出。
一 兴盛与衰老
兴衰是文学史里不断被提及的话题,宇文所安的论著里写道,“晚唐诗常常回瞻。过去的迷人时刻,无论是历史的还是诗意的,都引起他们的注意,萦绕着他们的现在”。其实这种回顾,在安史之乱前的杜甫这里已然开始。
其一是一场对话,白头的杜甫与年轻的决明的对话:
雨中百草秋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著叶满枝翠羽盖,开花无数黄金钱。
凉风萧萧吹汝急,恐汝后时难独立。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嗅馨香泣。
首联两句承题中之雨而写,百草之昏晦与决明之鲜亮形成颜色上强烈的反差。底色的灰暗突显出决明的一抹微光。“秋烂死”下笔极狠,言淫雨对植物的毁坏,且暗示了作者此刻心情烦闷。充斥视野的烂草,对困守长安的杜甫来说,有如尸体横陈,加之大雨倾盆,浇灭了一切生机,天地间呈现出的如地狱景象一般。此番情景,仿佛杜甫在长安生活环境的缩影。而带来惊喜的是耐雨的植物决明。决明素来作为明目的草药,在古典诗词中的出现频率并不高,然此时却与举目皆为炼狱的杜甫有了温暖的邂逅。首联与一首现代诗中的画面不谋而合:“天是灰色的/路是灰色的/楼是灰色的/雨是灰色的/在一片死灰之中/走过两个孩子/一个鲜红/一个淡绿。”娇小而鲜艳的决明正如那两个孩子一般,充满了青春的天真和无所顾忌,敢于向晦暗的人世彰显自己的美丽。决明作为青春的符号,具有初生牛犊般的力量。
以下两句承接首联,极言决明色泽之浓亮。“翠羽盖”,“黄金钱”在色彩之外更写兴盛之象,似将上文之“鲜”写到极致,然盛极则衰,诗人将“承”引向顶峰之时,也为下联之“转”作了辅垫。杜甫所经历的,正是唐王朝由极盛转衰的过程,他比任何人更为明白盛极必衰之理。对国之忧患,推而有对万物之忧患,因此在写决明之极盛时,他或许忆起了大唐王朝曾有的灿烂光景,又或许想到了自己风华正茂的岁月。于是下四句便引出了白首的杜甫与年轻的杜甫,与盛唐的对视和对话。由此下联笔锋一转,写对决明未来的担忧,从客观的描写转入主观的话语。“萧萧”,言其力量之众,“急”则体现一种压迫之感,正因为杜甫对奸邪势力来势之猛深有感触,才用了“急”字。“恐汝后时难独立”,这句是以长者的姿态作为过来之人的杜甫看着涉世未深的“杜甫”,发出一声由衷的叹息。杜甫看着决明,明知其和自己一样终要为逼仄的人生所困、为现实所伤,却也无能为力,虽有许多话想警示提醒,却不知从何说起,只好长叹一声“恐汝后时难独立”,如此便罢了。仿佛看到杜甫说此话时微微蹙眉,亦怜亦嗔的神色。
尾联合,“堂上”承首联中的“阶下”,相互呼应,也隐含了“阶下决明”终成“堂上空白头的书生”的意味。“空白头”体现了困守长安的杜甫,不但无法得到有所作为的机会,甚至连温饱都无法满足。在如此困顿之中,看岁月流逝,自有难言的焦虑。“堂上”设置了隔绝,书生面对“阶下”以外浑浊一片的人间,心有余而无奈力之不足。“临风”在此表现地并非潇洒,而是一身萧条的凄戚,临风之寒与馨香之暖,于此处碰撞、百感交集。诗人在长安,亦是严寒之时多,忽闻馨香,便如得共鸣,故而泪下。以“三嗅”承合前句,一嗅见决明之艳;二嗅生忧心;三嗅方得安慰,可见思绪之深。
二 混亂与危机
其二写世之混乱:
阑风长雨秋纷纷,四海八荒同一云。去马来牛不复辨,浊泾清渭何当分?
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妇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禂,相许宁论两相值?
四联呈总分之构,首联承其一写昏雨,二、三、四联分写自然之混乱,乡村之混乱,都市之混乱。不难发现,无论是写景或是言情,诗人的思绪和情感总是这样自然而然的由此及彼,延伸开去。
作者卧病于长安旅次,观窗外不止的风雨,如同自身之疾病,久而不愈,亦不知何时可愈。于是在颓唐中生出一丝绝望。病中之人最怕淫雨,何况又客居他乡,穷困潦倒。于是自然而有下句:“四海八荒同一云。”仿佛一切都被乌云所蔽,连决明那样微弱的光明亦无。“去马来牛”写动物之不辨,“浊泾清渭”写景物之不辨。原本分明的泾渭清浊不辨,是为凶险之兆,刺世之无目。下一联讽刺君之无耳。“禾头生耳”,植物尚且有听世间的呻吟,而君王却不知百姓的疾苦。“黍穗黑”,单以“黑”的直观感受令人心头一沉,“黑”看似简单,实则极重,似推入了绝望的深渊。“农妇田夫”写民之被弃,黍穗尚可见黑,而人是如此渺小,竟完全湮没在浑浊的天地间。可知杜甫写此句是无限怜悯在浊世中挣扎的芸芸众生。客居而卧病的杜甫,或许自身就有无所依傍,漂泊无助之感,因而备觉生命的脆弱。尾联内承于此,农事的荒废必然导致粮之短缺。全诗似乎在讲一个连锁反应,恶性循环,以衾绸换斗米,是拆东补西地做法,毕竟未到寒冬,而米却为日日所必须。“相许宁论两相直?”读此句几可见市民抱衣、被急去换米惶惶然之态。
读此段如历一场海难,处于底层的农人毫无自救之力,瞬间被淹没,而都市之人为求暂保纷纷挤上救生艇,却不知随时有翻船倾覆之险。唐代的长安,华丽壮观又等级森严,以秩序井然著称,而在杜甫笔下出现的却是一座失落的城池。身处长安的杜甫从内部看到了盛唐的毁坏过程,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三 回避与渴望
由其一其二到其三,如同镜头的移动。其一中内部之堂与阶下之外的雨中世界是对峙的,其二缓缓由阶下而去,一路走远,从田野到城郭,而其三中又将镜头收回,转而关注斗室之内:
长安布衣谁比数?反锁衡门守环堵。老夫不出长蓬蒿,稚子无忧走风雨。
雨声飕飕催早寒,胡雁翅湿高飞难。秋来未曾见白日,泥污后土何时干?
“长安布衣谁比数”,长安布衣,自谓语。长安繁华之都,布衣贫贱之至,二者相联,愈显杜甫身处长安之困顿。比数即相提并论,这里写的是文人普遍怀有的孤独感。范仲淹有“微斯人,吾谁与归”之问,东坡有“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尔”之慨叹,庆幸仍有如滕子京、张怀民这样声同气应的友人。而此时的杜甫却是寂寥之至,无朋无友。写于长安的《病后遇过王倚饮赠歌》有“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长相见”语,贫病之际偶得仗义之人款待,使老杜感激眷恋至此,足见其平素的孤独绝望。下一句“反锁”二字透露了作者的心理,他不写反关、反掩,而写反锁,可见并非真的平静,正因为外界的纷扰关不住,才要“锁衡门”,刻意不去接触。前提是“谁比数”,如此萧条却还须“锁衡门”,可见忧思难忘,只是刻意求静的安慰。人们常会逃避自己真心关注的事物,只因越在意,越怕为其所伤。杜甫此刻便是如此,他深爱着门外的世界,也深知这个冷漠的世界对自己并无温情,于是产生了一种矛盾的心理,行为上本能回避,心理上却渴望与之接触。
颔联写“环堵”中的小世界,老夫与稚子面对风雨的不同态度,老夫是不出而“长蓬蒿”,居所生草,心中亦生草;稚子是无忧而“走风雨”,因其天真无知而快乐并无所畏惧,此对比呼应了其一中“白头书生”与决明对比,亦有“恐汝后时难独立”的隐忧。
颈联似写斗室之内,其实又在关注外部情形,“雨声飕飕”,此雨声,有屋院内之雨,亦有院外之雨,诗人锁门以避世,而无边的风雨却早已将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催早寒”更是在催天下之早寒。看似写外界与内部的互相渗透,实写诗人心中波澜难平。“胡雁翅湿高飞难”写自身为恶雨所湿所困,点出诗旨。
尾联诗人因内心之困而发问,看似是失望之语,写君臣俱失道,实则却隐显了杜甫心中之希望与执着。杜诗尾句常作疑问。若陶渊明之诗,陈述之语多,李白则喜自问自答或作反问,而杜甫,正因他没有获得答案,又不作慰己之语,所以始终是执着的。杜诗中大量的疑问之语也值得引起阅读时的关注。
《杜诗详注》评《秋雨叹三首》为“感秋雨而赋诗,三章各有讽刺”,“语虽微婉,而寓意深切,非泛然作也”。认为是影射当时杨国忠恶言灾异,蒙蔽圣上之所为,侧重于其讽刺时事的创作动机。而在讽刺之外,诗人以咏叹之笔,写对自然、人生、国家黎民的种种忧思,担忧之外又有怜悯,而怜悯背后则是诗人洞察并体恤万物的睿智眼光和脉脉温情。正如《杜诗详注》原序中所论,“论他人诗,可较诸词句之工拙,独至杜诗,不当以词句求之。盖其为诗也,有诗之实焉,有诗之本焉”。又“称杜为诗史,谓得其诗可以论世知人也”。可见杜诗之“本实”在于论世知人。杜甫对于时事的关注和洞悉,并非故作高调的辗转附会,而是无不以“至情激发,可兴可观,可群可怨”。莫砺锋先生在《论杜甫的文化意义》中对杜甫的“至情”作了精当的论述,“杜甫的仁爱之心完全来源于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他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了儒家学说的合理性。儒家在倡导仁爱精神时,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把这种精神归因于人的自然本性”。在杜诗中,理性的洞悉与感性的悲悯完满地融合在一起,共同承载着儒家仁爱精神的实体。而杜甫始終执着践行的,也正是这样一种真与善的扩展与张扬。
今人读杜诗,往往以既定的认知套之以爱国主义、道德至圣的赞誉,未读先觉迂腐无趣。然而唯有沉下心来,细细品读其诗句本身,才能寻得一种恰当的语境与真实的诗人交流亲近。此外,诗为心声,不同的诗作往往传达出诗人不同的状态和侧面,而我们常常过于关注那些脍炙人口的作品,而失于对诗歌整体风貌的把握。《秋雨叹三首》虽不是杜甫最广为流传的诗作,却以其独特的风致,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沉思并探寻着的杜甫。
参考文献:
[1] (唐)杜甫,(清)仇占鳌注:《杜诗详注》(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
[2] 莫砺锋:《论杜甫的文化意义》,《杜甫研究学刊》,2000年第4期。
[3] 顾城:《黑眼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4] [美]宇文所安:《晚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作者简介:刘威韵,女,1988—,江苏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