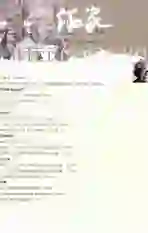被过滤的记忆
2013-04-29吴聪聪李仁杰
吴聪聪 李仁杰
摘要 韩东是一位极具“个人化”特征的作家,他在文本中表现出的对个人化的执着追求和对生活可能性的发掘,使他在中国当今文坛中占有重要一席。《扎根》是韩东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历史的书,更是一部真实的书。小说结束了老一辈作家对“文革”和“下放”题材的概念化处理,摒弃了该类题材的历史意义、政治意义,把一段血雨腥风的历史揉碎成平凡而琐碎的生活细节,用老陶一家时刻不忘的“扎根”诉说了一个“无根”的故事。
关键词:韩东 个人化 文学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随着市场经济中心地位的逐步确立,中国文坛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文学在经济和物质的挤压下走向边缘。这种边缘化的处境使文学轻装上阵,那些原本附着在文学创作中的政治文化、历史积淀被搁置了,中国文学正从集体性风格向个人化风格转型。韩东就是一位极具“个人化”特征的作家,他在文本中表现出的对个人化的执着追求和对生活可能性的发掘,使他在当今文坛中占有重要一席。吴义勤在谈到“个人化写作”时说:“正是在对经验自我的偏执和坚守中确立他们小说写作的基本支点和出发点的……将激情内敛为对生命存在的守望,以经验的自我敏感的触须去触摸生存的真实和本质。经由作家‘经验的过滤,真实和虚幻的界限已经消弭,心理想象与生活实在的边界不再清晰,过去、现在、未来融为一体。”韩东就是这样一个以经验写作的作家,他的创作都源于自我对真实的触摸,他很少写自己经验和体验之外的事情,我们总是能透过文本看到他真实的生存体验和个人渴望。
在韓东的众多小说创作中,“文革”题材的小说占有很大一部分,这与他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韩东说:“我8岁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我们家在生产队、公社和县城都住过。这段生活对我而言印象深刻,以此为材料进行小说写作是很自然的。”下放到苏北农村所发生的点滴构成了韩东记忆中“最温柔的部分”。《扎根》就是以这样的历史背景进行创作的,作品讲述老陶一家被“下放”到苏北一个叫三余的地方安家落户。种地耕田建房子,喂猪养狗挣工分,还主动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鼓励妻子做“赤脚医生”,全家人抱定了在那里“扎根”的理想,做好充足的准备要“打万年桩”。老陶家在乡村忙碌着,过着琐碎、平凡的生活。他们在乡镇和村庄之间穿梭不停,在河堤上翘首等待。希望原本熟悉在城里生活的小陶在陌生的乡间平安长大、娶妻生子,使他们真正扎下根来……但是,就在扎根计划取得一定成效的时候,形势又突发变化,“下放”结束了,老淘家在三余的“扎根”计划被迫止,他只好又重新回到以前的工作岗位上继续生活。命运像和老陶开了个玩笑。回城后的老淘成了著名作家,有过一段转瞬的辉煌。但最后无情的疾病却夺走了他的生命。
一 素材的选择及细节描写
《扎根》描绘的是“上山下乡”和“文化大革命”这段相对特殊的历史年代所发生的故事。对那段特殊年代所进行的文学创作,在近二十年来的文学书写中早已不再特殊,无数的作家涉笔于此,差不多这类作品都以“苦难”和“泯灭人性”作为主要特征来描述的,文学的“加工”和“升华”多少让我们对“文革”这类题材的小说抱有不信任的态度。而《扎根》却突破了相同题材原有的故事框架,去掉了以前同类小说中多余的烘托、夸张的修饰、大批判式的哄闹,把生活原本的样子完整地呈现出来。我们被这种艺术的真实性所震撼,“扎根”在被滤掉了历史和政治的意义后,被还原为那个时代的朴实生活,按韩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直接面临”,面临生活、面临自我、面临生活无尽的可能性。这是我们所盼望的惬意的阅读感受。韩东曾在《扎根》出版后的一次访谈中说:“我关注的不是‘文革题材而是日常生活,只是它恰恰发生在那个时期。这种日常生活是实际的,不是概念……他感觉到的可能是一些琐碎的细小的事情……这些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一样的。”韩东的“文革”题材小说没有伤痕文学中对历史的控诉和激昂的青春,他在创作中追求的是一种生活的真实,摆脱了沉滞的历史文化重负,把一段血雨腥风的历史揉碎成平凡而琐碎的生活细节。
韩东对以往的写作要“反其道而行之”,在生活里是韩东和他的父亲方之,在书里,就是小陶和老陶。在《扎根》第十二章《作家》中我们就会发现两代写书人的不同:“老陶若地下有知,对我的做法肯定是不屑一顾的。在他看来是重要的东西,我认为一钱不值。相反也一样,我所以为的珍宝他也觉得完全无用。”过去写同时期题材的作品里有意无意被删减了的,那些由精致细节构成的人物命运的真实以及那些外在生活和内心生活地真实,我们都可以在韩东的书里看的到。他的长处就在于此,在小说中,他用心的从一些很小的事情、很密切的人物关系展开密度很大的叙事,对细节描写也发挥到了极致。在阅读中,我们确实能体会到《扎根》所带来的新色彩。例如,在写老陶被批斗时,写道:“让小陶兴奋不已的不仅是这送上门来的火热场面,此外还有一种惊喜,翻译成成人的语言就是:‘我们家居然也出了坏蛋!我们家居然也有人被打倒了!这样的荣耀小陶连做梦都不会想到。”在描写下放的车队驶出南京时,写道:“小陶并没有陶醉在这热烈的气氛中,车行至此,他不禁想起了那件丢人的事。‘出来了,出来了。小陶想,觉得那长长的车队就像是一截长屎,终于从南京城里出来了。”韩东甚至用饲养不同动物的时间来划分“下放”的四个时期,如“老陶家养小花的时代,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他津津有味地写怎么盖房子,不厌其烦地叙写养猫养狗,仔仔细细地描绘家常里短、邻里关系。
作家对生活中的细节似乎具有异常的敏感,这使得《扎根》对细细密密的、摆不上桌面的小事显得极有耐力,韩东的笔像放大镜一般透过历史、政治的宏大叙事,把一个个生活细节突显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对《扎根》的叙事追求繁琐。相反,对细节的想象与创造正是《扎根》与众不同的重要表现。韩东具有很强的对细节的记忆、加工、组织、营造和驾驭的能力。在故事的开头,下放途中一位老太太从车上下来到野地里小解,韩东写到:“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就这样白发飘飘地移近金色的草垛”,“有几张像洁白的鸽子一样被风吹着飘向前面青绿色的麦地。”这是对散落便纸的描写,即便是叙述像小解这样最“低俗”、最日常的琐事,也传达出人的生存内部虽细微却不间断地冲突。“他的面孔微微抬起,以便看清前方,由于呼吸的缘故,稀疏的白胡须上挂着一些细小的水珠。”这是写陶文江在严妈河堤上迎接家人的样子,小说结尾处的细节让人印象尤为深刻,老陶去世时,作者没有一句话是写到小陶如何悲伤难过的,而是把笔墨用于描述小陶是怎样忙于买菜做饭给来参加葬礼的众多亲戚吃的,可以说小陶已经麻木到忘记悲伤。“老陶躺在一排塑料万年青后面,身着深色呢料中山装,头上戴着一顶同样质料的帽子,接受人们的鞠躬和致敬。他那愁苦的面容被油脂抹亮了,舒展开来。嘴唇上涂着鲜艳的口红,牙缝里的烟垢也被掩盖掉了。”韩东在谈到小说的创作时说过,对于那段被人不断写过的历史,细节比叙事更重要。他用类似超写实主义的手法,事无巨细、不厌其烦地用工笔画的技巧把生活的点点滴滴勾勒出来。韩东并非是要以彰显的局部来颠覆整体,而是用细节增强整体的密度,构筑起一个坚实的世界,一个任文学话语如何更迭都不为所动的世界。
二 叙事策略及语言运用
对《扎根》的书写,韩东放弃了以往对政治、历史题材所采用的宏大叙事甚至放弃了作家们都无比重视的“文学性”,将经典的叙事还原成了不动声色的、冷漠的、反“文学”的叙述语言;将一波三折的情节设计还原成“流水账”式地叙述结构。情绪的控制与文字的运用都极为收敛、简练,没有丝毫的夸张与升华,所有的描写都极为克制,读者在大量关于栽培庄家、修建房屋、养殖牲畜、邻里纠纷、家庭关系、寻医问药、开追悼会等“表面现象”的叙述和描绘中感受到了那个特殊时代所带给我们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就是生活的真实。通过对这段下放岁月的“流水账”般地叙述,揭示了人在这个世界中的真实处境。小说从开篇写老陶在地图上用红铅笔标出三余的位置,告诉全家人“下放”的地点,直到小说结尾写老陶因病在三余死去,小陶和他的朋友去老陶的坟冢吊孝,作者始终保持着冷静的态度,既不煽情更不滥情,无论生活是多么的惊心动魄。韩东在小说的创作技术上没有采用什么先锋性手段,他用最准确、内敛的语言以及最有力道的腔调,给我们复原了一个朴实无华而又真实的时代图景。小说中,我们看不到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中心思想和主流话语,封闭式的叙事模式、小说不再冠冕堂皇的关心真理、精神与终极价值,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平凡的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日常琐事,并对这些琐事进行反复的咀嚼。韩东曾经说过,他对小说的形式没有什么太大的野心。我们看到韩东构建小说的方式是松散、闲适的,可就在貌似流水账似的叙事背后,却能让人感觉到一种紧绷的张力。
韩东把他自己和人物设计成一种平行的关系,他始终像一个旁观者和局外人一样游离于小说之外。人物的情感完全依托于《扎根》中当时的历史情境,而不是韩东强加于他们的。小说的主要叙述者是小陶,小陶只是一个能看到生活浅层的小学生,韩东一直在让读者通过小陶的眼睛“看”,看得到的是生活零星的片断,而看不到的则是韩东的叙述。韩东并没有刻意挖掘人物的心理特征,也没有刻意制造矛盾冲突来完成小说,而是用那个时代的人物原本的行为举止来支持小说的叙述。韩东似是要不断的把自己从文本中剥离出来,直到剥离彻底为止,但这并不意味着韩东的叙事是纯粹客观的。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太主观了,他对小说中的事实进行选择、有意切断故事发展的惯常轨迹,而转向他所进行的故事可能性的开掘上,他以一种更为本色的方式进行叙述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写作者本身的主观介入。他想让我们从另一个途径回到那段特殊的岁月,为此韩东将他小说叙述中神经绷紧、高度收敛、极富控制的固有品质推向了极致。
韩东的文字功夫是非常另人敬佩的,从诗歌创作再转到小说的写作,多年的锤炼似乎赋予文字一种魔力,平静、从容、丝毫不花哨,所有的描写都极尽节制,可以写到十二分的却往往只用七、八分的力气。韩东对语言的苛求已经到了近乎绝地之境,没有退路了。他是那么吝啬,在文本中形容词之类修饰语的使用次数甚少,你别想找出一句多余的话。从某种角度来说,韩东的语言并不能激起现代读者的阅读兴趣,他剥掉太多语言的装饰,可这回到语言的本身的旅程确是危险的。“小陶站在楼梯口,能看见下面楼梯的扶手。他看见老陶的一只手搁在上面,一截一截地向前移去。然后再转过来,一截一截地向前移动。那只手越来越小,甚至比小陶的手都还要小了,然后就彻底消失了。自始至终,小陶都没有看见老陶的身体在楼梯口出现。”这是小陶看着老陶回干校下楼时的一段描写,这段文字里,我们丝毫看不到小陶的不情愿和恋恋不舍,故事所带来的挥之不去的冷冽感觉会让我们惊讶不已,再也没有什么虚妄的外壳能包裹温暖那个冷酷的时代。人物情感和心理活动的表达让位于现象的直接呈现,含蓄、冷峻的小说品质被充分地显露出来,韩东在这一点上的把握极为准确,因此也就赋予了《扎根》以难得的历史感与真实感。
参考文献:
[1] 吴义勤:《在边缘处叙事——九十年代新生代作家论》,《中国新时期文學思潮研究资料》(下),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2] 韩东:《扎根》,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3] 韩东:《答南方都市报记者》,《明亮的疤痕》,华艺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简介:
吴聪聪,女,1980—,石家庄人,硕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党建,工作单位:石家庄经济学院组织部。
李仁杰,男,1978—,石家庄人,硕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单位:石家庄经济学院人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