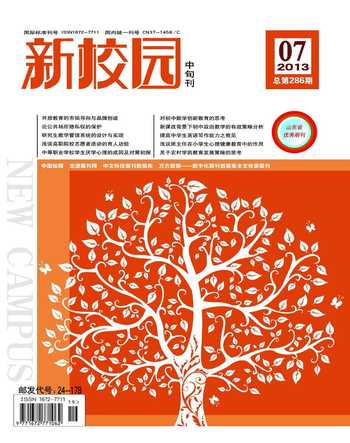如何实现语文教学的核心目标
2013-04-29杨松
杨松
语文学科的性质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所谓工具性,即语文是学习其它学科的基础性学科,其中的语、修、逻、文知识是语文工具性的体现。这些知识蕴含在一篇篇文质兼美的文学作品中。这些文学作品还传承着人类的科学技术和历史文化,担负着对学生思想情感道德品质进行熏陶的任务,因而,语文的人文性不可缺失。正因为如此,新课标规定语文课程的核心目标——学习祖国语言文字的运用。
如何去实现这一核心目标呢?从语言这一形式入手,去领会思想情感这一内容,从而使学生提高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披文入情。
文章的语言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般性的语言和特殊性的语言。文章的多数语言是一般性的语言,这种语言是为了将人、事、情表达清楚而敷设的。要达到对文本的深入理解,通过学习一篇文章达到对某种语言运用的技巧的理解把握,形成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我们还得对一些特别的语言进行咬文嚼字式的品味。
语文教师一般喜欢在文章描写优美的句段上下功夫,所谓优美的语句,常是运用了某种修辞手法或句中有一两个动词、形容词的传神运用的语句。如果我们对语言的运用仅局限在这个层次上,那只属于一般层次性的,要提高对语言文字运用的把握,我们还得从特殊的语言现象入手。
文章的语言,有合乎语法规范的,也有不合乎规范的;有常态下的语言运用,也有非常态下的语言运用。对于不合乎语法规范的,以及非常态下的语言,我们称它为特殊的语言。如果我们在阅读中能发现,并对这种语言的运用进行悉心体会,就能真正提高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
不合乎语法规律的语言,出现在了文章中,这往往是作者别具匠心的安排。抓住这样的语言作品析,就能理解作者深意,从而也会提高自己语言运用的技巧。如《孔乙己》一文,最后有这样一句:“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语句,一般情况下是一个病句。但在这里却表达出深刻的意思:因为没有亲眼见到,只能是推测。但是孔乙己在好手好脚的情况下都难以生存,那么在被打折了腿,又是在这寒冷的冬天里,就只剩下死路一条了。毕竟,这是一个冷酷的社会。孔乙己就是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在人们的笑声中来,又在人们的笑声中去,最后悲惨地死去。作者在这里表达出无限的悲哀与无奈,因而以这句话作为结尾,增添了文章悲剧的气氛。
在现代诗歌的语言表达上,常制造出一种“陌生化”的语言,这种语言常给予读者一种新颖别致的感受。如《天上的街市》中有这样一个句子:“不信,请看那朵流星,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流星,一般用量词“颗”来修饰,在这里为什么不用“颗”而用“朵”呢?经过一番思考,我们才能明白,“朵”是花儿的量词,而花儿是一种美好的事物,带给人以美好的感受,作者在这里用“朵”来表达,正是要引发读者这种联想,表达出天上街市的美丽,牛郎织女生活的美好,激起人们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再如《星星变奏曲》中的句子:“谁不愿意,有一个柔软的晚上,柔软得像一片湖。”用柔软形容夜晚,这明显是修饰不当,夜晚不会柔软,但人会产生这种感受。在夜晚带着安适与甜蜜入梦,这梦不就是温柔的吗?在静谧如诗的夜晚,自由闲适地在这湖边,这不也是柔美的感受吗?诗人在这里要给我们营造出夜的宁静与美好,表达出对心灵释放的追求。诗歌中这种语言现象比较多,这好像是在给读者制造出“阅读的麻烦”,其实,这是在延伸审美的空间。
非常态下的语言,即特定情况下的语言表达,它在表达上有深意。笔者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散步》开头有一段文字:“我们在田野散步:我,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和儿子。”这句话,初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这一句话却很特殊,有什么特殊之处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其一,为什么不说成:我,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和儿子在田野散步;其二,在交代一家人的情况时,为什么将“我”放在前面,不将母亲放在前面。对第一个问题,通过朗读比较,可以得出:改后的句子在表达上显得很冗长。其实还不仅是这个问题,原句将一家人的情况放在后面,前面一个短句简洁地交代了人物和事件,与标题形成呼应,突出地显示了事件——散步。另外,将人物放在后面,也起了醒目的作用。对第二个问题,好像这个人物怎么放都可以。其实不然,如按长幼关系,我的母亲应该放在前,然而课文没有这样表达,那又是为什么呢?从这一家四口人的关系来看,其关系都是以“我”为核心,都是建立在“我”的基础上的,所以,将“我”放在前面。也许,这还是一个表面的现象,更深入的一个原因是,“我”在维持这个家的关系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家的和睦与温馨,全在“我”的妥善处理。文中有一句话做了明确的表达:“不过,一切都取决于我……她总是听我的。”正是因为“我”的重要作用,所以在文章开头的这一句话中,才将“我”放在了前面,这也显示出了文章的主题。对这么一句看似平常的话,如果我们深入去思考,就能得出许多的理解,这对帮助我们理解文本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语言文字是载体,思想情感是内核,二者“唇齿相依”,因而古人在阅读文章中所采取的“披文入情”仍不失为现代语文教学的一种重要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