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沉默的大多数
2013-04-29张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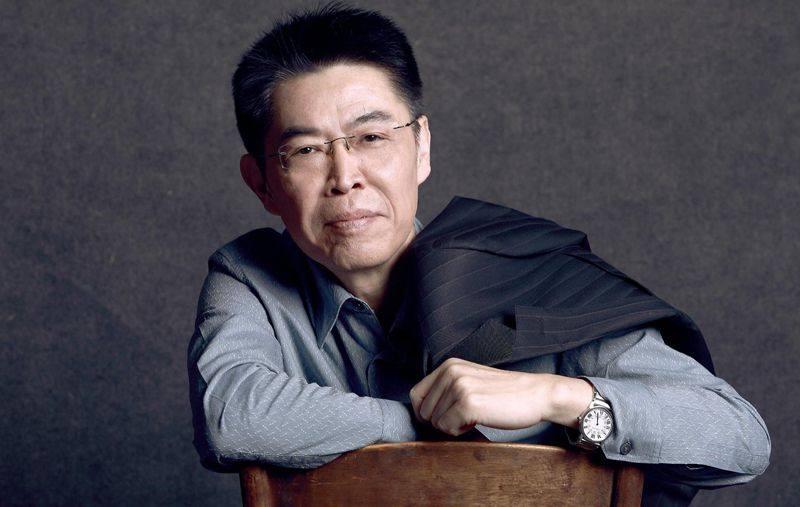

印象
你找到那片净土,整个环境的物理性就不存在了
任何一个小慨率事件如果稍微错位,都不可能成为现在的你。一次看似寻常的结缘,回头望望,其实都意味深长。
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张昭的人生可能有另外一番不同的书写。
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是一个正在恢复自信和商业活力的中国,她忙乱、骚动和热烈。同时对于很多人来说,充满了吸引力。赴美留学的张昭,毅然在香港回归祖国的1997年,回到了祖国。这一年,全球最热映的电影是美国好莱坞拍摄的《泰坦尼克号》。35的他,意气风发。(在此之前的七年,他在美国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后转入电影系,获得电影制作硕士学位。)
回到国内的张昭,收到不少片方邀约。其中有一个电视剧比较特殊,不仅全程需要在美国取景拍摄,而且当他们找到张昭的时候,电视剧已经开机了。也就是说,张昭要做的工作只是,接替上一任导演完成接下来的拍摄。这是一名在当时几乎家喻户晓的大导演,因病入院故拍摄终止。张昭去总政医院看他,谦卑请教工作,发现他无心恋战,令张昭深感意外的是,他为何在盛名之下活得如此痛苦?为何台前的风光带来的却是如此巨大的压力?他得了抑郁症。
从医院走出来以后,北京的天空下起了雨,地面有些滑,躲躲闪闪之下,一辆出租车停在了张昭身边,正准备上车,拉动车门,反复几次怎么也拉不开。见状,司机从车里钻出来,围着出租车绕了一圈,把门打开后,又冒着雨小跑了回去。“就这个场景,我心里一动,联想到那位导演,我问自己:你愿意活得像他那样吗?还是像这位出租车司机,能为别人带来点什么。我谢了他好几遍,他开心得不得了。”人生有一些启蒙点,跟年龄没关系。那一刻的感受,张昭形容说,突然间曙光照到了你。
加之,这期间张昭拍的几部影视作品,市场都不太成功。用张昭的话来说“中国电影当时没有商业市场的概念”,由此,他决定转型,从导演转型当制片人,后来他又转型做公司。“我总结自己的经历就是,不断的在撤退,退居到公共视野之外。其实你退了,往后退,你的事业越大,当然承担的责任也越大。”在复旦大学学信息工程的时候,他当过电视主持人,做过舞台剧演员,组织过学生运动。
而另外一方面,注重细节,思维习惯是以小见大的张昭认为,只有不断地往后退,你的眼睛才能看到更多的人。这双眼睛,曾帮他看到过中国民营传媒企业的希望。
这就是传媒界熟知的“一盘饺子”的故事。2003年冬天的一个早上,刚从美国出差回国的张昭,下了飞机就直奔当时还在紫竹桥办公的光线传媒。他与光线创始人、同为复旦校友的王长田一直谈到中午12点。到了饭点时间,王长田从办公室抽屉里拿出一大盒饺子,“这是我妈包的”。又从另一个抽屉里取出三种辣酱。“一下彻底把我打倒了,要想在中国做事,没有睡草席的力量是不行的。”无论多少次提到这件事,张昭的眼睛里都有光芒。那个冬天一过,他就从上一家“体制内”加入了光线。
在中国的创业环境里,有很多的沙漠,比如政策的沙漠、人才的沙漠、资金的沙漠。王长田倡导“骆驼文化”,平时将脂肪存在驼峰里,如果遇到危机,可以消耗自己的储备。它们置身于“被VC绑架的商业世界”之外,这种反周期生存的方法,在生意场上并不多见。张昭在光线八年,深受其团队文化影响,以至于今天有乐视的同事会对他感叹:“不愧是从光线出来的”。我们采访的地点就在张昭的办公室,与同一水平线上其他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宽敞考究的办公室相比,他的办公环境略显简陋,一张沙发接待来访者,办公桌上摆满文件,背靠着一面白色书柜,每一格都有拉门,也不知陈放何物?看得出他是个谨慎的人。而整个办公室,面积不足25平米,这是他自己的要求。隔壁是一间面积约60平米左右的会议室,他们曾建议张昭在这里办公,被张昭断然拒绝。“不管你今天市值多少,要永远处于一个创业状态。”而在商业社会里,艰苦朴素的风格,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力。
商业领域里还有句老话叫:渠道为王。学理工出身的张昭,相信公式的力量,万变不离其宗。企业里的公式,就是商业模式。商业模式包含了四个内容,产品模式、用户模式、营销模式、盈利模式。他认为中国电影的产业之路,就是渠道。2006年,他成立光线影业的时候,就很清楚自己的定位:不做大片,也不建院线,而是靠发行和营销制胜。
当今天我们津津乐道于光线在电影《泰囧》和《致青春》上创造的票房奇迹时,也许很少人知道张昭曾是一手打造光线发行团队的幕后功臣。“我还记得我面试第一个孩子的情景,他从外地过来。他们现在都跟我关系很好,当年我们是建了一所黄埔军校,后来大家都从光线挖人。”张昭说起来的时候,脸上挂着满足的表情。
张昭的做事风格是严格。在他的团队的工作,你可能会有一些压力。首先,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管理的探索,他有一定的标准,“我的团队文化是这样,什么事你别敷衍了事,这样走不远。”其次,他事无巨细,一个海报都要管。“我到现在都没有年龄感,我不是经常会想起自己是多少岁数的人,跟郭敬明合作,都是很平等的。”
还有一点,他豁得出去。这点更多的是表现在张昭的人生选择上。2011年,光线上市之际,他从光线转投乐视。许多人为他惋惜。虽然这背后的曲折、行业的发展等可能是另外一个商业故事,但单从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随时随地都可以重振旗鼓的乐观自信,非一般人。“我这一辈子就是一个不断重新开始的人,从信息工程到哲学到电影,从科学走向哲学走到艺术,我一直是这个状态。”
“你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勇气?”我试着问。
张昭笑笑,然后回答我。“那天我们公司的一个老总跟我说,你现在是公司所有的高管当中,唯一一个无房无车无户口的人。我现在还是个北漂,所以又怎么样。其实就是说从来没有拥有过什么,那为什么要怕失去呢?那你就永远可以重新开始了。每次我都从一个一年级学生开始,很好。我一直是这样觉得,其实生命的价值就在不断地创造,这个确实是我的人生观。”张昭的坦诚超过我的想象,这一段时间以来,他接受的采访可能超过了之前的所有,我以为我会面对一个随时都能信口开河的人。
又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个纽约的冬天,像所有中国留学生一样,二十八九岁的张昭也靠打工赚取一部分生活费。有一次,在送外卖的过程中,自行车刹车坏了,他措不及防地撞到了电线杠上,裤子破了,眼镜碎了,外卖也撒了,然后瘸着腿,推着自行车一步一步回到餐馆,把当天挣的小费还给他们。他没有抱怨,也不觉得狼狈,很麻木的回到家里,那是一间只够放一张床的小屋。回到家的时候才发现腿上流了好多血,简单清理完伤口,他打开一本教科书《电影导演I》,放在膝盖上,书的第一页什么内容也没有,他盯着这张空白页很久很久........
“对一个男孩子来讲,成长特别重要,经过这些事情,让你体会个人的渺小,人其实不能完全左右自己的命运,我从来不去想那些规定动作,到了几岁该做什么,我是一个严重不走寻常路的人。当一个事情成为你生命的支撑点的时候,你没有那么多的杂念,任何挫折对我来讲不意味着什么,你跟我谈什么房子、车子都没意义。那个空白页是一个很纯粹的很忘我的状态,这是我的幸福感。你找到那片净土,整个环境的物理性就不存在了。”
这也是他多年人生的一个写照。
对话#
我们共谋一个未来
一个职业经理人要藏起自己的个人梦想,要为产业服务。我很认同马云说的一句话: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有职业经理人素质的企业家,或者有企业家视野的职业经理人,把这两个结合起来,个人利益就在企业资本价值和产业回报。
林:前段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我想知道“二张”合作的细节,比如,你们怎么认识的?
张:其实挺简单的,就是一个偶然的场合,一次朋友聚会。我对他接下来做什么感兴趣,他对我离开光线也好奇,就聊起来了。讲到培养新导演、互联网国际化,这是我们共同关心的话题。
林:当时向他抛橄榄枝的公司和个人有很多。
张:有很多,但这个很正常吧。我觉得是巧合也不是巧合,巧合就是说,如果我没去,他没来的话,我们就聊不上。不是巧合是指,冥冥之中我们也应该合作,大家想法一致,都走在产业的这条路上,合作是早晚的事情。我们几十天就谈成了这个合作,其实最重要的是,大家是不是在一条道上走?
林:事实上,张艺谋电影的审美一直保持在那,很难改变。而乐视影业的定位是互联网时代的电影公司,用大数据说话,迎合市场。这跟张艺谋的品位是有偏差的,我疑问的是,他能不能、愿不愿意拍像《泰囧》这样的影片?
张:很好的问题,那我要问你的是,你觉得《泰囧2》还有这样的票房吗?
林:我觉得不会。
张:那好了,你按照这个思路去想。 我没有让他迎合,我跟他的合作,是奔着一个现在还没有呈现出的一个未来去的,然后我们共享这个未来,不是为我们今天服务的。你理解我的意思吧。很多人都用这样的思维想:他来了,对我们现在有什么用?
林:所以张艺谋他也不用着急,现在就呈现一个什么东西给大家看?
张:你说他还需要吗?他得过那么多奖。
林:说实话,这一两年来,我觉得他“胸中块垒酒难浇 ”,挺需要一个证明的。
张:产业这个事情,不是要去满足大家的期待。你满足了今天的期待值,就满足不了未来的期待值。其实价值就在于别人今天看不见你,但是你看见了你为之去努力的东西,这也就是企业对于资本的价值。前天我跟万达院线的叶宁聊起这个事情,他说:原来是这样,我们没想到。
林:什么令他没想到?
张:其实就是一些战略性的合作。我给你举个例子,两年前我跟你说《小时代》现在的营销方式,你肯定不认,今天《小时代》做出来了,电影还能做出这样的影响力来。我们跟张艺谋的合作也一样,我脑子里想去做的事,我一步一步会做出来。大家别忘了张艺谋的品牌是创新,他之所以变成大师,不是因为他这么多年一直在创新吗?
林:你怎么看“中国合伙人”,比如你跟王长田、你与贾跃亭、你和张艺谋?
张:这个可以很坦率,《中国合伙人》讲的问题是这些人在生命的某一瞬间,相互依靠做一些事情,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其次的。第一,还是资本责任和产业责任,你要搞清楚你对什么负责,你的商业模式是否满足最大多数的人?变得更有资本价值,同时推动产业的发展。第二,是职业化,这个很重要的。第三,如果大家有一些共同的理想,这些理想必须是同时满足前面两个条件,你才能有价值。
一个职业经理人要藏起自己的个人梦想,要为产业服务。我很认同马云说的一句话: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有职业经理人素质的企业家,或者有企业家视野的职业经理人,把这两个结合起来,个人利益就在企业资本价值和产业回报。
林:身为光线的股东,你如何看待未来乐视与光线的竞争?
张:我首先是希望光线做得好,这个很重要。另外就是,我希望能够告诉大家,任何一个公司都是厚积薄发的,真正扎实打下过基础的企业,一定会有表现好的一天。我觉得光线具备这样的品质,长田倡导的骆驼文化还是有他很大的空间。他们能做到今天,我一点都不吃惊,我心里清楚得很。第二,就像《小时代》和《不二神探》一样,同台竞技又如何?我们都在一个舞台,大家跳各自不同的舞,看谁跳得更精彩?这个行业发展很快,不过几年,我们都变成了老公司,看谁走得更远?新公司要起来,它要琢磨这个公司的商业模式,那个公司的发展模式,还挺有意思。
林:某种程度上说,每个公司的商业模式也可能将经历一轮或几轮洗牌?
张:理论上是的,其实现在任何一个产业的变化都是很快的,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其对所有传统行业都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互联网本身变化也很快,几年前有些所谓独领风骚的互联网公司现在已经不见了。所以我说传统行业的十年是互联网的一年。这个时候像电影这样的传统产业谈商业模式就很重要。乐视影业的商业模式就两个着重要出发点,一个是互联网,一个是国际化。
林:你和乐视影业的野心都不小。
张:中国已经诞生了全球最大的PC公司联想,吉利已经并购沃尔沃,诞生了全球性的汽车公司,每个行业都有相似的可能,可能是因为现在的中国人确实是比较有理想,有野心。第二,中国有这么庞大的消费人群,中国文化产业的消费人口红利才刚刚开始,所以依赖这么大的一个本土市场是有机会的,至于是不是要把国际化当作是一种目标,我觉得是看公司的发展。但是以哪种方式去国际化,其实是取决于创新,国际化是要创新的,你给世界的电影产业带来什么样新的商业模式,这个是走出去的核心,你要对整个的国际电影产业有贡献才有价值,不管是从产品上还是从商业模式上,如果有贡献那就应该分享,你出去其实是分享,对别人也有启发,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第二大电影市场,到了2020年说不定就变成第一大市场。你知不知道六大公司在美国的票房是多少,最大的不超过15个亿,而且很多年没涨了,以后也不会大涨。到了2020年中国市场的规模是多少,400亿、500亿,你占了市场份额10%是多少,40亿、50亿,差不多就10亿美金,你占20%就是100个亿人民币,近二十个亿美金,国际并购的机会理论上是成立的。所以不要妄自菲薄,我觉得依托中国市场的中国电影公司通过并购实现国际化是有这个基础的,但是要不要变成一个国际化电影公司,其实是取决于你的贡献,你没贡献别国际化,你有贡献了那你就应该拿出去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