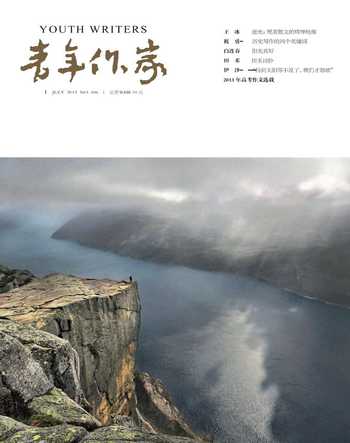水桥沟
2013-04-29第广龙
第广龙

水桥沟深处,是南山,弯曲的土路,缓和着升高。春秋季节,随时就起风了,土尘飞扬,迷眼睛,呛鼻子。
说是上到南山顶上,就是塬,塬面阔大,散落着人家。我没有上去过。走到半坡上,偶尔会遇见骑自行车,或者骑摩托车的人顺土路上下。上坡时,自行车得推着走。土路不平坦,疙瘩多,坑多。自行车、摩托车,颠簸得厉害,上头的人,颠簸得厉害。
土路两边,是庄稼地,是台地。山地都如此。十米二十米宽,种麦子,也种玉米。种玉米时,会间种毛豆。每一个台子,高度超过三米,是人工切削出来的。就在半坡一带,台子下面,间隔着,分布了一座一座坟头。年代久的,灰褐色,坟堆低、小;新坟潮湿,上头拿土块压着几张麻纸。清明节、春节,都是非来不可的日子,来南山的,尽是上坟的。春节来,山下鞭炮声不时炸响,山上升起一团一团烧纸点着产生的烟缕,似乎这之间有呼应关系一般。
我到南山,都只上到半坡。
我爷的坟,我爸我妈的坟,就在半坡的台子下面。
小时候,我就到水桥沟来。不会走路时,是我妈抱着来;会走路了,跟在大人后面来;长大一些,自己走着来,来的次数也多。
我妈就是水桥沟人。来水桥沟,是走亲戚哩。
从小,我就熟悉了我们家的亲戚,都是水桥沟的,或者,是水桥沟出来的,住在城里的街道上。只有水桥沟里的亲戚多,一家一家走,一天走不完。城里的亲戚,就几户;去的多的,是二姨家。二姨在粮站上班,身上所散发的是面粉的味道。
平凉城就一条主街道,东西方向,东头低,西头高。平凉城处在一条谷地中间,两边都是绵延的土山。北边的开阔,泾河自西向东流过,造成满是石头的河滩。平凉城的建筑,更靠近南边,虽然紧张到了土山跟前,却回避了洪水的侵袭。就在东头,主街道伸延,都快出城了,向南一个开口,进去,就是水桥沟。过去,它叫“生产队”;现在,叫“村民小组”。
水桥沟还真有一条河,河水量不大,说是泉眼里出来的。泉眼在南山方向。河道两边,一家挨着一家,一家一个院门,都是人家。垃圾,脏水,都往河道里倒;以前,水是透明的,现在流淌的是黑水。原因简单,现在的垃圾和以前的垃圾构成上、成分上,差别很大。我以前老是觉得水桥沟深,曾沿着河道,试探着走,想找到泉眼;走到一个转折处,一个高出来的石头台子上,有一道缝隙,水流外泄,没有看到泉眼,却看到近旁的一个阴森的大门——说是庙。什么庙?我没有印象了。长大以后,我曾经再次深入,想看看庙,看看泉眼,却什么也没有找到;而且,水桥沟也没有我记忆里那么深,快走着,一阵子就走到头了。
小时候的记忆,许多都稀薄了。可是,我还能回忆起来的,竟然是一次死亡——我也就四五岁吧,跟我妈去奶奶家。奶奶家在河道的西边。那时,奶奶家是一个大院子,有正房,有偏房;奶奶住正房,偏房住着奶奶的姊妹家。是晚上,院子里,是我的二奶奶还是三奶奶,已经放进棺材里了,线香的烟雾缭绕不散,气味浓烈;棺材边围着人,都在说话:放心走吧,都会安顿好的。我害怕又好奇,挤在棺材边看,看到的是枯瘦的脸,是厚厚的新衣服和簇拥在四周的麦草。以后许多年,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是我的二奶奶,还是三奶奶,当时已经咽气了,还是还有一口气?
奶奶家的后院,有一棵桑树,特别高大。猪圈也在后院。厕所也在后院。我捡过落在地上的桑葚,带着土,我也吃下去。桑葚把我的嘴唇都给染黑了。
后来,奶奶家搬地方了,由河道的西边,转移到了河道的东边,就和我的大舅、二舅、三舅一起住;奶奶家的院子,由原来的院子变成不再是大院子了。再后来,大舅成家,另家单过,又回到河道的西面开辟基地,盖了一院子房。我的三姨出嫁在外地了;四姨还在水桥沟,家在南山的坡底下,下雨天,难走。
奶奶的几个姊妹,我记住的就一个,记得我叫“大奶奶”,也在河道的东边,单独围了一个院子。大奶奶的小儿子,我叫“黑娃舅舅”;而黑娃舅舅的妻子,我却叫“大舅母”。黑娃舅舅真黑,脸,手,都黑,在我的舅舅中,却是个能人。就他,早早的,就不在土里头刨食吃,学了开车的手艺,先是给别人开;后来,有了经济,开自己的车,是那种超大的货运车。这个营生,早先还是很来钱的,黑娃舅舅家的日子,明显地,就亮堂多了。我走亲戚,一家一家的,自然就比较出来了。黑娃舅舅家电器新,大,过年摆的水果糖都是高级的。大舅母也是个泼辣人,说话声大,走路快,看着,觉得和身上时新的衣服不相称。可是,人的祸福,常常也是会颠倒的,大概在1995年冬天,黑娃舅舅出车到了宁夏一个镇子,晚上冷,睡觉前,给火炉子添了许多大炭,又把门窗关严实,结果,睡过去就没有再醒来。黑娃娃舅舅走了,大舅母日子虽然比以前暗淡,却坚强,人前是笑脸,人后有没有叹息,哀怨,没有谁知道。
奶奶在六十岁上,就把棺材备下了。就支在奶奶的炕头,睡觉,醒来,炕头就是棺材。这不忌讳,而且,还证明着活着的老人的福气。奶奶长寿,棺材一年一年烟熏火燎,看着像是老家具。确实,我看着棺材,不害怕。想到奶奶死后就要被装进这具棺材里,我也不害怕。奶奶孙子多,尤其是外孙多;奶奶生育了四个女儿、三个儿子,我妈是老大。到奶奶家,吃奶奶的好吃的,在棺材背后藏着呢;出去工作了,得拿好吃的,奶奶高兴收下,还是藏到棺材背后,哄更小一辈的孙子呢。奶奶吃烟,旱烟、卷烟,都吃。除了好吃的,再拿一条纸烟,奶奶也高兴,也吃。
奶奶离世,都是我出去工作多年之后了,我人在外地,没有赶回来一趟。后来,给奶奶过三年,我回来了,到奶奶的坟上也去了。奶奶的坟,也在南山的半坡上。
上南山,可以从水桥沟走,也能从更东边的一条路走。那条路,要经过宝塔梁。过去,这一带荒僻,杂草丛生,走的人不多。宝塔梁上的宝塔,几百年了,夏天,上空旋舞密集的燕子。我曾在宝塔梁旁边的外贸公司仓库,当过临时工。现在,变热闹了,新修了大路,和国道连接。可是,上南山,还是土路,没有变。
虽然走水桥沟方便,还是走这条路走得多。到南山上坟呢,不是走亲戚呢,遇见了,得客气,一客气,又显得生分,为了避免,就走这条路。
从我很小,就跟着我爸,到南山给我爷上坟。踩着麦苗,穿过玉米秆子,到我爷的坟上,点纸,磕头。坟上回来,身上的土,鞋上的土,用力甩打,笤帚扫,得清理一阵子。
对于活着的人,死亡,是最深刻的教育。我从小就经历这样的教育了。明白了人总有一死;还得明白,人死了,依然被亲人挂念着,生死两茫茫的感受,有时强烈,慢慢的,也会变得平和。就会觉得,人死了,是去了另一个地方,再也不会回来了;可是,一年里,那么几次,又可以团聚一般,又可以在一起吃饭一起说话一般。
我爷的坟地,是生产队的地;包产到户了,我爷的坟地,是亲戚家的地。城里人找一块坟地,不容易,多亏有亲戚在城跟前,而且还能够也愿意提供坟地。
我爷去世时,我才六岁。能记起来的,就是我爷的山羊胡子,花白了,穿黑衣服,裤脚是扎住的,穿布鞋——黑鞋面的布鞋。我爷去世,我的难受,不那么深刻。
我在陇东庆阳时,我妈来,住了一段日子。一天觉得不舒服,就到医院检查,结果查出了甲亢,当时就住院治疗。我妈不习惯住在病房里,心情也不好,每天我都骑自行车接上我妈,回到家里住。住了一段日子,疗程还没有完全结束,我妈急着要回去;我劝不住,只好办理出院手续,陪着回平凉。回去第二天,我妈就要去水桥沟,像是有啥要紧事情,实际就是和奶奶说说话。正是秋天,奶奶家的院子里,堆了小山那么高的一堆玉米棒子,金灿灿的;我妈坐到上面,我用我的海鸥牌照相机,给我妈拍了照片,冲洗出来,我妈看了很是喜欢。
只是,我妈回去后,病情并没有好转,这让我后悔不已,觉得把心没有尽到。
在我小时候,说到亲戚,那一定是水桥沟的亲戚;到现在,回去走亲戚,也一定是水桥沟的亲戚。我爸离开老家,在平凉站稳了,把我爷接过来一起过,老家就没有啥亲戚了。只是,我几乎没有见我爸到水桥沟的亲戚家去过,一次也没有。我爸进水桥沟,就是带着我们,给我爷上坟。
倒不是说,我爸对水桥沟的亲戚有成见,或者架子大,我觉得都不是。不论怎样,我爸直到咽气,也没有到水桥沟的亲戚家去上一回。
我爸的棺材,在卡车上颠簸着进入水桥沟,往南山的半坡走的时候,我蹲在车槽里,扶着棺盖,身子起伏,眼泪糊住了眼睛。
我爸的坟,是水桥沟的亲戚挖的。我爸到了另一个世界,也就永远成为水桥沟里的人了。
当年,我爸怎么和我妈认识,又是如何迎娶我妈的,从来没有给我们说起。但是,我爸和水桥沟的联系,就这么建立起来了,而且,再也不能中断。
我爸离世,我妈的身体,也是一天不如一天。记得我爸还活着时,一次,我妈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走,看到我妈的腿已经罗圈了,一条狗都能钻过去。当地有个说法,说老人的腿弯曲成这样,就活不长了。我就担忧我妈,心里隐隐有些感伤。人活到该活的岁数了,都得走,这没有例外。只是,走了的是自己的亲人,谁能经受得了这样的打击呢。死亡从来都不是一次性的。对于死去的人,也许如此;对于留在世上的人,可不是如此。我妈似乎一直都是病身子,一直不离药罐子。我爸却硬朗,吃睡都正常,爱在外面走动。我安家外地,我爸来过很多次,都是一个人坐班车来。我曾暗暗想过,我妈会走到我爸的前面,而我爸应该还能活很久很久。可是,我爸却走到了前面。一场突然的大病,摧毁了我爸的脑子和内脏。
2005年年底,在平凉盘旋路西边的街道上,我和我哥,正招呼雇下的人装车。是一块石碑。在给我妈过三年的这天,我们要把这块石碑运输到水桥沟的南山,立在我爸我妈的坟前。我爸我妈的坟,紧挨着,石碑就立在我爸我妈的坟前的中间。我爸过世五年后,我妈也离开了我们。坟地早就选好了,在我爸下葬的时候,就确定下来了,就在我爸的坟旁,把一块土地,落实下来了。
我妈几十年前离开水桥沟,最后,又回到了水桥沟。人在世上,都是这么循环的么?这样的结果,未尝不是福气。世上多少人,不知归处,甚至,没有归处。我最亲的人,能入土为安,未尝不是福气。在南山上往下看,东边的平凉城,全在;我们家的大致位置,也判断得出来。在长麦子、长玉米的地里,我爷我爸我妈,还有我奶奶,还有我的埋在南山的亲戚,会走动吗?都说些什么?说不说地上的事情?说不说家里的事情?
抬埋我妈那天,大舅说,你妈前面走了,后面的,就快了。说这话时,大舅的语气里,包含了伤感,只是,在程度上,是轻微的。即使平常的人,也有自己参悟生死的方式。对父母来说,有儿女养老送终,有一份满意;对我来说,有尽了心的安慰。也有后悔,后悔没有让父母出去旅游几次,后悔没有把好吃的让父母吃够。对于父母的思念,是断断续续的,有时强烈,有时清淡。只有到了南山的坟头上,才再次确认着,这个世上,我再也听不见父母的应答了。
水桥沟缓慢地变化着。南山还是南山,只是,一条省际高速路,要从南山的半坡下穿过,挖出了又深又宽的沟槽。开始担心着,影响到亲人的坟地,该怎么办;后来发现距离还远,才不再紧张。只是,原来清净的南山,要被呜呜的小车、隆隆的货车,日夜吵嚷了。
只要回到平凉,我都要到父母的坟上去,自然地,也要到水桥沟的亲戚家去。亲戚里的长辈,一年一年,在变老,身子都不怎么灵活了,记性也差了,有时,还会叫错我的名字。我也感觉到了某种生分,和我同辈的,怎么称呼,我都要问我哥,名字许多都叫不上来。以后,相互间,关系是疏远还是亲密?我说不来。从我来说,到水桥沟,主要的目的,就是给亲人上坟。也许,还在平凉生活的我哥我姐和弟妹,他们的来往,还会密切下去的吧。
人生一世,承受生,也承受死。亲人一个个离去,离得近的,离得远的,都意味着,这个世上,少了一个人。无论怎样,水桥沟里的一代人又一代人,都得把血脉的香火,延续下去,都有着水桥沟的记号,这是能追溯的,也是能互相辨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