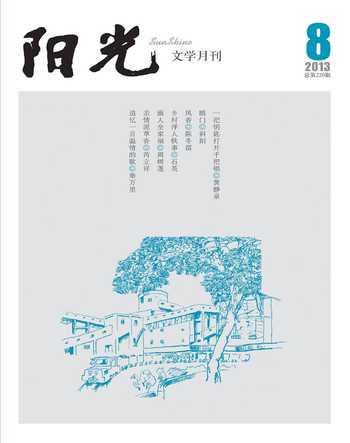友朋相偕话树芳
2013-04-29苏华
苏华
2013年一到,我就决心先做一件事:为老作家、忘年交黄树芳文学创作50年编辑出版两本书——一本是他的近作,一本是文友对他作品文品人品、本职工作和业余创作的评论及访谈集。
我在2011年《黄树芳随笔》编后记中曾说:“2013年,该是纪念黄主席创作生涯50周年的日子。我愿把编就的这本随笔集作为纪念作者创作50周年的一叶情愫,给他的每一位读者留下情深依然、绵亘不断的读与写的念想。”自己说过的话,记着的事,总该把它办了才算数,所以我要兑现自己说过的话。
还记得1997年8月,黄树芳作品研讨会上,著名文学评论家刘绪源所说的一句话:什么是作家?加入“作协”的不一定是作家,出了书的不一定是作家,甚至作品得了大奖的也不一定是作家。只有把创作作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长年累月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作,坚持几十年乃至一辈子而且取得了成就的,才可能是真的作家。刘绪源说这话时,黄树芳的文学创作活动已达40年;从2001年至今,他的退休生活也已12年,甚至到了老小孩的“圆锁”之际。但写作是没有退休年龄的,不但没有,而且还有激励的意义。曹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说:现在60岁才是“小弟弟”,70岁真正好,80岁不算老,90岁才古来稀呢。于是黄树芳便在退休之后把业余写作变成了正经的营生,从“小弟弟”到“真正好”,笔耕不辍,退休12年间出版了四本书。正是在持续不断的写作中,他得到了安慰,找到了寄托,受到了激励,而文友们也“黄老”来“黄老”去地继续关注着他的写作成绩,只不过把十多年前我们这一辈人习惯称之为的“老黄”调换为“黄老”而已——这是尊称也是他在文友们心中的地位。也正是由于他持续不断的写作,我在编完《黄树芳随笔》之后的两年,又编成了这本《黄树芳文录》。
《黄树芳文录》共收入他其他集子没有收录过的中篇小说一部,短篇小说七篇,报告文学一篇;散文随笔则以他的“阅读拾零”系列为底本,择要收入。
在编辑的过程中,我对《灼人的隐情》这部中篇小说感到了深深的惊讶——因为人物、故事、结构和叙事语境的成熟度,也因为所刻画的人物背后的思想刻度,远远超过他以前很有成就的中篇小说。于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即刻给黄树芳打了电话,不但嗵嗵一气说出了我对这部小说的喜爱之语,同时也表达了没有及时阅读这部小说的遗憾之情。为什么有遗憾之情?因为我还记着,那年在南戴河讨论他的作品时,不少文友都期望他以后创作出一个以煤矿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力作。如果我在十年前就看到这部中篇,即使给他以不算专业的鼓励,那么,我今年所编的也许就不是《黄树芳文录》,而是一部让众多文友都感到气象不凡的长篇小说了。这种鼓励,是一种深刻的文字因缘,也是一种深情记忆的惦念,失去了,就成为一件忆念的往事,让人感到有点后悔有点灯火阑珊处有点擦肩而过的那种纠结。
近两年,黄树芳定居在书房,驻足在书丛中,涉猎了大量世界文豪和大科学家的传记,并以自己的生活体验来理解这些大师的某些事,在写出的不少文字中,填满了生命的引号和问号。我将这部分文字统以“杂感”编为一辑。这一辑的文章,不说内容,其形式便让我想到了非常有趣的“混搭”现象。如《诗人皇帝乾隆和作家首相丘吉尔》《想起了“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爱因斯坦的遗嘱和雨果的葬礼》等等。“混搭”的流行,源于十多年前的时装界,一本时尚杂志曾写道:“新世纪的全球时尚似乎产生了迷茫,什么是新的趋势呢?于是随意配搭成为了无师自通的时装潮流。”没想到年逾70的黄树芳居然在“混搭”流行了十多年之后,把世界名人也“混搭”了一把。这些“混搭”的文字,一半是追寻,一半是诠释,我是感到品位正极了。
黄树芳的文学创作生涯按说已不止50年,从他1957年发表第一篇散文《永远怀念您》算起,实有55年;但以他1963年刊发第一篇成名小说《王林林》为标志,来纪念这位文坛长者漫漫五十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似乎更符合喜庆之事“十年一大庆”的惯例。《走近黄树芳——一个业余作家的跋涉之路》,即是一个文化符号,是一个集评论、访谈、作品研讨于一体的写人的人与被人写的互读读本,是老少文友聚集一堂,取长补短,相互祝愿,感念生活,亲近文字,追忆岁月,祈望未来的真诚表露。
1998年,我曾和阎晶明、黄树芳共同编过一本《文友同行》。《走近黄树芳——一个业余作家的跋涉之路》就是在《文友同行》这个选本的基础上,补充了该书出版后围绕着黄树芳新近出版的各种著作发生出的二十余篇序言、评论和采访记而成的。
关于这本书的意义,黄树芳在《文友同行》后记中说:
本书所收文章,都是对我这个业余作者以及作品进行分析和论证的。开始,我对汇不汇编这本集子有些忧虑,后来,经过文友们反复讨论,才逐步放下了包袱。因为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无论哪一位作者或编者,除了为繁荣文学创作这个大目标和文友之间互相沟通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以外,谁也不会有什么其他想法,这一点读者自然是会理解的;再者,虽然文章往往以我为例,但其涵义绝不仅仅限于一人,许多问题都是有普遍意义的。
我想说的是,黄树芳十几年前所说的这番话至今仍然是我汇编《走近黄树芳——一个业余作家的跋涉之路》的主旨。尽管写作这门手艺或者说是这个行当与十几年前相比,不再那么令人心潮澎湃,那样激动人心,而且即使过去的从业者也出现了无数的分化和裂变,但一个以此为净土为心灵安魂的群体不是变少了,反倒是愈来愈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走近黄树芳——一个业余作家的跋涉之路》就更具有了一个“范本”的作用。
《走近黄树芳——一个业余作家的跋涉之路》共编为三辑,第一辑是“走近黄树芳”,第二辑是“作品论评”,第三辑是“作品研讨”。在这三辑中,我以为“走近黄树芳”最为重要。
纵观震烁古今的大文人,他们何以名传千古?古文大家姚鼐的侄孙姚莹在为清代爱国诗人、教育家黄培芳诗集所写的序中说:“吾以为学其诗,不可不师其人,得其所以为诗者,然后诗工,而人以不废。否则,诗虽工,犹粪壤也。无怪其徒具形声,而所自命者不存也。”
黄培芳(1778-1859),字子实,号香石,广东香山县人,被姚莹尊为与张维屏、谭敬昭齐名的“粤东三子”。鸦片战争初起,林则徐撤职,琦善撤防,英军侵占清国海防炮台,黄培芳于此时写下愤懑于胸的《道光庚子腊月中旬感事六首》,指陈抗英失败之原委,悲叹自己无济于事,其名句即是“母老不堪为世用,书生洒泪向平原”。鸦片战事失败后,黄培芳与数十名名士联名呈文,推动广东巡抚怡良上书道光帝,揭发琦善对英妥协,私订《穿鼻草约》,擅割香港的卖国罪行,促使道光降旨将琦善革职,锁拿进京。咸丰六年(1865年),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翌年年底,英军一度攻入广州城,清廷不少官员慌忙逃跑,居民纷纷外迁。年届八旬的黄培芳,以先宗祠图书之所在,对劝他逃难的人说:“就算遭到不测,也算得大丈夫死宗庙之义!”在广州沦陷期间,黄培芳作了《粤东省垣失守感赋》十首,痛斥清廷封疆大吏的庸懦、八旗兵的无能。所以,姚莹才借为黄培芳诗集作序的机会说出凡千古有诗名者,是“不惟诗,惟其人也”。
由此可见,为文之人的人品是何等重要!现在的写作群中,徒具形声者有之;得了公款资助,出书后拼命为己博名取利者有之;不读书无知且没有公德者有之……反观黄树芳,他用文学抒发自己的情怀,更用这样的方式写他身边的人和事;他的人品与作品同样,总是充满了温情,充溢着一种平和、安宁、纯朴、慈爱的胸怀;遇事不温不火、从容大度,对事从善如流,分得清孰先孰后,待人善解人意,低调中流露出的尽是高尚的点点滴滴。也正因为如此,从事文学创作五十多年来,从领导到同事到工人,从亲属到文学界的朋友,他的创作总是受到鼓励和支持,他也因这种异于“犹粪壤也”者的人品与文友的关系更为融洽,与写作的最终目的更为接近。这样的人,这样的作品,仿佛白杨绿叶前吹过的晚风,字字有道,篇篇传统。我所惦念的正是黄树芳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作品,心中的敬意这么熟稔了也久久不散。
犹记起许多文友在黄树芳文学创作40年之际说他真不容易,我现在仍想说,黄树芳坚守他的这种爱好也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