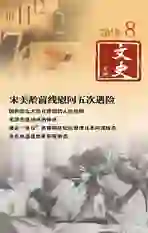那个年代的领导真是可亲可敬
2013-04-29济中
一、车子抛锚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春天。
吕梁山区,咋暖还寒。
这天早饭后,我带上昨夜便准备停当的行囊,要随同易风局长到石楼、交口两县考察农村文化工作站。
当年,全区第一批52个农村文化工作站建立不久,下面情况还停留在汇报材料上,这回选定了石楼县的城关、义牒和交口县的双池这三个站,是要重点了解他们对地区文化局、地区艺术馆所制订的“农村文化站工作条例”的落实情况,同时了解已经经过培训的辅导员们的工作情况。
地区文化局只有一辆天津吉普车,还是去年冬才配发的,还没有个正式司机。
局里有位年轻人,当过几年兵,能拨弄两下车子,叫任建根。他自告奋勇,要开车送局长下乡。
易风局长性情温和,对下属一贯宽厚有加,凡事都好说话。
昨天下午下班前,局长跟我说:“建根要开车送咱去下乡,反正也没个正式司机,就让他开吧,你说呢?”
“行。”老局长的话,我当然听。
“那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出发。”说罢又叮嘱我,“那边天寒,多带件衣裳。”
我们仨上路了。
小车一溜风地向南,出离石城,经中阳界,过桃红坡。一路上,观不尽的山峦风光,赏不完的初春美景。进入交口县地面,山峦起伏明显加大,盘山道上,车子左转右拐,爬坡下坡。我跟老局长并排而坐,只见他两眼随着车窗外不尽的春光闪现出欣喜之色,双手紧拄着他那只弯头手杖。他的双腿因战争年代连续行军得不到休息,住破庙、歇野地,落下了腿疼的毛病。
“这三个文化站你都去过了,对他们印象如何?”老局长引出了话头儿。
我把这三个文化站的简况先讲了一遍,然后说:“这三位辅导员都是高中毕业爱好群众文化的青年,去年秋天都经过培训。在我印象中,这三位在五十多个辅导员中属上乘。”接着我又告诉他,“义牒那位女辅导员,民歌唱得不赖。”
一提到民歌,老局长的话匣子就打开了。
“咱山西可是民歌的海洋啊!”老局长脸上泛出兴奋的光彩,“咱吕梁民歌在山西民歌中是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
我接应着:“咱山西的民歌多,民歌的歌唱家也不少呀!”
“是啊。郭兰英、王爱爱,都是好手!那郭兰英的‘翻身道情,真是经典呀!”
这时,一直专注开车不曾开口的建根突然来了一句:“老赵唱的翻声道情就不赖!”
“是嘛!”老局长高兴起来,“那你唱一段听听!”
我和同事们下乡时,为了让大家高兴,倒是唱过不少歌儿,因为自小我就爱唱歌嘛!郭兰英的翻身道情正是我的最爱,从头至尾可以唱下来。
于是,在颠簸的车里,我便唱开来:
“太阳一一
一出来呀哎嗨嗨哎嗨哎嗨哎哎哎……
老局长以手击腿,口里哼着过门儿为我助兴。
“满山一一红呦哎嗨哎嗨哟
共产党来了
翻了呦呵身咯哎嗨哟
……”
正唱得起劲呢,突然,车身一颤,熄火了! 我心中一紧,歌声嘎然而止。
原来,小车在一段凹道处,一前一后悠开了——往前悠几米,再往后悠几米。
可是,老局长不着急,他竟然风趣地说:“咱的车扭开秧歌了!哈哈!”
建根把车刹住,试着打火,却怎么也打不着。
我们仨都下了车。建根打开车盖,查看机器;我和老局长舒展几下筋骨,看看高高升起的太阳,再看四周。啊,山道弯弯,车就抛锚在大拐弯的“u”形底部。半晌午的山野里,不见一个人影》
建根急得什么似的,涨红着脸,使手头工具拧拧这儿,敲敲那儿,摆弄了半天也没整出个道道来。脑门子上早已渗出豆大的汗珠。
这时,老局长笑眯眯地逗他:“任师傅,慢慢弄吧,天还早呢。”说着抬头看看天,接着说:“能赶上午饭就行,不用急!”
忽然,建根朝我叫了一声:“上车去给我踩住油门!”
我急忙上车,遵照指示用脚踩住油门,学着师傅们的样子,快速地一踩一松地操作着。不知他怎么弄的,“突突突……”马达轰鸣了起来。
我们仨几乎是同时喊出一声“吆”!
车身一震,加大油门,车爬上了坡,我们又前进了。
我提着的心,这才放在肚子里。我觉得在这儿足足日捣了有半个多钟头。
“建根呀,可真有你的,真行!”你看,局长还夸他呢。
这时,老局长又朝我说:“济中,接着唱!”
“往年一一
这眼泪,肚里流
如今咱站起来
做主人呀哎嗨哎嗨呦!
……”
几天后,结束了此行。在一次会议上,老局长给大家讲了这一小段经历,笑眯眯地说:“建根同志非常勇敢,而且遇事不慌,有耐心,善琢磨。这是很大的优点。”
你瞧,局长还表扬他呢。
二、40多个人和6个涨工资的指标
会场上,四十来人,错落而坐。
易风局长将会议宗旨和议题讲过后,大家本应跟往常一样,热烈讨论开来,可这次却反常。十几二十分钟过去了,还没有人发言。
这是一次什么会议?
还得从头说起。
“四人帮”被粉碎后,百废待兴。可就在这个当儿,党中央体恤下情,拿出一部分钱来,为已经十七年没动过工资的广大干部、职工提升工资。然而,钱有限,提升的比例不大。
老局长请大家根据文件精神发表意见,可大家大眼瞅小眼,继续保持沉默。
是啊,在场的每个人都是十七年不动了,这个言怎么发?这个态怎么表呢?
这时,老局长发话了:“唔,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党和国家关心大家,却又拿不出再多的钱;大家呢,工资都不高,说实话,都该提一提。咱们局、馆这次才有六个指标,这就让大家为难了。可这个言要发,这个话要说呀!那么,我先说吧,这回我放弃,因为我的工资比大家都高。”
听到这儿,我憋不住了,举手发言:“刚才局长都讲清楚了。我表个态,这次放弃。请大家考虑别人吧。”
“理由呢?”局长问我。我心里明白,有些话他说不出,才追问这一句。
我说:“我的工资虽然不太高,可比我低的同志们很多,所以,把机会留给大家。”
会场上有了嗡嗡之声,大家开始议论着什么。有些人相继发言了。
那时,文化局、馆都挤在这个影剧院北侧、临东川河南岸狭长的两排房子的院子里,会议在北排西首一问屋子里召开。屋子本不大,那么多人,还有人在抽烟。我起身走出会场,大口呼吸着外面清新的空气,心里清松了许多。
会议结束了。是哪六位提上了这一级工资,我已不记得了。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老局长到我办公室来。一进门,还没等入座,老局长便开了腔:“咱们申请了半年多的事,今天才有了回话。哎呀,实在是费劲啊!”
“什么事呀?”我莫名其妙。
“咱们盖办公楼的事。地委要求咱们先搞一个初步的设计图,作为向省里要经费的附件。反正就咱这六十米长四十米宽的地皮。济中,我们研究了一下,让你来画这个大楼的设计草图。”
“行。”原来如此。
我答应着,又问:“就在这院子盖?”
“拆了这两排房子,盖一座大楼。”
“甚时候要?”
“明天下午。”
于是,我将正在编辑的《群众文化》的稿件收拾起来,放到柜子里,在桌子上铺开一张四开大小的水彩画纸,坐在椅子上沉思起来。
根据老局长讲的意思,我到院子里拿卷尺量了一次。东西60米,南北40米,要保留现有的办公用房先不拆;将来文化局、艺术馆、文联都要进来,还要在楼内设置图书馆、展览馆、活动室、会议室等场所,只能是盖一座东西单开、南北双开的两翼四层,加中间主体部分四层带帽的L形的拐角楼。
我动手了。
一个下午,一座四层带帽的办公楼效果图,跃然纸上。第二天上午,我在图纸上设了色。中午下班前,一张铅笔淡彩的大楼设计草图交到老易手上。
之后很久,终于批复下来。两年多后,1982年,大楼落成。
我又遵照老局长指示,用仿宋美术字写好了“山西省吕梁地区行政公署文化局”、“山西省吕梁地区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山西省吕梁地区艺术馆”三副大牌子。5月23目,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纪念日这天,文化大楼正式挂牌办公。
对了,再提一下那次提工资的事。记得好象那年元旦之后,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易局长偕同郝超副局长到我家来报了个喜。两位领导一进门便冲着我和玉梅说:“元旦既过,春节在望,我俩给你家拜个早年吧!”
我爱人连忙拉过两只凳子,让座奉茶。我母亲也从里间迎出来,互致问候。然后,郝超开口道:“济中,去冬评工资结束,我们到宣传部汇报,把你主动放弃的事讲了。王局长又把你作为文化局业务骨干的情况说了一遍。其实,王鸣歧部长和办公室主任杜志也熟知你的情况。后来,宣传部跟上面要了一个指标,这不,给你也提一级工资。”老易接了一句:“今天我俩给你来道贺!”
我听了之后,非常感激老局长和文化局、宣传部领导对我的肯定和关怀。
我心里想,今后,只有在工作中继续努力才对!
三、天安门诗抄
1976年4月,王局长派我到北京出差。
走前,向我交代了此行的任务之后,他特别叮咛了我半天,生怕发生什么意外:“当前,形势不稳,到了北京,少在人多的地方逗留。办完事就快点回来。”
六天之后,我回到吕梁,心事重重。汇报完毕,返身回家。
第二天早饭刚过,王局长就敲开我家门。一进门,他也不打话,坐到一只凳子上,两眼盯住我问:“我看你一脸的心事。昨天人多,不好问甚,今儿我是来听你说说北京见闻来了。”
玉梅给老局长递上一杯茶,我坐在他对面,讲述起来:
“北京城被笼罩在一种紧张、肃穆和灰色的气氛中……”我清了清嗓子,整理了一下思绪,接着说,“大街小巷,人们行色匆匆,见面也不搭话。天安门广场上,花圈、挽幛如海,人流涌动如潮,虽无鼎沸之声,却似蕴藏巨大能量,蓄势待发!”
“那么多人呀!”老局长急着接道:“听见人们说些什么?”
“远处只闻低沉的嗡嗡声,走近却见一伙一伙的人围拢在一起窃窃私语——‘怎么不让开追悼会?!‘他们到底要干什么?!‘说话小声点,注意便衣……”
我呷了一口水,接着说:“花圈和挽联挽幛都是送给总理的,上面尽是写着‘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呀我们怀念您这类语言。我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纪念碑四周挤得水泄不通,人们都面朝纪念碑排成长队,呈放射状向四方排列,不是在拥挤,而是一个伏在前一个人的背上在抄写着什么。
我凑近一看,原来是在抄录贴满在碑体上、栏杆上的怀念周总理的诗词。后面的人看不清楚,站在栏杆旁的人就高声朗读,一句一句让大家听!哎呀!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简直太让人激动了!”
我边说边比划,不觉已经站了起来,“我赶快掏出钢笔和小笔记本子,学着大家的样子,伏在一个人的背上记起来。”
“那你抄下来了?”老局长急着问。
“直抄得我头晕眼花。实在累得吃不消了才罢手。”
“快拿出来我看!”
我回到里屋,从背包里取出那个被揉得皱巴巴的小笔记本儿,双手递给他。
他一句不落地看着,读着,眼角潮湿了,用小手帕擦试着。
我的家人见状,都默不作声。
看完了,他把小本子轻轻放在桌上,长吁了一口气,突然,双手拄着那只弯头手杖,使劲在地上“咚咚咚”地杵着,口里自言自语地说:“这是怎么啦!到底为什么呀!”然后,他告诉我:“上级通知,不让开追悼会!群众自发集会都禁止!!”
临走前,他又问了我一些其它见闻,我告诉他:“太原的五一广场上也是人山人海、花圈无数,有几只花圈足有七八米高,是太钢和太重的工人们送的。”
“唉!你那个小本子,切勿再示于外人。这不是件小事!”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便“追查反革命”起来。我被叫到组织部盘问了一大阵子,还命我将此行情况写出来交上去。
回办公室的路上,我忽然想起在老局长去我家之后,同院子的几位也曾向我询问过,可我没有展示诗抄。哦,对了,在临县工作时就相识的好友,宣传部的张德芳后来也来过我家,他也曾看过那个小笔记本。坏了!我的事会不会引出更大麻烦?肘腋之患就在眼前!于是,到家后,我马上将那小笔记本一页一页撕下来,填到灶火中去。
第二天,我找到张德芳质问他,张德芳有点生气了,说:“我是那种人嘛!”
我怎么也觉得不对劲,就到局长办公室,向他汇报了被盘问的情况。老局长压低声音安慰我:“用不着担心,只要你不留把柄就好。剩下的,有我呢。”
“四人帮”打倒了!
1977年1月8日,离石各界举行集会,隆重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我设计并布置了作为大会会址的离石体育场,写了会标及四边的大幅标语,还拍了纪念大会的照片。会后,老局长手持总理遗像,大家围拢到一起,拍了一张留念。算是为老局长和大家还了这个心愿。
1978年11月,地委给因1976年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人平反时,我受邀到地委常委会议室,参加了由时任地委副书记的李玉明主持的平反会。
过了两天,地委组织了一场《天安门诗抄》朗诵会。
四、群众文化活动搞得如火如荼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省里组织编纂《中国民歌集成·山西卷》,王局长召集艺术馆的几个人部署任务。
他在会上传达了文件精神后,给我们讲了一段话。他说:“编纂民歌集成是件大事。咱山西是民歌的海洋,吕梁民歌在山西民歌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重点发掘整理地区。大家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发掘整理过程中,首先要摸好底,不打无准备之仗。这个嘛,咱艺术馆已经有过这个基础。其次,搞好第一手资料,不单要做好记录,更重要的是搞好录音,一定要让民间歌手充分展示其个人色彩,保持民歌的原汁原味原生态。最后,是撰写文字,一定将民歌的出处、采集地区、民歌特色以及民歌手的姓名、性别、年龄等信息记载清楚、准确,纳入济中已着手建立的艺术档案中。”然后,他又说了些关于组织方面的细节,并说:“这件事由济中牵头,常士继、老马、小王你们几个合作完成。”
我组织各县文化馆的同志分头实施这项工程,各自负责搜集所在地区的民歌,然后汇总编排,并根据老局长的要求,在时间、质量等方面也作了规定。我们艺术馆的几个人,则负责重点采集和统筹指导。
经过近三年的努力,《吕梁民歌》一、二、三集都集结成册。当时,老局长已调任吕梁地区文联主席,仍在大楼内办公。当我拿着三本民歌去向他汇报时,他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老花镜后面的两眼笑成一条缝:“大功告成了!大功告成了!”
老局长在地区文化局任职的几年中,文化局和艺术馆的业务建设和群众文化活动搞得如火如荼,每年都有新套套,每年都有新成就。而且,许多工作都是在他的倡议、组织、启发和鼓舞之下得以完成。艺术馆的工作也成绩斐然。别的方面已不能详述,单就我分管负责的就有:建立全区艺术档案;编辑《群众文化》杂志(还是由老局长请书法家徐文达题了字的);组织《民歌集成》和《民歌舞蹈集成》;组织“摄影艺术培训班”(我主持共办了7次);组织举办了全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吕梁民间文化”等大型展览等多项工作。回想起来,那时吕梁地区的群众文化活动真的是热火朝天。人们常挂在嘴边称道的,还有每年一度的春节、元宵节的大型文化戏剧调演活动,便又是一例。
五、老局长和我的交情
老局长和我的交情,始于他被下放插队到临县那年。
省里文化界的人到来,实际上对临县来说,应是如获至宝。这个“情报”早已被县文化局、文化馆获取了。而且,我由县委政工组段存象同志那儿抄回来一份花名。我们设想着把这些人以某种名义抽调回来帮助工作,以提高我们的业务水平。
当时,县里正筹备搞“农业学大寨”展览;跟往常搞展览时一样,这次也是由我这个总设计人先将材料归纳,写好展览草案,并且将设计总图及其几大部分的大小标题、文字段落、图片位置等项都用铅笔稿在数米长的纸卷上画好,送审。然后,就抽调人员准备动手制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老易等几位省文化局的同志,由农村抽调来,而且,就被安排在文化馆大院内的那两孔窑洞里。
关于老易的事,我早有耳闻,知道他是战争年代就参加革命的文化界老前辈。出于尊重,也是好奇,我总爱往他住的那间窑洞里跑,去了便有意地问这问那。他也不抖什么架子,有问必答,有求必应,一来二去就熟悉起来。
文化馆开会、学习、研究工作,他们几位都参加;我们在展厅里制作,他们也经常过去观看。后来,交流多了,在一次学习会上,我就提出请老易通览一下设计稿,并请成锡龙参加绘画,请罗仁佐为版面写说明词。领导当然同意,制作人员当然想请他们参与。从此便跟他们几位在一起工作上了。
还是说说设计稿的事,我把总体图稿和草案交给老易,他看了一夜。第二天上午,他叫我到他的窑洞内,见面就说:“济中,通览一遍之后,总体感觉可以。我提三点建议吧。”我连忙说:“慢点,我拿个本本记一下。”“不用,不用,咱就图说事吧。”于是,我伏在他左侧仔细听他讲述。他把数米长的画稿铺开,从头到尾地说开了,说得很细,而且在我的铅笔稿子上用红蓝铅笔做了很多记号,有的地方还删了一些,又增添了一些小字。他指着画稿说:“这三大部分,分得合适,只是第一部分里对大寨精神表现得还不够鲜明、突出,你看是不是这几条经验的部分,字号再大些,版面底色和文字颜色反差也再大些呢。这样就更加重点突出了。”我说:“对,对。”“这第二部分看来是这个展览的主体部分,你这里列举的先进单位也不少,就是要发现典型,进行表扬嘛,气可鼓而不可泄嘛。咱们临县农村的艰苦条件不比大寨那边次,治山治水精神一定要通过文字说明,用图片来突显,所以,我建议你把孙家沟治山治水的图片搞得再大些,占上半个版面也不为过,放到第一家。大峪沟的小麦丰收田,这个在临县比较少有,放在最后也可以,让观众加深印象。这个麦田的照片,弄到压轴的位置。关于第三部分,是总结县里学大寨的经验、学习过程中的问题等等,那就条文式的强调一下。”他连同文字带图片,边说边比划,一口气说了近一个钟头!我听得入神,连给他倒杯水都忘了!
根据老易的建议,我又将总体设计图稿修订一遍,感觉到这样一改,展览整体图纸就焕然一新,效果好极了。于是,赶快拿到展览制作现场,给大家讲了,让大家也领会贯彻。老成和老罗一直跟我们一块儿,苦干20余天,终于把临县第一个“农业学大寨”展览搞成了。开馆那天,我们在文化馆门口拍了一张纪念照片。
老易在临县文化馆期间,还常找当时的文化馆负责人乃至文化局的领导谈话,指导工作;还召集临县的民间艺人座谈,和盲艺人宣传队的盲艺人们座谈(我当时负责管理着临县盲艺人宣传队七八十个盲艺人呢),使这些身处基层的文艺骨干们受益匪浅。这些事,我都亲历,虽不能详述,可记忆没有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