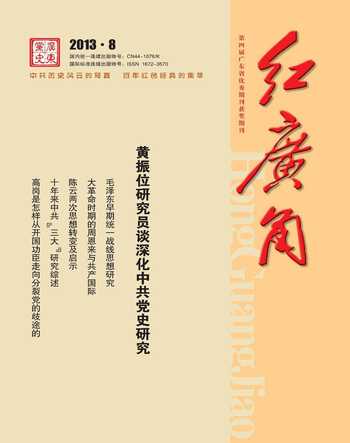十年来中共“三大”研究综述
2013-04-29潘李军凌弓
潘李军?凌弓
【摘 要】自纪念中共三大召开80周年以来,学术界围绕“三大”的会址、议题、评价,“三大”与党的建设、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不少突破和新成果,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综述其要将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共三大;研究成果;综述
中共三大作为中共成立以来第一次公开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发展史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一直备受中共历史学界关注。特别是在2003年“三大”召开80周年和2006年中共成立85周年暨“三大”纪念馆落成之际,更是出现了对“三大”研究的高潮,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的研究论文,本文仅就管见所及作简要综述。
关于“三大”会址
有关“三大”会址的研究,近年来学者主要围绕着“三大”的具体会址及何以选择在广州召开,进行分析论证。
1、“三大”会址的考证。“三大”具体会址从1971年开始调查到2006年最终确认,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洪霓认为,大致经过了寻找线索、初步确定、最终确定和考古勘察四个阶段,尤其是考古勘察,不仅确认了“三大”召开的原址,而且为恢复旧址奠定了科学依据。①舒顺龙阐述了确认会址的一些细节,认为“三大”亲历者徐梅坤起了关键作用。徐梅坤应邀来穗后寻访辨认,确认原址即现在的广州市恤孤院后街31号,而当时广州市档案馆新发现的史料也恰好印证了他的说法,②故三大会址的认定应该无疑。
2、“三大”在广州召开的原因。“三大”是迄今为止唯一在广州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为什么选择广州?学者们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分析,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从广州自身独特的条件来看,“广州是当时中共领导人和共产国际代表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地区”,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国革命的红色之都”。同时,广州稳定的政治形势和日益壮大的革命力量,“为大会的顺利进行和圆满完成会议的各项任务提供了安全的保证”。③第二,从共产国际的战略重心来看,当时苏俄和共产国际对华战略重心已经南移,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已经是其拉拢团结的对象,要求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早已成为了共产国际的对华方针,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不得不听命于苏俄、共产国际的指示,积极配合其战略重心的转移。第三,从国共两党的现实情况来看,当时的国共两党都是革命性质的政党,都有发展力量、开展革命活动的需要,因而“都有实现两党合作的共同意愿,这使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具有可能性”。④
关于“三大”议题
“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但与此相关的国民革命、国共合作和农民问题等,也颇受学界重视,一些研究者通过深入剖析,提出了许多新观点。
1、关于国民革命。黄振位认为在中共历史上,“三大”首次公开提出了“国民革命”口号,“反映了当时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共同进行这一革命的意志和愿望”,对于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国民大革命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进一步考查了这一口号提出的来龙去脉,指出国民革命这一提法最早是孙中山使用的,“反映了他已经把革命矛头直接指向国内军阀和帝国主义”。随着对华政策的调整,苏俄和共产国际在中共“二大”至“三大”期间对中共的指示中,进一步明确了国民革命的概念,同时对国民革命的具体内容也作了阐述。随着中共“三大”对该口号的公开提出,孙中山、共产国际和共产党三方关于国民革命的根本任务的看法已趋于一致,国民大革命的伟大实践已呼之欲出。①姚曙光在仔细研读了“三大”的大量文件后,认为国民革命问题才是“三大”的中心议题,国共合作的原则和方式只是国民革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属于这一议题下的一个子目。②
2、关于国共合作。国共合作问题由于涉及到对“三大”的评价,一直都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主要聚焦在合作有无必要以及用什么方式合作两个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共合作具有历史必然性。杨雪从四方面展开论证,认为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是合作的理论基础;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是合作的政治基础;国共两党对中西文化的共识是合作的文化基础;两党对国家民族利益的体悟是合作的思想基础。③有论者则从当时国共两党面临的具体环境探讨指出:一方面,一战后列强在加紧对中国经济掠夺的同时,加强了对中国的政治控制,“打倒列强,铲除军阀”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另一方面,“二七”惨案使中共认识到建立反帝反封建同盟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因此,国共合作既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国共两党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作出的正确选择。④
对于国共合作方式,目前学界存有争议,大体可以归结为三种观点。一是肯定说,这也是党史学界的传统观点。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指出,党内合作是“三大”主要的历史功绩,因为它是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所能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不仅能够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广泛发动群众,推动国民革命的历史进程,而且有利于改进国民党,为中共的锻炼和发展提供广阔的政治舞台。⑤二是否定说。持该观点者认为,党内合作损害了中共的独立性,限制了中共对革命的领导权,是国民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韩广富、吕玉莲从三个层面对此进行了论证,认为从提出的依据来看,党内合作是建立在马林片面高估国民党的革命性和力量基础之上的;从共产国际采纳这一方式的原因来看,党内合作是共产国际基于苏俄的战略利益而推动国共两党合作不得不采取的合作方式;从孙中山坚持“党内合作”的目的来看,孙中山是在不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前提下,把共产党当作“新鲜的血液”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去拯救正在“堕落”的国民党。⑥三是折中说。持此说者认为,应该把党内合作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客观理性地分析,既要看到其历史必然性,又要认清其历史局限性。吴九占、李付安就认为,一方面国共两党有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因而党内合作是国共两党的历史选择;另一方面,随着国共关系的发展,党内合作存在着的影响中共独立性,束缚共产党人手脚的弊端也开始显露出来,因此党内合作不是当时国共合作的最好方式,但是唯一的方式。⑦
3、关于农民问题。在中共历史上,“三大”开始高度重视农民问题,并第一次作出了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因此吸引了不少研究者的目光。吴映梅主要探讨了“三大”对农民问题的理论贡献,认为“三大”作出的《农民问题决议案》,不仅使人们认识到要扫除中国农业落后、农民生活贫困的根源,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重重压迫实现全民族的解放,而且使全党认识到联合农民参加革命、增强中国革命的群众性基础的重要性,从而为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民运动提供了理论前提。之外,“三大”开始把农民作为中国革命的价值主体,使党能够作出代表农民利益的政策。①郑惠玉则结合当今中国实际,揭示了“三大”关于农民问题决议的历史启示,认为“三大”以来,“我党正是由于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农业生产,才保证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反观当下也应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把农民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价值主体。②
关于“三大”与党的建设
“三大”在党的建设方面同样留下了宝贵遗产,也引起不少研究者关注,近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三大”与党的组织建设。许多研究者对此作了较高评价。首先,“三大”依据党自身状况和形势发展所提出的更高要求,对“二大”制定的党章进行了首次修改,并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为加强党员的管理、发挥地方各级党委的积极性提供了制度保障。有研究者更是把“三大”对党纲党章的完善同推动国共合作一起视为“三大”的两项历史功绩。其次,“三大”制定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它是中共党史上第一次以法规条文的形式规定党的中央组织结构和工作制度,极大地推进了党的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对于当今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③ 最后,“三大”是扩大党内民主、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典范。在大会的筹备过程中,不管是选举大会代表还是研究确定大会的内容和议题,民主集中制都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在大会的召开过程中,不仅广开言路使各种不同的意见充分涌流,而且对那些坚持自己错误意见的代表不是采取组织上的打击,而是互相说理,讲清问题;在大会各种决议的形成过程中,不是依据少数领导人和共产国际的意志,而是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作出的。④
2、“三大”与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有研究者指出“三大”根据对中国国情的正确判断,实现了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从反对到同意认识上的转折,体现了鲜明的实事求是精神;“三大”为使国共合作从设想转变为现实而确定的党内合作方式又展现了鲜明的开拓创新精神。⑤王国梁根据《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认为,陈独秀在“三大”对自己工作的检讨是中共早期批评的范例,为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的形成奠定了较为重要的基础,对于完善当下党内民主生活制度,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⑥
四、关于“三大”的评价
“三大”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会议,目前学界对其历史作用的评价较为客观,认为其贡献是第一位的,但也存在局限性。
1、“三大”的历史贡献。在众多研究者中,由李君如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一书论述较为全面,指出了“三大”的四方面深远影响:第一,“三大”是“党的历史上专门研究统一战线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启了统一战线的先河”;第二,“三大”在正确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之上,作出了把国民革命作为当时党的中心任务来抓的决定,从而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第一次战略转变;第三,“三大”对于党的制度建设和组织建设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为以后党的自身建设积累了宝贵的财富;第四,“三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对开创国民革命具有重要意义。①笔者认为,李的评价涵盖了诸多视角,比较全面和客观,最能代表目前学界的观点。
2、“三大”的局限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认为,“三大”的主要不足是没有提出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对国共两党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力量作了片面的估计。②陈丽华等著《中共历次代表大会焦点写真》从多方面论述了“三大”的不足,指出大会在批评党内“左”倾思想的同时,并没有有效防止右倾思想的抬头,因而“三大”带有右倾的性质;在农民问题上,虽然认识到了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却没有提出解决农民问题的切实办法;在革命军队问题上,虽然认识到了没有民众支持的军事行动是不可能成功的,但却没有注意军事武装的问题。同时该著也指出,其原因是中共正处于幼年时期,对革命中的各种问题还缺乏成熟的分析和理性的判断,因此不可避免的存在许多局限性。③
共产国际与“三大”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它的各方面活动都会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考察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可以把共产国际对“三大”的影响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共产国际推动了中共对国民党态度的转变,为“三大”的召开提供了先决条件。鉴于刚成立的苏俄所面临的外交困境,共产国际制定和完善了东方革命战略。在中国推行这一战略策略的过程中,共产国际致力于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建立,从而最终促成了中共从排斥国民党拒绝与其合作到接受国民党,将其看成革命力量的态度的转变。④其次,共产国际推动“三大”确立了党内合作方式。共产国际根据马林对中国革命力量的判断,认为中国工人阶级还未形成独立的力量,国民党才是唯一的民族革命集团,因而共产党员需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式与国民党进行合作。正是迫于共产国际的压力,所以尽管在“三大”讨论党内合作时存在诸多争议,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主张。最后,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迁粤,客观上为“三大”选择了开会地点。广州是当时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是国民党的活动中心,因而把广州作为中央机关所在地为中共的公开活动提供了条件,方便了“三大”的筹备工作,为“三大”的胜利召开提供了保障。⑤
重要人物与“三大”
中共“三大”的重要人物研究是党史学界关注的重点。十年来学术界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对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与“三大”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看法。
1、陈独秀与“三大”。王国政认为“三大”通过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来之不易,它与陈独秀在这一问题上认识的转变有很大关系。“三大”召开前,陈独秀的心路历程大体上经历了从排斥与国民党合作到主张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再到初步接受马林提出的国共合作模式,最后到完全接受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曲折过程。⑥王海琳则对陈独秀在“三大”前后的政治思想进行了梳理,揭示了陈独秀政治思想的合理内容:一是对中国资产阶级作出了合理划分并揭示出其两重性;二是顺应时势,提出了各阶级合作建立革命联合战线的思想;三是正视现实,在充分肯定农民的革命作用同时,对农民阶级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四是所谓“国民革命公式”,这是出于当时实际需要而提出的,是完全符合党的“三大”关于国共合作方针的精神的。据此王海琳认为,简单地认为“三大”前后陈独秀的政治思想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开始,是有失公允的。①
2、李大钊与“三大”。“三大”是李大钊第一次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他为这次会议的召开付出了大量心血。在会议召开前,他为中央确立国共合作方针建言献策;会议召开期间,他力陈正见,平息了争论,使国共合作方针最终确立;会议召开后,他积极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建立统一战线尽心尽力。②有研究者着重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分析李大钊对“三大”国共合作方针的确立所做的贡献。从在理论上看,大会召开前李大钊先后发表了《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实际改造的中心势力》等文章,为统一战线的建立进行理论宣传,扫除了人们的思想包袱。从实践方面看,李大钊奔走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与孙中山、越飞、鲍罗廷等人进行多次接触,为革命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③
3、毛泽东与“三大”。近年研究者更多地把重点放在两件事上:一是毛泽东与“三大”农民问题。研究者普遍认为毛泽东对“三大”关于农民问题的认识有着重大贡献,农民问题是毛泽东首先在“三大”上提出来的,他非常强调农民的重要作用,认为党的工作应首先重视农民问题,同时毛泽东还参与起草了《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不仅为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作了重大理论贡献,也极大地影响了毛泽东本人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④二是毛泽东在“三大”首次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三大”对于毛泽东的政治生涯来讲是一次重大的转折,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被选入中央局成员,并担任中央局秘书,从而进入了中央核心领导层。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所以能够入选中央局,除了陈独秀对其在湖南工作的肯定外,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他的赏识和褒奖也起了重要作用。⑤
综观十年来学界对中共“三大”的研究,可以发现其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研究的广度大为拓展。不仅延续了学界传统的研究题目诸如“三大”重要人物的研究、会议议题的研究,而且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如“三大”与党的建设研究。其次,研究的深度进一步加强。学者们依据新的史料对许多细节问题进行剖析,使研究更加具体、更加细化,进一步推动了研究的规范化、科学化。最后,研究的方法更加多样。实证研究、理论研究、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在“三大”各个问题的研究中都有体现。这些为进一步深化“三大”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也应看到,“三大”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至今为止,研究专著可谓凤毛麟角,同时对“三大”应该划归在中共创建时期还是大革命时期仍不清晰。2013年正值中共“三大”召开90周年,相信“三大”研究可借此东风能取得更大突破。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