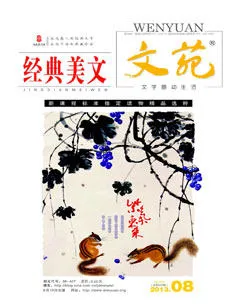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棵树
2013-04-29杜君立
杜君立
在混凝土美学泛滥的冰冷城市,树几乎成为唯一的温情与诗意。离开了树,鸟们将无处栖身;没有了树,人们会丧失栖居的诗意。在灵魂深处,城市里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流浪的游子。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是鲁迅先生的散文《秋夜》开头的一句话。对一个乡村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树是他最早的记忆。几乎每个人都这样在树下长大,或者说,是和树一起长大。树是家园的象征,总是静静地等待。电影中,树所传递的是一种典型的人类情感,从早期的《乱世佳人》到如今的《阿凡达》,树所承载的不仅仅是一身婆娑的叶子,它是家园的温暖旗帜。
如果人是从猴子演化而来的,那么人就是从树上下来的,或者说,人本来是生活在树上的。卡尔维诺有一部著名的小说叫《树上的男爵》,说的是一个叫柯西莫的小男孩与父亲赌气,就爬上一棵树,从此他在树上度过了自己的一生,拿破仑还专程来到树下拜访这位“树上的男爵”。对柯西莫来说,这个世界有两种生活——地上的生活和树上的生活。前者象征平庸、世俗、乏味,后者象征理想、高尚和精神性,“树上的生活”高于“地上的生活”。柯西莫爬到树上象征他不甘于平庸的生活,他坚持不下树象征他绝不放弃自己的理想,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种“抵抗”。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树是自然的象征,人作为自然之子,一直在背叛自然的道路上狂奔,乃至提出“战胜自然”的口号,至此,自然已经成为人类的敌人,或者说,人类成为了自然的逆子。
在煤炭和石油时代到来之前,树是人类的生存基础。工具、住宅、家具、车辆、燃料都来自树。对中国来说,直至30年前,树依然只是一种珍贵的生存资源。这种“珍贵”体现在树木的极度匮乏。一场席卷全国的大炼钢铁运动几乎将所有的树木都付之一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没有足够的木材盖房子、做家具,更不用说做燃料。煤炭和石油使树木被解放了,煤炭和天然气成为主要燃料,工具、住宅、家具、车辆都使用更结实的钢铁和塑料,树木完全沦为一种可有可无的摆设;如果抛开夏日遮阳的作用,那么树仅仅只剩下审美上的价值。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从文化上来说,树完全是乡村时代的象征,这种文化象征对中国人来说更为刻骨铭心。《诗经》上说:“惟桑与梓,必恭敬之。”桑梓早已成为故土家园的标志。在中国北方,一直流传着“大槐树”的故事,“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明初洪武至永乐50年的时间里,有多达百万的山西子民背井离乡,被迁往冀鲁豫秦等省份。600多年来,这些移民落地生根,繁衍绵延,其子孙后代,数以亿计。就这样,洪洞县的一棵大槐树成为他们共同的记忆故乡。一棵普通的槐树,连接起了亿万中国人的家园情结。
人是一种寻根的动物,遗憾的是,乡村时代的记忆已经随着童年一起变得遥远而模糊,城市文化擦写了一切。在青年被城市带走之后,老树也被贫穷的农民出卖到城里,据说一棵老树可以卖到数十万元。树是乡村的灵魂,没有了老树的村庄已经不成为村庄。被夺(剁)去枝干和主根的老树来到陌生的城市,它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记忆,这里的人跟它没有任何关系。
“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对于一棵历经人间沧桑的老树来说,曾经在树上筑巢的鸟儿们到哪里去了?曾经爬到树上吃槐花、榆钱的孩子到哪里去了?如果一棵树没有来历、没有记忆、没有身份,那么这棵树还是这棵树吗?
城市时代,人和树一起失去了故乡与童年。
传统时代的城市其实只是一个大乡村,那里有并不宽阔的街道和高大魁梧的梧桐,一条条林荫大道郁郁葱葱,浓密得如同一道幽深的游廊。绿树荫浓夏日长,自行车的铃声、斑驳的阳光与飘零的树叶,城市如同一个日光隧道,伴随着一代人成长,迎送着一代人老去。马路永远是生活中最浪漫的一部分,谈情说爱其实就是“轧马路”。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村里的青年到城里来了,村里的树也到城里来了,终于,推土机也到城里来了。马没有了,路越来越宽阔,甚至让人望而却步,穿越马路不仅变得困难而且危险。汽车消灭了自行车,城市的扩张变成了路的扩张。路越来越宽阔,路两边的树却越来越矮小,高大朴实的梧桐和白杨遭到鄙视,矮小但昂贵的女贞、银杏和桂树成为浮华城市的新宠,林荫大道被彻底消灭了。城市不仅越来越成为树的敌人,也正成为自然和人类的敌人。
世界上有很多城市,中国正急切地奔向城市化,一切与乡村有关的东西都被弃之如敝屣。在这座古老的新城市,我被人们对树的虔诚崇拜震惊了。一棵古老的大槐树下,石桌、香火、供品,对树的膜拜体现了人的谦卑和对自然的敬畏,这来自于一种植根于传统的智慧和文化。
在一个新建的住宅小区,有许多来自乡村的老树,我们已经无法知晓它们来自哪里。但从现在起,它们将在这里扎根发芽,继续在春来秋往里花开花落;这里的阳光仍然灿烂,这里的泥土仍然肥沃。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一棵栽在小区中庭的老槐树上,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一个巨大的鸟巢。这个鸟巢与老槐树一起来到陌生城市,在一片优雅的住宅深处,鸟与人找到一种共同情感,那就是家的归属。鸟与人之不同,或许在于前者是“树上的生活”,后者则是“地上的生活”。
在混凝土美学泛滥的冰冷城市,树几乎成为唯一的温情与诗意。离开了树,鸟们将无处栖身;没有了树,人们会丧失栖居的诗意。在灵魂深处,城市里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流浪的游子,“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与金钱相比,树重要么?诗意重要么?说到底,就看人的最终目的是生活还是生存。
佛曰: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砂一极乐,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一念一清静。西班牙有个美丽的传说,说一个人要是爱上另一个人,他就会在自己的心中栽下一棵树。但愿,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棵树,春天开花,秋天结果,一直成长,永不老去。
摘自上海三联书店《历史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