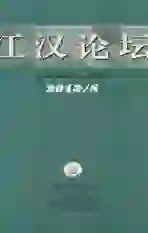死亡叙事的演变与小说美学的关联
2013-04-29王列耀池雷鸣
王列耀 池雷鸣
摘要:死亡是“北美留学生小说”的重要书写主题。“死亡书写”的叙事策略呈现出变化与发展的集体趋势。在母题的不变与叙事策略的多变中,从“留学”到“学留”再到“后留学”时期的“北美留学生小说”,死亡书写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蕴含着独特的精神气质与美学风格。通过“死亡书写”探析文学的叙事策略、精神气质和美学风格上的变动,具有现象学的类型分析价值。
关键词:北美留学生小说;死亡书写;精神气质;关学风格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8-0054-05
以开启北美留学生小说历程的於梨华为参照,“北美留学生小说”已历时50余年。若要从中找出能够贯穿始终的“轴线”,来证实在时间无情流逝中蕴藏的一般趋势,“死亡”可能正是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节点。我们从“北美留学生小说”中可以发现许多作品涉及死亡书写,因此,死亡是“北美留学生小说”的一个重要母题,通过“死亡书写”探析文学的叙事策略、精神气质和美学风格上的变动,具有现象学的类型分析价值。
一、“死亡书写”与小说的叙事策略
纵观延续50余年的“北美留学生小说”,不同时代的“死亡书写”存在着叙事策略的变化:先后历经了“间接书写”、“直接书写”、“亲历书写”等几个不同阶段。所谓“间接书写”,是指在20世纪60年代的死亡叙事中,可以感受由死亡迷惘带来的一种有意逃避或躲闪的叙事态度;而70年代以后出现的“直接书写”不再是60年代的“逃避”,而是刻意渲染死亡过程及其场景;新世纪的“亲历书写”,我们不妨借助“遗书”这一相关意象来加以阐释,作品中的遗书作为死者最后的言说,降低了死亡降临的突兀感和偶然性,填补了“间接书写”和“直接书写”因死亡而在作者、人物和读者之间产生的叙事空隙。
1.间接书写
20世纪60年代的“北美留学生小说”对死亡的书写方式是间接的。在《芝加哥之死》的结尾,吴汉魂这样叙述自己的死亡:“他心中不由自主的接了下去:‘一九六零年六月二日凌晨死于芝加哥,密歇根湖。”这显然违背了死亡的基本逻辑。一切死亡都是他人才能见证和表述的死亡,自我对于死亡不具有陈述的亲历性。也就是说,小说仅叙述了吴汉魂之死的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吴汉魂到底有没有死,取决于读者个人的情感体验,是一种开放式的结尾。《又见棕榈,又见棕榈》虽然只涉及邱尚峰的死亡,但对于优柔寡断的主人公牟天磊而言,精神导师的死,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令其下定决心留在台湾,“至少一时不去美国,正好这件事对学校对邱先生都有点好处,所以不但我自己觉得舒服,同时也可以让邱先生在地下安心”。虽然牟天磊没有死,却因邱尚峰的死,在“留”与“不留”的迷惘中,寻觅到了一条不甚明朗的出路,进而带来了“替代之死”的叙事意味。《桑青与桃红》中的“死亡”同样来自于小说人物的自我叙述:“我不叫桑青,桑青已经死了!”事实上,桑青与桃红只是一个人的两种精神状态,但在小说中,桑青之于桃红具有死亡的真实性,而对于“身在其外”的读者而言,桑青就是桃红,并没有死。其中要旨,正如白先勇所言,“这是精神上的自杀”。
相对于“间接之死”,《谪仙记》中的李彤之死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李彤在威尼斯跳水自杀”,这“自杀”在友人的惊诧中却显得不可思议。李彤没有留下遗书,仅有一张漂洋过海而来的照片。从对这张从意大利寄来的彩色照片的叙述来看,“佻达”、“扬得高高的”、“笑得那么倔强”等修饰性词汇并没有暗示出死亡迹象。再者,整个故事通过陈寅这个人物讲述,准确地说,李彤的故事是由限知性的第三人称来转述的,信息在转述中因某种遮蔽而造成的不准确性,在陈寅见证李彤的美丽中就已发生过。转述中的李彤之死,会不会如她的美丽一样,非得亲眼所见才可以被确认呢?这是陈寅的质疑。对处于“转述的转述”位置的读者而言,李彤之死更具有不确定性,这种质疑或不确定性与叙事结果的确凿形成冲突。
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北美留学生小说”有关死亡的间接书写,似乎有意造成叙事的困惑,其中隐藏着作者躲闪甚至逃避的叙事态度,给处于不同时空的读者带来了感同身受的迷惘体验。
2.直接书写
在60年代的“死亡书写”中,很少见到死亡场景再现,尤其是关于死亡的具体感受。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死亡书写”由间接叙述转向直接,具体亦可分为三个角度展开:死亡描写方式的“直播”、死亡情感态度的渴望和死亡体验的一致。
……你打开折刀,用力将手腕按上去。一阵剧痛,你举起手腕。红色的液体,顺着手腕淌下,形成一道细流。你望着那股细流,慢慢流下手臂,流向胸前。它不再是一股细流,它形成了一条巨河,包围了你,你在里面载浮载沉。你并不感到特别痛楚。你尽可能张大眼睛。红色的巨流,似乎逐渐转变成蔚蓝色。你漂浮在蓝色的河水里,你看不清楚两岸的景色,但你知道这是多瑙河,蓝色的多瑙河,河水带着你流向那无牵无挂的地方。
“死亡”的细致表现,适时穿插富于煽情气息的解说,运用蒙太奇手法在血液与河流之间切换,如同直播自杀一样。令人奇怪的是,主人公在自杀过程中,不仅“并不感到特别痛楚”,而且还置身魂牵梦绕的蓝色多瑙河中,“流向那无牵无挂的地方”,用死亡答复普希金的诗句:“世界!哪儿才是我毫无牵挂的路程?”还有丛甦小说《想飞》中的“他”从大厦上跳下来的刹那,真切地感受到了鸟的飞翔,仅仅为了用死亡反驳黑衣人的裁定,“人永远没有鸟的解脱,因为人有无地的欲望,这其实是自己的过错”;以及《在乐园外》陈甡的最后遗言:“不必追究原因。我死是因为‘不为什么。”几乎是用死亡验证加缪“自杀是对荒谬意识的解决之一途”的箴言。由此可见,小说人物对于死亡的态度并非如吴汉魂、李彤那样苍凉悲伤,恰恰相反,表现出对死有大寄托、大希望的渴望之情。
无论是描写方式的“直播”,还是向死而生的情感态度,这些小说似乎都在强化死亡的事实,渲染死亡的气氛,让读者身临其境般地观看、感受他人的死,增强死亡本身带来的震撼力与感染力。此外,叙述者还在讲述过程中有意强化这种感染力,用第二人称的“你”,来唤醒读者的感同身受(《蓝色多瑙河》),或用第三人称的“他”引起读者观赏的冲动(《想飞》)。总之,70年代以后的“死亡书写”用刻意拉拢来填补叙事的距离。通过直播驱散死亡带来的思想与精神迷雾,这种文本内外的“一致化”处理,旨在澄清某种生存/死亡的真相。
3.亲历书写
进入“新世纪”,死亡书写最显著的变化是遗书作为一个道具在小说结构布局中获得显赫地位。在此前的死亡书写中,“遗书”对于死亡的指引意义并不被看重,因此在《谪仙记》、《想飞》、《艳茉莉妇人》、《蓝色多瑙河》、《冬夜杀手》等小说中,并没有显示出它的作用;即便《在乐园外》、《纸婚》、《千山外,水长流》等小说中出现了遗书,成为调动叙事顺利运转的重要棋子,但在情节发展中并不具备关键性的影响。而在《Danny Boy》中,一份云哥给韶华的遗书,就占了小说三分之二的篇幅;《彼岸》中,何洛笛的遗书成了小说的结尾;《Tea for Two》中,大伟与东尼的遗书,在情节发展中具有转折性的重大意义:让“欢乐族”从死亡的阴霾中重获生活的勇气。
遗书作为死者与他者的最后一次沟通,或者作为死者留在人世的最后印记,无疑具有死者生命回显的意义,再现出死者对于死亡的预见性或主动性。云哥、大伟与东尼、何洛笛正是如此,而对吴汉魂、李彤、《想飞》的“他”、《蓝色多瑙河》的“你”而言,死亡更多体现出突如其来的生命冲动,带来始料未及的震惊感。此外,遗书还具有指引生者的意义。云哥在遗书中回顾了自己由无望到希望的生命历程,深深触动了韶华的悲悯情怀:“我在床边跪了下来,倚着床沿开始祈祷,为云哥,为他的Danny Boy,还有那些千千万万被这场瘟疫夺去生命的亡魂念诵一遍‘圣母经。”大伟和东尼的遗书里,乐死安生的生存态度为生者驱散了死亡阴霾,并指引前行的方向。何洛笛的遗书则更多地体现出对儿女子孙的最后关怀,“临别唯一赠言乃是你们三个人的互助互爱,并相互尊重,切记”,凝聚无限深沉的母爱。
小说中的遗书是人物(临终者)在生命终结之前完成,带有亲历性的特征,由于遗书具有人物和读者在阅读时间和阅读内容上的一致性,因此它所带来的亲历性并不独属于小说人物,还同时属于作者和读者。在笔者看来,这意味着此种死亡书写体现出对作者、人物和读者亲历死亡的强调,以此在作者投射、人物体验与读者感受之间形成感知的统一。显然,小说对遗书这一独特道具的使用,增强了生与死的关联,降低了死亡的突兀感和偶然性,使读者对死亡有一种亲历感受,即便是虚构的,但它至少提供了一种想象死亡的场景。
简言之,“北美留学生小说”的死亡书写在叙事策略上呈现出时代性和阶段性:也表明了不同时期的美学追求,以及植根于其上的时代状况。而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种叙事美学追求何以超越个案而成为一种具有集体无意识的趋势?换句话说,不同时期的叙事策略的选择隐藏着怎样的精神气质?
二、死亡书写与小说的精神气质
“北美留学生小说”的死亡书写在不同时期呈现的不同叙事策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家在寻找最适宜的途径以传达内蕴于特定文学母题中的自我精神气质的过程。换句话说,特定母题的叙事策略改变蕴含着作家思考社会、人生以及文学的变化。笔者将其统称为“精神气质”。
1.“留学”时期的迷惘
在间接书写的叙事策略所带来的美学体验中,我们并没有感受到浓郁的死之悲情和自我与他者的紧张氛围,“死亡”在此阶段文学里并不代表某种人生结局,而是一种与主体迷惘相关的人生选择。或者说,其意义所指,并非人生的单向结束,而是介于过去与现在、记忆与憧憬之间的停留。
“腐尸”是《芝加哥之死》里一个至关重要的意象,所隐喻的正是文化。当吴汉魂在睡梦中将母亲的尸体推入棺材时,也就意味着母亲所代表的中国文化被吴汉魂亲手“斩断”与“拒绝”,取而代之的是《艾略特全集》、《荒原》和芝加哥的高楼大厦等代表的西方文化。当比母亲死讯更重要的《艾略特全集》、《荒原》等书籍“全变成了一堆花花绿绿的腐尸”,二十二层大厦也成为“埃及的古墓”时,也就意味着被吴汉魂极力拥抱的西方文化终成泡影。记忆中的中国被自己摧毁,憧憬中的美国又成为一座坟墓,吴汉魂只能祈求“一个隐秘的所在”:与其说它代表肉身的死亡,不如说是内心精神的崩溃。
吴汉魂的文化取舍、李彤的性格转换、牟天磊的去留彷徨、桃红的精神分裂,无不体现出二元对立的行文结构。这种对立模式所隐藏的仍是文化上的中西对立。有趣的是,这种原本明晰的二元对立因为死亡而在结尾变得模糊起来。因此,对立不是选择中的困惑,而是选择后的空洞。如李彤之死,群体困惑没有就此终极解决,反而更加扑朔迷离。初始的二元对立,转变为“二元无解”。这种精神迷惘造成的无措和认知迷宫,作为结局应属于小说角色,作为呈现过程则应属于小说作者,因为他们60年代负笈北美,新天地获得的生命感性刚刚起步,体验“心慌意乱和四顾茫然”的生活,文化冲撞,身份抉择,弱国子民,故园眷恋等这一代人特有的“双重放逐”,郁积于心,挥之不去,难以释怀。以致陷入去留两难的迷惘状态,难怪白先勇当年借黄庭坚词浇胸中块垒:“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
由于缺少审视距离和斑驳岁月的过滤,理性思索“当代”的解决之道,显然不是60年代青年学生力所能及的文学理想,而传达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精神共鸣,遂成为“最迫切的事”。死亡作为人类的终极关怀,在60年代的“迫切”中多少显得不合时宜。对青涩的作家而言,与其深切呈现,不如浅尝辄止,去开凿“死亡”背后那口深深的井。如此一来,对“死亡”的间接书写遂成为一个时代的集体谋略,与“留学”时期作家们“雾里看花”的精神气质不谋而合。
2.“学留”时期的焦灼
与60年代的死亡假象不同,70年代以后的文学大多“死得真切”。当然它同样是作者思索与认知的结果,但死亡本身不再指向迷惘的过程,而是有意义的终点。作为一种解脱或是一种关注,死亡显然带着太多对于人以及社会的焦灼。
勒维纳斯曾说,死亡意味着“一种存在的终结,那些满是意义符号的运动的停止”。因此,死亡或许是人在生存荒诞与虚无境况下最直接的归宿。面对浓雾弥漫的现实处境(《半个微笑》),在人的机能、本性、欲望所造成的漆黑黑洞中永恒陷落的身体(《想飞》),不断折磨的世界(《蓝色多瑙河》)等种种生存困境,人是如此地无能为力、渺小,反不如“小小”的蟑螂(《长廊三号——一九七四》)。正如陈牲那不经意的遗言:“不必追究原因。我死是因为‘不为什么。”面对生的虚无,死成了充实的归宿。反差和对立所造成的强烈震撼力在死亡降临时聚焦,行文中点滴积累的虚无与恐惧,终在结尾处瞬间的死亡美景中稀释。由此引起巨大的叙事张力以及意味深长的叙事效果。呼唤读者积极介入人和境遇关系的思索:贯穿始终的焦灼究竟因何而来?
死亡引起的焦灼表面上来自“死亡书写”所导致的深度阅读体验,而对人的深刻思索和对社会的广泛关切则是更为内在的原因。70年代以后大多数作家都已结束了留学时期,进入了“学留”时期,除了物质生活的改善之外,最明显的变化在于个人法律身份的改变:由华侨变为华人。虽然法律身份的改变并不意味着个体文化身份也随之而变,但随着个体对美国文化的日益了解和深入以及与母国文化在时空距离上的逐渐调整,那种深层次的文化二元对立所引起的无措思索和迷宫式认知,在理解和怀念中不再成为文学的主题。步入中年的他们将死亡这一表现利器从个体宣泄中转向生存关切,从狭小的留学生圈子转向更为广阔的人类社会,“作者本人早已走出了象牙塔,真正地面对现实中的丑恶与残酷”。
海德格尔说:“临终到头包括着一种对每一此在都全然不能代理的存在样式。”因此一切死亡都是他自己的死亡,所谓死亡解脱只是作者自我的文学想象。作者渴望读者能够明白自己的“煞费苦心”,并与之对话,也就意味着死亡的想象不仅仅是个体的,更是群体的。这一时期的作家采用直接的叙事策略营造和渲染死亡想象的真实性,他们期待“沉浸其中”的读者在确凿的死亡事实中一起思考和认识生存的本来面目。
3.“后留学”时期的坦然
与“留学”和“学留”时期文学死亡书写的迷惘和焦灼不同,“后留学”文学主要表达出对人生与社会的坦然。
从遗书使用“十分满足”、“了无遗憾”作为人生自我总结,可以体会出何洛笛(《彼岸》)的自杀与吴汉魂(《芝加哥之死》)、林萍(《半个微笑》)、“癫妇”(《癫妇日记》)等人的自杀心态和成因等诸多差异。何洛笛的死不是迷惘、冷漠、恐惧、无奈等生存困境造成的,而是直面生命的坦然。白先勇的《Danny Boy》、《Tea for Two》和之前的《芝加哥之死》、《谪仙记》、《夜曲》、《骨灰》等相比,死亡书写关注的不再是灰色人生中的迷惘,而是张扬一种超越生命的精神力量。云哥(《Danny Boy》)在遗书中回顾生命历程,庶几为白先勇同性恋题材的总结与超越。云哥大半生都有着白先勇笔下同性恋人物类似的孤绝与悲凉:“大多数都不能安定下来,也控制不了自己,堕陷在肉欲与爱情追逐的轮回中,总是移动游荡,急切探索,不断地追寻,却像绕圈子一般,从少年时期到老年,永远找不到解脱的出口。”但在生命尽头,云哥发现了向死而生的力量,由此重新确立生命的精神基调:“在我生命最后的一刻,那曾经一辈子啮噬着我紧紧不放的孤绝感突然消逝……我不再感到寂寞,这就是我此刻的心境。”云哥在死亡面前领悟了生命的意义,悲楚凄惶的人生境况亦因此升华到坦然充实。而在大伟与东尼(《Tea for Two》)的告别信里,死亡仿佛成为又一个快乐生命的旅程:“再会了。孩子们,我和我最亲爱的终身伴侣东尼我们两人要踢踢跶一同跳上了‘欢乐天国去。”正是这“踢踢跶跶”给了艾滋病阴霾笼罩下的“欢乐族”重拾欢乐的勇气和意志。
如果说“留学”时期的“死亡”是一种间歇,意味着“断裂”,即过去和未来因为现在的不确定性而被悬置,那么“学留”时期的死亡则体现了延续,意味着“超越”。未来是一种希望,同时在超越期待中弥漫着社会焦灼。在笔者看来,“后留学”时期的“死亡”又有不同,意味着“传承”,过去只是一种托付,在传承中隐喻了生命自身的坦然,是岁月磨洗后的生存法则和人生智慧的华丽呈现。进入新世纪,大多数作家都已进入“耳顺”之年,60多年沧海桑田的世事变迁和日积月累的人事经验,有助于一生都在思索人生意义的他们达到“无碍于心”和“参透人生”的人生境界。正是这种自然生理和人为心智上的成熟,让他们拥有了青年和中年时期难以达到的“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坦然。作家的这种得之不易的气质也自然地投射到小说之中,艺术地呈现在人物身上,以致实现了作者和小说人物在精神气质上的一致。“死亡”作为回溯中的托付与传承,实际上是一种“盖棺论定”式的人生总结。它最佳的呈现载体莫过于遗书。
三、“死亡书写”与小说美学的关联
自柏拉图以来,死亡讨论一直是个严肃的哲学问题。海德格尔说:“只要此在生存着,它就已经被抛入了这种可能性。”但是他认为死亡不是存在的终结,而是向着终结的存在。在死亡面前,每一个生者只能作为一个观察者。这一角色也正是在“留学”和“学留”时期的“北美留学生小说”作家们所担当的。他们对死亡表现出的无论是迷惘与逃避,还是焦虑与渴望,都无法改变这一基本事实。西蒙·韦伊在《重力和恩惠》中说死亡是一个“既无过去也无未来的即刻状态”,也就意味着观察者不可能获得关于死亡的真正体验,即便在文学世界中也只能借助于想象。正因如此,死亡呈现于文学作品,是一个植根于观察和想象的美学问题,死亡不同于对死亡的表述。
联系“北美留学生小说”作家主体的身份变动,我们可以从社会学角度试作探析:“留学”时期的青年作家沉浸于倾诉自己的人世迷惘,他们无暇释放自己的死亡想象,只能做一个逃避的观察者,以间接的死亡书写方式去表现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迷惘情绪。“学留”时期的中年作家走出个体的拘囿,自觉肩负起人性拷问和社会关切的历史使命,用想象充实无法经历的死亡体验,用直接的方式幻想死亡到来时的种种情景,通过凸显死亡的现场感来增强死亡事实的感染力,以让读者沉浸在“无望的生”与“希望的死”之中,并体味与思索贯穿始终的焦灼。显然,没有真实体验的想象,终究带来的只是一种空洞的“真实”。但在“后留学”时期的亲历书写中,感受到的已不是观察者的死亡言说,而是努力书写出亲历式的死亡体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生活事实,但确实是充盈的文学真实。它得益于“后留学”时期的作家对人情世故以及存在经验的深刻理解,通过遗书意象的发掘对小说人物的临终状态予以精心塑造。
死亡书写的变化表明了作家的成长,相对于“留学”与“学留”时期,“后留学”作家更深刻地体会到了死亡的存在意义,当然,也包括了死亡书写的他人性和间接性,因此,他们只能通过借助于道具的方式去再现死亡的内在过程,用诗性的方式去探讨此在如何失去了意义,必须通过毁灭的方式去延续。
不管是坦然的死亡心态、真实的死亡想象,还是遗书的死亡承载,都离不开作家在死亡书写中的发现:临终状态的艺术存在。“临终状态”可以理解为“临终”这一动作的时间延展,临终是死亡在此岸的必经之途。在这个意义上,“留学”时期在死亡书写中表现出的有意逃避(间接书写)、“学留”时期的刻意亲近(直接书写),之所以会带来空洞的真实,正是由于处于青年、中年时期的作家们对于临终有意或无意的忽略,而对它的重新发现甚至浓墨重彩地艺术再现,显然与作家因成长而达到的心智的澄明有关,从作家自身的生命个体来说,探讨死亡及其过程也是与生命相关的内容,死亡即是为存在去蔽。
作者简介:王列耀,男,1955年生,湖北武汉人,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510632;池雷鸣,男,1984年生,河南虞城人,文学博士,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632。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