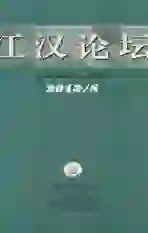创伤体验与早期左翼小说的革命叙事
2013-04-29周仁政
摘要:伦理化的精神创伤体验是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叙事特征,它开启了现代小说政治化叙事的先河。张闻天的《旅途》和蒋光慈的小说分别以情爱和困厄为中心,从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角度为早期左翼小说的政治叙事确立了方向。
关键词:创伤体验;左翼小说;革命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8-0044-06
一、伦理与革命:鲁迅小说的伦理化精神创伤体验及其政治叙事
从中国现代文学史来看,说五四“发现”了文学,文学演绎了情爱,情爱遭遇了革命,并不为过。这条轨迹也正反映了五四文学的情感表现向政治化表达的位移。即是说,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或许并不像有的论者所说,是一种陡转或逆转,即所谓“革命压倒启蒙”,而是顺承或呼应,即启蒙造就了革命。
革命是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主题,不可否认的是,五四前后均是以知识分子作为政治主体。辛亥革命之所以被称为资产阶级革命,乃是因为其主体是当时业已“近代化”的知识分子上层,他们诉诸政治革命的方式是由上而下。其革命的后果是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不能不说这是近代中国政治革命的莫大功勋。然而,属于经济层面的“平均地权”却因为袁世凯的复辟帝制而未果,这就给后来的社会革命留下了看似简捷却极其繁难的任务,以致于这一沉重的“尾巴”拖垮了前此革命造就的辉煌。
从文化史上看,五四作为现代启蒙运动并没有真正承担起多少货真价实的使命。现代教育不是从五四发源的,现代科技在五四时代并没有什么耀眼的成就。恰恰是借助了早年改良派遗留下来的文化阵地——北京大学,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群体才得以跻身历史之中。以《新青年》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启蒙运动实际上是一场以政治为目的的社会救亡或文化革新运动。因此,它的诉求是单一的,基本上是政治性的。这一运动的直接后果。就是造就了一批不同于辛亥革命时代的新的知识分子群体。这是一批主要在国内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受到《新青年》哺育的新的政治弄潮儿。较之其前辈,他们少了些“洋气”多了些“土气”,但革命性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不承认没有经济成果的社会革命,把一种民粹主义的社会担当视为革命的法宝。就像鲁迅在《阿Q正传》中把辛亥革命时代的知识分子称为“假洋鬼子”,经过了五四洗礼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劳工神圣”的口号下则成了阿Q革命的引路人。
诚然,在《新青年》的旗帜下,五四新文化运动曾经是一场以广义的文化批判为目标的社会文化革新运动。但是,一切文化批判的手段却都呈现出直接而鲜明的政治目的性,无论是陈独秀主导的“伦理的革命”,还是胡适主导的文学革命,莫不如此。只不过,陈独秀所谓“伦理的革命”着重于倡导科学主义的实利和经济至上的平等,即价值观上的唯物主义和政治观上的社会主义;胡适的文学革命则以创新文化工具为手段,走改良主义的文化普及和政治民主化道路。鲁迅的出现使这二者的结合成为可能,但却是在陈独秀意义上的结合而非胡适意义上的结合——《狂人日记》使尚属理性的政治文化批判(伦理批判)滑向了政治化表达的渊薮。从此,指向传统的一切理性表达在社会政治学意义上都失去了地位,“吃人”的标签和感性色彩浓郁的伦理审判把一切关于文化历史的理性思考拒之门外。虽然这并非鲁迅本身思想的简单化,但一种看似深思熟虑高屋建瓴的独断由于未能给受之者开辟思想和理性判断的空间,从而导致认可和接受成为不容置疑的选择,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必然是政治性的。所以,与其说《狂人日记》是一篇思想启蒙的小说,不如说它是为陈独秀“伦理的革命”张目的政治檄文,日后的文学表达都较多地带有政治表达的鲜明意味。这造成了两个显著的后果:文学和政治的结缘及知识分子文学表达的政治化(包括表达方式的感性直观化和情感化)。
五四固然“发现”了文学,但所“发现”的文学是“科学”。以《新青年》为代表,以科学的“拜物教”属性确立文学的意识形态价值,从而使文学与政治发生更深的捆绑。这诚然是五四和《新青年》的功绩,但也使文学交上了魔咒式的现代厄运。
显而易见的是,作为文化启蒙阵地的《新青年》,不仅存在着独立思想和自由表达的文化诉求的缺失,而且它所有的文学表达都具有政治表达的鲜明特征,除了作用于现代政治史,作用于现代文化史。它的影响无疑是具有消极性的——真正的启蒙或许仅在其圈外进行。但同时,在现代政治史上,它则每每先声夺人。从对社会主义的提倡到对俄国革命的认同。及于民粹主义特征鲜明的“劳工神圣”口号的提出等,它要造就的是一场不同于辛亥革命的新的社会革命,其着重点在于:经济优先和民众参与。但就其自身看,预设的政治主体却依然是知识分子。
然而,知识分子革命意识的产生无非具有如下思想底蕴:一是民本主义的道德关怀,如历史上知识分子对农民革命的参与和认同:二是自身的政治理想,如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三是精神性的创伤体验。这需要一个由个体向群体延伸的过程,五四正是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环境,开启了这样一种历史进程。五四时代,文学在启蒙的意义上如何激发了知识分子的革命意识,过去一直认为有赖于《新青年》等的政治宣传,即与知识分子确立自身新的政治理想有关。但这显然并非一个发生学意义上的具有说服力的观点。胜于那些纸上谈兵的政治理论,作为情感表现的文学提供了一种具有精神现象学和社会心理学意义的揭示。
以文学作为政治代言实则源于梁启超,即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胡适、陈独秀发动于《新青年》的文学革命承袭了其文学理念。但与梁启超着力提倡政治小说不同,《新青年》的文学革命是以否定传统为前提的,它对白话的提倡及新诗白话化(散文化)实践是以文学革新为手段的文化破除行为。其文化破除的基本方式是否定文化的贵族化,而实践了文化的平民化。因此,平民化成为文学革命的第一大政治诉求。正是在这一诉求中,胡适、陈独秀发现了白话的作用,以及白话文学的威力。但同时,陈独秀、胡适的分野也正体现在这一问题上:胡适发现了平民之于文化的要求,即文学之于启蒙(政治民主化)的任务;陈独秀发现了平民之于政治的要求,即他们现实需要中所蕴含的经济性质的革命诉求,力促用文学的方式表现他们的生存境遇,即政治和文化上的受压迫状况。当周作人以《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演绎出胡适的命题时,鲁迅则以自己的方式把文学导向了陈独秀式的表达。
就鲁迅而言,他以小说《狂人日记》迈上启蒙文坛,并非止于《新青年》的要求(伦理革命或文学革命),而是与其长期以来对政治性问题的思考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鲁迅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偏于伦理性,即视人的精神救赎重于物质拯救。但同时,他所思虑的人的救赎性问题重点不在个体,而在群体,从而看不到这一问题本身所具有的改良性质,而在不断的历史性考察和长期的心理郁积中产生焦虑。借助《新青年》一隅,他以《狂人日记》所表达的伦理革命的理想是激进主义的政治诉求,即通过揭示个体心灵的创伤性体验把一种伦理诉求政治化,将精神的创伤肉体化,从而使社会内在的文化矛盾转化为外在的政治对立——保守和激进正是五四时代所具有的最典型的政治对立,也是革命时代政治对立的基础和前提。
实际上,当一种精神性的创伤体验由个体出发上升到文化高度并诉诸社会性解决的时候,文化问题就已然政治化了。不仅如此,揭橥者因其获得普遍认同的程度跻身文化革命的主将或领袖之列,个体意志转化为群体意志,社会革命的星星之火便由此燎原。同时,当一种伦理化的精神创伤体验以文化的历史形态和感性化的文学形态被其揭橥者和追随者不断作出新的颠覆性表达的时候,在政治意义上它就陷入了否定性的渊薮,其背后的伦理秩序和文化价值便沦为被抛弃和解构的集体意志。当这种集体意志获得高度认同和被不断强化之后,以其“文化”为目标的社会政治革命就势必发生。
因此,现代政治革命既是以“文化”为对象,也以“文化”为目的。这源于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的伦理化的精神创伤体验。在“文化”中,当几乎所有一代知识分子把他们获致于传统的伦理观念和社会认同视为谬误和诳骗的时候,不仅这种“文化”的公信力会全然失去,而且置身其中的文化主体——知识分子,也会以否弃自己的文化权威为代价,转化为政治主体——视自己为一无所有的社会阶层,犬儒主义地认同底层道德观和政治诉求。这是现代民粹主义政治价值观的伦理基石。
在鲁迅小说中,《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和《阿Q正传》中的阿Q是本质上具有道德认同感的一对,他们虽身份不同:一是具有伦理化的精神创伤体验的知识分子;一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但社会地位的差距并不妨碍他们在道德认同感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从而使他们的政治价值观趋于一致。如果说“假洋鬼子”们不准阿Q革命是因为缺乏道德认同感,那么狂人(当其被“正常化”之后)正是未来阿Q革命的引路人。
显而易见,狂人是一个未来化的政治形象,从而也是区别于辛亥革命时代的新的政治主体诞生的标志。他不仅是巴金《家》中觉慧等的雏形,也是蒋光慈《田野的风》(《咆哮了的土地》)中李杰的原型。
二、情爱与革命:张闻天小说《旅途》的欲望化精神创伤体验及其政治叙事
就现代政治革命的历史品质而言,经济诉求实则只是一个理论性命题,即为着满足某种政治哲学的认识原则而附设的观念前提,而非一个实践性命题,即除了革命中的实际需求,革命者和革命进程并不需要。也没有预设任何一个经济性目标。这在于,现代社会革命以激烈的社会动荡和激进的政治行为所展开的,实则只是一个“文化性”事件,这个文化性事件的本质是伦理价值的颠覆与重建——颠覆家族性的伦理文化,建构政治性的伦理文化。
当然,较之辛亥革命的开展,现代政治革命由单一主体(“假洋鬼子”们)转化为双重主体——价值主体(“狂人”们)和行为主体(“阿Q”们),联系他们的不是经济的纽带而是伦理的纽带,亦即政治化的道德纽带(犬儒主义的道德认同)。而在经济上,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舍弃:舍弃家国而归于政党(政治群体),舍弃个人而归于集体(就“阿Q”们而言,经济舍弃被视为一种政治觉悟,但本质上是受到革命伦理的裹挟,被迫认同于“狂人”们的社会理想)。此外,前者较之后者的舍弃还多了一种道德优势:舍弃亲情归于“阶级情”(政治伦理),从而赋予作为革命的价值主体——知识分子以道德上的高尚感和政治地位上的优越性。
但是,如果说正是鲁迅笔下知识分子的伦理性的精神创伤体验赋予了现代社会革命以正义感和高尚性,那么,“高尚的”伦理革命只是培育了观念的“狂人”而非行为的巨人。实则五四时代颠覆性的伦理革命实践养育了一批具有现代政治行为能力的“狂人”,他们把启蒙者的“高尚的”伦理革命理想化作现实的社会革命行为,从被否弃的“家”(亲情)中涅槃而出,在道德的保守性与欲望的革命性中择“善”而从。情爱成为涅槃于旧家庭、旧道德的新一代“狂人”们最具政治价值感的革命性诉求,因而也是现代社会革命具有诱惑力和火药味的叛逆性的政治行为。
从理念的叛逆到行为的叛逆,正是批判的现实主义向行为的浪漫主义的转变。前者以鲁迅和《新青年》群体为代表,后者则以创造社为主力。就创造社而言,无论是郭沫若还是郁达夫,他们以情爱为主题的创作无论是诗还是小说,所传达的都是一种欲望化的精神创伤体验,其中带颠覆性的伦理表达都可以上升到诉诸社会革命的政治层面。和鲁迅不同,他们的精神创伤体验是经验化的而非理念性的,他们不再是向历史表达,而是向现实表达。因而,其诉诸社会革命的方式是更直接的行为化。他们不是思想的巨子而是行为的狂人,就像喝着狼奶长大的一群,满身的欲火必将化作政治的烈焰。
毋庸置疑,文学上的浪漫主义是现实革命的火种,而浪漫主义火焰中燃烧着的是情欲。情欲是火,青春是油,社会土壤中多有助其燎原的干柴。1930年代曾在江西苏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在遵义会议上成为中共最高负责人之一的张闻天,早年便是创造社文学道路的追随者。1924年,张闻天以其赴美国勤工俭学的经历写成小说《旅途》,确是一个较早以其欲望化的精神创伤体验展现恋爱加革命的重要文本。
小说描写年轻的钧凯远渡美国成为某家工程局的工程师,但他全然没有工作的兴味,终日郁郁寡欢。一个名叫蕴青的女子自中国来信,告知她即将出嫁的消息——嫁给一位她不爱的男子。钧凯和蕴青本是一对恋人。他们自由恋爱,却不容于双方的家庭,未成正果。赴美之前,双方本在热恋中,钧凯原想放弃赴美,无奈冲不破重重阻力,分离恰似一种了断。这在双方心里留下了无可愈合的创伤。
这种情爱叙事反映的正是创造社作家的特征,如冯沅君、王以仁等。张资平、叶灵凤的小说,早期也多用这种模式。但值得注意的是该小说的叙事背景,与郁达夫的《沉沦》一样,它表现的是一个身处异国他乡的青年的情爱心理。
《旅途》的主人公钧凯和《沉沦》的主人公“他”都是旅居国外的病弱的青年,不同的倒并非他们的身份(工程师和学生),而是他们的际遇。他们的“病”也都一样:情欲导致的精神创伤。但《沉沦》中“他”的心理病因是情欲无法释放产生的心理变异,以致向动物本能的性欲滑落。郁达夫借此展示了一个现代人受社会和道德情感压抑,向自然本质回归的模型。按照周作人的说法,他是要“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的写出升华的色情”。郁达夫“非意识展览”的正是自己基于情欲的精神创伤,这既来自道德,也来自本能,所谓“灵与肉的冲突”。但这仅仅是“现代人的苦闷”吗?其表达的“苦闷”也许并非现代性的,而“展览苦闷”却是现代性的,即所谓“青年忧郁病”的解剖。在五四文学中。创造社作家的自我解剖成为一种现代性的叙事策略,源于其被泛化的精神创伤体验。“展览”乃是一种具有解剖性的透视,而非平面观瞻。浪漫主义确乎使文学富于立体感,因而往往被称为“自然主义”。也正是在“自然主义”的意义上,郁达夫的小说曾受人诟病。“自然主义”的精神创伤体验被人视为颓废的和“不端方”的文学,源于其道德上的自我贬损,这在政治上沦为一种不高尚的行为。因此,以《沉沦》为代表,郁达夫的小说并非关涉革命,但含着对革命的召唤式叙事,这不仅在于《沉沦》结尾作者让主人公喊出了“祖国呀,快强起来”的呼号,更在于作品的整体叙事中渗透着现行道德失据,青年一代情欲贲张,灵肉冲突的矛盾产生了不可回避的文化否弃力和政治冲击力的深厚意蕴。
《旅途》中的钧凯本质上也是“他”一类的人物,但完全不同于郁达夫式的自然主义,作者运用了极具政治正义性和道德优越感的理想主义表达。因此,同为身处异国他乡的“青年忧郁病”患者,钧凯和“他”的际遇全然不同。不同于“他”的遭遇冷眼,钧凯得到的是温情——他先后获得同事之女克拉小姐和密斯玛格莱的爱情。前者为他的冷落而殉情自杀,后者因他要回国陷入相思之苦,在追随的途中染病而亡。不仅如此,在其几乎所有的美国同道和朋友中,这个东方气质的“青年忧郁病”患者俨然一位光环满身的圣贤,异性的爱恋、同事的称道、朋友的安抚,一样都不缺少。与《沉沦》中“他”在日本的境遇有天壤之别。应该说,这种差异的产生并非反映了某种历史的真实,所依据的无非是观念。从最广义的政治学意义上讲,
《沉沦》凸现的是一个与辛亥革命多少有些关联的民族主义话题;《旅途》则把时新的国际主义引进了浪漫主义的叙事文本。它要达到的无非是对情欲合理性的强调。从一个国际化的层面,把恋爱自南正义化和道德化,免去各种“非端方”的指责。从而。情欲的浪漫主义俨然具有了政治行为意义上的道义感和正当性。
基于此,《旅途》的叙事采用了理想主义的表达方式。其中主人公处置情欲的方式,从道德意义上讲是节制,在政治层面则是牺牲。但节制和牺牲的是情欲,带来的并非思想的理性和行为的稳妥,它的政治效果(行为范式)和《沉沦》式的放纵其实一样,都是激烈的破坏欲。所以,《旅途》下部钧凯执意要回国参加革命,置玛格莱的情爱于不顾。情欲的内在冲动如不演化为革命的政治行为,恋爱自由的理想就是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神话。同时。如果说钧凯在克拉小姐、玛格莱身上遭遇的情欲是人本主义的,那么唯有国际主义色彩的革命才能使加之其上的政治、道德枷锁被打破。所以,深明大义的玛格莱在诀别钧凯时激昂地说:“革命!这是我们的一切,把我们俩驰向于血浪中的就是它!”这种有关情欲的普适价值的表达。亦是赋予情欲的精神创伤体验以政治正义性。恋爱神圣的理想或情欲的精神创伤体验成为现代中国社会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最强音,显而易见的是其中所折射的现代中国及其所欲适应的世界文化中的欲望政治学。因此,从郁达夫式的自然主义“展览”到张闻天式的理想主义粉饰,欲望化精神创伤体验的书写在浪漫主义文学的意义上完成了基于行为范式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政治化表达。
三、困厄与革命:蒋光慈小说的底层化创伤体验及其政治叙事
在左翼文学的革命叙事中,国际化代表着最高的政治化,底层化代表着彻底的政治化。早期革命小说中,底层化创伤体验的书写带有鲜明的政治符号的性质,盖因其取材于底层,代表了革命诉求的广度和深度。
一般认为,蒋光慈的小说是早期革命文学的范本,开创了革命英雄主义叙事的先河。但纵观其创作,真正独特的是他的底层书写。与五四时代一切现实主义意义上的底层书写不同,即与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创作观念迥然有别,蒋光慈的底层书写富于浪漫主义特征,亦如张闻天对郁达夫的改写,鲁迅之“哀”化作蒋光慈之“幸”,鲁迅之“怒”化作蒋光慈之“争”。但鲁迅的“哀”在于精神层面(哀其愚弱),蒋光慈的“幸”是政治抗争,即通过设计一条行为化的革命之路,阿Q式的颟顸转化为英雄主义的强悍,在政治化的意义上重估被启蒙忽略的底层价值。
在蒋光慈的小说《少年漂泊者》中,少年汪中的复仇即表现为从困厄到强悍的生态化的政治行为展示。以地主逼债(父母死)为起点,通过报仇离家、病(获解救)、乞食(被猥亵)、进城当学徒、恋爱受阻、恋人(老板女)自杀、结识革命党人(维佳)、革命、牺牲等环节,刻画出一条汪中革命道路的连接线。这显然并非现实主义的个人化叙事,而是神话式的英雄叙事。困厄从而也不再是个体化的生存危机和行为阻遏,而是展示其政治生态的灯塔和坐标。然而,汪中之能从困厄到强悍,其英雄行为的展开离不开革命党人的塑造。在结识维佳之前,汪中摆脱困厄的方式仅仅是一种颟顸的个人行为(复仇),其后的经历因伴随着不断的革命高潮,困厄的个人命运转化为强悍的政治行为。虽然其结果——牺牲(死亡)使主人公汪中遭受到最大的困厄,但却被政治化地描述为一种道德的升华——英雄汪中的“最后的微笑”。死亡的崇高化亦即困厄的崇高化。从精神现象学的意义上讲,革命是展示困厄和摆脱困厄的二律背反。但在个人层面,革命不能消除困厄,只会不断衍生困厄。所以,单纯的困厄之于革命,不是动力而是阻力。但通过其英雄主义叙事。个人化的困厄体验作为传达政治意志的特殊方式,转化为道德化的政治认同,强化了其在群体中的政治表达功能。感性化的困厄体验和本能的复仇因其特定的表达方式成为塑造政治凝聚力和强化现代政治伦理的有效手段。
困厄体验也是鲁迅小说底层书写的重要途径。在《阿Q正传》中,鲁迅甚至也写出了阿Q的困厄体验与其“革命”的内在关联。但对鲁迅而言,正由于阿Q式的困厄是凸现其本能和感性化生存方式的外在标示,“革命”才成为其困厄的终极(死及其动因)。在非理性、非道德的意义上鲁迅状写出了阿Q因其困厄而闪现的卑微欲念。基于此,鲁迅毫不留情地解构和否定了阿Q式革命的伦理意义和道德价值。也就是说,阿Q的革命是其无理性的困厄的终极,是非道德的政治狂想,因而也是“背时”的和“反启蒙”的(在鲁迅意义上。精神胜利法本质上是一种“反启蒙”的思维方式)。
但这一切,在蒋光慈笔下都已然改观。比较一下鲁迅笔下的阿Q和蒋光慈笔下的英雄们,可以发现,他们的区别不在于共通的困厄,而在于赋予其困厄体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在鲁迅那里,阿Q肉体的困厄源于其精神的困厄,革命是其困厄所制造的“反启蒙”的生存悲剧——相反,“启蒙”的阿Q如果能在精神胜利法的意义上自我矫正和自行释解,就能获得理性,即避免革命。但不同的是,尽管蒋光慈在《田野的风》(《咆哮了的土地》)中刻画了一个类似于阿Q的“典型”张进德,但他的困厄体验却是某种政治生态的表达形式,显示了启蒙伦理与政治伦理的重大区别。
首先,作为农民的张进德也和阿Q一样,生年不知,姓氏不确,籍贯莫名,是作者观念范畴中的“这一个”。其次,张进德到了矿山,立即就遇上了工人罢工的风潮,“莫明其妙地被推为罢工的委员”。他的生活,他的思想,“从此变动起来了”——张进德成为英雄,多赖于此种“莫明其妙”的时运:“他遇见了不知来自何处的革命党人,他们的宣传使他变换了观看世界的眼睛”。这与阿Q进城后的经历又的确不同——阿Q由于“恋爱的悲剧”在未庄遇到了“生计问题”,于是“进城去”,从而有了他一生中难得的一次“中兴”。但向往“革命”的阿Q最终却碰到了不准他“革命”的假洋鬼子。这与张进德的命运大相径庭——张进德一到矿山就“被推为罢工的委员”,他遇见了从天而降的革命党,这显然不是当年不准阿Q“革命”的“假洋鬼子”的革命党。进而,张进德“渐渐变成了矿工的领袖”。工人们拥护他,资本家憎恨他。这样,他又离开矿山回到了家乡。
一进一退,同异之间大有玄机。钱杏邨说,当年阿Q“莫名其妙”地“蠢动”只是“泄愤”,现在有“智识”的中国农民已在进行着“有意义”、“有目的”的“政治斗争”了。这种转变不知因由何在,张进德式的“莫名其妙”的“智识”更不知该作何解释?但可以肯定的是,主张启蒙的鲁迅为着否定或质疑革命而塑造了阿Q,主张革命的蒋光慈为着政治的需要塑造了张进德。可见,启蒙与政治,不在于被塑造者,而在于塑造者。循着革命的伦理思路,被塑造的张进德其实也不是塑造者蒋光慈的功绩,决定其政治意志的是革命党,即其政治表达的伦理终结者。鲁迅笔下的阿Q和革命党“属他”,他无意站在任一立场上说话;蒋光慈笔下的革命党“属我”,是其塑造张进德的力量之源。至此,阿Q的后裔们被革命党“收编”,“假洋鬼子”的后裔们以道德优势换取了政治优势,现代革命挟带着伦理革命的旋风,催促着革命的阿Q们勇往直前。
因此,就现代政治的认识论而言,革命的神圣不如革命党的神圣,英雄的“阿Q”、张进德不如英明的革命党。在革命党的立场上,困厄中的阿Q们无关哀怨,幸而有怒。革命赋予其高度感性化的政治价值观:卑贱者聪明,高贵者愚蠢;贫贱者高尚,富有者卑劣。困厄的生存体验成为培植“憎”的欲望政治学的伦理基因。
本来在《阿Q正传》中,欲望政治学的种子已然萌芽。当“生计问题”出现及未庄的“鸟男女”们无视阿Q革命的愿望,阿Q在土谷祠中即已愤愤然地揣摩:“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但这涉及的仅是阿Q的欲念——妄想,而非革命。然而,当张进德把革命的消息带到了乡间,他身边的刘二麻子、王贵才、吴长兴等人(类似于阿Q身边的小D、王胡等),立刻兴奋起来了。牵拽着他们的是公愤——“憎”的欲望政治学。如果说阿Q的革命无关政治伦理的表达。张进德们的革命则展现了现代政治伦理的建构模式。这在于阿Q的革命作为其创伤体验的终极无关救赎:而张进德的革命在其底层意识支配下成为政治救赎的最高形式。
因此,现代政治救赎的伦理理想与传统政治的道德观念相去甚远,即确立救赎的思想基础是“憎”而不是“爱”,获得救赎的途径是“恶”而不是“善”。产生这一变异的社会土壤则不得不归因于五四伦理革命带来的文化基因突变:从陈独秀的倡导到鲁迅《狂人日记》的演绎,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叙事结构上,现代伦理革命造就的“憎”的文化政治学通过政党政治的中介,置换成行为主义的革命伦理——“斗争哲学”。
于此,伦理革命、情欲体验和底层困厄交互作用,表达知识分子政治伦理的欲望的文化政治学已然改写了历史:在《田野的风》(《咆哮了的土地》)中,蒋光慈塑造的张进德不仅以革命克服了困厄,也满足了自己的情欲(知识分子出身的何月素对他崇拜倾心),成就了其基于知识分子的伦理理想和政治设计的英雄形象。在蒋光慈笔下,这条政治救赎之路几近坦途,从而把鲁迅诉诸阿Q的灵魂救赎与绝望抛诸脑后。
而且,当年不准阿Q革命的假洋鬼子,依据新的政治设计成为阿Q的救赎者和革命的引路人。一方面,这可归功于五四开创的伦理新风:打出家庭的“幽灵塔”,割断了血缘的伦理纽带,现代革命伦理塑造的政治“狂人”登上了历史舞台。现代革命的伦理理想是以激进主义为基础的阶级复仇。这就不难理解李杰指挥农民军向自己父亲开火,并烧死无辜的母亲和妹妹所具有的政治正义性。从伦理革命的意义上讲,不难看出它与《狂人日记》中狂人对亲情的质疑相关联。革命,这架由知识分子的欲望政治学所开动的暴力机器负载于阿Q们身上,使他们油然而生一种担当的畅快,被塑造的荣光,但其本位的需求也在一种理想主义的政治幻觉中遗失了。另一方面,现代革命作为一场伦理化的政治革命,体现为伦理的革命化和文化的政治化,从而回避了启蒙赋予文化的最深厚的理性建构任务。在革命中,文化命题的终极性等于政治的虚妄化。缺乏经济理想和制度设计的革命,必将沦为一场非理性的乌托邦梦魇,并不具有真正的现代性。
作者简介:周仁政,男,1962年生,湖南津市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410081。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