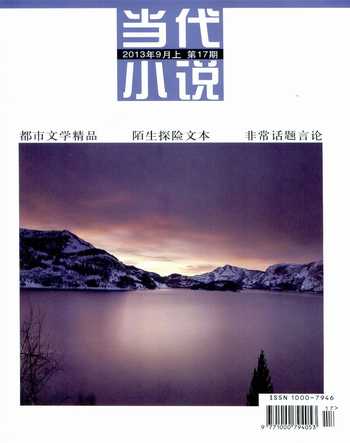郊外
2013-04-29刘亮
刘亮
1
破晓时,在天空斜上方,一轮圆月仍留恋着天际,低垂着挂在西天边上,犹如一个没有指针的钟。
张连振从红缨的理发店出来往家里走。
暗黄色的月光落在了他那魁梧的身躯上,照得那么自然,如同黑夜的降临和春季的天空一样恍恍惚惚的。离他的住处不到五百米就是一个废弃的凉水塔,那里经常人满为患,每天从镇里来这里的流浪汉们、拾破烂儿的、贴广告的、还有一些乞丐们都好在这里过夜。使得凉水塔白天一片狼藉,晚上则是热热闹闹的。
快到家时,张连振停住步,拐向了去村委会的路。这个时候刚过六点半,看门的老余头把院子扫完了,正弓着腰给北墙根的一溜月季花浇水。张连振也没打招呼进了办公室,他想眯瞪一会儿,就在门外挂上了“请勿打扰”的牌子。
一会儿,敲门声响起,张连振以为是文书小李子呢,结果进来的是儿子张雨龙。
在过去还是个完整的家中(五年前,他老婆因胃癌去世),儿子就让他不得消停,曾多次因为逃课或者打架被老师叫去训话。
“唉,熊孩子呀,”张连振哀叹着说,“我费了很大的劲把你往技校里送,你不好好上学,跑这里来干什么?”
“给我点零花钱吧,老爸?”
“我都不知道了,”张连振摇了摇头,“你这样吊儿郎当的将来能干什么!”
“你晚上去哪了,爸?”
“别打岔!”张连振咕哝着,“我说的意思就是那个意思。你以为我这沟沟坎坎的一辈子都是为别人奋斗的嘛?兔崽子,还不是为了你。”
有那么一会儿张雨龙没有开口。“老爸,家里就我和你,我妈走了,我需要钱了不给你说给谁说。反正不能跟那个女的要吧。”
“你废话太多了,小子,”张连振赶紧接过话,脸红扑扑的,“你还是听我的,明年毕了业找个工作,别管它是什么公司,干什么工作,也不用管你多讨厌它,在里面一直干下去,直到老了干不动了;这也是惟一的生存方式,为将来做准备。哎哟,快七点了小子,拿着这一百块钱,别忘了先买两个包子再去技校啊。”
现在最让他发愁的就是儿子张雨龙了。这孩子根本不打算使自己有一技之长,对于没有生活目标的危险也根本不认识。有一次他给张连振开玩笑说,他打算找九个女朋友之后再结婚。张连振反驳他说,等你找完得多大了?实际儿子的女朋友他见过两个,大多都比儿子小。对他这个年龄,刚满十九岁,张连振也表示理解和尊重,同时他也怀疑儿子是不是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将来又想干什么。总而言之,张连振认为,他的家是一个不完整的家,一个不协调运转的家庭。在这个家里,自从老婆去世后,他和儿子总是大眼瞪小眼,一周也说不上两句话。同时他又时不时地感到寂寞和空落落的忧伤,至少在背地里他是这样的。
一想到这些张连振就愁心重重,等和村委班子开完碰头会后,他安排文书小李子听电话,自己又去了红缨那。这个时候来理发的人寥寥无几,倒是门口几个老头下着象棋显得热热闹闹的。张连振故意咳嗽一声,有人接了话:
“来了村长,杀两盘吧?”
张连振摆了摆手,“你们下你们下,我理个发。”
“你前天不是刚整完头吗,村长?”另一个老头笑嘻嘻地说。
“是嘛?那我刮刮胡子还不行!你个贺老三,臭棋篓子一个。”
众人哈哈笑起来。
红缨瞅着张连振的狼狈相,也抿嘴笑了,接着转身进屋。待张连振坐下后,红缨一边给他系围巾一边悄声问:“活都安排完了?”
张连振点点头,突然把红缨的手攥住了。她一方面不安地脸红起来,另一方面又因张连振的胡闹而激动。对于张连振的这种亲热她既不是多同意,也不表示反对,实际上她有点紧张。她害怕他们之间的这种缠绵和亲热被突然进来的人看见,可心里又想让人看见他们的这种亲热。最后,弄得她不是羞怯地笑,就是拂袖而去,要么就是骄傲地涨红了脸把张连振的头推一下。
过了一会儿,来了几个理发的小媳妇,一看张连振坐里面,就笑笑走了。倒是门口几个老头闹得欢,时不时地喊上那么两嗓子,像下棋又像和张连振开玩笑,“上马!上马!吃你的子老贺……熊东西的,你还不出车,出车呀……”
中午红缨做了红烧肉,张连振吃完有个习惯,喜欢眯瞪会儿,这时手机突然响了。电话那头吵吵嚷嚷的,张连振费了半天劲才听明白怎么回事。他先是愣了愣,接着吼了一嗓子:
“不许你们动他一个指头!奶奶的,你们敢把他关起来了?”
“等一下,等一下。我打电话就是想让你过来一
趟,我们是按手续办事的。”
“去你奶奶的手续!”张连振用命令的口气说道,“你听明白我的话了吗?赶紧照着做,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在一旁刷碗的红缨吓了一跳,赶紧过来扯了扯张连振的衣襟。
“喂喂,等等,等一等,你小声点行不行?”
“奶奶的熊,你这个小子,宋秃子呢?让他过来听电话。”
“俺所长去镇委开会了。”
……
挂了电话,红缨就问他发的哪门子火?
张连振气呼呼地说:“熊孩子因为打架又被镇派出所的人扣住了。”
红缨劝了又劝,张连振还是不解气,他感到气愤之极,真想扇张雨龙和那个民警两巴掌。红缨不放心,又劝起张连振,说啥事到了那里再说,派出所不会无缘无故抓人的。
张连振光抽烟不吱声。
这会子,副所长小周正和值班民警等着他。
派出所进门的大厅里蹲了两溜半大不大的学生,张连振一眼就认出了这是技校的校服,扫了两圈后他没发现儿子张雨龙,稍稍松了口气。
“张雨龙呢?”他严厉的目光直刺值班民警和副所长小周的脸,“好好听着小子,快把我儿子放了!”
小周抱了抱肩膀,“你说完了吗?”他身材瘦长,小鼻子大眼,看起去精神抖擞的,“你是张雨龙的爸爸?”
“你瞎眼啦?”张连振火了,“好好瞅瞅,我是平刚村的张连振!宋秃子呢?奶奶的,他躲哪去了?”
地上蹲着的那些学生都注视着张连振,好像他是个怪物似的,竟敢在派出所里大喊大叫。这时他突然明白了,大家为什么这样看他,是因为他高举着双臂朝前乱舞着,那姿势很像一个随时要挖人脸的村妇。当他明白过来时又有些羞愧了,全然忘记了自己是多大的人,连突然进来的张雨龙都惊呆了。
就在他明白过来又有些不知所措的时候,值班民警语气坚定地说:“张雨龙伙同别人打群架,他不光参与了,而且还是里面的头头。我们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先批评教育一次,写个决心书啥的……”
“宋秃子呢?”张连振没接那个茬,打断了民警的话,“奶奶的,当年在部队我还是他的老班长。现在你们竟然给我来这手,把他给我叫出来!”
“我说了,俺所长去镇委开会了。”
副所长小周挥挥手,示意张连振上里间屋说话。
“张村长,”小周关上门说,“刚才我给所长去电话了。他一听是你的儿子,也很着急,就想着先把雨龙放了。可最要命的一个问题就是:雨龙是那些学生的大哥,我把他放了他却不走,非要我把他的弟兄都放了他才肯走,你说咋办张村长?加上他们两派的学生打群架正好把人家店铺的玻璃门碰碎了,人家让赔,张雨龙又不肯走。这不刚才……他还去那屋把我们吊扇的调速器修好了,他说他在技校里学的就是电修。”
“是吗?”张连振微微一怔,脸上露出了色彩,“熊孩子还是他们的头头?奶奶的,在家里他就是个闷葫芦,出来还成他娘的头头了,真是好笑……这样,你放心小周,我一瞪眼他就立马滚蛋了。”
张雨龙在门口听见,嘻嘻地笑起来。
尽管儿子没惹什么大祸,在回去的路上,张连振还是有些担心和郁郁不乐。这会儿,也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小雨,阳光下细柔的阵雨雾蒙蒙地洒在他的周围,在摩托车的前面形成了一圈七彩光环,和他的心情一样,什么味都有了。
到了晚上,张连振没去红缨那吃饭。他看了一会儿电视后猛地想起一件事:三个月前他给儿子提起过自己和红缨的事。原想着儿子能理解自己,理解这件事,可他听完竟二话没说,晃晃头回学校了。张连振想着,是不是最近光沉浸在和红缨的缠绵之中疏忽了儿子那头,从而让他产生了腻烦心理才惹事生非的?还是他从心底就讨厌自己再婚?或者讨厌红缨这个人?后来,也就是过了半个月之后,张连振又问了张雨龙。张雨龙先是不吱声,过了会儿才不耐烦地回答他,你想结就结了,给我说干什么!当时张连振就急了,真想扇儿子一巴掌,后来他忍住了,随即就气呼呼地骂:“给你说干什么?奶奶的,你不是我儿子嘛!”
张连振边抽烟边猜测,快到八点时红缨打来电话,问他孩子的事怎么样了?
张连振无精打采地应付了她几句就挂了电话。这个时候,外面的天气好像回应着他的心情似的,突然间传来一阵巨大的爆炸声,在此之前外面没有任何征兆——伴随着爆炸声而来的就是令人头皮发麻的鞭炮雷,这声音转而被一阵急促促的雨点声所代替,把他吓了一跳。接着这声音又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急速地飞过所产生的强大震荡,使他觉得自己的房子快要被它连带着刮走了。
2
这个周六的上午,张连振去买了五斤排骨,想等着儿子回来给他解解馋。可十二点过去了他也没到家,张连振急得打了三圈电话,后来才通过儿子的同学追到镇医院找到他,之后张连振就带着令人棘手的问题离开了。红缨知道后给他出了主意,让他去找宋秃子,毕竟他是派出所所长,让他和受伤学生的家长调解一下最合适。
张连振说:“熊孩子前几天刚打了架,现在又打伤人了,我还得去给他擦屁股。最后他也没落下好,自己也在医院里躺着呢!奶奶的,你这叫什么事?什么狗日的事呀!”
红缨说:“别管啥事了,你赶紧去办,省得人家再往上告。”
张连振点点头,最后叹着气说:“说得也是!熊孩子现在咋成这么个玩意儿了。”
红缨推了他一下,“你嘟囔啥呀,还不赶快去找宋秃子。我先上医院了。”
红缨又去商店买了点东西,到镇医院时,她看见张雨龙正脸朝上躺在病床上打吊针。她敲了敲门,张雨龙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没有说话。门开了一条缝,他抬抬脸,看见了红缨那张满面挂笑的脸,脑门白净净的,乌黑的头发像一片一片的纱巾垂在耳朵根。他仍没吱声。红缨羞答答地顺着床沿走过来,确认是张雨龙后,眼睛忽闪一下,突然变得明亮起来。
“雨龙呀,”红缨小心翼翼地说,“你看看你……没事了吧?还疼不疼了?”
“喂,”张雨龙没好气地问,“你是谁呀?”
瞬间,红缨就觉得房间左右摇晃了一下,她赶紧调整了自己。这使她想起当年喜凤后妈就和喜凤闹得不可开交,这个张雨龙和喜凤一个样,对他再好,他也觉得你是外来的,和他交不到一个心上去。她脸上强挤了一丝笑容,但感觉着还是火辣辣的。最让她受不了的是张雨龙两个同学的目光,像两道发出烈焰般光束的白灯似的紧盯着自己,老让她想寻找到光束的位置。当她转了转眼珠试图寻找时,两道光束也在随着她的目光移动着。最后,她把目光转回来,移到了张雨龙的脸上,他这会儿正微笑着,显得单纯无畏、天真无瑕且充满了杀气。他还不满十九周岁,清秀标致,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派头,在红缨眼里,他似乎比村里其他的男孩子更具活力:他的头发也乌黑发亮,又短又硬,像个圆乎乎的刺猬似的。
“看你说的雨龙,”红缨缓过了劲,口气依然柔和着,“我是你红缨婶呀。你好多了吧?怎么样,能不能坐起来?我给你买了鸡翅、鸡腿……还有面包、巧克力、薯片啥的。”
张雨龙没接红缨的话,指了指那两个学生,“老二老三,过来一块儿吃吧。”
三个人围拢在了一起,一边吃一边吹嘘着自己当时怎么勇猛,怎么把谁砍了一刀,又是把谁的头开瓢了,估计得缝六、七针之类的……红缨越听越瘆得慌,也感到气愤之极,且不知所措、孤立无援,还不敢插上嘴,怕自己在张雨龙同学面前颜面尽失,同时也异常地失落——张雨龙全不正眼瞧她,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她现在已经四十二了,在这群小孩面前,尤其是张雨龙面前,就像个可有可无的木头人似的。这时,红缨的身子晃了晃,真想发疯地吼叫一声,让这群肆无忌惮的毛蛋孩子有所收敛。她右手瑟瑟颤抖着。在场的人,也只有张雨龙觉察出这会儿不同寻常的气氛,他没有发作,而是轻蔑而又开心地看待这一切,继续嘻嘻哈哈地聊着他们的英勇故事。
红缨气哼哼地出了医院。
晚上七点过后,张连振又习惯性地去了红缨那。他一进门,先是把张雨龙骂了一遍,接着又咯咯咯、哈哈哈地笑起来,说宋秃子去调解完了,鉴于双方都受伤,再给那个孩子五百块钱医药费就能两下扯平。
张连振眉飞色舞地说完,红缨并没附和,而是陷入了郁郁寡欢的丝网之中。张连振抱了抱她,问她出什么事了?红缨想着以后的事,就是她和张连振之间还隔着一个张雨龙,就觉得以后的麻烦事会越来越多,从而使她痛苦和压抑,禁不住流出了眼泪。张连振把她抱到了床上,红缨很严肃地把张雨龙下午的所作所为告诉了张连振,接着又趴在他的怀里悄悄地哭起来。张连振先是一怔,随后笑呵呵地开导她,说雨龙不过是个孩子,你值当的和他治气吗?接着,他就用热吻来安慰起红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红缨也明显地感觉到张连振的下身已经硬了。她闭上眼,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接受着张连振——一种焦虑压抑与相互关心,又夹杂着体贴和安抚的复杂心情。此时的张连振先花了一点时间来揣摩着她的反应,然后再让自己酒后的身体痛快地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渐渐地,红缨也把僵硬的身子打开了。她不知道自己这会儿需要不需要这种爱,需要不需要这种满足。可当她看到张连振十分满意的表情、而暂时忘记张雨龙带给他的负担后,心里还是很高兴,接着又把张连振的身子抱紧了。
“你有点发福了,连振,”过了一会儿,红缨才说出话。她每个字都说得那么艰难,似乎是声声的叹息。她的声音又粗又低,几乎是耳语,“你也有不少皱纹了,没准还矮了两公分了。你从前可瘦了……你的头发都有点灰白了,还稀了不少……我的也一样。哎,跟我说说,你心里怎么想的?还经常想雨龙的娘吗?”
3
等红缨再想问张连振这个问题时,张连振已经忙得两脚不离地了:镇里开了会,让村里重新建新水渠——以前那条是二十年前修的,现在已豁烂得不成样子。等把这事弄利索之后,张连振就觉得嗓子开始疼起来,感觉那儿像长了什么东西,喝水咽食都有点困难,尽管他现在还没有发烧。他像对待平时的感冒一样,吃了一点消炎药。可效果不好,第三天就开始发起烧来,红缨看着这个平时像山一样魁梧的汉子,现在却躺在床上像只虾米似的哼哼叽叽,也是心疼得要命,就顾不上问了,赶紧给他量了体温,随后又扶他去卫生所挂了吊瓶。
一会儿,文书小李子也来了,张连振就让红缨回去,说是理发店不能没人守摊子。小李子也在一旁劝红缨回去,说他在这看着就行。可等红缨一走,张连振不知怎么了,突然就感觉着脑门猛地一下麻了起来,像是有一种不祥之兆要落在自己身上,来得又是这么迅速、这么自然,犹如黑夜的降临和村里坚硬的黄泥地一样平常,把他着实吓了一跳。他赶紧问小李子,现在是不是上午十一点?小李子点点头。他接着又问,我是不是叫张连振?小李子又笑嘻嘻地点了点头。张连振这才把心放在肚子里,而后长叹了一声说:
“李子,帮我给雨龙打个电话吧,问他这个周末几点回家。”
小李子就去门口打了。“村长,雨龙说了,大概十二点吧。”
张连振点点头,接着掏出钱包,“李子,你也别在这守我了,赶紧去郭胜利家帮我买十斤大骨头,我想等熊孩子回来给他熬大骨汤喝。”
“是那种大龙骨吗?”
“嗯,最好上面能带一点肉的。”
“好,我这就去。”
现在房间就剩下张连振一个人了,他脸上又悄悄布满了失望的表情——他渴望能跟红缨在一起生活,而夹在中间的儿子却好像不为所动,甚至有些讨厌他俩在一起。他想到儿子,说不定熊孩子在心里还骂我不是个东西呢。还有,他也想到了,像儿子这么大的人了,再开口叫红缨娘的话,换成他自己也不会情愿……张连振使劲盯着墙,他下定决心再试试,等儿子回来再把这个话题给他聊聊,说不定儿那个啥——他在给自己鼓着气。至少说他想对儿子诚实一些,要么他总觉得到老了就会时时感到痛楚的。
晚上红缨给他做了炒青皮和鸡蛋海带汤。张连振慢腾腾地吃完,憋了一会儿后才把自己下午想的给红缨说了一遍。红缨听完没怎么高兴,反而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忧愁之中。张连振安慰她说,这样也好,起码熊孩子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兴许他能突然想开了呢。红缨勉强笑了一下,接着扑拉扑拉围裙说:
“我想了连振,要不咱们俩……就照现在这个样子过吧。”
“你傻呀红缨!”张连振一本正经地说,“难道你忘了咱俩都是多大的人了?”
“不瞒你说,想到这些呀我就头皮发麻。”
“去他的吧!”张连振一抹嘴,恶狠狠地说,“奶奶的,我就不信了,熊孩子还能当了他老子的家……”
张连振正嗷嗷骂着儿子时,门嘭的一声突然开了,两个男孩像被旋风刮着撞进了屋里。张连振吓了一个后仰,看见进来的两个男孩双手是血,嘴唇哆哆嗦嗦的,手腕也在瑟瑟抖动,像是着了什么魔、撞了什么灾似的。
“我大哥被人捅了,叔!”一个男孩挥舞着手喊,“就是刚才……在我们学校门口,可能……可能快不行了……”
张连振的脑子转了两个圈也没反应过来眼前到底出了啥事,他怒气冲冲地厉声喝道:“奶奶的熊!啥大哥?你大哥是谁?”
“张雨龙呀,叔,他被人捅了!”
“你说的啥?再放屁我他娘的就扇你了!”
“真的张叔,我们和雨龙一个班。”
张连振侧了侧头,身子突然晃了起来,随即,啪的一声就坐到了地上。这个山一样的汉子没有哭,朝上凝视着屋顶,嘴巴一张一翕的,像小鱼在使劲喘着气,倒是红缨的眼里涌出了泪。她心惊胆跳地看着张连振,生怕他心脏会突然痉挛,会停止跳动,会大脑动脉血管破裂。吓得她大气也不敢喘,身上却是呼呼地冒着冷汗。
“上呀,再上一蹬,”张连振终于开了口,却是笑嘻嘻地在说,“对对对,乖儿子,再上一蹬,上一蹬,我等你儿子,上一蹬呀……”
红缨一下愣住了。
“张叔,你快去看看吧。”
“连振,连振……”红缨清醒过来,上前拍了拍他的脸,“你缓缓神,这是咋了?你说的啥?什么上一蹬?来人呀,你俩快过来,帮我打你叔的脸。”她慌慌张张摸到了手机,“小李子,是小李子吧?快给周秃子打电话,把他的车叫来。对对,连振吓住了,是的是的,吓住了,快点呀……”
半小时后,镇医院里乱成一团,人头攒动,哭喊声震耳欲聋。医生这边抢救着张雨龙,红缨则一个劲地喊张连振,而他却是没点反应,老是重复着那几句:上一蹬,对对,乖儿子,上一蹬,再上一蹬,我等你儿子,上一蹬呀……
一个星期后,红缨从医院把张连振接到了自己家。他仍无好转,还是老嘟哝那几句“上一蹬,上一蹬”的话。
村里人都说张连振是因为儿子突然死了而疯的,是没法治的病,属于心病。可红缨不这么认为,她觉得张连振没疯,只是急火攻心攻的,一时没转过这个筋。她又去张连振家,把张雨龙的照片拿了几张,贴在了镜子上,让张连振天天看。她盼望着张连振能出现什么奇迹,甚至她从电视上看到了别处的景致,想等着张连振好了,能领她出去看看。当然,得先去一趟省城,再去北京、上海……她记得东北还有一个舅老爷仍住在那儿。
过了不久,一向身体健康的红缨开始感觉不适了:乳房胀痛,月经停止,恶心厌食。她意识到了……难道自己怀孕了吗?她把喜讯告诉了张连振,他仍旧笑嘻嘻地喊:上一蹬,我等你儿子,上一蹬呀……看着张连振无动于衷的样儿,红缨的眼里又泛出了泪花——她想要这个孩子。她知道他们俩不管是谁,能有孩子的年龄不会再有了。
她坚信自己是对的。
同时她想不出自己的想法有什么不对。她是个心里有什么就想说什么的女人,而现在她在心里想的是:假如自己耐住了性子,不轻易放弃,张连振终有一天会清醒过来,会像以前一样对自己缠绵有加,听她的意见,把这个孩子好好带大。即便他不同意,对孩子的争论,她相信自己也有充分的理由说服他。
第二天一早,为了给自己一个放心,她想去县医院检查检查,就把张连振安置好了之后出了理发店、出了村口。路边,一群人正给豁豁烂烂的旧水渠垫着石头。这些人很面熟,好像从上个月开始他们就在这里修了。她全神贯注盯着这些人看了一会儿,根本没注意到一辆出租车已经停在了她身旁。
责任编辑: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