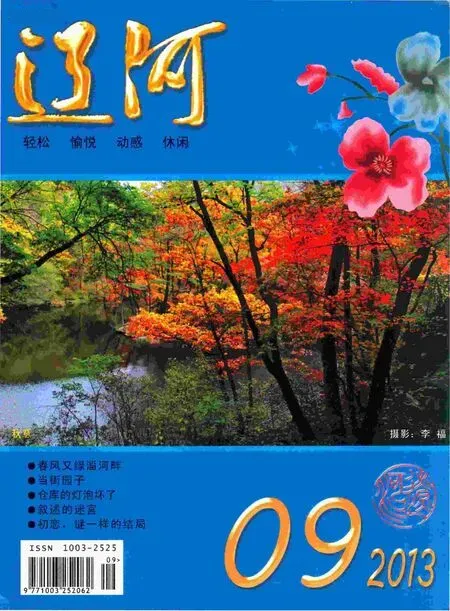作为思念凭证的伤口
2013-04-29钱秋菊
钱秋菊
母亲的伤口,如何下笔呢?母亲有着怎样的伤口,它是怎么形成的?做为母亲,一生的伤口应该会很多吧,那么,哪个伤口会永远留在一个儿子的心里呢?带着这个疑问,我走进了这首诗。
我在找伤口,纵观全诗,与伤口有关的词有这么几个:“疼、刺、痛”,这三个词,一下子使场景立体起来了。这三个词,两个形容词,一个名词,我们可以想到因为扎了刺,所以母亲疼了,我心痛了。
这刺是怎么来的呢?诗中说了——
“栅栏边,成熟的曼陀罗
刺痛了母亲的手指”
想来这曼陀罗是一种带着刺的植物,它扎到了母亲的手了,母亲的手为什么会被植物刺到,她为什么不躲开被刺痛的危险呢?
诗中又说——
“灶台里,成熟的曼陀罗燃烧着
母亲煮出来的晨曦与黄昏”
这两句里,一个勤劳的农村的女人形像一下子丰满了,不同于城市里的液化气和电饭锅,农村的煮饭做菜都是靠烧各种植物来完成的,于是,母亲必须靠近这种带刺的叫做曼陀罗的植物,用它来给大家做出美味的食物来,于是,那刺便扎进了她的手。
“母亲不说,我不知道母亲的疼
一生也没有拔出来的刺”
这两句里,是作者的又一种感受了,母亲她依然在忙碌,做为儿子的“我”其实并不知道母亲的手上或是身上还有多少这样的伤口,因为母亲没有说,我也不知道这样的伤口有多疼。十指连心,手上扎了刺,又怎么会不疼呢?可母亲平静地把这种疼咽下了。
“后来,我不歌唱
记忆里我的嗓子哑了
我的泪从那年的腊月
一直流到了清明”
作者用“歌唱,哑了”,來表达自己对母亲的深切思念,同时,我们也从这四句诗里知道了,这位坚强无私的母亲逝去了,而“我”哭哑了嗓子,却也换不回母亲的身影了,这样深切的思念,在腊月开始一直一直地无法停息。现实里,作者的母亲早逝在一个腊月,于是这个腊月便成了作者心中永远的痛。
如果诗也如词,那么我们可以把上面的几句诗做为上阙,以述事为主,形像而深刻地写出了一个勤劳、坚强、慈爱的母亲,轻描淡写,铺陈出一段陈年的情景,入笔时非常的自然,曼陀罗、灶台均是农村常见的,而农村的女人自嫁人便围着锅台转,为全家人准备好吃的饭菜,让全家人温暖,作者却抓住这些最为普遍的情景,勾勒出一副让人过目不忘的母爱图。
母亲的伤口,至此写好了,也没有谁再说什么吧?母亲伤口形成的原因写得很清楚了,对不对?如果只是写到这,那么这首诗就不足以有新意了,只能说,作者抓到了一个别人没有在意的情景罢了,于是,我们可喜地看到了下阙,诗意进一步升华了。
“清明淅淅沥沥的雨
萌芽了母亲坟上的青草”
紧承上段的泪,这是谁的泪呢?当然是“我”的,因为母亲的逝去,“我”流了那么多的泪。清明是自古以来的祭奠哀思的节日,古人有句话叫“每逢佳节必思亲”,于是,清明的时候,我哭哑了嗓子,清明的时候,我的眼泪催生了坟上的青草,这是作者最为奇妙的比喻,却也非常形像地写出了悲痛之情。
“祭扫以后,青草的根
刺入我的内心”
这又出现了一个“刺”字,不同的是,这个刺是动词,与前面的名词相呼应着,母亲的伤口是曼陀罗的刺形成的,而母亲坟上的青草扎进的是“我”的心里,这又是一个伤口了,这个伤口是“我”的,不是母亲的,母亲已逝,我终于感受到了她的疼……
“母亲,你陈年的伤口
开始痛在我的心里”
纵观全诗,这是唯一的一次出现伤口这个词,结尾的升华自然而流畅,母亲的爱,“我”懂了,“我”的爱,母亲却无法感应了,母亲的伤口又何尝不是“我”的伤口呢?
附原诗:
母亲的伤口
作者:高坚(雨问梅香)
柵栏边,成熟的曼陀罗
刺痛了母亲的手指
灶台里,成熟的曼陀罗燃烧着
母亲煮出来的晨曦与黄昏
母亲不说,我不知道母亲的疼
一生也没有拔出来的刺
后来,我不歌唱
记忆里我的嗓子哑了
我的泪从那年的腊月
一直流到了清明
清明淅淅沥沥的雨
萌芽了母亲坟上的青草
祭扫以后,青草的根
刺入我的内心
母亲,你陈年的伤口
开始痛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