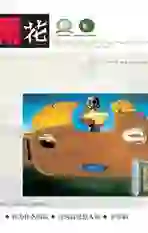截访之途
2013-04-22孙旭阳
孙旭阳
7个月前,小明还是一名“黑保安”,在北京靠暴力截访为业。“帮政府办事”,一度成为他们家庭的骄傲。然而,在他们被诉诸审判后,禹州市政府公开声明与此事无关,这让涉案的农村家庭陷入了恐慌和愤怒。之前,他们认为被截访的上访者都属于无理取闹。现在,他们也试图进京上访,去讨一个说法。
“2号院”
2012年5月2日上午,北京警方从双合村126号院和102号院里带出20多名河南人,部分村民隐约听说,这两个院子原来是传说中的截访“黑监狱”。第二天,有10名河南禹州农民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刑事拘留。一个月后,他们中的8人被逮捕,其余的两名未成年人被取保候审,回到禹州付家村的老家。至今,他们都经历了两次庭审。“我要是再差个两分钟,就没事了。”小明说,警察来时,他正带着几个上访的外出放风。待回到院门口附近,见有数辆警车停靠,还没转身,一个警察朝他招招手,他乖乖地走过去。而按照报案人金红娟和贾秋霞的说法,她们当时带着警察,正发愁找不到那个曾拘禁她们的“黑监狱”呢,几个黑保安押着几个上访者返了回来。
根据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调查,2012年2月,河南禹州付家村农民王高伟出资承租了双合村126号院和102号院,由同伙付朝新雇佣至少九名老家农民看管河南籍上访人员。根据当事人的描述,126号院被称为“1号院”,与其相距300米的102号院被称为“2号院”,月租都在3000元左右。几个月来,至少上百名上访者曾栖身这两个院子。其中,“2号院”的住客中,包括报案的四名禹州女上访者。
这四人回忆说,当跨进“2号院”的一扇防盗门后,她们失去了自由,也没有了时间。她们被困的房间没有窗户,只有一盏昏暗的灯泡,手机被收走,她们只能靠三餐来勉强推测斗室外是白天或黑夜。她们的早饭和晚饭是馒头咸菜,因为没有稀饭而难以下咽,午饭则一般是面条。
2012年4月27日深夜,她们被王高伟的手下从久敬庄的信访接济服务中心接到双合村。“我们反抗,就被打了”,宋雪芳说,在那辆白色中巴上,反抗最厉害的金红娟被掀起上衣蒙头,上身仅着胸罩被抽耳光。她听出打人者中有禹州口音,就劝他们别打了,“这个女同志都能当你们妈了”,没用。
和其他几名上访者一样,宋雪芳指认李玉柱(河北涿州人,未归案)和小明打得最凶。小明则否认了此事:“我坐在副驾驶上就没动,不知道她们为啥咬着我不放。”在受雇于王高伟前,小明曾在郑州做过两年搬运工,人小力不亏。
双方都证实存在这场冲突,但描述不一。不过,这成为“1号院”和“2号院”被端的导火索。4月29日晚,宋雪芳等禹州上访者被送往老家。翌日,在禹州高速路口,各单位和办事处的信访干部,“一手交钱,一手接人”。5月2日,四名上访者又回到了王四营乡双合村,拨打了110,救出了另外10名上访者。
“为政府做事”
在派出所里,“1号院”和“2号院”的黑保安们被关了起来。隔着一层铁窗,上访者和他们互相瞪眼。这是一次双方心情各异的重逢。一个年轻的黑保安声称,他们很快就会被放出来。但这次不同往日。被警方控制的第二天,10名黑保安全部被刑事拘留。一周之后,他们的家人陆续接到来自北京市警方的拘留通知书。他们顿时成为村里谈论的焦点。“我都快活不下去了。”黑保安王世磊的母亲说,孩子刚被抓,她只听到“出事了”,打电话也不通。涉案的其他黑保安逃回村里,却也知道得不多。大家都在猜测中度日。
有人去禹州市信访局问,得到的回答是,政府一直在协调,10个人将很快放出来。但家属们从5月初等到12月初,却等到网上曝出10人被判刑的消息。家属们又重新聚在了一起,女人们在哭,男人们在商量,直到一筹莫展。
根据家属的讲述,这些黑保安进京,一开始说好的工作都是“当保安”,月薪1800元。“他们说我们先帮政府看看上访的人,等形势松了,就介绍我们进高档小区当保安,工资一个月两三千块。”小明说。
小明之所以信任这个承诺,是因为招他去的人,是村委会会计付朝新,而小明的父亲是村里的电工,算是半个村干部,彼此很熟悉。而50岁的付朝新之所以帮42岁的王高伟招人,是因为王是他的远房外甥。在禹州的农村,出外谋生,大家习惯亲戚串亲戚。被诉黑保安王壮壮,则又是王高伟的外甥。2012年4月份,王壮壮赴京前,又拉上了17岁的同学小龙。
这份月薪1800元的工作,因为管吃住,没有进厂辛苦,又在“为政府做事”,曾经还是一份挺不错的工作。已成年的从略,拿三个未成年黑保安来说,小明在入行前,曾在郑州做搬运工;小龙则在许昌读一所就业无望的中专;小刚2011年丧父,母亲只能供他姐姐继续读书。比上访者好不了多少的出身,也让部分黑保安一度怀疑这份工作。付家村的王二飞和赵俊杰先后给父母打回来电话,表示不想干了。
“二飞说这个工作不好干,整天都挤挤扛扛(推推搡搡)。”王二飞的父亲说,儿子只有90多斤,“一点力气没有,能打谁?”他干了不到一个月就被抓。父亲很后悔当时没让他立即回家,而是劝他干够一个月拿到工资再走。
赵俊杰告诉父亲,“干的不是一个好活儿”。父亲只是叮嘱他,无论遇到什么吵骂,千万不要动手打人。小龙是唯一被逮捕的未成年人。他母亲哭诉,小龙上有两个姐姐,从小跟个女孩子一样,富有同情心,根本不可能去当打手。事后,她听说儿子还给被关的上访者分被褥盖,给他们买方便面吃。夫妇俩就拿着一纸证明,去找被关过的上访者,试图让他们证明小龙是一个好人,求法院从宽处理。
事实上,这是一个原本不应聚结的团伙。从2011年年底开始,北京已展开对黑保安公司和截访团伙的集中整治。在王高伟到双合村租“1号院”和“2号院”之前的2012年1月底,北京对保安公司实行准入制度,所有保安都必须经过培训后持证上岗。
但禹州这个截访团伙在被端掉之前,生意一直很顺利。四名女上访者回忆说,在2012年4月27日晚,他们被带出久敬庄分流中心时,看到来截访的禹州口音男子有人还挂着“出入证”。上访者贾秋霞拉着旁边一个警察求助,对方劝慰她,“没事儿没事儿”。然后,她就被抬上中巴。
谁雇了王高伟?
王玉柱患有严重的内风湿,走一步路,腿脚就有刀割般的疼痛。这个70岁的老农,现在准备背上93岁的老娘,到北京上访,搭救42岁的儿子王高伟。王玉柱一生悲苦,他是父亲的遗腹子,母亲整整守寡70年。他生下两个儿子,老二王高伟小学四年级便辍学下煤窑,为家里挣口粮。
“高伟从小就见不得有人欺负老人。”王玉柱说,曾经有一次,王高伟路遇一男青年打一名七旬老人,围观者无人敢管,他过去一把拉开男青年。现在,还是这个儿子,被指囚禁和殴打女人和老人,让王玉柱颇难接受。
两年前,王高伟的妻子撇下三个孩子,跑得无影无踪。而王高伟这么多年,一直辗转在煤矿、铝矿和大城市里打零工。在他的卧室内,放着破旧的家具和老式的衣服,还有一台蒙尘的17寸黑白电视机。王家有三间青色的小平房,其中一间还接着一个已成危房的窑洞。
去年春天,王玉柱为治风湿病,向一个村民,借了几千元钱。作为报答,他允许对方在自家院子里盖一个大猪圈,养了20多头猪。这个时候,王高伟正在北京大做他的截访生意。在仅有的几次探家电话中,他没有跟父亲多讲,只是让父母放心,他在“为政府做事”。王玉柱说,早在2011年,大约是年底,禹州市信访局来了两三个人,为首的姓白,说是给儿子“找个好活儿”。这也是王高伟从事截访生意的源头。
曾参加过庭审的上访者宋雪芳说,王高伟在庭上,直言其截访受禹州市信访局干部白中兴的委托。另一个上访者贾秋霞则证实,2012年4月27日晚,在她被强行塞上中巴之前,看到白中兴在门口处闪了一下。
但禹州市信访局则否认此说。禹州市信访局党组书记朱子建说,案发后,市委市政府成立调查组,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全市信访系统无人承认认识王高伟。至于白本人,职务为主任科员,因患严重眼病而无法上班,也无法接受采访。其手机也已关机。“现在基层截访压力太大。”禹州市委一主要领导说,不少乡镇一把手因为上访一票否决制,已经不愿意继续任职,宁肯退居二线。
可是,工作还得做,压力层层下压到每一个村组社区。据朱子建介绍,在禹州市,已经广泛建立了信访信息员制度,负责监控区域内的上访动向。而在北京,尽管禹州市驻京办早已撤销,但信访局有人轮换常驻,主要负责遣返三类人:非法进京上访人员;国家机关无法劝阻的上访人员;流浪疑似上访人员。朱子建没有解释,为何王高伟能获取禹州市、许昌县、长葛市和襄城县(四地皆归辖许昌市)上访者的信息,还能获得授权,从久敬庄接人送出上访者。
上访者们
对黑保安家庭来说,官方的表态近乎背信弃义。他们在网上看到黑保安已经被判刑的消息后,也曾打算去北京,却很快成为乡镇干部们的谈话对象。一个未经官方证实的消息是,这些被起诉的黑保安,一个月可以从政府领取2000元“工资”。
对曾被拘禁的上访者来说,在经过短暂的欣喜之后,他们发现黑保安们被抓,并不一定有助于他们的维权。宋雪芳等人分别向黑保安们提起刑事附带民事索赔,数额高的超过30万元。但即使判决支持,这些年轻农民们,又赔得起吗?
在起诉书中,宋雪芳、贾秋霞、金红娟等人一概以“宋某某”等称呼。在庭审内外,这些曾被囚禁的上访者,无论从黑保安还是其家属那里,都没有得到过一声道歉。在黑保安家属们看来,这些上访者都属于胡搅蛮缠,以上访向政府要钱为生。双方之间,横着一条很难跨越的鸿沟。
“我不会原谅黑保安们。”47岁的宋雪芳说。17年前,怀孕4个月的她在给单位送货时,遭遇车祸,双腿粉碎性骨折。生孩子时,她的双腿还打着石膏。但至今,她还无法获得工伤待遇。她甚至连事故认定书都拿不到,这堵死了她起诉的道路,只能上访。
她打着石膏生出的女儿,跟黑保安小明同岁。2012年7月13日,娘俩一起在禹州市永锦能源公司门口,因讨说法被打了一顿。从2009年起,宋每年进京十几次上访,得罪了太多人,被拘留3次,其中一次是因为给市委书记下跪。
和宋雪芳一样,被从王高伟窝点解救出来的上访者侯朝彩也要继续上访。她的孩子还没断奶,跟她住在20元一天的上访村里。12月7日,北京最高气温零下1度,侯朝彩和母亲轮流抱着20斤重的婴儿在国家信访局门口排了一天队,快轮到她时,下班了。2012年5月2日当天,宋雪芳等四个报案人,其实已经记不起来“2号院”的位置。在电话中指点她们的,是曾两次入住“2号院”的上访者张月玲。案发后,张因非法上访被劳教。
(原载《读报参考》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