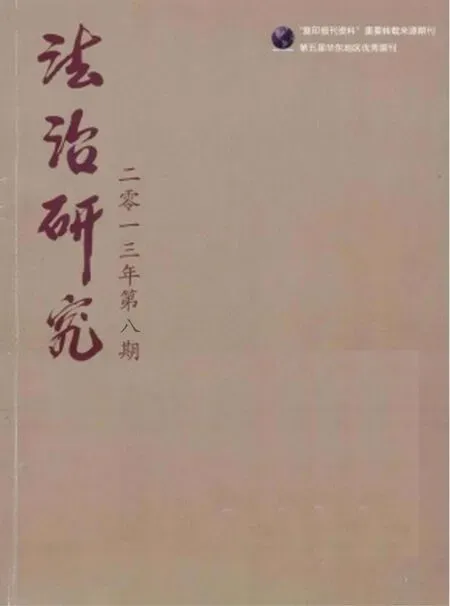僧人遗产纠纷中的深层法律问题解析
——宗教团体自治与司法审查
2013-04-18黄晓林
黄晓林
僧人遗产纠纷中的深层法律问题解析
——宗教团体自治与司法审查
黄晓林*
由于僧侣身份的特殊性,致使僧侣遗产纠纷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状态:涉及宗教团体及其他社会主体的利益,既是国家法律规范的范畴,又与宗教团体的自治有关。各国一般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通过司法权介入此类纠纷,以平衡各类主体之间的利益,防止宗教团体滥用自治权。日本司法实务中区别宗教事务和世俗事务,司法审查可以介入后者,但不能审查有关宗教教义、信仰价值等宗教性问题。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经验,遵循信仰自由的理念,明确司法审查介入宗教团体自治的标准和审查的范围。
遗产纠纷 宗教团体 自治 司法审查
一、问题的提出
2010年1月26日夜间,云南省玉溪市灵照寺的方丈释永修,被前来投宿的吴某、翟某杀害。玉溪市中院及云南省高院作出判决,认定吴某、翟某犯抢劫罪,判处死刑。①参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玉中刑初字第116号刑事判决书、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云高刑终字第1484号刑事判决书。寺庙僧众和其亲属整理遗物时发现,释永修个人在当地银行存有400余万元存款。释永修的女儿张某(刑事判决中确认父女身份)以玉溪市红塔区灵照寺佛教管理委员会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继承父亲的遗产。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该案,于2012年9月20日作出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是:原告不能够提供证据证实释永修名下款项的来源,而被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款项来源于信徒布施、捐赠、寺院卖香火和素斋的收入。所以,释永修出家后,其本人或寺院接受的布施、捐赠以及通过宗教活动取得的财产均属寺院所有。
在本案之前,也曾发生过多起类似纠纷。在鞍山市千山香岩寺僧人释本愿遗产纠纷、②参见鞍山市千山区人民法院(2008)鞍千初字第846号民事判决书。鞍山市千山香岩寺方丈释本愿因病死亡,留有以其名义的存款、汽车等财产,其三子女之间因遗产继承而起纠纷,起诉到法院,千山香岩寺被列为第三人。法院认定汽车为千山香岩寺出资购买,以释本愿名义存入银行的28万元来源于信众的捐赠,并非释本愿的个人财产,应当归千山香岩寺所有,驳回原告的继承请求。绍兴县石佛寺僧人释本耀遗产纠纷③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浙民一终字第134号民事判决书。朱某长期服侍绍兴县石佛寺住持释本耀的生活起居。释本耀立下遗嘱,其名下的存款与现金除去办理后事开支外,剩余部分均归朱某所有。释本耀去世后,朱某因遗产继承与绍兴县佛教协会发生纠纷,起诉到法院。两审法院均未支持朱某的诉讼请求,理由是原告无证据证明存款是释本耀个人合法存款。中,与上述释永修遗产纠纷案的处理方式一样,法院也是依据原告未能举证证明所争财产是被继承人的合法财产而驳回原告的遗产继承请求,判令财产归寺院(佛教管理委员会)所有。此外,在上海玉佛寺僧人钱定安遗产纠纷④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钱伯春能否继承和尚钱定安遗产的电话答复([1986]民他字第63号):1981年钱定安在上海玉佛寺出家,1984年死亡,丧葬由玉佛寺料理。钱定安的侄子钱伯春凭公证处出具的继承权公证文书,从银行提取了钱定安的遗产1500元存款。之后,钱伯春又去玉佛寺要求继承已被玉佛寺收取的钱定安的其它遗产,于是双方起了争议,起诉到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请示最院如何处理,最高院电话答复:(1)我国现行法律对和尚个人遗产的继承问题并无例外规定,因而,对作为公民的和尚,在其死后,其有继承权的亲属继承其遗产的权利尚不能否定;(2)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况,同意对和尚钱定安个人遗款的继承纠纷,由受理本案的法院在原、被告双方之间作调解处理。中,法院以调解方式结案。
上述案例引发了各界对僧侣遗产处理问题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僧侣的财产应当按照佛教戒律处理,还是应当依《继承法》处理。产生争议的主要原因在于僧侣身份的特殊性:既是宗教团体的成员,应当遵守宗教团体的规则,同时又是普通公民,是法律上的自然人,应当受国家立法的约束与保护。佛教从释迦牟尼创立僧团之后,就形成了财产共同共有的丛林规则,即“一切亡比丘物,尽属四方僧”,这一规则在《毘尼作持续释》、《佛说目连问戒律中五百轻重事》《百丈清规》等很多佛典中都有记载,从而奠定了寺院僧团管理制度的基本原则。在我国的佛教历史上,寺院财产共同共有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即僧人出家入寺意味着脱离俗家的权利义务关系,基于佛教信仰,自愿遵守佛教团体内部的一切戒律和规则,与寺院之间形成经济共同共有的关系:寺院负责僧人的生老病死,僧人的财产是寺院(僧团)共有财产的一部分。所以僧人去世后,其俗家亲属不能继承僧人的遗产。⑤中佛协关于僧人遗产处理问题的复函([1998]第197号)、中佛协关于寺院僧人遗产问题的复函([2002]第128号)。然而,《继承法》又规定,近亲属之间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正因为如此,最高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时认为:“……我国现行法律对和尚个人遗产的继承问题并无例外的规定,因而,对作为公民的和尚,在其死后,其有继承权的亲属继承其遗产的权利尚不能否定……”⑥同注②。
僧侣遗产纠纷涉及宗教团体、成员及其他社会主体的利益,既是国家法律规范的范畴,又与宗教团体的戒律有关,非常复杂。围绕法院对上述纠纷的处理结果,产生了针锋相对的两派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按照宗教戒律处理这样的纠纷,相反观点则认为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暂且不论该类纠纷的解决依据及处理结果如何,无论哪派观点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即法院能否介入宗教团体自治纠纷审理判断与宗教信仰有关的纠纷?只有首先厘清了法院审判权在处理宗教纠纷中的界限,才能进一步讨论如何适用具体规则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如何界定宗教团体自治与司法审查的界限。
二、宗教团体自治与司法审查的一般理论
中国正处于转型阶段,宗教团体与其他非营利性社会团体的健康良性发展,对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作用。随着这些社会组织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扩大与加强,因其自我管理行为所产生的法律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法院审判权应当如何介入社会组织自治管理的问题,更是备受瞩目,例如:体育协会对其成员的处罚、行业协会规则的合法性、大学对学生的处分以及本文将要探讨的宗教团体戒律等,这些问题均与社会团体的自我管理有关。虽然学术界对自治权的性质、地位等未达成一致,但普遍承认社会团体享有自我管理的权利。团体自治权一般包含有下述内容:制定团体管理规则、任免内部管理人员、处罚成员、解决内部纠纷等。自治管理权是培育、发展社会团体的重要保障。
宗教团体作为社会团体中的一员,当然也享有自我管理的权利。不过,宗教团体的自治权的渊源与其他社会团体略有不同,宗教团体的自治权源自宗教信仰自由的人权思想。《世界人权公约》、《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等国际公约中,均宣示了宗教信仰自由的人权思想。1981年联合国的《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第6条详细列举了信仰自由的范围,主张个体和集体都享有宗教自由,从不同的角度承认并号召对宗教团体自治权的保护。宗教团体是以宗教教义为中心,宣扬教义,举行宗教仪式等宗教活动,由圣职者和信徒、礼拜设施等结合而成的团体。为了维持教团的发展,扩大其规模,需要制定自治规范,就此点而言,宗教团体与学校、政党、劳动组织及其他社会团体没有本质区别,拥有管理团体内部事务的自治权,即不受其他主体(主要是国家)的干涉,对团体事务、活动、人事等事项作出决定,并能够依据团体的决定进行活动。
然而,随着社会团体组织规模的扩大,管理层与成员之间的利害冲突日渐频繁和激烈,社会团体滥用自治管理权,侵害成员或其他主体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在国家权力中,司法权被认为是“最不具有危险性”的中性的权力,是人权保障的最后堤坝。⑦刘风景:《界分审判权与团体自治权的理论模式》,载《河北法学》2007年第3期。所以,为了防止社会团体滥用自治权,德国、英国等国家运用司法审查的方式控制社会团体自治,违反自然公正秩序的自治行为是无效的。⑧管瑜珍:《社团自治离不开法律》,载《行政法学研究》2007年第2期。日本法学界从“有社会,就有法”的理念出发,建立了“部分社会论”的理论,任何社会组织和团体都有各自的法,国家立法只是众多法秩序中的一种,并且各类社会组织的法都有各自的调整范围和职能,国家立法不能完全取代其他社会组织的法。社会团体有依据内部规则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利。然而,团体的自我管理行为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合理的,存在侵害成员个人利益的可能。此外,社会团体的自治行为也会与团体之外一般社会秩序产生联系,影响其他主体的权利。所以,针对涉及社会团体自治的纠纷,日本法院从维护公共利益和保护个人权利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司法审查。在我国,也承认社会团体的自治权,学界普遍认为应当借鉴国外的经验,在国家权力介入团体自治时,选择司法审查的途径。⑨黎军:《论司法对行业自治的介入》,载《中国法学》2006年4期;李海平:《论作为宪法权利的团体自治权》,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6期。
同样,宗教团体在自我管理过程中,也会在不同主体之间产生各类矛盾,引发诸多问题。为了平衡各类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作为国家权力构成要素的司法权有必要介入宗教团体自治,以防止宗教团体滥用自治权危害社会公共利益。但是,宗教团体毕竟不同于其他社会团体,它的产生基础是成员对某一宗教的共同信仰,关涉人类的精神自由,并且宗教的内容、宗教活动会影响一个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具有政治的敏感性。所以,既需要对宗教团体的自治行为进行管制、审查,又需要有一定的限度。
三、日本司法介入宗教团体自治的经验
(一)圣俗分离理论
日本宗教法界一般认为,宗教团体的活动大致包含两方面:一是举行宗教活动的具有宗教性的一面;二是拥有财产,运营、维持财产等世俗性的一面。这两方面的活动相互联系,形成手段和目的关系,很多时候无法将两者泾渭分明地截然分开。然而,既然宪法确立了宗教自由与政教分离的原则,为了遵守这些原则,就有必要在法律层面上将宗教团体的宗教面和世俗面区别开来,也就是所谓的“圣俗分离”。有一种解释是,宗教法人的“圣”的一面被称为“宗教性”、“出世间性”,“俗”的一面被称为“世俗性”、“世间性”。世俗性的事务由法律规范,宗教性的事务受宪法保障。为了实现宗教法人的目的而从事的业务活动中,针对世俗的事务制定法令,依据法令进行行政管理;对于宗教事务,不允许立法行政干预。⑩[日]井上惠行:《宗教法人法的基础研究》,东京第一书房1995年版,第355页。
《宗教法人法》是规范宗教法人活动的基本法律规范,学界认为该法所调整的范围应当仅限于宗教团体世俗面的活动,宗教面的活动被排除在外。因为《宗教法人法》的立法目的在于通过赋予宗教团体法人人格以确保其从事活动的物的基础,所以《宗教法人法》的着眼点是宗教团体的社会活动,规范宗教团体管理、运营及维持财产的行为,即从世俗面出发,确立宗教团体的基础。⑪[日]蓧原义雄:《宗教法人法的解说:神社关系》,东京神社新报社1951年版,第10页。在《宗教法人法》的具体规定中,也处处反映了圣俗分离的理念。比如,行政机关在宗教法人设立时,对申请事项的审查仅限于从形式上审查申请者是否具备立法规定的作为宗教团体的条件,只需确认教义是否存在即可,而不能审查宗教教义的内容等宗教上的事项。⑫[日]洗建:《法律与宗教》,载《国家与宗教(上卷)》,东京法藏馆2008年版,第29页。又如,宗教法人的自治规则是该宗教法人有关世俗事务的根本规范,根据《宗教法人法》第12条第1款的规定,仅记载宗教团体的财务、管理机关及其他世俗事务,不涉及纯宗教性事务的一面。还有,宗教法人的世俗事务和宗教事务由不同的人员进行管理。与第三人之间的买卖契约、不动产借贷契约等均由代表役员代表宗教法人签订。与此相对,宗教仪式的举行、教义的宣扬等宗教活动则由该法人的宗教活动负责人宫司、住持、牧师、司祭等进行,这些人员作为圣职者,具有宗教上的地位和身份,不同于代表役员。⑬[日]桐开谷章:《围绕宗教法人法修改的问题点:对宗教团体管理要素的导入与评价》,载《创价法学》1997年26号。
(二)宗教团体自治与司法审查的关系
日本《裁判所法》第3条规定,除日本国宪法特别规定的情形以外,法院拥有裁判一切法律上争讼的权限,并拥有其他法律上的特定权限。所谓“法律上的争诉”,指的是当事人之间具体权利义务的争议以及是否存在法律关系的争议,并且能够适用法令最终解决的纷争。⑭[日]最高裁判所昭和41年2月8日判决,载《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1966年第20卷2号;最高裁判所昭和56年4月7日判决,载《判例时报》1981年第1001号。宗教团体的纠纷既有与一般社会纠纷相同的诸如财产归属的问题,还有基于宗教团体的特殊性而产生的纠纷,即“圣”的纠纷和“俗”的纠纷。如前所述,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均不得随意介入宗教团体“圣”的一面,那么作为国家权力构成的司法权又当如何面对宗教团体的自治呢?下面通过几个具体的司法判例对该问题加以说明分析。
1.不属于法律争讼的案件——慈照寺住持地位的确认。宗教法人慈照寺(通称银阁寺)的住持某甲(根据该寺院的自治规则,住持兼任代表役员、责任役员)向其上级宗教组织临济宗的管长某乙表达了辞去慈照寺住持的意思,于是该管长任命了下任住持。之后,某甲以意思表示不真实为由,主张任命无效,要求确认自己的住持、代表役员、责任役员的地位。最高法院认为,住持是主持宗教仪式、宣传教义等宗教活动的负责人,不具有作为寺院管理机关的法律地位。由于寺院的自治规则规定由住持兼任代表役员及责任役员,因而住持也就具有了寺院管理机关的法律地位及相应的权利(例如报酬请求权、寺院建筑物的使用权等)。所以,请求确认代表役员、责任役员法律地位的同时,也就提起了确认住持地位的请求。这种诉讼其实是确认宗教上地位之争,而非法律关系的确认,欠缺适格的诉讼条件。⑮[日]最高裁判所昭和44年7月16日判决,载《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1969年第23卷8号。最高法院通过本案的判决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宗教法人代表役员、责任役员地位的确认请求,是合法的法律关系确认之诉;而寺院住持地位的确认对象是宗教事实关系,并非具体的法律关系,欠缺法律上确认之诉的适格条件。其后,该原则被许多判例引用,成为法院解决类似纠纷的重要依据。⑯[日]最高裁判所昭和55年1月11日判决,载《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1980年第34卷1号;福冈地方裁判所平成12年11月7日判决,载《判例时报》2001年1750号。
2.属于法律争讼的案件——本门寺代表役员地位的确认。在本门寺事件中,最高法院进一步发展了慈照寺判决中的规则,受理了确认代表役员地位的诉讼请求,其理由是:宗教法人是从事宗教活动的社会团体,团体的内部事务原则上由该团体自我管理,作为国家机关的法院不应该介入团体自治的领域,更无权审查判断与宗教事务有关的实体问题。不过,在不干涉宗教活动自由及宗教团体自治的情况下,可以介入与宗教团体自治有关的纠纷。本案中,原告请求确认自己具有代表役员的地位,而合法有效的寺院住持的选任是拥有代表役员地位的前提。为了解决法律关系,应当先确认住持的选任是否合理。在判断住持选任的效力时,需要审查选任过程是否遵守了寺院的选任程序、选任程序的内容是否合理等。由于这些问题不涉及宗教教义的解释等宗教性的一面,因而法院可以进行审查判断。⑰[日]最高裁判所昭和55年4月10日判决,载《判例时报》1980年973号。在本案中,是否拥有住持地位是判断是否拥有代表役员地位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不介入宗教活动自由,不对宗教事务的实体内容进行审查,就可以对住持地位的有无进行审理判断,但审查的范围仅限于选任程序的合理性。
此外,在近松别院事件中,确立了司法审查介入宗教团体内部惩戒的界限。京都地方法院认为,根据一般法理,社会团体有管理、惩罚内部成员的权利,法院无权介入。但是,如果惩戒处分颠覆了被惩戒者的生活基础,对其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与市民法秩序有重要关联的问题时,就不得不成为司法审判的对象。……当内部处分行为的程序明显与正义相悖,或者处分完全没有事实根据,或者虽然遵循了内部自治规则,但处分行为明显缺乏社会观念的适当性时,惩戒权者就没有自由裁量的权利。……本案中,寺院作出的惩戒决定程序与正义不悖,决定的事实依据充分,从社会通常观念来看,没有明显不妥之处,所以处分决定是有效的。⑱[日]京都地方裁判所昭和52年5月20日决定,载《下级裁判所民事判例集》1977年第28卷5号。本案确立了宗教法人内部惩戒须接受司法审查的三种情形:(1)惩戒处分程序明显缺乏正义;(2)惩戒处分完全没有事实根据;(3)惩戒处分的内容违反社会通常观念,明显缺乏妥当性。京都地方法院在其他判例中也遵循上述三个原则,将宗教团体的内部惩戒行为列为司法审查的对象。⑲[日]京都地方裁判所昭和61年7月31日判决,载《判例TIMS》1986年621号。
从前文的叙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以宪法中信仰自由的人权理念为基础,围绕圣俗分离的理论,通过大量判例确立了司法权与宗教团体自治的关系:因宗教团体行使自治权而产生纠纷时,从保障信教自由、尊重宗教团体自治的角度,原则上应当作为宗教团体内部问题加以对待,不允许司法权的介入,不能作为司法审查的对象。但是,当宗教团体的自治行为不涉及宗教教义的解释、信仰的价值、宗教地位的有无等宗教性问题时,国家司法权可以审判宗教自治而产生的纠纷。
四、解决我国宗教团体自治与司法审查关系的基本思路
在前文所列举的僧侣遗产纠纷中,法院自然而然担当了审判者的角色,并且从举证程序的角度,驳回了僧侣近亲属要求继承僧侣财产的要求,因为宗教团体能够举证证明死亡僧侣名下的财产源自与寺院有关的宗教活动,而近亲属无法证明其财产的来源。在几个类似的判例中,法院也是通过诉讼技术解决了问题,既维护了《继承法》的精神,又尊重了宗教团体的自治,但未说明如此处理的深层法理原因,而判决的法理原因是今后更好地解决类似纠纷的基础。为了厘清僧侣遗产纠纷判决背后的法理基础,需要深入探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司法审查权与团体自治权的界限,即司法审查介入与宗教团体自治有关的纠纷的标准是什么?第二,如果司法审查权可以介入宗教团体自治,那么审查的对象范围又是什么?根据前述社会团体自治与司法审查的一般理论,以及日本处理宗教纠纷的司法经验,分析僧侣遗产纠纷的判决结果,归纳我们今后处理同类问题的基本思路如下:
第一,关于司法审查权介入宗教团体自治的标准,最好参考以下标准:当宗教纠纷涉及团体之外其他社会主体利益时,司法权应当介入。英美国家和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在界定司法审查权介入社会团体自治领域的界限时,均使用了“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的理念,当宗教团体等社会团体的自我管理与公共利益相冲突时,法院有权介入进行审查。日本法院在处理宗教纠纷时,也以“与市民法秩序有重要关联”作为司法审查介入的依据。僧侣遗产纠纷不但涉及作为宗教团体自治的戒律,还与国家立法《继承法》有关。很明显,在这类纠纷中,宗教团体的自治涉及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与市民法秩序发生了联系。所以,法院有理由介入这类纠纷,对其加以审查。
由于我国特有的宗教发展历史背景和宗教管理制度,关于宗教团体自治方面的纠纷,除了前述列举的僧侣遗产纠纷之外,其他类型的纠纷目前还未浮出水面。未出现并不意味着没有,也不等于以后不会发生。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推行,宗教团体活动范围的扩大、规模的增长,除了僧侣遗产纠纷之外,类似于日本的更加复杂多样的纠纷也会逐渐产生,如宗教团体的内部惩戒、教职人员的任命等。对于这类纠纷,可以参考日本的司法经验,将司法介入的标准界定为:内部惩戒行为对被惩戒者的正常生活造成重大影响。实际上,这些纠纷虽然与宗教团体之外的社会主体没有直接联系,但会影响宗教团体成员的日常生活,也就与社会公共秩序发生了联系。
第二,关于司法审查对象的范围问题。当法院有必要介入宗教团体自治,对宗教团体的自我管理行为进行审查时,审查范围将是下一个不得不面临的问题。在僧侣遗产纠纷中,法院因僧侣的近亲属无法证明僧侣遗产的合法来源,而宗教团体能够证明其财产来源于信徒的布施、捐赠及宗教活动,所以驳回原告继承遗产的诉讼请求。法院的裁判中似乎蕴含着这样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实体上将僧侣的财产按照来源、取得的时间加以区别,出家之前的财产以及出家之后取得的与宗教活动无关的财产,属于僧侣个人所有;出家之后因从事宗教活动而取得的财产归宗教团体所有。前者可以依据《继承法》由僧侣的亲属继承,后者则按照佛教团体的戒律归团体所有。这种思维模式,既不违背《继承法》的精神,又承认“一切亡比丘物,尽属四方僧”的佛教团体的内律,试图在两者之间取其平衡。暂且不论这一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否合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法院并不打算审查宗教团体戒律的内容是否合法合理,表现了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由于戒律的内容涉及信仰自由,不对其进行审查是合理的,符合人权精神的要求。从前文可以看出,日本宗教法界也秉承不介入宗教信仰自由领域的原则,不审查教义的解释、信仰对象的价值、宗教地位等宗教事务的“圣”的一面。即使审查宗教团体的惩戒行为,也只审查惩戒行为作出的程序是否合理。可见,不审查涉及信仰自由的自治行为,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原则。所以,日本的“圣俗分离”理论有其合理性,值得我们借鉴,可以据此为司法审查对象的范围划定界限:原则上不审查涉及信仰自由的宗教方面的事务,比如教义的含义、宗教仪式等。
五、结语
宗教团体自治权源于宗教信仰自由的人权理念,而宗教信仰自由一向被认为属于精神自由的范畴,应当受到尊重与保护。同时,各国又都通过司法权对其进行审查,防止宗教团体滥用自治权危害社会公共秩序。司法权与宗教团体自治权的关系非常微妙,如果司法权介入宗教团体自我管理过多,会被认为过度干预宗教信仰自由;如果不介入宗教团体的自我管理,可能会使个别成员的利益无法维护,并进一步影响信仰自由法制环境的建立。僧侣遗产纠纷的判例虽然为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基本思路,但是并不完全、彻底,还需要在具体的实践中继续发展完善。此外,这些判例中与宗教信仰有关的问题还有继续探讨的必要,例如戒律关涉宗教信仰自由,将《宪法》中的信仰自由与《继承法》中的继承权置于平等地位,是否符合宪法与普通立法之间的效力关系理论。再如,将“亡比丘物”根据不同的来源判给不同的主体,是否存在司法权过度干涉信仰自由之嫌。司法权既是信仰自由的保障,也是对信仰自由的限制。因此,如何运用这把双刃剑才能真正实现宗教信仰自由与社会公共秩序之间的平衡,是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黄晓林,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