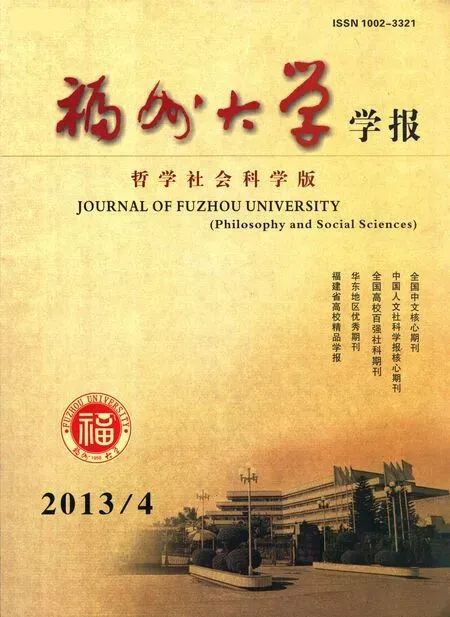《李白与杜甫》:悼己、悼子、悼李杜的三重变奏
2013-04-18王琰
王 琰
(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商丘 4 7 6 0 0 0)
郭沫若在“文革”开始的几年间,连续失去了两位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晚年丧子,并且是死于残暴。在那史无前例的岁月里,这些惨死的冤魂是“死有余辜”的——“自绝于人民”。作为父亲的郭沫若,有难以言说的痛苦、悲伤、内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天天端坐在书桌前,用毛笔书写爱子世英和民英的日记、家书,并整齐地装订为八册,放在床头的窗台上。抄写两位死于非命儿子的日记、书信,并不足以抚平这位文坛学人的内心波涛。这位以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闻名的诗人、学者,抄写儿子的日记、书信,固然可以寄托哀思,但这位“五四”时期的文坛骁将,在1 9 4 9年后的经历和遭遇并没有让他退却搁笔,在这大革文化命的岁月里,在儿子惨遭摧残亡命的时候,何以解忧呢?依然借学术文字,极为隐蔽地表达自己的心曲了。研究学术,领域甚广,从什么选题切入既与“圣意”相符,又切合自己的兴趣爱好,这是使郭氏颇为斟酌的,不然的话,又会带来新的罪名,招来更大的祸端。幸好中国文学史上的李白、杜甫两位大诗人的轩轾臧否,长期以来,未有定论,“圣意”所向恰和作者相成。这样一来,一部既是这位大学者的封笔之作,又充满争议的《李白与杜甫》问世了。
《李白与杜甫》充满了矛盾与悖论,是郭氏所有学术著作中最复杂也最为人们垢病的一部书。之所以这样,源于这部书所产生的特殊现实和文化环境。而今看来,这部著作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作者借学术研究寄托哀思、表示忏悔;对特定残酷环境不满和无奈;有意无意检讨自身,以及对古人进行月旦所表达复杂感情、传达复杂信息的著作,具体而言,《李白与杜甫》是一部悼己、悼子、悼李杜的三重变奏曲。
一、悼己:非杜而似杜,慕李而非李的尴尬
郭沫若是一个球形天才。他在文学创作、历史学研究、文字学研究、政治活动以及其他诸多方面都有所成就,即使是像这样的球形天才,他的才华也是有倾向性的。作为一个诗人、学者、戏剧家是无可争议的天才人物,但作为一个政治家,较之上述几个方面则较为逊色,具体来说,他缺乏一个大政治家的纵横捭阖、虚与委蛇的秉赋才能。人们都津津乐道于郭氏在大革命失败后讨伐蒋氏的两篇文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敬告革命战线上的武装同志》。两篇文章为郭氏争得了现实美誉,而郭氏在这方面的伟绩,这时只需有胆有才即可,不需要纵横捭阖和虚与委蛇;但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郭氏身居高位,地位显赫,参与国是,是头面人物和活跃人氏。适逢共和国左倾思潮泛滥,在这种情势下,只有大革命失败后讨伐蒋氏的勇气和才华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种更高的审时度势的智慧和秉赋,对此,郭氏便显现出政治才华的缺陷来。在他的后半生,是他政治活动的顶峰,也是他遗憾最多的时期。他对自己的检讨,尤其是在“文革”惨祸中的检讨,很大程度上便集中在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之中。《李白与杜甫》可以说是郭沫若对自己一次无情的解剖,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与忏悔,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解剖。他在追问,李杜两人忠君爱国,艺术上卓尔超群,为什么最后是那样的结局。
说《李白与杜甫》是悼己的文章,似乎在语意上有违常理,自己怎么能悼念自己呢?在这里,郭氏是以逝去文学创作上自我以及逝去主体的自我来悼念辉煌时期的自我;以今日愧疚之我怀念过去之我。郭氏说:“自从《女神》之后,我已经不再是诗人了。”[1]“连续失去了两个风华正茂的儿子,郭沫若还能再昧着良心说什么一‘受之甘’吗?这样虚伪地活着,比死去要痛苦百倍。”[2]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说《李白与杜甫》的悼己因素是存在的,他有意无意运用历史的背景与人物,流露自己真实的心态。
1 9 4 9年以后,郭氏位居科技、文艺两界的首席,但历次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批判运动使这位有着独立人格和独特思想能力的文人学者渐渐失去了自我。最初的思想批判运动来自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此次来势凶猛的思想批判运动,对郭沫若的学术品格的影响是负面的,“经过这次文艺上的批判运动,郭沫若的学术品格、学术风格发生了转变,由原来的知识分子传统的代表者向主流文化的代表者转变;由人民本位的陈述立场向官本位陈述立场转变。”[3]特别是在十年浩劫中,郭氏更是身不由己、言不由衷,最为人垢病的是1 9 6 7年6月5日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毛泽东的讲话2 5周年的纪念会,郭沫若作了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好学生》的闭幕词并朗颂了一首《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的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这显然是言不由衷的。大量的资料表明,郭沫若对江青是反感的,甚至是鄙视的。这逢场作戏的诵诗,是一种可悲无奈的自我保护临时性措施。郭氏一生最反对做假,但这个时期,他不得不做假了。他不得不面临着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的“我”与逢场作戏、虚伪做假以求自保的“我”的矛盾痛苦。在文革前夕,他告诉陈明远:“我一生最厌恶最憎恨的就是虚伪造假,不过,我们自己有时也不幸沾染,这种恶习。……如果大家都回复纯真的童心,那多么好啊,不要有这么多的假面具,这么多装腔作势的表演。大家都恢复赤子之心吧!”[4]众多的资料表明郭氏这时分裂成两个“自我”;一为虚伪做假、逢场作戏以为自保的“我”;一为曾有过的爱憎分明、诚实坦白的“我”。在我看来,这两个“自我”,形成了《李白与杜甫》中的悼己的矛盾性。
细读《李白与杜甫》,尽管他的衷肠极为隐晦曲折,但还是可以从中搜寻出一个端绪来。“作者用较大的篇幅论述李白政治活动中的大失败,暗示着作者与李白古今有相似之处,一个大诗人(学者型的诗人)参与政治成功的可能性是极小的,李白在历经坎坷与灾难之后,他终于‘苏醒了’‘云游雨散从此辞’最后告别了,这不仅是对于吴筠的告别,而且是对于神仙迷信的告别,想到李白就在同一年的冬天与世长辞了,更可以说是对于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的告别,李白真像是‘了然识所在’了。”[5]而对于杜甫,作者写道:杜甫从早年经过中年,以至暮年,信仰佛教的情趣是一贯的,而且愈年老而信笃。郭氏在这里所诉说的两位大诗人的信仰无以寄托,转身走向宗教。
从这里可以窥测出郭氏是在借扬李抑杜而曲折表达心曲。他抑杜在某种程度上是抑己,他慕李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恶劣环境的鄙视和超脱。而事实上,他非杜却似杜的处境始终没有改变,他慕李而非李的理想始终没有实现。[6]郭氏虽然没有表明他在积极觅求“五四”时代的强大“自我”,甚至自我贬损,扬言“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来,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7]。这里扬言要烧掉以前所有的著作,实质上是否定作品中强烈的“自我”。这显然不是由衷之言,而是迫于严酷的政治形势的违心表态。在这违心的背后是一种逆反心理,表层的“自我”否定,深层的“自我”怀念,“自我”否定愈烈,“自我”怀念愈强,这种情绪表现在最后的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中,表面上是对为“抑李扬杜”的流行观点进行反驳——应该“抑杜扬李”。但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他“非杜”而处境“似杜”,他“慕李”而处境却“非李”。这种学术立场和作者现实处境的反差,实在是太微妙了,是一种特定时期的典型学术现象,只有在十年浩劫中才能出现。因此《李白与杜甫》的存在,从一个侧面反映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文化状况。
二、悼子:爱其才华、惜其遭遇的矛盾心理
在“文革”浩劫中,两个儿子的去世,使郭氏痛不欲生,世英和民英都是爱子,他们各自有不同的爱好秉赋,民英爱好音乐,世英爱好哲学,对问题喜欢进行反叛性的思考。虽然同为爱子,但世英的去世,更使郭沫若悲痛欲绝,一是因为世英是被虐杀,二是因为世英有着乃父的秉赋。历史不能假设,设若世英没有死于文革,说不定一个出色的哲人会出现在中国学坛。
世英在求学阶段对左倾思潮提出质疑:1.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2.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3.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4.什么是权威?有没有顶峰?等等。表现了作为一个青年学生的反叛性思考的秉赋和才华。世英少年时代的思维雏形是许多思想家共同的思维轨迹,令人惋惜的是,世英生活在一个不允许进行思考,尤其是不允许进行反叛性思考的年代,如果世英是一个平庸之辈,对左倾思潮毫无怀疑,或者是一个跟风小人,他或许不会遭此荼毒,可事实上世英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子,是一个正直坦荡的知识分子,这就注定了他的不幸命运。想来世英的命运和父亲郭沫若对儿子的希冀存在着悖论:郭氏是希望儿子很好地活在世间的,但活在世间的前提是平庸和跟风,这又是郭氏不愿看到的;郭氏是希望儿子有思考判断的才华的,但恰恰由于有才华才导致他死于虐杀,这是作为父亲最不愿意看到的现实。这种矛盾的心理也表现在《李白与杜甫》中。
对于李白和杜甫,郭氏无论是抑杜扬李,抑或是抑李扬杜,对他们二人的才华都是赞赏和仰慕的,但对两位诗人的政治活动都有某种程度的非议和否定,特别是对李白的政治活动持不赞同的立场,用大量的篇幅论述李白政治上的失败。标题为“政治活动中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大失败,固然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使是其他篇幅中也流露此意。作者这样的论述固然缘于李白创作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实际,但郭氏对此的反复强调、高调陈述也标明了郭氏内心的隐衷——世英的死和政治有密切的关联,如果世英与政治无涉,不疑惑左倾思潮,他的悲剧就不会发生。这种悖论和矛盾在《李白与杜甫》中不时表现出来。尤为明显的是作者对李白的《下途归石门旧居》评价甚高,这首诗在李诗中极为平常、平凡,历来不为研究者重视,各种诗选版本均无收,但在《李白与杜甫》中作者对此不仅逐段评析,而且对此评价是出类拔萃:“这首诗,我认为是李白最好的诗之一,是他六十二年生活的总结。这里既解除了迷信,也不是醉中的豪语。人是清醒的,诗也是清醒的。天色‘向暮’了,他在向吴筠告别:生命也‘向暮’了,他也在向尘世告别。”[8]在今天读来,作者对此诗的评价之高,并不是此诗在李诗中特别优秀,而是隐约以此来悼子。文中的想念、哀悼之意,看破尘世之绪,了却内疚之心以及希冀儿子在九泉得到慰藉之隐衷都可以感受到。
《李白与杜甫》的收束之篇为《杜甫与苏涣》。作为“诗圣”的杜甫,对苏涣特别钦佩与倾倒。苏涣在文学史上并不显名,杜甫佩服他的是他的思维方式和人格魅力。对苏涣的《变律诗》三首,郭氏都一一评价,赞赏备至,《变律诗》(一)是苏涣的宇宙观:“一开复一闭,明晦无休息。”和世英的宇宙观暗合;《变律诗》(二)表现的是民瘼关怀:“一女不得织,万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难。”和世英对“大跃进”的怀疑一致;《变律诗》(三)是对文革坏人掌权好人受难政局的讽刺;“毒蜂一成窠,高挂恶木枝。”和世英被害情势相类。在论述苏涣因造反而遭难的成因时,作者写道:“李白并不曾认真造反,而以谗毁终其身。苏涣说他‘不知几’——不懂策略。怎样才算是懂策略呢?照着苏涣后来的行径来看,那就是要沉默寡言,发动群众认真造反吧?苏涣是这样办了,造反持续了两年半,但他也终至遭到杀身之祸。”[9]这些论述不能不说和自己及世英的处境以及对时局的看法有着某种心灵上的联系。
三、悼李、杜:人民本位学术观的流变
郭氏是一个球形天才,是一个通晓古今的大学者,他的学术观是“人民本位”论,他说:“批评古人,我想一定要同法官断狱一样,须得十分周详,然后才不致有所有冤屈。法官是依据法律来判决是非曲直的,我呢是依据道理。道理是什么呢?便是以人民为本位的这种思想。合乎这种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恶。”[10]这种学术观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他的历史研究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是因为有这种学术观作为武器。但“人民本位”的学术观还必须和当时的环境密切联系,离开环境侈谈什么成败功过是空谈。但是,人们对《李白与杜甫》最大的垢病便是作者脱离了时代环境,对历史人物过高过严的苛责。“因为这是一部特殊环境中的学术著作,它打上了左倾思潮的标记,很多地方以左倾思潮的思维来做结论,但与此同时又对左倾思潮、文革灾难进行怀疑,加之作者使用的春秋笔法,曲折地表达心曲,充满了以人喻己,以古讽今,指此说彼,所以,对之视为学术而又不能单以学术析之。”[11]这部书对李白肯定多,是对“抑李扬杜”的反驳,但却没有把“人民诗人”的桂冠加在李白头上。
第一部分《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具有政治外交意义。当时和苏联争论,我方指责对方在历史上侵占中国领土。《李白与杜甫》一出便又多了一个根据。为此,毛泽东还表扬了郭沫若。作品论述了李白政治上的失败,李白流放及道教迷信及觉醒,最后论述了李白和杜甫的交往,对李白艺术上肯定的多,但作者无论怎样肯定李白却很吝啬一个“人民诗人”的桂冠。
对于杜甫,作者列举了“杜甫的阶级意识”、“杜甫的门阀观念”、“杜甫的历史欲望”、“杜甫的地主生活”、“杜甫的宗教信仰”等等,对他进行贬斥,认为他作为一个“人民诗人”是不够格的。单从语言符码的能指来说,这里是对杜甫的否定性评价,但如果我们从语言符码的所指讨论在表层语意所蕴含的东西,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过去一个阶段,学术界认为,凡是农民起义都是好的,凡是反对农民起义都是反动的。这种绝对化认识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郭氏在这里指责杜甫对农民起义持否定态度,在我看来,这里的语言符码所指是丰富的。事实上,郭氏对农民起义并不是全部肯定的。“这样加强了段功,便使段功和车力特穆尔的斗争更加突出了。而在另一方面也可以释去一部分朋友的忧虑。他们认为段功是和农民革命军的明二作对的,加以赞美,似乎是有问题。本来农民革命军是应该代表农民利益。但假如以剽劫为事,就那不是农民革命军了。”[12]“曹操虽然打了黄巾,并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曹操虽然是攻打黄巾起家的,但我们可以说他是承继了黄巾运动。”[13]所以,郭氏在这里指责杜甫反对农民造反的含义是多项的。“造反派”一词成了“文革”劫难的恶谥。但郭氏并不反对农民造反,造反得代表农民利益。
因之郭氏在这里反对的“造反”,应该是特指那种“剽劫”式的造反,是社会灾难的根源,从郭氏的行文中,这里是一种反讽,在指斥杜甫的背后蕴含着对杜甫的肯定:对动荡生活的厌弃,对安全稳定正常生活的渴望。郭氏对杜甫的门阀观念进行了陈述。所谓“门阀观念”,实际上是“文革”时期流行的“血统论”,在“血统论”的观念下,疯狂的人们互相残杀,先是“爹是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继之是争抢正牌的“造反派”,谁是嫡系和嫡亲,最后争夺对“女皇”效忠的“传人”。这种“血统论”的危害是巨大的,是“文革”灾难的酵母。这里郭氏借此喻彼的手法,对“文革”“血统论”进行贬斥和否定。郭氏对杜甫的生活进行了描述,认为他在诗歌创作中夸大自己困苦的生活,他实际上是过的“地主生活”。郭氏对杜甫的种种评价,在学术上并不严谨,但如果联系当时的作者处境,我们觉得,作者的论述倒有某种真实性、甚至于是真理性。
杜甫是不是过的贫苦农民生活,当然不是,但杜甫是不是过的“地主生活”,当然也不是。杜甫当过小官吏,出身名门,他的生活应该是时好时坏的,但郭氏为什么一口咬定杜甫经常哭穷,在创作中说的不是实话。这又回到“文革”的特定环境之中。“文革”是以“谎言”“莫须有”为前提,以“夸大事实”“捏造罪名”为基础的错误政治运动。郭氏在论述杜甫“夸大”自己的困苦生活的时候,作者如果不是有意寄寓着对“文革”的发动者、支持者、疯狂者进行讽刺的话,起码在客观上也有这样的作用。
1 9 4 9年以后,郭氏在极困难的环境中,做出这样以隐晦的方法表达自己的心曲并不是从《李白与杜甫》开始,在5 0年代末6 0年代初,郭沫若创作的两个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便可略见端倪。“曹操对文姬的渴望,应该理解为在灾难性后果的情势下作家某种隐秘的企盼。武则天对骆宾王的宽恕,是不是作家内心企盼对近六十万知识分子的宽恕呢?……因之,这两部历史剧在张扬汉唐气度的背后,蕴藏着一种深沉的忧虑。”[14]如果我们回顾那场不堪回首的灾难时,就不难理解郭氏为什么这么隐晦曲折、欲言又止地表达自己的心曲了。
透过《李白与杜甫》可以看出郭氏性格的复杂性。“研究郭沫若现象是透视中国现在与未来的好窗口,有巨大的现代启示意义。令人不解的是,现在有的学人,不去对历史与现实进行详尽科学的分析,而是孤立的责怪个人,不去对悲剧环境进行责难,而是对悲剧个人进行苛求,这是一种极有害的学术品格。”[15]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杜甫是“人民诗人”,这符合郭氏“人民本位”学术思想的要求,但在《李白与杜甫》中,作者却很吝啬没有把这个桂冠送给杜甫。在这本书的最后,作者却把“人民诗人”的桂冠送给了另外一位诗人苏涣——“如果要从封建时代的诗人中选出‘人民诗人’,我倒要很愿意投苏涣一票。”这种“人民本位”学术观的流变多么剧烈。这种流变的内在因素,便是作者在写作这部书的特殊处境。事实上,他“投苏涣一票”的内在因素是在于借苏涣表达对时局真实的感受,主张苏涣式的造反,反对“红卫兵式”的造反,这种流变是极为隐晦的,但也是有迹可循的。
必须指出是,《李白与杜甫》的“悼己、悼子、悼李杜”是相对的,三种悼念呈现互文关系,三种悼念互相纠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我们指出那个地方是悼己,那个地方是悼子,那个地方是悼李、杜,那仅仅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并不是界线分明的呈现。这本书的本身便是借古人来发己情,所以,把三者截然分开那是十分不明智的。再者,作者的用意十分隐晦,有的地方我们并不能充分理解作者的意图所向,因之,以为全部打开这部著作的奥秘,似乎还为时过早。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界研究郭沫若的深入,揭示《李白与杜甫》的本质内蕴的日子,应该不会太遥远了。
注释:
[1]郭沫若:《序我的诗》,《沫若文集》第1 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 9 6 3年,第2页。
[2]陈光中:《风景——京城名人故居与轶事》,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 0 0 2年,第4 6页。
[3]王 琰:《郭沫若——相逆的文化巨人》,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 0 0 3年,第2 2 3页。
[4]贾振勇:《焚书:郭沫若在文革初期》,《共鸣》2 0 0 5年第1 0期。
[5][8][9][1 1]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 0 1 0年,第9 2,1 3 7,4 3,1 4 2页。
[6]王 琰:《特殊环境中的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的新阐释》,《都江学刊》2 0 0 0年第1期。
[7]龚济民等:《郭沫若传》,北京:文艺出版社,1 9 8 8年,第3 2 4页。
[1 0]郭沫若:《十批判书·后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 9 5 9年,第1 7页。
[1 2]郭沫若:《孔雀胆·后记》,《郭沫若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 9 8 6年,第2 6 5页。
[1 3]郭沫若:《蔡文姬·序》,《郭沫若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 9 8 7年,第7页。
[1 4]王 琰:《双声话语世纪梦——解放后郭沫若两部史剧解读》,《郭沫若学刊》1 9 9 7年第4期。
[1 5]王 琰:《桃源梦中的文人徘徊与寻求——郭沫若精神历程求似方程》,《郭沫若学刊》1 9 9 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