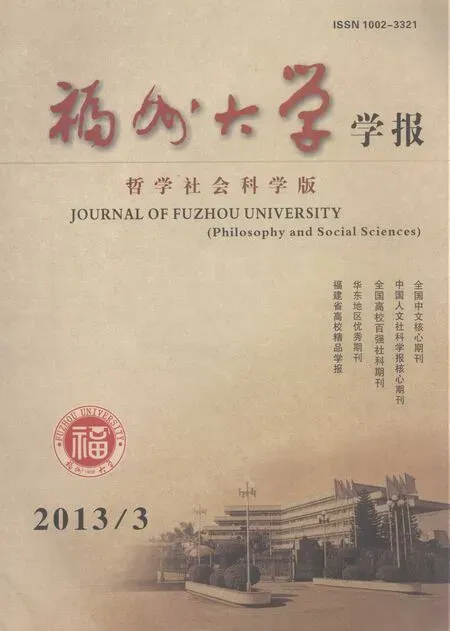论《禹贡》半月刊的编辑特色
2013-04-18黄艳林郝玉香
黄艳林 郝玉香
(1.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福建福州 350002;2.济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济南 250022)
论《禹贡》半月刊的编辑特色
黄艳林1郝玉香2
(1.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福建福州 350002;2.济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济南 250022)
由历史学家顾颉刚创办于1930年代的《禹贡》半月刊,正式英文刊名为《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是我国第一份以“历史地理”一词命名的学术期刊。《禹贡》始终以“学术救国”为办刊宗旨;倡导分工合作的研究精神;坚持“无间新旧,兼容并包”的办刊风格;重视青年作者的培养。《禹贡》的办刊经验为人文社科学术期刊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顾颉刚;《禹贡》半月刊;编辑特色
《禹贡》半月刊(以下简称《禹贡》),由历史学家顾颉刚与谭其骧(后为冯家升)主编,1934年3月1日创办,1937年出完第7卷第10期因七七事变爆发而停刊。《禹贡》共出版82期,在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有300余人,刊登文章700余篇,发行量初为500份,后逐渐增加到2000份。刊物内容包括中国地理沿革、边疆史地、国内民族史、中外交通史等。
顾颉刚(1893—1980),江苏吴县人,历史学家。顾颉刚不仅以疑古辨伪著名于学术界,而且擅长办刊。1920年顾颉刚从北大毕业,继傅斯年、罗家伦之后编辑《新潮》月刊,从此与期刊出版结下不解之缘。至建国前,顾颉刚曾任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复旦大学教授,而每到一所大学他至少要办一个刊物。顾颉刚共编辑过《国学季刊》、《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民俗》周刊、《燕京学报》、《禹贡》、《边疆周刊》、《责善》、《齐鲁大学国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凡十余种,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禹贡》。本文试对《禹贡》的编辑特色作一阐述和分析。
一、“从真实的学识里寻出一条民族复兴的大道来”
1923年5月,顾颉刚在《读书杂志》第九期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在史学界引起一场古史大辩论,成为古史辨学派的代表人物。上世纪30年代,顾颉刚将研究注意力从“古史辨”转到中国地理沿革,原因之一是由于中日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之后步步紧逼华北。日本御用学者也同时不断抛出不利于我国边疆安全的言论,为本国的侵略活动提供学术上的先导。作为一名中国学者,顾颉刚希望通过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尽救国之责任。1932年他开始在燕大、北大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专讲《禹贡》。《禹贡》是《尚书》中的重要篇章,他试图通过研究古籍使人们明了我国的疆域及其流变的情况。1934年3月,顾颉刚与谭其骧商定以北大、燕大、辅仁三校学生课卷为基础办一个刊物,因“《禹贡》是中国地理沿革史第一篇”,故取刊名为《禹贡》,随即又创办了禹贡学会。顾颉刚在“发刊词”中道出了办刊动机:“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地叫起来了。这不是我们的耻辱?”顾颉刚决心以《禹贡》所收集的论文为基础,整理出几部详备精确的专著,如《中国地理沿革史》、《历史地名大辞典》、《地理沿革图》。[1]
在此后出版的《禹贡》“序言”、“编后”、“纪念辞”中,该刊反复阐明了这一办刊宗旨,如“由认识国家民族之内涵,进而谋改造之方术,以求与他国方驾驰骋于世界”[2]。“希望在真实的学识里寻出一条民族复兴的大道来”[3]。
《禹贡》创刊号的“编后”曾指出:“我们所讨论的地理沿革,并不限于上古地理;就是中华民国的设区设道以及市县的增减材料,也在我们的搜集之中。……希望读者能承受我们这个意思,勿重古而轻今。”[4]这表明,《禹贡》从创刊起就强调既重视登载从故纸堆里整理而出的古代地理沿革论文,也重视现实问题的研究。事实上,随着时局的变化,《禹贡》逐渐增加了边疆史地、民族演进史等方面的研究内容。
创刊后不久的8月,顾颉刚冒着酷暑来到百灵庙与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的德王会谈。这次实地调查让顾颉刚了解到德王背后有日本人撑腰,察哈尔、绥远有继东北沦亡的危险。由此他认为“当这强邻狂施压迫,民族主义正在酝酿激发的时候,更应当有许多人想到考究本国的民族史和疆域史”[5]。《我的研究东北史地的计划》也指出了研究东北史地的迫切性:“我国学者对于自己的边疆素少研究,在前清时代和别国起了境界问题交涉时,已不知吃了多少大亏。民国以来,一旦遇上这类问题,仍是受人欺骗。如东北四省,就历史上、地理上、法律上说,明明是中国的领土,而日本为了施展领土野心,早几年前就在国际上宣传矢野仁一的‘满蒙非支那论’,可怜我国学者没有一个能起来加以有力反驳。”[6]
《禹贡》的边疆史地研究,以东北、内蒙、西北为重点。经过冯家升等学者的努力,共编辑出版了东北、西北、后套水利调查、康藏、南洋、察绥等六个专门研究边疆史地的专号,涉及边疆历史和地理沿革、交通状况、经济开发等内容。《禹贡》力图从学术上廓清我国疆土的范围,从而激发国人保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使得荒塞的边疆日益受本国人的认识和开发,杜绝了野心国的觊觎。我们要把我们的祖先努力开发的土地算一个总账,合法地承受这份我们国民所应当享有的遗产。”[7]
在民族史研究方面,《禹贡》展开对古代的戎、狄、肃慎、契丹、突厥等族,现代的藏、满、蒙等族的研究。白寿彝等学者对回教、回族文化教育、回汉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编辑出版“回教与回族专号”和“回教专号”。顾颉刚认为,研究民族史,将“使得国内各个种族领会得大家可合而不可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使命,彼此休戚相关,交互尊重,共同提携,团结为一个最坚强的民族”[8]。
《禹贡》一直重视研究地理沿革史,即使在该刊把研究重点放到边疆史地的阶段,编者依然强调这一传统研究的特殊意义:“苟欲洞悉边情,一赖实地调查,一在考究典籍。”[9]1937 年《禹贡》停刊前的6月还由童书业主持编辑了一期“古代地理专号”,童书业在序言中指出:“历史乃是整个的物事,决没有放弃一部分而永远不问的道理。……先从搜集考订材料的工作上奠定了史学的基础,然后再向高处走去。”[10]
《禹贡》的刊文内容,无论边疆史地、民族史、中外交通史、历史地图、地方志还是地理沿革研究,无不反映出强烈的救亡图存的爱国史学思想。
二、“用平凡的力量,合作的精神,来造成伟大的事业”
顾颉刚在考辨古史时就认识到:“许多学问没有平均发展时,一种学问也要因为得不到帮助而不能研究好。”[11]顾颉刚在《禹贡》的“发刊词”中强调了学科贯通的重要性:“要提出若干关系自然地理而为我们自己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征求科学家的解答。……就是社会和政治方面,我们需要专家的解答正同样的迫切。例如《禹贡》的五服,《王制》的封国,《山海经》中的原始宗教,《职方》中的男女人数比例,都不是我们自己所能研究出最终的结论来的。”接着他呼吁合作研究:“我们不希望出来几个天才,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而只希望能聚集若干肯作苦工的人,穷年累月去钻研,用平凡的力量,合作的精神,来造成伟大的事业”。[12]1937年顾颉刚在《禹贡》三周年“纪念辞”中又对自己所提倡的分工合作精神作了阐释:“以前的学术界不懂得分工,……所以学术的进步形着迟缓。近十余年来,受了外国学术的刺戟,加以大学中筑好了分科研究的基础,学术界便有蒸蒸日上之势。可是但能分工而不能合作,仍不能有长足的进展。”[13]
1934年2月4日,“禹贡学会筹备处”成立,经过顾颉刚、谭其骧、冯家升等人紧锣密鼓的准备,《禹贡》于3月1日正式付梓问世。作为禹贡学会的机关刊物,《禹贡》的稿件主要由学会这个学术团体的会员提供。范长江曾经撰文写道:“《禹贡》的研究工作,完全侧重在‘中国沿革地理’方面。在方法上是采取分工合作的办法,对于中国地理作‘断代’和‘分部’的研究。就其现在工作分配情形而论,计保定培德中学马培棠专攻《禹贡》一书,北京大学教授钱穆专研西周地理,钟凤年专注战国,辅仁大学教授谭其骧专究汉代,厦门大学教授叶国庆研究三国……”[14]《禹贡》或将研究者各自的专题研究成果编辑成册,或“约为某一问题之研究,集合而成专号”[15]。
在《禹贡》把边疆史地作为研究重点的阶段,这种分工合作的研究方式更加受到编者的重视。顾颉刚曾说:“我们必须组织旅行团,分道四出,作实际的调查,搜集现代的材料。”[16]1934年8月,顾颉刚与郑振铎、吴文藻、谢冰心、雷洁琼等专家组成“平绥沿线旅行团”赴绥远调查。1936年顾颉刚又组织各方面专家进行了两次联合调查,一次是暑期一个月的后套水利考察,另一次是11月的察绥地区调查,两次调查结果集结成《后套水利调查专号》和《察绥专号》。
顾颉刚在《禹贡》三周年“纪念辞”中写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人们,大家肯来拥护这集团工作的确立,他们不但为本刊开辟了许多新园地,并给予我国学术史上一种新的生命。”[17]可见,《禹贡》重视学者的合作研究,不仅在刊物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学术同仁,而且在当时的社会科学界倡导了一种研究新风气。
三、“无间新旧,兼容并包”
顾颉刚常说:“我最喜欢有人驳我,因为驳了我才可以逼得我一层层的剥进,有更坚强的理由可得。”[18]他的7册《古史辨》就是以讨论集形式出现的。《禹贡》一创刊,顾颉刚就在“发刊词”中提出要打破学术上的权威思想:“在这个团体中的个人是平等的,我们的团体和其它的团体也是平等的。我们大家站在学术之神的前面,为她而工作,而辩论,而庆贺新境界的开展,而纠正自己一时的错误。”[19]1937年顾颉刚又在《禹贡》三周年“纪念辞”中重申:“我们无间新旧,兼容并包,使得偏旧的人也熏陶于新方法的训练,而偏新的人也有旧材料可整理,他们有相互的观摩和补益而没有相互的隔膜和冲突。我们常有剧烈的争辩,但这争辩并不是有所挟持以凌人,而是把自己搜集来的材料和蕴蓄着的意见贡献出来,共同讨论一个问题,寻求适当的解决。”[20]《禹贡》一直遵循顾颉刚提倡的这一平等讨论原则,广采博收、兼容并蓄地选登文稿。
《禹贡》的争论文章中,有著名学者之间的学术讨论,也有青年学者对大学者的观点提出质疑。顾颉刚本人是“古史辨派”的领袖,但从不以权威自居。如刘兴唐致信顾颉刚认为:“九州将不至全为汉人之伪造,不过古代之九州绝非汉代之大九州,乃古代中华民族开化最早之伊川一带而已。”顾颉刚将信件刊登出来,并在信后加“案语”:“刘先生来函所言,即刚数年来蕴之于心者,异地同符,曷胜欣幸。刚四年前在《燕大史学年报》所发表之《州与岳的演变》,本刊本期所发表之《九州之戎与戎禹》,均乞刘先生检览赐正。”[21]从中可见顾颉刚容纳他人意见的胸怀。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当时作为北大的一名学生撰写了一篇《夏民族起于东方考》,对老师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中“夷夏对立,夷在东方,而夏在西方”之说提出不同看法,主张夏代起于东方。傅斯年看过这篇文章并且不赞同杨向奎的观点,但《禹贡》还是把它登了出来。此外,唐兰的《与顾颉刚先生论“九丘”书》和《辨冀州之“冀”》,孟森、劳干、叶国庆、顾颉刚的《〈尧典〉著作时代问题之讨论》,钱穆、于鹤年的《清代地理沿革讨论》,方授楚的《洞庭仍在江南屈原非死江北辨》等文,均属于不囿于“定论”的议论。
《禹贡》刊登不同学派的学术文章。在“层累说”引起的古史论战中,南京高师的刘掞藜是顾颉刚的主要对手,但他们私下却互相敬佩对方的人格,成为朋友互通信件。刘掞藜36岁英年早逝,顾颉刚在《禹贡》发表了他的论文《晋惠帝时代汉族之大流徙》,并在文前加“按语”:“我想我们总有握手的一天,我想将来我们该再来打古史的官司,直到把我们心头的问题打出一个结果为止,哪知道到了现在只断定是一个虚愿呢!”失去了这位“在贫穷中奋斗,在疾病中支撑的有志之士”[22],顾颉刚感到无比惋惜。
《禹贡》刊登一些日本学者的文章。《禹贡》重视翻译国外的历史地理文章以进行比较研究,其中日本学者的有20多篇。而刊登某些日本学者的文章确要考验编者的兼容度量,如,森鹿三的《禹贡派的人们》一文针对《禹贡》“发刊词”中所制定的工作计划发表议论:“我们很希望,这自负甚大的《禹贡》派的人们赶快编纂一部可以称‘大’的历史地名词典;绘制不但印刷精良,而且没有错误的历史地图;著作一部精确详备而卷帙又不繁冗的《读史方舆纪要》!”文章由周一良翻译后刊于第5卷第10期,并加按语:“他的感想和意见也未始不足以供我们的反省和参考。”[23]而某些日本学者的文章,《禹贡》对其学术价值予以肯定,对其谬误则从学理角度诘驳。如青山定男声称中国研究历史地理之风复炽,乃受王国维影响,而“他(王国维)的伟大贡献,是由日本史学培养成功的”[24]。《禹贡》翻译了他的文章并同期发表张宏叔的《对于日本青山定男“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变迁”之辨正》进行反驳。又如成田节男将《禹贡》的“东北研究专号”看作是对《历史学研究》“满洲研究专号”的模仿,“然而就学术的研究而言,二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王怀中在译文后加“案语”反驳:“像他们的《满洲史序论》那样的文章,以矢野仁一为底子,大唱‘满蒙非支那论’,才是没有学术意味。”[25]
1935年9月,《禹贡》采纳丁鹤年“半月刊中似宜多发表本会计划,通讯,谈话,消息,以便团结精神”[26]的建议,决定从第4卷第4期起,在半月刊上开辟“通讯一束”专栏。“通讯一束”先后发表会员通讯165则,内容多是对《禹贡》中的文章进行讨论甚至争论。“通讯一束”栏目的开设使《禹贡》的学术讨论变得更加活跃。
《禹贡》为各种史学观念提供了一个碰撞和交流的园地,对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进行具有积极意义。
四、“聚集一班青年,唤起他们对于学问的热心”
顾颉刚曾自认他在做学问上是“偏于开风气”[27]的。即善于大胆假设,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顾颉刚31岁靠近乎课艺之作的半封通信《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举成名,而“层累说”其实是存在漏洞的,如他据《说文》中“禹”的解释提出“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假设。此说一出,即遭刘掞藜、胡堇人等学者写文章痛驳。但是,顾颉刚在批评声中渐渐成熟,最后奠定了自己在史学界的地位。受自己成名经历的影响,顾颉刚办刊,也鼓励学生要勇于把自己不成熟的“课艺之作”拿出来发表。顾颉刚在《禹贡》的“编后”这样教导青年学者:“谨慎的前辈常常警戒我们:发表文字不可太早,为的是青年作品总多草率和幼稚,年长后重看要懊悔。这话固然有一部分理由,但我敢切劝青年不要受他们的麻醉。在学术上,本没有‘十成之见’,个人也必没有及身的成功。”[28]顾颉刚认为《禹贡》一个重要的任务是要“聚集一班青年,唤起他们对于学问的热心”[29]。
谭其骧辞去《禹贡》编务工作赴广州任教时,顾颉刚曾写信挽留:“我们若为自己成名计,自可专做文章,不办刊物;若知天地生才之不易,与国家社会不爱重人才,而欲弥补这个缺憾,我们便不得不办刊物。”[30]信中他还以钟凤年、孙海波、马培棠借《禹贡》成名为例说明办刊对于培养人才的重要性。
借助《禹贡》这个平台,顾颉刚把许多有志于学问的青年才俊引上了治学之路。
谭其骧正是第一位由《禹贡》培养出来的知名学者。谭其骧是顾颉刚在燕京大学的学生,顾颉刚最早发现他在中国地理沿革方面的研究才能,他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写道:“谭君实在是将来极有希望的人,他对于地理的熟悉,真可使人咋舌。”[31]于是他邀请谭其骧与自己一起办刊。谭其骧在《禹贡》发表《〈辽史·地理志〉补正》等论文11篇,迅速在学术界脱颖而出,并以研究历史地理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侯仁之、史念海、张维华、郭敬辉后来成为历史地理学界的专家,当时都是刚步入学术领域的青年。他们既是禹贡学会的会员,又参与《禹贡》编辑工作,学术上深得顾颉刚的指点。1981年,侯仁之回忆:“一次在上课的时候颉刚老师告诉我们说,《禹贡》半月刊的出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练习写作的园地。他还亲自为我们每一个人拟定了写作的题目。我分到的题目是:《汉书地理志中所释之职方山川泽寖》。……很快就在《禹贡》半月刊上登载出来。尤其使我惊异的是这篇文章的绪论和结语,都经过了颉刚老师的修改、补充和润饰,竟使我难于辨认是我自己的写作了。”[32]史念海等历史学家的“少作”发表在《禹贡》前,也如候仁之的文章一样,都不同程度经顾颉刚修改过。
据吴丰培回忆,当年他刚出校门进入编辑部,顾颉刚就要他编辑10余万字的“康藏专号”,而且只给半个月时间。顾颉刚手把手教给他不少编辑校对的方法,使“专号”得以顺利出版。吴丰培说:“跟着顾先生工作,是没有钱可赚的。但他尽量给人以出名的机会。”[33]吴丰培从此走上了研究藏族史和边疆史籍的道路。
童书业原是浙江省图书馆一名校对员,中学都没毕业,顾颉刚看到他写的《虞书疏证》,认为他是个可造之材,于是请他来作自己的私人研究助理并任《禹贡》编辑,童书业在《禹贡》共独立发表《蛮夏考》等论文7篇。1949年童书业由杨向奎引荐担任青岛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童书业、杨向奎二位禹贡传人,以《文史哲》杂志为依托,掀起了古史分期讨论,影响了全国史坛。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对《禹贡》在培养人才方面的贡献评价如下:“现代历史地理学领域中的大师,几乎全是当年禹贡学会的成员。以此而论,《禹贡半月刊》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办得最成功的杂志之一。”[34]
《禹贡》创刊时英译刊名为《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从第3卷第1期起,英译刊名改成《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是我国首份以“历史地理”一词命名的学术期刊。《禹贡》不仅实现了“学术救国”的办刊初衷,而且促成了中国传统的地理沿革学向现代历史地理学转变,在学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禹贡》倡导合作研究、提倡学术争鸣、重视青年作者的培养等办刊经验为人文社科学术期刊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注释:
[1][12][19]《发刊词》,《禹贡》第1卷第1期,1934年3月1日。
[2]《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禹贡》第4卷第10期,1936年1月16日。
[3][7][8][13][17][20][29](《纪念辞》,《禹贡》第 7 卷第 1、2、3 合期,1937 年4 月1日。
[4]《编后》,《禹贡》第1卷第1期,1934年3月1日。
[5][16]《编后》,《禹贡》第1卷12期,1934年8月16日。
[6]冯家升:《我的研究东北史地的计划》,《禹贡》第1卷第10期,1934年7月16日。
[9][15]《本会三年来工作略述》,《禹贡》第7卷第1、2、3卷合期,1937年4月1日。
[10]童书业:《序言》,《禹贡》第7卷第 6、7合期,1937年6月1日。
[11]顾颉刚:《走在历史的路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2页。
[14]范长江:《顾颉刚主持之〈禹贡〉学会与中国沿革地理之研究(续)》,《大公报》1935年1月26日第4版。转引自杨军辉:《禹贡学会与<禹贡半月刊>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18][33]顾 洪、顾 潮:《顾颉刚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24,132页。
[21]《通讯一束(一五八)》,《禹贡》第7卷第6、7合期,1937年6月1日。
[22]顾颉刚:《按语》,《禹贡》第4卷第11期,1936年2月1日。
[23][日]森鹿三:《〈禹贡〉派的人们》,周一良译,《禹贡》第5卷第10期,1936年7月16日。
[24][日]青山定男:《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变迁》,魏建猷译,《禹贡》第5卷第10期,1936年7月16日。
[25]王怀中:《案语》,《禹贡》第6卷第11期,1937年2月1日。
[26]《通讯一束(一)》,《禹贡》第4卷第 4期,1935年10月16日。
[27][30][31]葛剑雄:《禹贡传人—谭其骧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8,40,34 页。
[28]《编后》,《禹贡》第1卷第2期,1934年3月16日。
[32]侯仁之:《回忆与希望》,《历史地理》1981年创刊号。
[34]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勤奋为学 终身以之——纪念顾颉刚先生110周年诞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5月20日第1版。
[责任编辑:陈未鹏]
G237.5
A
1002-3321(2013)03-0093-05
2012-12-06
黄艳林,女,江西萍乡人,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编审;郝玉香,女,山东招远人,济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