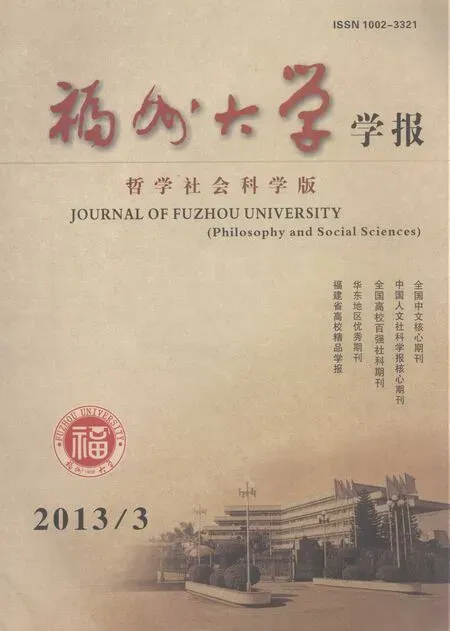英加登“形而上学质”辨析
2013-04-18李晓林
李晓林
(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厦门 361005)
英加登“形而上学质”辨析
李晓林
(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厦门 361005)
英加登在《论文学作品》中提出文学作品有四个层面,每个层面都有审美价值质,“形而上学质”是再现客体层的审美价值质,文学艺术作品只有在形而上学质的显示中才达到顶点。“形而上学质”在文学本体论部分提出,却有待审美经验论和审美价值论部分阐明。“形而上学质”不仅是审美风格和审美范畴,而且有类似宗教和形而上学的价值。英加登这一概念不仅与现象学美学有内在相通,也与形而上学美学传统遥相呼应。
英加登;审美价值质;形而上学质
“形而上学质”是波兰现象学美学家英加登在《论文学作品》中提出的概念。他指出伟大的文学作品有特殊的气氛、光辉,它笼罩作品,使读者震撼。相比英加登文本结构的划分对中西美学、文论界的影响,“形而上学质”的内涵及其与审美价值质、文本结构、价值论美学的关系,这些问题在学术界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也没有得到清晰认识。本文拟就上述问题展开阐述,作为理解英加登现象学美学和文论的切入点。
一、《论文学作品》涉及价值吗?
作为现象学美学家,英加登《论文学作品》体现了胡塞尔为现象学定下的基调,既反对物理主义,也反对心理主义;他主张文学作品既非实在对象,亦非观念对象,而是“纯粹意向性对象”;他着重文学作品本体论,将分析文学作品的一般结构作为此书的目的。
英加登在《论文学作品》开篇申明,“我要说的是一种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具有的基本的结构,而不管它们有没有价值。”[1]这个观点引发了诸多批评,最有代表性的如韦勒克所说,“不谈价值,我们就不能理解并分析任何艺术品。能够认识某种结构为‘艺术品’就意味着对价值的一种判断。纯现象学的错误就在于它认为二者是可以分离的,价值是附着在结构之上的、‘固存’于结构之上或之中的”[2]。可见,韦勒克认为“艺术品”概念暗含着“价值”,没有“价值”也就不是“艺术品”,谈何艺术品的结构分析?
我们首先要对英加登几个基本概念作出辨析,才能看出韦勒克的批评是否有道理。
首先,“文学作品”概念。关于“文学作品”,英加登并未侧重文学作品与其他意识形态、其他艺术门类的不同,而是侧重其内涵界定,“‘文学作品’这个称呼我是指每一部‘美文学’的作品,不管是真正的艺术作品,还是没有价值的作品。”[3]也就是说,他在“文学作品”概念下进而区分了“真正的文学作品”(他亦称之为“文学艺术作品”、“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伟大的文学作品”)和“没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亦称之为“美文学”、“一般文学作品”)。但是“没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之为“文学作品”的依据是什么呢?英加登并未做出理论阐释。我们通过他将“报纸上的侦探小说、学生的爱情诗习作”作为没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的例子,不妨理解成是依据形式的新奇性、故事性、情感性、节奏韵律等。
其次,“价值”概念。英加登有“艺术价值”、“审美价值”和“审美价值质”等一系列与“价值”相关的概念。尽管英加登声称《论文学作品》不谈价值,但是在文本四个层面的分析中,他都谈到该层面的“审美价值质”。从书中看,“审美价值质”概念,其实就是艺术特色。以英加登一向的严谨,为何不称以“风格”、“特色”而称之为“审美价值质”?本文认为,是因其与艺术价值的关联,相应地与具体化中的审美价值的关联。既然英加登分析的是一般文学作品的结构,而每一个层面都涉及了审美价值质,显然“没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中的“价值”一词指的不是各层面的审美价值质;英加登所谓“没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是说作品缺乏整体的“艺术价值”,不是说缺乏“审美价值质”。
关于“艺术价值”,尽管英加登声称《论文学作品》不涉及价值问题,但是英加登指出各层面的审美价值质及其更高级的综合“这些价值最后便构建了属于整部艺术作品的独特的、不可能重复出现的成分,这就是它本身的艺术价值。”[4]将艺术价值视为内在于作品、独立于欣赏者,是欣赏者体验到的审美价值的依据。
后期价值论美学研究中,在区分了文学作品和对文学作品的具体化即审美对象两个概念的基础上,英加登进而区分了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两个概念。在1966年发表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一文中,英加登指出:“艺术价值——如果我们将其存在归因于作品本身并依据于作品本身,审美价值则是只有在审美对象中和决定作品整体特征的特定时刻证明自身的东西。”[5]在1968年维也纳国际哲学大会提交的论文《哲学美学》中也有类似观点:只要我们将艺术作品与对艺术作品的具体化区分开,那么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也就区分开了。[6]
既然英加登指出《论文学作品》要分析的是所有文学作品的一般结构,并非“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的结构,那么价值一词的含义、如何区分一部作品有无价值之类问题就可以悬而不论。按照英加登的思路,只要我们能够辨认出审美价值质,从而知道面对的是文学作品,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问题悬而未决并不影响对作品一般结构的分析。
英加登的文学理论可以分为几方面,作品本体论、审美经验论、审美价值论,分别体现于《论文学作品》、《对文学艺术作品的认识》和后期著述。鉴于英加登《论文学作品》要分析文学作品一般结构,只是一个切入角度,并非否定文学有艺术价值,所以评论界对他“作品与价值二分”的指责是无的放矢。
下面我们梳理四个层面的审美价值质,看英加登怎样从中引出“形而上学质”。
第一,声音层和以此为基础的更高一级的语音组合。声音层的审美价值质就体现在节奏及韵律,“节奏——对文本来说,它是一种由一群语词所确定的、内在的东西”[7],就是说文学作品作为有机整体,不仅由一个个音组成,而是有更高级的单元如句、段,形成作品的节奏和韵律,这是声音层的审美价值质。
第二,不同等级的意义单元层,包括句子层、句子关联、事态。关于意义层的审美价值,书中指出,“它表现为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语言的风格或者诗人的风格……作品语言的这种独特的风格赋予了整个作品的复调一种特殊的价值。”[8]即意义的展示方式是清晰或含混、简单或复杂等特质。
第三,多重图式化观相及观相连续体与系列层。图式化观相最重要的功能是使再现客体层最终呈现,图式观相层面也有自身的审美价值质。英加登举例说,新的文学流派带来新的观相,不同文学流派观相呈现的方式不同,现实主义呈现方式是连续的,现代主义则是跳跃式的。
第四,再现客体及其变化层。英加登将再现客体层视为“作品的轴心”,其他层面都为了它的最终显现。英加登指出将再现客体理解为“反映了一个历史的实际”是“幼稚的”,而将再现客体从与读者的、作者的关系角度分析也是不合适的,“这就忽视了作为一个文学的艺术作品中的最重要的因素,也就是客体层次的功能直接创造的因素”[9]。他强调“再现的客体的情景最重要的功能在于表现和显示特定的形而上学质”,而“文学的艺术作品只有在形而上学质的显示中,才达到了它的顶点。”[10]在英加登,“形而上学质”就是再现客体层面呈现的审美价值质。比如《红楼梦》提供了一幅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全方位的图像,当然如此,却不仅如此。如果满足于将再现客体层面与社会现实对应,不是阅读文学的方式,而是阅读历史的方式。《红楼梦》的美学意义在于通过再现客体展现了“悲”的形而上学质。
综合英加登的阐述,对文学作品、审美价值质、艺术价值的关系总结如下:文学作品四个层面都有审美价值质;形而上学质是再现客体层面的审美价值质;四个层面的审美价值质形成复调和声;复调和声与形而上学质是文学作品价值所在;文学作品就是四个层面、审美价值质及其复调和声构成的有机整体。
二、形而上学质只是审美价值质吗?
《论文学作品》第一部分,英加登申明,“那个相同的结构不能成为分析文学作品的价值的依据,要在有价值的作品中找到一种完全不同于没有价值的作品的新的原则性的结构,这是毫无疑问的。”[11]从随后的分析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形而上学质是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的特质,不能为“没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分享。
那么形而上学质作为再现客体层的审美价值质,只是与其他三层面的审美价值质并列,还是有不同于其他审美价值质的特殊性呢?
如果仅看书中的某些段落,我们会轻易地认为形而上学质不过是再现客体层的审美价值质,至多是作为更有概括力的审美范畴。《论文学作品》第48节小标题即“形而上学质”,英加登开篇举出崇高、卑鄙、悲剧性、可怕、神秘、恶魔般、神圣等,仅仅从上述列举,无法看出形而上学质与“形而上学”的关联。
紧接着的一段话将“形而上学质”与审美范畴区别开来,“这既不是通常所说的某些客体的属性的性质,也不是这样或那样的心理状态的特性,而通常是在一些复杂的、常常是在相互之间有很大的不同的生活环境或者人们之间发生的一些事件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气氛。这种气氛将凌驾于它们之上,也在这些环境中出现的事物和人们的周围,它深入到一切,用自己的光辉照亮了一切。……一个‘事件’发生了,它使我们和在我们周围展开的这个世界都笼罩在这一个非常奇特和无法描述的气氛中。不管它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性质,是使人感到可怕,还是使人心醉神迷,忘却了自我,它都说明这个事件不同于那些平庸的灰暗的日子,它是那么五彩缤纷,光彩夺目,已经上升到了我们生活的顶点。……形而上学质的显示构成了我们的生命的顶点,同时也是我们的生命和所有一切存在的东西中最深邃的东西。”[12]这段话需要注意之处有三点,一是“形而上学质”是一种“气氛”、“光”,二是它对欣赏者的巨大影响,三是审美体验与日常体验的不同。
首先,“形而上学质”作为“气氛”和“光”。“形而上学质”远远超越了前三个层面作为“韵律、语言或作者风格、观相呈现方式”的审美价值质,而是有强大凝聚力的能量。英加登并未对“形而上学质”的内涵做出概括,只是指出形而上学质并非文学作品的独立层面和必备要素,只是“伟大的文学作品”的质素。从英加登的描述来看,形而上学质尽管在作品中体现为悲、喜等“气氛”,却不是审美风格或审美范畴这么简单。审美范畴是自然、社会、艺术之审美风格的最高凝聚,应该说一切文学作品都有风格。英加登区分文学作品高下的标准,是说一般文学作品只有前三个层面的审美价值质,而没有形而上学质;一般文学作品带来愉悦,伟大的文学作品带来灵魂震撼。以“光”意象来称呼审美对象,这点并非英加登的独创。新柏拉图主义和中世纪美学的神之光,叔本华美学的理念之光,伽达默尔美学的语词之光,都是以光来传达对审美对象的敬畏和赞叹。
其次,形而上学质对欣赏者的影响。英加登区分了欣赏者的二重身份,一是现实生活中的自我,蝼蚁一般卑微;一是审美体验中的我,沐浴在五彩霞光中。审美体验的我是对现实生活中自我的忘却、超越、否定。这种截然二分,我们在其他现象学美学家也可以看到。盖格尔将审美经验中的自我称为“存在的自我”,杜夫海纳将审美体验中的自我称为“有深度”的我,其他诸如海德格尔对现实生活中“闲谈、好奇、无聊”的我与“本真自我”的区分,普莱以“无人称的”的“第二个我”来区别于现实生活中的我。而在盖格尔-英加登-杜夫海纳之间不仅有理论的相似,而确实有思想的继承关系。
英加登提到与形而上学质对应的,是人的形而上天性,“但我们心中有一种期待它们的实现,并且通过‘体验’来觉察它们的秘密的渴望……一直在渴望着沉浸于这种思考,连自己都无法消除它。这种渴望就是我们所采取的许多行动的秘密的根源”[13]。英加登将哲学思考和艺术活动称之为这种渴望的体现。因此,形而上学质是作者基于形而上天性,在创作中予以传达,不是作者自我表现;作品比现实能更集中地传达形而上学质;读者基于同样的天性,在作品中期望这种要求得以满足。形而上冲动是艺术创作的动力,也是审美满足的根源。关于人的天性,后现代哲学否定人有固定本质或天性,只有对人不同的解释,这种看法在今天的学术界甚至成为定论。后现代哲学既然主张多元,那么对人的看法也是哲学史上众多解释之一。不仅康德、而且尼采和海德格尔、杜夫海纳都曾探讨人的形而上学需要和人的形而上学天性,他们也认可艺术是人的形而上学需要得以实现的栖息地。
再次,审美体验与日常生活的不同。他将日常生活称之为“平庸的灰暗的”,却将形而上学质的显现称之为读者遭遇的“恩赐”,能提升欣赏者至“生命的顶点”。实用主义认为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并无鲜明界限,英加登则不同,把审美体验与日常生活截然二分,将日常生活看作心灵麻木的、缺乏感受的,将日常生活意义上的人生看作灰暗的、无意义的、蝼蚁一般卑微的,对于审美体验却极力推崇。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灰色,并非由于贫穷,并非由于无力对日常生活进行粉饰,而是由于日常生活与审美体验是两个不同的领域。英加登对于“形而上特质”作用的分析表明,它与人生的意义密切相关,它是一种价值。
本文认为,英加登称再现客体层面的“审美价值质”为“形而上学质”的原因如下:“形而上学质”是把伟大的文学作品统一起来、从而使其成为“有机整体”的东西;“形而上学质”才能凸显文学作品的价值,而非审美风格;“形而上学质”才能说明文学作品对欣赏者的提升作用,而不只是审美愉悦;“形而上学质”连接了英加登的作品本体论和审美价值论;“形而上学质”体现了英加登与美的形而上学传统的关联。
英加登用“光”来比喻形而上学质,正是光,改变了万千事物的模样。比如,《红楼梦》作为长篇小说,前三个层面呈现的审美价值质很复杂,有的句子和段落节奏欢快、有的悲伤、有的平缓、有的是完全客观的记录。其再现客体的展现也是众多而复杂的,有木石前盟的深情,有海棠诗社的风雅,有黛玉葬花的凄美,甚至有酒桌上粗俗的谈笑。这些好似自相冲突的因素是怎样统一的呢?在诸多的人物、场景和故事中,是什么统摄全篇、使其成为一个有机统一体的呢?英加登曾说,不同的文学作品起主导作用的因素不同。具体到《红楼梦》之类伟大作品,则是形而上学质作主导,是它作为“悲凉之雾”,使一切笼罩在虚幻哀伤的气氛中,统一了万千事物的色调,使小说呈现繁华逝尽的悲凉。
但是英加登指出《论文学作品》对“形而上学质”的探讨并不够,审美价值质作为文学作品四个层面的“艺术风格”、“审美特色”,为文学作品横切面所具有。鉴于四个层面的分析,“使得文学作品的结构中就好像出现了一个横向的剖面……但是在这个剖面中,还看不到文学的艺术作品的全部本质”[14]。因此在书末,英加登又简单展示了作品构建中“纵向的剖面”。这一“纵向的剖面”只有在具体化中才能被充分领略。也就是说只有在欣赏者的审美体验中,即当艺术作品成为审美对象时,文学作品作为有机整体才能被完整感受,大量空白能够被填充,潜在的复调和声、形而上学质才能显现出来。
三、形而上学质:艺术形而上学?
关于形而上学质,在1931年首版的《论文学作品》书末说到,“通过对它们的观察,我们就可看到存在的深邃和本源……因为在它们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在别的情景下被隐藏和神秘的东西,而且也是刚刚显现出来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存在的本源,是本源的一种形式的表现”[15]。甚至提到欣赏者对“形而上学质”的感受与人的“原始情感”的关联。“存在”、“原始情感”、“显现”之类概念,似乎表明他受到海德格尔的影响。1937年首次出版的《对文学艺术作品的认识》第48节,也引用了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理论。1927年,英加登拜会胡塞尔时确实与海德格尔就《存在与时间》有几次交谈,甚至提到海德格尔“谈及尚未出版著作中的观点”[16]。但是英加登却否认受到其影响,声称自己的“存在-生存概念与海德格尔及其德法生存主义追随者没有相似之处”[17]。可以说,英加登与海德格尔在“本体论”、“存在”、“此在”的理解上的确有差异。
在《论文学作品》书末,英加登也指出,形而上学质在文本中只是处于“潜在”状态,只有在文学欣赏的“具体化”中才能得以彻底显示。五年后即1936年出版的《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是审美经验研究,但是此书对“形而上学质”的探讨也未使他满意。关于形而上学质,他多处的欲言又止或意犹未尽,说明他认为脱离审美价值论的孤立考察并不能看清形而上学质。
首先,形而上学质的内涵和意义在《论文学作品》和《对文学作品的认识》中都未明确,只有在英加登后期的价值论研究中才得以阐明。在1968年《哲学美学》一文中,他提出了许多闪光的观点及独创的设想。他指出哲学美学的研究领域包括相互联系的几方面:艺术作品本体论、审美对象本体论、作品风格及其与价值关系的哲学分析、相关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研究、审美价值理论,这些相互依赖、不可分割、不可孤立研究。[18]英加登提出了哲学美学的研究范围,最后一条就是“艺术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或者“艺术的形而上性质”,指出它和艺术的“审美价值”等因素密切相关。可见,英加登之所以对于韦勒克没有认识到他对艺术“审美价值”耿耿于怀的原因。审美价值、艺术的形而上性质,英加登早期尽管没有详尽的阐明,却只是悬而不论,这些是他后期理论的重要内容。
其次,将英加登的“形而上学质”放在现象学美学的背景上,可以看到他之前的盖格尔、之后的杜夫海纳同样发现了艺术的形而上性质、艺术对人的提升作用。现象学美学的特殊性在于,从审美经验切入艺术的形而上性质。现象学哲学的意向性概念及“朝向事情本身”的本质直观方法,为现象学美学提供了打破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模式。盖格尔将“审美价值”作为美学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标志,一方面对于艺术有这样的见解,“每一个新的、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揭示了人类存在的新的深度”[19],另一方面如此描述人对艺术作品的审美经验:“产生了这样一种奇迹、产生了从性质上来说与我们一般所体验到的任何东西都不相同的效果、只有对宗教情感的理解和对形而上学方面学习的理解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这种精神过程”[20]。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从审美经验角度论及艺术作品在感性、再现、表现三个层面以外的“形而上的前景”(metaphysical perspective)。杜夫海纳给美学研究的启示是,艺术作品的结构分析,并不能清晰呈现这一形而上维度,只有在欣赏者的审美经验中,艺术作品作为审美对象会“当下发生”地呈现它的“气息、宗教维度”,这也是英加登以欣赏者领略到的“气氛、光辉”来说明文学作品最高意义的原因。英加登与盖格尔、杜夫海纳在研究方法、艺术作品的一般结构和审美知觉分析、审美价值研究方面都颇多相似,在审美价值的“形而上学”建构方面更是遥相呼应。
最后,英加登的“形而上学质”不仅与现象学美学家盖格尔、杜夫海纳的思想有共同之处,更与美的形而上学传统有关联。西方美学史上,美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beauty)和“艺术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art)是从可见的美的事物(人、自然、艺术作品)抵达不可见的美的本体。柏拉图作为美的形而上学之父,其“美本身”、“美的理念”是美的现象背后独立自足的实体,是美的事物的原因。黑格尔“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经典命题既是美的定义,也是艺术的定义。尼采则更多使用“艺术形而上学”,即艺术能传达真理,艺术能给人最终的慰藉。英加登的“形而上学质”依然是对艺术的最高礼赞。
关于形而上学质,奎多·孔恩撰写、收入《现象学运动》一书的英加登条目中有中肯的评价:“人们在这里找到了英加登全部著作中最深刻的信念”,相对于日常生活,“人们对形而上学属性的这种沉思,即对生活的‘意义’的沉思,在艺术和哲学中是可能的,这种沉思构成了使这两种努力会合起来的共同的终极目标。”[21]这是艺术与哲学的对话,是艺术与哲学的最终意义所在。我们有理由相信,艺术和哲学的对话永远不会结束,美和艺术也永远以“光”启示我们、震撼我们、提升我们。
注释:
[1][3][4][7][8][9][10][11][12][13][14][15]英加登:《论文学作品》,张振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29,26,77,69,217,283,286,283,284,286,295,285 页。
[2]韦勒克、沃 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73页。
[5][6][18]Roman Ingarden.Selectedpapersinaesthetics.Edited by Peter McCormick.Washington: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1985,p97,p20,p19.
[16][17]Jeffrey Anthony Mitscherling.RomanIngarden’sOntologyandAesthetics.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1997.p29,p115.
[19][20]盖 格:《艺术的意味》,艾 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94,139-140页。
[21]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31页。
[责任编辑:陈未鹏]
I01
A
1002-3321(2013)03-0083-05
2012-12-2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象学美学史”(11BZX084)
李晓林,女,山东金乡人,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