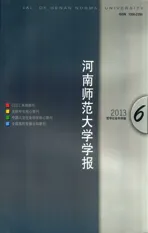论受贿犯罪惩治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运用
2013-04-12于雪婷
于 雪 婷
(吉林财经大学 法学院,长春 130117)
论受贿犯罪惩治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运用
于 雪 婷
(吉林财经大学 法学院,长春 130117)
受贿罪是腐败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历来是我国重点治理的犯罪行为之一,其惩治效果的优劣,对全党、全社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受贿罪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为《刑法》中规定的该罪名之法定刑,然而,其法定刑设置中存在的诸多弊病已对受贿罪的惩治形成了司法上的阻碍,同时,法律的滞后性和长期的稳定性决定了期待通过完善受贿罪的法定刑进而满足迅速提升司法效果的迫切要求并非现实可行。在此情形下,运用刑事政策,弥补立法不足,当是防治受贿犯罪手段体系中不应被忽视的重要部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乃构建和谐社会时代主题之下的刑事政策主旋律,通过科学设定受贿罪中的“宽”“严”情节,在惩办受贿犯罪的司法过程中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区别对待,从而使惩治犯罪的需要与刑罚实施的司法效果之间达到一种最大程度的“和谐”性平衡。
受贿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效果
一、受贿犯罪惩治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运用的必要性
(一)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适度弥补受贿罪法定刑立法缺陷的必然选择
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贿赂也随着社会形态的变迁而不断演变,然而其本质特征和对社会秩序的危害程度却不曾改变,向来是各种社会制度之下法律所重点规制的犯罪行为之一[1]8,在我国,尤其是重刑惩治的对象。然而,现实却是贿赂犯罪的惩治效果并不理想,且犯罪行为手段“花样翻新”。从既往受贿案件的判决结果来看,有的犯罪人受贿几千万元获死刑,有的犯罪人受贿400多万元获死刑;有的犯罪人受贿10万元获刑10年,有的犯罪人受贿200多万元获刑11年,也有的犯罪人受贿20万港元获刑1年零7个月。由此可见,受贿案件情节相似但量刑悬殊或情节悬殊但量刑近似的情形非常普遍。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同样在于受贿罪法定刑设置存在诸多问题,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很难做到最大程度上的同罪同罚,而设置科学的法定刑同样关乎受贿罪的惩治效果及其刑罚目的的实现[1]8。
刑法在惩治犯罪、教育改造犯罪人的同时,同样应当很好地兼顾这一法律功能的内在要求。当前,刑法对于受贿犯罪的惩治,主要依赖于刑法典中关于受贿罪的法定刑,且受贿罪法定刑的重刑色彩浓重,其科学性也已广受质疑,据此做出的刑事裁判,相对于犯罪人来说,其信服力也必然大打折扣。随之而来的是大大增加了犯罪人的内心反社会情绪,为社会再次注入不安定因素。
立法的稳定性和程序的严谨性决定了通过完善受贿罪法定刑的方式使受贿罪的惩处依据更加科学化是一个远景目标。就当下的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而言,通过合理运用刑事政策,以其之“柔”克法定刑规定之“刚”,刚柔并济,当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因法定刑设置的不当而引发司法效果上的不足之必然选择。
(二)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提高惩治与预防受贿犯罪司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内在需求
犯罪的惩治不仅要重视其司法效果,也应重视其社会效果,案件的判决结果不仅应当使犯罪人易于服判、接受改造,也应使案件的判决依据易于理解,使社会民众在情感上易于接受。贪贿等腐败案件的处理易牵动国民的敏感神经,关乎国民对司法公正的确信程度,因此更应注重司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十八大报告将反腐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彰显了党和国家打击腐败犯罪的坚定立场和决心。近来国内掀起了一轮司法惩治腐败的新高潮,一系列大案要案走入民众视野,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案件的处理结果更是备受关注。但和以往相同的是,民众对案件处理结果的不解和质疑声仍旧此起彼伏,究其原因,仍然是由于相比之下,很多案件情节相似但判决结果差别迥异,或情节迥异,但处理结果大同小异。如此状况,在普通民众看来,的确是一件让人费解的事情,犯罪人自身也难以真心服判,司法效果和社会效果随之大打折扣。同样地,这一问题也无法期待通过法定刑的立法改进一朝得以解决,只能在现有法定刑规定的空间之内将立法的模糊性规定合理地、有依据地服务于案件的公正判决之目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要求宽严有度,以法为据,也要求重罪重罚,轻罪轻罚,同时强调区别对待,力图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氛围。这与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核心内容、本质要求、价值追求等方面具有高度的契合性”[3]。概言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指“根据不同的社会形势、犯罪态势与犯罪的具体情况,对刑事犯罪在区别对待的基础上,科学、灵活地运用从宽和从严两种手段,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3]。当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宽严相济将会是我国刑事政策的主旋律,其科学的精神内涵决定了在现有受贿罪法定刑框架内充分挖掘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精神的空间,是提高惩治与预防受贿犯罪司法效果及社会效果的内在需求和必由之路。
二、受贿犯罪惩治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确立进路及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惩治受贿犯罪刑事政策内容之演变
历史上,我国有着重刑主义传统。虽然历朝历代都有统治者施仁政、大赦天下、休养生息的时期,但仅限于“新国用轻典”。“轻典”是相对而言的,刑法仍干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死刑中诸如车裂、腰斩、凌迟等酷刑仍扮演主要角色,对各种犯罪行为处罚相对轻于刑罚最严酷时期,但重刑仍占据主要地位,对贪贿犯罪的惩治同样如此[4]。
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矛盾突出。20纪80年代初期,为了改革开放政策的顺利推进、打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针对犯罪的高发态势,党中央下发了开展严厉打击犯罪专项行动的决定。同时期,邓小平于1982年作出了对经济犯罪的打击应从快从严从重的指示,这一指导精神也始终贯彻在此后的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司法活动中。严打行动开展一段时期过后,社会秩序明显好转,但同时刑讯逼供、任意拔高处罚标准、重结果而轻程序的现象比比皆是,与法治理念背道而驰,社会秩序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得到专项治理的犯罪并没有就此保持低发态势。仅就贪污受贿案件而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开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种体制和制度上的缺陷导致贪贿犯罪愈演愈烈,难以遏制。可以说,严打对于包括贪贿犯罪在内的所有犯罪而言,都没起到有效而长期的作用。专项治理期间,情节类似、危害程度相近的犯罪行为得到的处罚结果往往比平时严重得多,甚至一些不该以犯罪论的行为也被定罪判刑,这种状况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刑罚裁判无法使犯罪人信服。重刑的实施不仅耗费大量司法资源,无法彻底改造犯罪人,相反增加了犯罪人内心的反社会情绪,再次为社会秩序注入了不安定因素[4]。
当前,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我国当前乃至以后相当长历史时期的时代主旋律。鉴于国际上越来越趋同于轻刑化的刑罚理念,以及对我国长久以来的重刑理念和实施了20多年严打政策之实践效果的反思,“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运而生,也必将成为我国惩治受贿犯罪的主要刑事政策。有学者认为这是从逻辑上向“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回归[5],而不同之处则在于“宽严相济”侧重于以“宽”济“严”,从而使惩治犯罪的需要与刑罚实施的效果之间达到一种最大程度的“和谐”性平衡。
(二)受贿犯罪惩治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运用存在的问题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核心内涵的科学性毋庸置疑,然而其在司法实践中所显现出来的问题同样不可回避。
1.“宽”“严”标准模糊不清,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
一方面,“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统筹刑事立法及针对所有犯罪的刑事司法活动,具有高度概括性和统摄性。但是,“在当前中国刑事法制的背景下,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关注更多的主要是司法层面,即利用现有的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资源……审判阶段,正确运用定罪和量刑的自由裁量权”[6]。然而,这种宏观的原则性做法,落实到不同类型的犯罪治理活动中时,其具体样态和标准有很大差别,而刑事政策本身与生俱来的灵活性,加之刑事立法中的模糊性规定和法官个人素质的参差不齐,直接导致了“宽严相济”之宽严标准的不统一。
另一方面,我国法治现代化的发展不过经历了短短数十年,伴随着显著成就的同时,追求法治的道路上也可谓荆棘重重。这其中最难克服的、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中国数千年的人治传统。在中国数千年“家天下”的封建、半封建的社会背景下,统治者的意志处于权力的最高位阶,其效力大于法律;官员之间的门第、裙带关系也影响着裁判者对案件的裁判结果。我国古代法律传统的特征可以概括为“礼法结合、以礼为主、等级有序、家族为本、恭行天下、执法原情……缺乏规则意识和规则权威”[7]。刑事政策的特征之一便是灵活性,这本是刑事政策的优势所在,正因其所具有的灵活性,才能够使处于相对静态的刑事法规适应不同社会形势下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公平正义的客观需求。然而,在我国悠久的法律传统影响下,人们的内心深处或多或少存留着遵从“天理人情”的情感趋向和处事习惯,受贿犯罪行为人为国家工作人员,有的甚至位高权重,当其受到刑事追究并有自认为的情有可原之处时,往往会利用宽缓政策不明确之现状,利用其自身的身份和人脉关系在不同程度上左右司法者对法律规定的理解。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刑事政策的“灵活性”很可能演变成“随意性”,为司法肆意打开方便之门。如此,将与法治精神相背离,于法治目标渐行渐远。
2.“宽”“严”情节规定不明确、不统一,未能体现《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中相关刑事政策的指导性规定
通常来看,目前受贿犯罪的惩治宽或严的处罚标准,除了刑法当中明确规定的通用性从轻或从严处罚情节以外,“受贿罪与其他很多犯罪的法定刑一样,都采用了概括式的法定量刑情节规定模式……但作为划分法定刑档次(子刑度)或同一档次刑度中法定刑升降格设置的主要依据,用语如此含糊、界限不清,实不可取。虽然,有些情节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成为适用惯例,如受贿行为间接导致他人死亡的情形,通常都会被视为‘情节特别严重’”[1]106。这些量刑情节上的适用惯例不仅未能得到任何形式的明确规定,作为适用惯例的情节不仅有失全面性、不利于司法公正,而且《公约》中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关的指导性规定,诸如“明知、故意或者目的”等主观要素的合理推定、扩大腐败行为的法律后果、对腐败行为可以采取特殊侦查手段、多种资产追回方式等,此为“严”;对被告人提供实质性配合的,应规定可以考虑减轻处罚的具体情形,以及刑罚的执行上应考虑到犯罪人重新融入社会的需要,此为“宽”,等等,均没有适用上的统一规定,恐会影响此类犯罪的国际刑事司法协作。
三、受贿犯罪惩治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运用的具体标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科学的精神内涵对于司法活动的整体而言意义重大,然而鉴于其自身的特性和我国的司法现状、文化传统,针对不同犯罪,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操作标准予以规则化落实是非常必要的。我们需要强化规则理念,使同类案件政策性的宽严标准相对规则化、统一化。“刑事政策的调整和犯罪对策的设计,都有赖于对犯罪现象的正确认识”[8]。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主旨为该宽则宽、该严则严、以宽济严、区别对待,而受贿犯罪哪些情节可宽,哪些情节可严,如何区别对待,这些问题的依据是什么,怎样予以规则化等,要科学地解决这些问题,同样需要从认识受贿犯罪现象入手。
(一)受贿犯罪惩治中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依据
“贿赂行为的产生及贿赂犯罪的出现有其特定的生成原因和深厚的历史渊源。……在我国,惩治贿赂犯罪的立法可谓是源远流长,惩治贿赂始终都伴随着中国政治社会的变迁”[1]8。但时至今日,贿赂犯罪仍然是热点犯罪之一,未曾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而有所淡化。当然,贿赂犯罪乃世界性犯罪,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犯罪的产生是自然、社会、文化和个体等各种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且在我国,伴随着特有的深刻文化背景,贿赂犯罪的情形更加复杂且难以遏止,具体缘由,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历史传统因素。我国自古乃礼仪之邦、人情社会,礼尚往来的习俗世代相传,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特别讲究关系的维系和平衡,受人恩惠不忘报答,正所谓“你授之以李,我报之以桃”。几千年的封建人治背景下,人们对权力者的重视、敬畏与遵从更胜于规则与制度。因此,权力者以职权施惠,受“恩惠”之人更要“知恩图报”,权力者若不接受“报答”,又有不给情面之嫌。这使得“权力者以职权行为给予他人方便”与“他人的财物性利益回报”二者的对应成为必然。
其二,社会现实因素。虽然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前列,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国民人均收入却并不高。而受贿罪的主要群体,即国家工作人员的收入水平相比很多行业整体偏低,且放眼世界,我国国家工作人员队伍的薪酬也无法达到高薪养廉的标准。现如今,人们尤其是中产阶层以上人群有着很高的物质生活追求,一些不正的社会风气,如攀比风和某些潜规则,也在不同程度上助长着这种对物质的追求欲望。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权钱交易简单易行,很多国家工作人员在心理上便无法抗拒那些行贿者提供的触手可及的物质利益。
其三,个人心理因素。从犯罪心理的角度来说,贪贿犯罪人具有某些心理上的共性特征。例如“错误的社会心理,权力者通常有时间上的紧迫感,认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他们的灵魂深处蕴藏着以权谋私、金钱至上的错误信条;复杂的动机冲突,此类犯罪人通常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对与自己职务相关的纪律、法律、规章制度也相当熟知,但物质欲望和动机在以权谋私的心理驱动下,强烈到将名誉、恐惧和自尊等反动机压制下去的程度,在动机斗争的过程中往往寻找各种‘合理化’理由去减轻自身的心理压力”[9]。此外,消极的职业人格特征和职务优越感也对贪贿犯罪人犯罪心理结构的稳定程度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受贿犯罪严重损害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及国民对公职行为的信任度,危害之大不容置疑,刑法应对此类行为严加处罚。从以上的剖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受贿犯罪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同时,多次实施受贿犯罪的行为人其受社会负面环境的影响程度更深,其内心负面心理结构往往更加坚固。因此,同样是实施受贿犯罪的行为人,多次反复实施者和偶发实施一次者,其改造难度是大大不同的。因此,在刑罚处罚上应当给予区别对待;同时,鉴于此类人员通常具有较高的文化层次和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犯罪后重新实现个人价值的欲望变得迫切,再次投入社会往往也会显现出较强的创造力。因此,对于改造难度较小的一类贿赂犯罪人来说,刑满后应该被允许得到更广阔的二次发展空间,如此,无论对于犯罪人个人亦或是其家庭乃至社会都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
(二)受贿犯罪惩治中政策性“宽”“严”情节之明析
鉴于受贿犯罪现象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结合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区别对待”的精神内涵,以及《公约》中有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性规定,笔者认为,在现有立法情境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受贿犯罪惩治中应从如下角度予以明确化、规则化,统一运用标准。
一方面,在适用严格政策方面,应当在严格执行现有法律条文的原则性规定的前提下,加大犯罪的追究力度。其一,虽然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现有的数额规定已经无法体现出立法之初其所能征表出的社会危害性,但是在刑法条文未经修改的情形下,决不能随意提高贪贿罪的立案标准,应当够罪必究,绝不放宽追究条件。其二,对索贿的及对国家、集体、人民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犯罪人,限制适用或不适用减轻、从轻处罚情节,并加大罚金刑的处罚力度,正如新加坡所提出的反腐口号那样,对腐败犯罪人,不仅应让其在政治上身败名裂,还应让其在经济上倾家荡产。其三,完善犯罪所得的监控、追缴机制,全力堵截、追缴贪贿犯罪所得财产及其收益,使犯罪人无法通过跨国转移财产的方式藏匿、转移犯罪所得,此举不仅有积极的惩治效果,还能够降低犯罪分子的侥幸心理,进而达到减少、预防贪贿犯罪发生的目的。
另一方面,在适用宽缓政策方面,应当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及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其一,在现有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如前所述,一些受贿犯罪行为人收受他人财物并非情愿,而是在重重顾虑之下、迫于人情世故勉强接纳,在此情形下,所实施行为也未对国家、集体或人民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在追诉前上缴收受财物的,可予以不起诉处理;在严格追究机制的同时,对数额达到法定追诉最低标准,但未造成其他严重后果且如数返还非法所得的前提下,可以更多地运用缓刑制度,以减轻司法压力、促进刑罚趋近轻缓化。其二,对于那些迫于生活压力而收受财物的;在合作经营中虽未真正投入资金,但在民事关系上风险共担,同时为经营切实投入与职权无关(或从行为整体角度看利用了一些因影响力而产生的便利条件)的其他形式的努力,进而收取分红或报酬的;在工作中一贯积极上进、恪尽职守、贡献突出且系初犯的,在同等数额犯罪所得且未造成任何损害后果的情形下,应予以从轻处罚之区别对待。其三,在贪贿罪死刑适用的问题上,应严格以“造成他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为必要前提之一,否则,无论造成多大经济损失也不应适用死刑。
[1]于雪婷.受贿罪法定刑设置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8.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报告[R].2007-03-29.
[3]赵秉志.和谐社会构建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1).
[4]于雪婷.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中国当代刑罚观[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2(3).
[5]储槐植,赵合理.构建和谐社会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实现[J].法学杂志,2007(1).
[6]张树昌,张文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现实与未来[J].中国检察官,2012(3).
[7]房清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用的理性思考——以我国法律传统为视角[J].河北法学,2008(11).
[8]徐润章.犯罪学(第三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4.
[9]罗大华主编.犯罪心理学(第五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165.
[责任编辑孙景峰]
AResearchofIssuesontheUseofCriminalPoliciesofTemperJusticewithMercyinthePunishmentoftheCrimeofAcceptingBribes
YU Xue-ting
(Jil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angchun 130017,China)
The crime of accepting bribes is a major form of corruption crimes. It has long been one of the mostly focused criminal behaviors in our country. The quality of the punishment effects is significant to the CPC and the whole society. The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of the crime of accepting bribes is chiefly based on the items from the Criminal Law. Nevertheless, the many problems in its setting of the conviction have actually become the judicial obstruction in the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accepting bribes. At the same time, the hysteretic nature and long-term stability determines that it’s not feasible to intensify the judicial effects rapidly through perfecting the judicial conviction of the crime of accepting bribes. Under such a situation, using the criminal policies to make up the defects of legislation should become an essential part of preventing as well as coping with the means and system of the crime of accepting bribes. The criminal policy of temper justice with mercy is the major tendency of criminal policies in the modern society, which is expected to be constructed into a harmonious one. By applying scientifically the “temper” and the “mercy” into the crime of accepting bribes, and in the judicial process of punishing the crime of accepting crimes acting with “temper” and “mercy” differently in accordance with various situations, so that the needs of publishing criminals and the judicial effect of implementing punishment can altogether achieve a maximal “harmonious” balance.
the crime of accepting crimes;temper justice with mercy;criminal policies;judicial effect
D914
A
1000-2359(2013)06-0093-05
于雪婷(1981-),女,吉林通化人,吉林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刑法学、犯罪学研究。
2013-05-22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2012B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