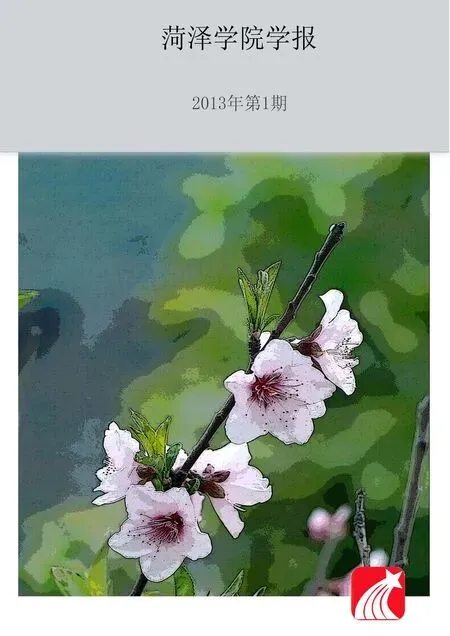宋江与李全*
2013-04-12张同胜
张同胜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水浒传》中宋江这个艺术形象,在文本叙事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突兀的地方,如宋江前面没有两个哥哥,只有一个弟弟宋清,为何被称为“黑三郎”?再如宋江本是衙门胥吏,并未有拜师求艺的叙述,何以又能够教授孔明、孔亮枪棒?如此等等,都表明宋江形象的塑造,采自多个原型,并经过了多次的改编,因而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
王利器先生认为《水浒全传》所根据的底本,“大致有三种:一是以梁山泊故事为主的本子,二是以太行山故事为主的本子,三是以述及方腊故事的施耐庵‘的本’”[1]。这三个底本就是水浒故事的主要来源,我认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来源,那就是宋末、金末元初的“忠义军”头目李全的故事。下面试论述之。
一、忠义(军)
袁无涯在《忠义水浒全传小引》中说:“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李贽认为“非无涯不能发卓老之精神”,袁无涯此论深得《水浒传》之肯綮。
而之前李贽在容与堂本《忠义水浒传序》中说:“太史公曰:‘《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盖自宋室不竞,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鹊,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
夫忠义何以归于《水浒》也?其故可知也。夫水浒之众何以一一皆忠义也?所以致之者可知也。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若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犹以小力缚人,而使大力者缚于人,其肯束手就缚而不辞乎?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则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然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今观一百单八人者,同功同过,同死同生,其忠义之心,犹之乎宋公明也。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真足以服一百单八人者之心,故能结义梁山,为一百单八人之主。最后南征方腊,一百单八人者阵亡已过半矣;又智深坐化于六和,燕青涕泣而辞主,二童就计于‘混江’。宋公明非不知也,以为见几明哲,不过小丈夫自完之计,决非忠于君义于友者所忍屑矣。是之谓宋公明也,是以谓之忠义也,传其可无作欤!传其可不读欤!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朝廷矣。兵部掌军国之枢,督府专阃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读也,苟一日而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为干城心腹之选矣。否则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干城腹心,乌在乎?在水浒。此传之所为发愤矣。若夫好事者资其谈柄,用兵者藉其谋画,要以各见所长,乌睹所谓忠义者哉!”[2]我们看,李贽批评《水浒传》完全是从“忠义”立论,这可以说是抓住了《水浒传》的灵魂。
《水浒传》中宋江宁可毒死结义兄弟李逵,也不愿意李逵把他“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他说:“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第一百二十回“宋公明神聚蓼儿洼,徽宗帝梦游梁山泊”)从这个意义上说,《水浒传》完全可以称之为《忠义传》。那么,“忠义”在历史上和传说中又是如何的呢?
《宋史·李全传》中的“忠义”之称,似专指从金归顺的民兵如“红袄军”、太行山义军等。如“(李)全亦请往,涉不能止,乃帅楚州及盱眙忠义万余人以行”[3]。再如:“十六年二月,涉劝农出郊,暮归入门,忠义军遮道,涉使人语杨氏,杨氏驰出门,佯怒忠义而挥之,道开,涉乃入城。自是以疾求去甚力。五月被召。卒。秋,(李)全新置忠义军籍。初,涉屯镇江副司八千人于城中,翟朝宗统之;分帐前忠义万人,屯五千城西,赵邦永、高友统之;屯五千淮阴,王晖及于潭统之,所以制北军也。(李)全轻镇江兵,且以利啖其统制陈选及赵兴,使不为己患;唯忌帐前忠义,乃数称高友等勇,遇出军必请以自随,涉不许。(李)全每燕戏下,并召涉帐前将校,帐前亦愿隶焉,然未能合也。及丘寿迈摄帅事,(李)全忽请曰:‘忠义乌合,尺籍卤莽。莫若别置新籍,一纳诸朝,一申制阃,一留(李)全所,庶功过有考,请给无弊。’寿迈善而诺之。(李)全乃合帐前忠义悉籍之,尽统其军,时人莫悟。”再如,(赵)拱曰:“忠义反楚州,扬州人见忠义暮归,岂不相疑?不若暂驻兵城外,然后同见提刑,提刑急欲知楚州事也。”[3]他如“(李)福数见翀及佥幕促之,皆谢以朝廷拨降未下,福曰:‘朝廷若不养忠义,则不必建阃开幕,今建阃开幕如故,独不支忠义钱粮,是欲立制阃以困忠义也。’”[3]前引中的“忠义”或“忠义军”,其所指是明确的,那就是李全领导的“红袄军”。
由是观之,“忠义”或“忠义军”即从金王朝投诚归顺宋王朝的民兵,这与《水浒传》中的水浒好汉的“忠义”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即都是受招安归顺大宋朝廷为国出力的忠义之士。或曰水浒好汉实乃异姓结义兄弟,但宋周密《齐东野语》卷九曾记载李全“结群不逞为义兄弟”;《宋史·李全传》也记载了李全与原金元帅张林“置酒结为兄弟”;……在这一点上,二者也是相同的。
二、忠义粮
《水浒全传》第七十回“没羽箭飞石打英雄,宋公明弃粮擒壮士”中有这么一段描写:“张清手执长枪,引一千军兵,悄悄地出城。是夜月色微明,星光满天。行不到十里,望见一簇车子,旗上明写:‘水浒寨忠义粮’。”此时,梁山泊尚未受朝廷招安,何来的“忠义粮”?这里之所以有“忠义粮”的叙述,显然是宋末、金末元初时期,“忠义军”的作为以及南宋朝廷支援忠义军的“忠义粮”等历史事实在口传水浒故事中的一次遗留。或曰“忠义粮”来自于“忠义堂”。宋江掌舵梁山之后,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其军粮自然也顺理成章地改为“忠义粮”。此等解释容或有之,但在正史《宋史》中却真有“忠义粮”的记载。
《宋史·李全传》记载:“时江、淮制置李珏、淮东安抚崔与之皆令纯之沿江增戍,恐不能御,乃命先为机察,谕意群豪;叙复铎为武锋军副将,辟楚州都监,与高忠皎各集忠义民兵,分二道攻金。先遂以李全五千人附忠皎,合兵攻克海州,粮援不继,退屯东海。全分兵袭破莒州,禽金守蒲察李家,别将于洋克密州,兄福克青州,始授全武翼大夫、京东副总管。纯之见北军屡捷,密闻于朝,谓中原可复。时频岁小稔,朝野无事,丞相史弥远鉴开禧之事,不明招纳,密敕珏及纯之慰接之,号‘忠义军’,就听节制。于是有旨依武定军生券例,放钱粮万五千人,名‘忠义粮’。”[3]从此处的记载来看,《水浒全传》中的“忠义粮”的确是渊源有自,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出自想象臆造。
三、水浒寨
在金、元时期,黄河夺淮入海,其地理位置与今天大为不同,但梁山泊却与《水浒传》所描写的颇相一致,因此,可以想见当时黄河两岸红袄军等义军占据着水寨,而这些水寨便是“水浒寨”。
据粗略的统计,截止到20世纪50年代,黄河较大的改道有二三十次之多,其中最大的改道有六次,史称“六徙”,而宋、金时期就占了两次(分别为第三次和第四次):北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黄河在濮阳决口,向西北经内黄、大名沿海河由天津入海;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黄河由原阳决口,分南北两派入海,此次改道的特征是主流南移。[4]梁山泊就是在黄河第二次大改道期间形成的。“黄河第三次大改道期间三次决口注入,两次改道流经梁山泊,湖面进一步扩大成‘八百里梁山泊’。”[5]
根据《历史时期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统计表》可知,五代、宋、金、元(908-1368)期间,历经460年,共决口235次,每次决口平均间隔年数为1.96,即不到两年就决口一次。[6]
而金代是我国历史上黄河泛滥最为严重的朝代之一。宋建炎二年(1128)东京留守杜充于河南滑县人为决河,遂使河道东决夺泗入淮。金明昌五年八月,黄河在开封府阳武故堤决口,洪水流入山东境内,由寿张(今山东梁山北)冲入梁山泊,又分为南北两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南派从泗水入淮河,侵夺了淮阳以下淮河河道。[7]
金末爆发的红袄军,尤其是李全领导的那一支,主要活跃在山东和江苏淮安一带,因而义军时常驻扎在水边,设有水寨。《水浒传》中的“水浒寨”应该是源自元杂剧。《黑旋风双献功》中宋江说:“……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国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济阳,南通钜野、金乡,北靠青、齐、兖、郓。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数百只战舰艨艟。三十六万座宴楼台,聚几千家军粮马革。”但众所周知,历史上的“淮南盗”宋江等人,并没有占据过水浒寨,也没有进行过水战,只是在逃窜海上的时候,尚未上船就遇伏被擒。既然如此,那么《水浒传》中的水浒寨,又是依据什么作为其叙事的原型的呢?
金代时期,黄河流经徐州,而在徐州有十八里寨,此乃金朝廷于黄河岸边驻军重地。红袄军与金兵转战于大河、海滨地区。泰安刘二祖、霍仪等人领导的红袄军则设有水寨,1215年2月,仆散安贞派提控纥石烈牙吾塔等攻破巨蒙等四堌及马耳山。刘二祖军四千余人战败牺牲,八千余人被俘。红袄军宣差程宽、招军大使程福被擒。仆散安贞又派兵与宿州提控夹谷石里哥同攻刘二祖军的据点大沫堌。红袄军千余人迎战。金提控没烈自北门闯入,另一军攻打红袄军“水寨”。胶西李旺领导的起义军又在“朱寒寨”与金军作战,失败。余众仍分布在胶西、高密的农村与海岛之间,坚持战斗。金将王九思攻破石州冯天羽领导的义军“寨栅”,起义群众二千人牺牲。后两处“寨”虽不确定是水寨,但未必不会被书会才人演义为“水浒寨”。李全在占有全山东之后,就往楚州发展,并在长江、大河之上拥有水军。后来,南宋朝廷密令制使图他事发,他便率军溯流而上,攻打泰州、扬州,虽然没有大的水战,但是元杂剧创作的时间去金、宋不远,或许也借用了红袄军水寨的故事吧?
四、排行第三
在《水浒传》中,宋江被江湖好汉称之为“孝义黑三郎”:“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第十八回)。但是,通览《宋史》可知,宋江只有结义的三十六人,并没有亲兄弟。即使是在小说《水浒传》中,宋江除了有一个弟弟宋清之外,并没有大哥、二哥,也没有什么大姊、二姊等,那么,宋江为何有“三郎”或“排行第三”的说法呢?显然,《水浒传》的祖本《宋江》或者说水浒故事的雏形历经说书艺人和文人的增删补削之后,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今本(也是多个版本)由于是罗贯中“编次”而成,于是就无意识中又保留了祖本的一些叙事。
《宋史·李全传》记载,“李全者,潍州北海农家子,同产兄弟三人”[3],而当李全在青州被大元兵长围,而夏全听从朝廷旨意准备诛灭尚在楚城李全的妻子杨氏的时候,杨氏称李全为“三哥”:“杨氏盛饰出迎,与(夏全)按行营垒,曰:‘人传三哥死,吾一妇人安能自立?便当事太尉为夫,子女玉帛、干戈仓廪,皆太尉有,望即领此,诚无多言也。’”[3]又,当李全偷袭金人所统治的泗州东城的时候,“俄城上荻炬数百齐举,遥谓曰:‘贼李三!汝欲偷城耶?’”[3]金军也知道李全是排行第三,称他为“贼李三”。
因此,我想宋江之所以有“孝义黑三郎”的绰号,或许就源自于金末的李全。我们知道《水浒传》是水浒故事经过世代累积,最后由罗贯中“编次”而成,这个“三郎”并没有被删除干净,因此《水浒传》便无意之中将其保留下来了。
据《宋史》,李全“以弓马趫捷,能运铁枪,时号‘李铁枪’”[3]。而《水浒传》中宋江能够教授孔明、孔亮兄弟枪棒,恐怕也是“李铁枪”故事的遗留吧?
五、朝廷负人
《宋史·李全传》记载:“八月,(李)全上谒,宾赞戒(李)全曰:‘节使当庭趋,制使必免礼。’及庭趋,(许)国端坐纳(李)全拜,不为止。(李)全退,怒曰:‘庭参亦常礼,全归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与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统谒贾制帅,亦免汝拜。汝有何勋业,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赤心报朝廷,不反也。’”[3]从历史上看,李全之所以在宋、金之间反覆,不应仅仅从道德这个层面上去一刀切,而是应该看到当时的历史情势使然。南宋小朝廷,危难之际便“利用”义军民兵,美其名曰“忠义军”;一旦事缓,便责令大臣陷害图其性命。即使是如此,李全仍然说“赤心报朝廷,不反也”,在这一点上宋江与其何其相似乃尔!
况且,李全在青州被大元兵长围一年之久,不见南宋小朝廷发一兵一卒以相救,也不见有一粒粮食相支援。不仅如此,南宋小朝廷在战争危急的时候便利用李全;但只要事缓,就暗中指使权臣图谋陷害李全,这是明文在案的,《宋史·李全传》记载:“初,楚城之将乱也,有吏窃许国书箧二以献庆福,皆机事。庆福赏盗箧者五百千,未之阅。(李)全始发缄,使家僮读之,有庙堂遗(许)国书令图(李)全者,(李)全大怒。”[3]试想,一代枭雄如李全者,受辱于文官小吏尚能“赤心报朝廷”,此实属不易;但蝼蚁尚且恋命,偏安于东南一隅的南宋小朝廷“遗(许)国书令图(李)全”,如此,怯懦小人恐怕也会铤而走险,以图保命也;遑论盗贼出身的李全!所以说难以责怪李全在宋、金之间反覆也。
小说《水浒传》中的宋江,其最终的悲剧也是朝廷负人的悲剧。宋江“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李贽语);率领众好汉兄弟们受招安后,一心“保国安民”,先北战大辽,后南征方腊,可谓是为宋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宋朝廷却“恩赐”药酒,毒死了宋江、卢俊义等忠臣义士。这便是赵宋王朝小朝廷辜负忠臣义士在小说中的真实的反映。而赵宋王朝廷辜负宋江,与其辜负李全又是何其相似乃尔!
六、红袄
《水浒传》第二回写陈达“上穿一领红衲袄”。第二十三回写“武松穿了一领新衲红绸袄,戴着个白范阳毡笠儿”。第三十二回写锦毛虎燕顺身穿“枣红苎丝衲袄”……这里的“红袄”岂不是“红袄军”的标志吗?以历史上的黄巾起义、赤眉军、红巾军等标志“黄巾”、“赤眉”、“红巾”例之,此处的“红袄”也是无言的自我诉说。
红袄军指的是金末爆发于山东、河北两地的农民起义军。他们身穿“红袄”为标志,故称红袄军。其中较大的的起义军,山东益都有杨安儿,潍州(今山东潍坊)有李全,沂蒙山有刘二祖,河北有周元儿。贞祐二年(1214)杨安儿东取莱州、登州;郭方三据密州(今山东诸城),进攻沂海两州;李全进攻临朐,扼穆陵关;棘七据辛河,有众四万;史泼立据宁海州(今山东牟平),有众二十万。金政府派重兵到山东,进行镇压。杨安儿败死,所部归其妹杨妙真统率。刘二祖遇害,其部下彭义斌等归李全统率。郝定自成一军。后李全与杨妙真在磨旗山(今山东莒县东南的马鬐山)会合,结为夫妇,合成一军。金兴定二年(1218,宋嘉定十一年)李全投宋。宋政府称之为“忠义军”,发给粮饷,谓之“忠义粮”。
《水浒传》中屡次出现的“红袄”,我认为便是小说依据历史上的红袄军的故事集撰过程中的遗留。否则,小说为何一再描写水浒好汉身穿“红袄”呢?此乃物的言说,小说故事虽然几经修改,但仍然多多少少地保留一部分下来,从而表明水浒故事之其一源头是来自李全领导的红袄军。
七、节度使
在水浒故事中,有宋江被封为“节度使”的传言。这种传言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多多少少有点事实依据的影子在的。假如宋江真的是曾以李全为摹本所编撰的,那么其间的联系就很好解释了。李全的确是曾被南宋朝廷封为“节度使”的。
民间传说宋江在海州被擒之后,投降了宋朝廷,后来随着大军剿灭了方腊,被封为了“节度使”。一般说来,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战功显赫的刘延庆、王禀、王涣、杨惟忠、辛兴宗等都没有被封为“节度使”,而仅仅是一分队中宋江岂能荣获此厚赏?一说宋江等人并没有参加征方腊的战役。
然而,宋江的原型之一李全却是真正曾被南宋朝廷封为节度使的。《宋史·李全传》:“六月,金元帅张林以青、莒、密、登、莱、潍、淄、滨、棣、宁海、济南十二州来归。始,林心存宋,及掴败,意决而未能达。会全还潍州上冢,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陈说国家威德,劝林早附。林恐全诱己,犹豫未纳。全约挺身入城,惟数人从,林乃开门纳之,相见甚欢,谓得所托,置酒结为兄弟。全既得林要领,附表奉十二州版籍以归。表辞有云:‘举诸七十城之全齐,归我三百年之旧主。’表,冯垍所作也。秋,授林武翼大夫、京东安抚兼总管,其余授官有差。进全广州观察使、京东总管,刘庆福、彭义斌皆为统制,增放二万人钱粮,徙屯楚州。”[3]后来,李全的哥哥李福与张林争利,张林听从了李马儿的劝说,归降了大元。十五年“冬,加(李)全招信军节度”[3]。从中可知,李全的确是曾被南宋朝廷封为了节度使。
后来当李全被逼反叛南宋小朝廷时,曾将节度使的官服烧毁。朐山于道士“及见全焚诰命,谓人曰:‘相公死明日,我死今日矣!’人问之,曰:‘朝廷以安抚、提刑讨逆,然为逆者,节度使也。岂有安抚、提刑能擒节度使哉?诰敕既焚,则一贼尔。盗固安抚、提刑所得捕,不死何为!’”[3]于道士的说法固然有迷信的成分在,但他强调了李全曾被封为节度使的事实。宋江的原型之一为李全如果成立的话,那么水浒传说故事中宋江被封为“节度使”的说法就可以得到较为圆满的解释了。
八、馀论
《宋史·徽宗纪》上记载宣和三年(1122),“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今山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3]。海州就是现今的连云港,而楚州则是今天淮安一带。可见,小说中的宋江之所以死于楚州,与历史上的宋江败降在海州无关,而是与李全有关。在《水浒传》中,梁山泊好汉灭方腊回来之后,宋江被任命为楚州安抚使。半年之后,喝了朝廷恩赐的药酒,被毒死在楚州。而李全这位忠义军首领,以楚州为根据地,他与妻子杨妙真等家人的生死存亡与楚州息息相关,这应该也是宋江之所以死于楚州的影射意义吧。
《水浒传》中宋江这个形象的最后定型,还加入了元末张士诚的故事。历史上的宋江据说是“勇悍狂侠”,而李全也是一位桀骜不驯的枭雄,这与小说中仗义疏财的宋江形象可以说截然为二人。元末的张士诚仗义疏财,礼贤下士,颇得民心,这一点便是宋江艺术形象的最后的上色。
《水浒传》所采用的史料中,李全不是唯一宋末、金末元初时期的历史人物,其他还有颇多,如张顺。《宋史·忠义传》记载:元兵围襄阳五年,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督师进援,张顺与张贵应募为都统,率3000人赴援,于淳熙八年(1272)五月,发舟百艘,直奔襄阳,各舟置火枪、火炮、炽炭、巨斧、劲弩。当时元军舟师满布江面,他突破封锁,斩断铁索木桩数百处,转战百余里,黎明抵城下。但张顺身中四枪六箭,英勇战死。《水浒传》中的“浪里白条”张顺,据考证,就是依据宋末抗元的同名同姓的张顺改编而成的。再如李全领导的楚州军中有“穆椿”,与《水浒传》中的穆春有无关系?《宋史·李全传》记载完颜霆(李二措)手下骁将张惠号称“赛张飞”,而林冲绰号“豹子头”,我们知道张飞的典型形貌特征之一就是“豹子头”,二者之间难道就没有一点关系?由此推之,《水浒传》所依据的材料委实是与宋末、金末元初的忠义军有着密切的关系。
[1]王利器.水浒全传是如何纂修的[J].文学评论,1982,(3).
[2]李贽.水浒传序[A]//水浒传[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3]脱脱,等.宋史[M].中华书局,1977.
[4]李爱琴.海河的改道及其影响[J].濮阳教育学院学报,2002,(4).
[5]喻宗仁,窦素珍,等.山东东平湖的变迁与黄河改道的关系[J].古地理学报,2004,(4).
[6]陈志清.历史时期黄河下游的淤积、决口改道及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J].地理科学进展,2001,(1).
[7]和希格.论金代黄河之泛滥及其治理[J].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