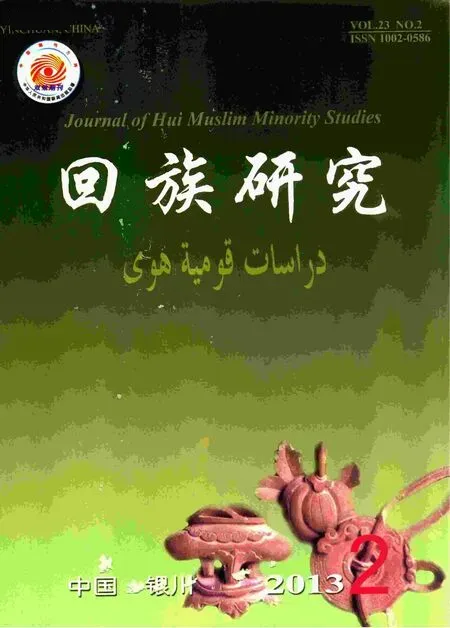民国时期上海回族商人结构的新变化
2013-04-12杨荣斌
杨荣斌
(北方民族大学 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宁夏 银川750021)
一、民国时期的上海回族商人
自古以来,回族就以善于经商著称,重视商业、鼓励经商也是伊斯兰教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年轻时就有过经商的经历,“他从不玩忽职守,事实上他证明自己是个精明、诚实的经理人”[1]。先知穆罕默德也曾这样高度评价商人:“商人犹如世界上的信使,是真主在大地上的可信赖的奴仆。”[2]
对于伊斯兰商人的商业道德,先知穆罕默德要求:“忠实可靠的商人,在复活日,将与烈士们在一块。”且“诚实的商人在报应的日子将坐在主的影子之下”[2]。回族商人在重视商业经营的同时,必须恪守伊斯兰商业道德。其中,诚实经商:“他曾规定公平,以免你们用称不公。你们应当秉公地谨守衡度,你们不要使所称之物分量不足”(55∶7—9)[3](P401);严禁重利:“吃重利的人,要像中了魔的人一样,疯疯癫癫地站起来。这是因为他们说:‘买卖恰像重利。’真主准许买卖,而禁止重利。”(2∶275)[3](P32);提倡施舍:“你们为吃利而放的债,欲在他人的财产中增加的,在真主那里,不会增加;你们所施的财物,欲得真主的喜悦的,必得加倍的报酬。”(30∶39)[3](P305)民国时期的上海回族商人不仅积极探索商业发展,而且自始至终恪守伊斯兰商业道德,意图保持传统经商理念的同时实现回族商业新的突破。
上海,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畅通的交通条件,自古就有“江海通津,东南都会”的美誉,自1843年开埠之后,上海成为西方文化输入的窗口,并逐步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进入民国后,随着上海社会的进步、经济的繁荣,全国各地的商人、贫民纷纷涌入。其中,也包括一部分回族商人、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他们的到来,一方面,加速了上海的人口汇集和人口流动;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上海经济的发展,以及回族经济的振兴。其中,江苏籍回族商人从事的商业活动,初期主要是皮货业,后改为珠玉业、古玩业、鸡鸭熟食业、手工业及进出口贸易,等等。湖北、山东、安徽、河南籍回族,有的当起了劳工,有的发迹后开办工厂,绝大部分从事传统的清真行业。20世纪20年代后,上海回族商人经营范围扩展到皮毛、医药、棉花、印刷、五金、进出口贸易等业。经过回族商人们的不懈努力,民国时期的上海回族商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据统计,新中国成立时,上海回族经营的工业、商业总数为1276 户,其中商业(包括坐商、摊商、行商)为1214 户,占工商总数的95.14%,而工业只有63 户,只占4.86%,可见上海回族的商业经济比例之大”[4]。然而,民国时期,内忧外患、时局动荡,商业环境并不理想,“目前工商剧战,机械日新,魄力之宏,吾华难与比并。试阅海关年册,进出相较,每年溢出外洋金钱八千数百万之巨,而赔款尚不在此数。年年如是,无怪财尽民穷。若再因循,不出一二十年,将索华人于枯鱼之市矣!岂不哀哉?”[5](P40)面对动荡的时局,民族危亡之际,上海回族商人开始认识到:“惟商贾能兴百业,工艺可塞漏厄。故欧美均以二者为立国大本。”[5](P40)故决心“亟宜合群图谋,扩充工艺,去短取长,坚持勿懈,加以集合商力,广开实业、学堂,一面造就人才,改良商务,事事足踏实地,诚信相孚,以为进寸进尺之计,万勿再效近时倒账覆辙,败坏大局”[5](P40)。这一时期,上海回族商人结构也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
二、阿洪商业职能的加强
(一)阿洪参与商业经营
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阿洪们广泛参与商业经营活动,日用百货、皮毛、金融、出版印刷、饮食业及对外贸易等都有涉及。阿洪们行商人之举,旨在为振兴上海伊斯兰教事业筹措资金,并加强和海外伊斯兰教国家的宗教、经济及文化交流。
在阿洪们的经营范围内,有的发挥传统行业的优势,如祖籍河南洛宁的买俊三阿洪,在上海广西路80 弄卫7 号开设皮毛业商号“裕昌义皮毛行”[6](P177),经营回民擅长的皮毛生意。有的尝试新兴行业,如李玉书阿洪在小沙渡创办的信一和鞋店,专营自制男女鞋[7](P577),拓展了传统的商业经营范围。有的经营项目旨在帮助赤贫的回族商贩,如浙江路清真寺教长哈德成主持办理的免利借贷处,专为扶助教中赤贫无力营生者而设,不取利息[7](P591)。这正是遵循了《古兰经》中的债务施舍原则,“如果债务者是窘迫的,那么,你们应当待他到宽裕的时候;你们若把他所欠的债施舍给他,那对于你们是更好的,如果你们知道”(2∶280)[3](P34)。也有的意在宣扬伊斯兰教教义,如民国19年(1930年),买俊三阿洪自任总经理兼发行人,在南市西仓桥街创建中国回教经书局。以及民国23年(1934年),由达浦生阿洪发起创办上海穆民经书局和上海伊斯兰文化供应社等出版印刷机构,经营目的都是为了发展伊斯兰教,沟通回汉文化交流。
民国时期,上海各清真寺教长都非常支持回族商人的商业经营,并热衷参与商业活动。据记载,“当时,为增强清真牛羊肉菜馆业的实力,扩大清真菜馆业的影响,在上海各清真寺教长的支持下,该行业的穆斯林走上了联合之路。于1936年成立了上海清真牛羊饭菜业同业公会……清真寺教长哈德成、达浦生及杨莲生、宗棣棠等出席会议表示祝贺”[7](P567—568)。
随着上海回族商人们经营业务的不断扩大,全国范围内的阿洪们亦参与到他们的经商活动中。民国3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等国,因军需急用牛羊生皮,上海回族商人马晋卿利用时机,将绝大部分资金转入对外贸易。在全国各地,马晋卿广聘阿洪做经理开展业务。其中,聘请熊宝贵阿洪为沪宁线上“昌记号”经理,李幼三阿洪、武文连阿洪为津浦线上“厚记号”经理,郭子良阿洪、王四阿洪为陇海线上“志记号”经理,刘耀三阿洪、马俊斋阿洪、王大明阿洪为京广线上“晋号”经理[8]。
(二)加强对外贸易,以商养文
民国2年(1913年),为了筹集兴学资金,振兴上海伊斯兰文化教育事业,以商养文促教,以及加强和海外伊斯兰教国家的宗教文化交流,由回族商人马晋卿,阿洪刘彬如、杨福州、哈德成等人,在上海创办协兴公司。总公司设在上海西马桥的晋昌厚商号,由刘彬如阿洪负责;香港为中转站,由刘耀卿阿洪负责;民国3年(1914年),公司在科伦坡(今斯里兰卡首都)设分公司,由杨福州阿洪负责。哈德成阿洪于民国8年(1919年),受协兴公司委派,出任驻锡兰科伦坡经理[6](P177)。此外,民国10—17年(1921—1928年)阿洪达浦生受聘于上海协兴公司。为进一步促进中外穆斯林经济文化交流,在公司资助下,达浦生阿洪于民国10年(1921年)出国,遍访印度、东南亚、中东各国,边经商筹资,边学习、考察伊斯兰教育[9]。
(三)经营书局,宣扬伊斯兰教
“发扬宗教,尤重宣传不力,误会频来,而教胞知识粗疏,教育迟滞,为一重大原因,抑尤有进者,外界对于伊斯兰之真相,误解至多,因由于种族、宗教、风俗之隔阂,而宣传不力,理解未清,吾人实负有相当之责任,此伊斯兰文化供应社之所由发起也”[10]。民国时期,上海阿洪们经营的经书局大多以宣扬发展伊斯兰教为宗旨,以沟通回汉文化、加强交流、消除隔阂为目的。
民国19年(1930年),阿洪买俊三在南市西仓桥街创建中国回教经书局,自任总经理兼发行人,以及书局主编。民国23年(1934年),由阿洪达浦生于上海南阳桥全裕里14 号发起创建上海伊斯兰文化供应社,并在上海蒲柏路380 号开设经书销售处。同年10月,达浦生又创办上海穆民经书局。阿洪们创办经书局,主要翻印经销伊斯兰经书、传播宗教文化、满足清真寺经堂教育。其中,中国回教经书局翻译出版伊斯兰教经典和文化书刊,编印宗教基础知识丛书和阿拉伯语初级读本。同时,与埃及哈勒比书局签约经销其原版式经典书刊[11](P690)。上海穆民经书局主要翻印、出版由朝觐者带回国的《古兰经》、“圣训”,以及相关教义、教法、伦理和阿拉伯语法、修辞等学科的经典和书籍。上海伊斯兰文化供应社主要服务项目包括:出版前人遗著,各种书籍;经销书报、杂志;代办广告、制版、校对、影印、文具等业务;代办报考学校、朝觐等事项[11](P281)。以及代售埃及、土耳其版的《古兰经》,以及王静斋、马坚等国内伊斯兰教学者的著作。
在众多经书局中,阿洪买俊三经营的中国回教经书局,被誉为民国时期中国伊斯兰教维持时间最长、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出版机构,经销、影印原版经典,编译中阿文对照知识丛书,重印明清著作,共发行约20 万部(册)[12](P1511)。该书局编译出版《中阿对照拼音读本》《中阿对照连五本》《中阿对照六大信仰问答》《中阿模范会话》《中阿对照礼拜必读》《汉译赫提》《字源学》等。又继重印明清伊斯兰学者王岱舆、伍遵契、马注、刘智、张中等人的著译,以及王静斋、杨仲明、马坚、金吉堂等现代穆斯林学者的著译。此外,民国24年(1935年)8月,上海伊斯兰文化供应社由周沛华、汤伟烈合作翻译出版了伦敦清真寺教长柱乍加么屋甸所著《穆罕默德言行录》。
自古以来,为了达到以商养寺的目的,阿洪们就一直延续着积极参与经商的传统。就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阿洪们而言,时局动荡,民不聊生,伊斯兰教文化遭受巨大的冲击,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阿洪们开始广泛参与商业活动,积极创造商业价值和财富,以保障伊斯兰教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走上了一条经商、传教并举,以商兴教的道路。
三、回族买办的出现
(一)上海回族买办的出现
所谓买办,即指在外国资本家所设立的银行、公司及商业机构中,被雇佣的中国经理,外国资本家利用买办在国内的销售网打开中国市场。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洋行迁入上海,买办亦随洋行入沪。上海开埠后,对外贸易全部由洋行把持。由于利润丰厚,洋行迅速发展。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广州英商怡和、宝顺、义记、仁记、广源等洋行在上海开设分行。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上海有洋行24 家,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增至116 家。英商洋行就占约60%。19世纪60年代以后,航运、银行、保险等业开始独立发展,买办制度形成,80年代约有买办2000 余人[12](P2095)。民国25年(1936年),上海有洋行675 家,其中,欧美洋行561家、日商洋行114 家。抗日战争胜利后,洋行减少,日商洋行全部关歇。民国36年(1947年)共有洋行370家,英美洋行有182 家。民国38年(1949年)6月共有376 家[12](P2916)。其间,民国23年(1934年)英美烟公司在上海设立颐中(怡中)烟草公司[13]。怡中公司垄断了河南许昌烟叶的收购权,在天津、青岛、蚌埠等地设卷烟厂,总公司设于上海,上海除卷烟厂外,还有卷烟纸厂、印刷厂及包装木材加工厂。此外,英商创办的罗森泰洋行,主要经营拍卖、进出口及零售业务[14]。
20世纪初,全国买办超过万人,上海约有0.2 万—0.25 万人。其中就包括上海罗森泰洋行的买办回族商人喇文发。据记载,“永发祥文玩号店主兼经理喇文治,祖籍四川,世居上海,为回教徒。兄弟四人,君最幼,其兄均已先后逝世。闻其第三兄文发,生前曾为罗森泰洋行买办”[15](P89)。以及上海怡中烟草公司的镇江籍回族买办童楚江。
(二)上海回族买办的商业特征
最初,洋行的买办,大多是临时雇用,“一宗交易既毕,则雇用关系亦遂解除”。之后,代理人盛行,买办开始代理洋行推销鸦片和洋货,到原产地收购丝、茶等土特产品交洋行出口。随着洋行业务不断扩大,有的买办集经纪人、代理人、翻译及顾问于一身。回族商人童楚江就拥有这样特殊的身份,据记载,“童氏与怡中公司的关系不是雇佣关系,而是代理关系”[16]。清末民初,随着商业上重要职能的凸显,上海买办逐渐成为一个庞大的势力阶层,并享有一定的特权。清光绪九年,上海道公布的《上海洋泾浜章程十条》规定:“凡为外国服务及洋人延请之华民,如经被讼,先由该委员(指专任洋泾浜管理各国租地的同知官员)将该人所犯案情移至领事馆,立将应讯之人交案,不得庇匿……”[12](P2946—2947)进入民国后,上海地区的买办制度日趋完善,买办强大的职权功能在洋行内部发挥着支配作用。回族商人童楚江就成为英美在华最大烟草公司——怡中公司的大买办,公司内部称之为“童大办”。童氏独揽总公司的人权、财权。童氏还拥有商品的调配权以及定价权[16]。
买办除了要对洋东绝对忠诚外,还必须具备广泛的业务能力。民国13年(1924年)4月,“兹因徐州府区主任傅兰雅君,因事告退,总公司特任童楚江君以承其乏。童君饱学多能,声誉久著,此次擢升此缺,必能游刃有余也”[17]。回族商人童楚江在英美烟公司工作多年,积累了声誉,赢得洋东的信任,并且由于自身过人的业务能力,从而得到提拔和重用。民国时期,上海回族买办的另一特点在于他们对于西方教育的接受和吸纳,以童楚江为例,“他的生活方式也异于老一辈回族商人,而是全部欧化”[16]。
买办的收入一般除领取洋行买办间开支外,主要以进出口贸易佣金为主,平均约为进口货值的2%、出口货值的1%。此外,还包括如佣金、吃盘、利差、银平洋水差额、出口商品陋规收入等。喇文发和童楚江等回族买办都是“按总产值的一定比例提取报酬”[16]。
上海开埠初期,买办逐渐增多,买办作为洋行的雇员,尚未拥有自己独立的商业,只是承担替洋行收购土产或推销洋货。随着买办制度的不断健全,洋商们开始鼓励买办创办独立的企业。19世纪50年代以后,上海不少买办开始开设商业机构,利用自己的名义和资本,从事自己的商业活动,并且巨额投资商业、工矿、金融、房产、行运等业。例如仁记洋行买办徐萌生开设谦泰利炒茶栈,怡和洋行买办徐惠人开设顺记五金号,礼和洋行买办虞芗山投资棉布号,平和洋行买办朱葆三创办慎裕五金号[18]。回族买办童楚江在南京开办久大烟公司,逐步建立起销售网络,并得到英美烟公司的信任和器重,获取了南京地区香烟推销和管理权。久大烟公司下辖芜湖、清江浦、蚌埠、南京、太县、镇江、安庆、徐州等8 个段,地跨江苏、安徽、江西、山东4 个省,辖包括甲级经销商合肥等35 个、大经销商南京城等83 个及236 个小经销商的庞大垄断销售网。[8]回族买办喇文发则大力投资珠宝业,“闻其第三兄文发,生前曾为罗森泰洋行买办,为钻石巨商”[15](P89)。
上海开埠以后,进出口贸易繁盛,洋行几乎垄断中国所有的对外贸易。回族买办的出现,进一步加强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垄断,包括回族买办在内的买办阶层成为了帝国主义对华贸易的桥梁。但是,回族买办在为洋行服务过程中,广泛接触了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积累了一些经营管理方面的新经验和新方法,在各项经营活动中,买办远远走在其他阶层的前面。回族买办们改变传统闭塞、守旧的观念,在其他阶层尚未萌动之前,率先投资新式企业,成为上海回族商人群体近代化转型的先行者,开启了上海回族传统商业结构向近代化商业结构的转型,促进了上海回族商业的繁荣。
[1][巴基斯坦]赛义德·马茂德.伊斯兰教简史[M].吴云贵,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0.
[2]南文渊.伊斯兰教对商业经济的影响[J].宁夏社会科学,1989(3).
[3]古兰经[M].马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张志诚.上海地区的回族及其经济活动概述[J].回族研究,1994(4).
[5]劝戒同教箴言[A].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B].档号Y3-1-195.上海:上海市档案馆,1911:40.
[6]《上海民族志》编纂委员会.上海民族志[Z].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177.
[7]阮仁泽,高振农.上海宗教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577.
[8]袁纣卫.苏南回族商帮[J].回族研究,1998(1).
[9]王建平.近代上海伊斯兰文化存照[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35.
[10]人道.1934(5).
[11]《上海宗教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宗教志[Z].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690.
[12]《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通志[Z].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1511.
[13]《中国近代史稿》编写组.简明中国近代史知识手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74:343.
[14]刘宁元.拍卖法原理与实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4.
[15]上海储蓄银行有关古玩业调查资料[B].档号Q275-1-1954.上海:上海市档案馆,1932:89.
[16]郑勉之.近代江苏回族经济概貌[J].宁夏社会科学,1985(4).
[17]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3 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1297.
[18]朱国栋,王国章.上海商业史[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