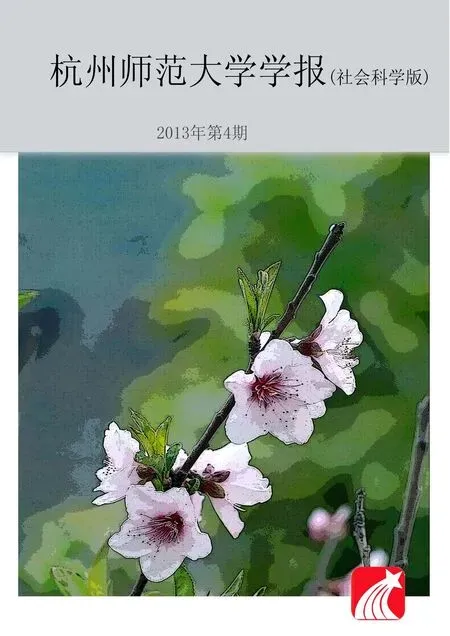情感与品味:影视剧观赏的受众美育
2013-04-12孟丽
孟 丽
(中国传媒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24)
文艺新论关于“观赏文明与审美教育”的讨论
情感与品味:影视剧观赏的受众美育
孟 丽
(中国传媒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24)
作为艺术观赏的一部分,影视剧的观赏在社会美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影视剧的观赏过程中,虚拟性消解了欣赏者与审美对象之间的距离感,欣赏者融入到对象中。影视剧通过它的情感化效应作用于观赏者。因此,我们的影视剧创作应该是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受众获得心灵的震撼和净化,在审美愉悦的过程中得到情感的感染和向上的力量。影视剧观赏可以成为社会性美育最为便捷、也最为有效的途径。
观赏文明;影视剧观赏;情感化效应;社会美育
“观赏文明”的提出,是对精神文明内涵的充实与具体化。当然,观赏文明只是精神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当下,随着艺术观赏的日益普遍化,人们在观赏过程中得到情感体验。艺术观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占有的份额越来越大,社会和家庭环境中的审美教育成为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关于美育,已有为数众多的研究成果,单纯谈论美育,对于当代精神文明建设和美学理论,都没有什么裨益。而从美育的角度来理解观赏文明,无论是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实际提升,抑或是对于美学理论的发展,都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观赏文明古已有之,而且中国和西方有着各自的观赏文明传统。但在大众传媒成为人们主要审美方式的今天,观赏文明一方面应该具有自觉的理论建构,另一方面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应该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
观赏文明关涉到的对象领域其实有很多,诸如文艺演出、美术展览、体育赛事等等,而影视剧的观赏,则是当代人们最为普遍的艺术观赏方式。美育是国家的教育方针之一,学校美育是学校教学计划的组成部分,那么,学校之外呢?社会与家庭,其实更应成为更为广泛、持久的美育场所。这是因为:美育对于人来说,不能止于学校,而是终其一生的教育方式。学校美育,更多的还是有计划的、自觉的、带有某种灌输的痕迹,而在社会和家庭环境里,美育则是不自觉的,带有普遍性和娱乐性。影视剧的观赏,是社会美育的主要途径,但它的实现,往往都是在工作之暇的放松情境下进行的,而且是抱着愉悦自己的态度。这种情境下获得的美育效果,恰恰是潜移默化的。这样,影视剧作品作为审美对象的内容和艺术效果,对于受众来说,就十分重要。“寓教于乐”是关于教育或美育的老生常谈,对于影视剧的观赏来说,这也许远远不够。影视剧作品作为社会的精神产品,其品味的高下,艺术水准的优劣,会直接作用于受众的心灵。因此,当我们将观赏文明与美育作为议题时,影视剧观赏自然不容忽视。
影视剧成为大众主要的娱乐方式,是不可避免的,这与图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日益强化的趋势相关。这里所说的图像,自然不是以往时代艺术家们创作出来的视觉艺术作品,而是凭借当代的大众传媒,通过电子等高科技手段大批复制生产出来的虚拟性形象。[1]在日常生活中,图像越发地突显出其重要位置,成为消费文化发展的中心。
所谓“审美化”,德国的韦尔施讲它源于人类的形式感觉和形式情愫,指的是用审美因素来装扮现实。随着传媒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审美化发生了改变,由物质的审美化转向了非物质审美化。因此,审美化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首先,锦上添花式的日常生活表层的审美化;其次,更深一层的技术和传媒对我们物质和社会现实的审美化;其三,同样深入的我们生活实践态度和道德方向的审美化;最后,彼此相关联的认识论的审美化。[2](P.40)
在韦尔施看来,审美化最终的结果是对现实产生新的认知,技术和传媒所带来的审美化在这一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此时所言的审美化,归根到底是指虚拟性。韦尔施注意到图像的产生是有选择性地采取素材,而非现实的纪实见证,因此,现实是图像的供应商,图像呈现的是虚拟性的现实。所谓虚拟性,是对现实的一种特定的审美把握。正是由于虚拟性,人们对于现实的单纯建构、现实的存在模式及现实的认知发生了改变。这种意识的建构,已经远离了现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真实状态并不等同,这也正是博德里亚所言的“超真实”。
但是,不同于博德里亚,韦尔施为图像的虚拟性进行了辩护。他指出,真正审美化的文化是具有高度敏感性的,它对差异和被排斥的事物是很敏感的。“首先,(真正的审美化,笔者注)不是光沉浸在艺术形式和设计的关系之中,而是同样关注日常生活,关注生活的社会形式……不是那种艺术的愉悦,而只是契合当今现实的一种反思的审美意识,才提供了同样也能具有社会内涵的情感性潜质。其次,它的结果不是被直接理解,而是被间接理解的。但是,通过艺术条件和生活条件的相似性,有可能发生的是审美情感向社会问题的转化。”[2](P.43)能够对审美化做出如此判断,在于韦尔施对认知的审美化并没有持消极的态度。他承认相对于现实世界,审美世界是一种特定的悬置状态。可对此他又进行了恰当的修正,在他看来,我们的认知和我们的现实在最初就含有审美成分,没有审美化就没有我们的认知和现实,这是它们本来的存在模式。麦克卢汉讲“媒介即信息”,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对此解释,认为信息在此应理解为隐喻,即媒介是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定义现实的。就韦尔施的分析,认知也是隐喻,从认知的隐喻再转向图像的虚拟性,这一角度并不新鲜,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也有相似观点。但韦尔施的不同在于,他将图像的审美化提升到一定高度,是“反思的审美意识”,关注的是与受众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而且审美化通过审美情感影响受众,提出“审美化通过它的情感化效应,可以干预社会过程”的命题。技术与传媒审美化的这一潜能,促使信息和行动之间的关系不再抽象而疏远,信息-行动比*“信息-行动比”,参见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书中他谈到当电报出现后,大量的信息便随之产生,人们了解的信息不再具有影响行动的价值,不同于口头文化及印刷术文化盛行的时代,所以信息-行动比失衡。可趋向于平衡。所以,韦尔施对审美化并不持批判的态度,核心就在于情感化效应。
情感化效应的出现,在于在影视剧的观赏过程中,人们不再采取传统艺术所具有的观照的审美态度,虚拟性消解了欣赏者与审美对象之间的距离感,欣赏者融入到对象中。就此,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中有详细地阐述:
梦境最值得注意的外在特征就是作梦的人总是居于梦境的中心……可以说,他与各个事件的距离都相等。各种事件也许就发生在他的周围,也许就出现在眼前,他参与或打算参与活动,或者痛苦或是沉思,但是,梦境中每件事物对他来说都同样有直接的关系。
这种美学特征、与我们所观察的事物之间的这种关系构成了梦的方式的几个特点,电影采用的恰恰是这种方式,并依靠它创造了一种虚幻的现在。就其与形象、动作、事件以及情节等因素的关系而言,可以说,摄影机所处的位置与作梦者所处的位置是相同的。[3]
在苏珊·朗格看来,在拍摄中,摄像机是导演的眼睛,而到影片观赏阶段,摄影机又成为了观众的眼睛,观众变成为作梦者,观赏如同做梦。苏珊·朗格对此看得十分透彻,电影之所以能比喻为梦境,在于逼真性,二者在时空的表现方式上很相似:在空间上,电影不同于舞台上的戏剧,没有固定的空间框架,它是从属性的幻觉,忽隐忽现,是随事件的发展而变化的;在时间上,影片中镜头闪回的节奏丝毫不输于我们的思维,意象的展示便是思维在银幕上的投射,呈现的是我们内心的生活。无论是做梦还是观影,眼前的一切都是如此逼真,仿佛置身于现实之中。
但是,尽管逼真性的存在,苏珊·朗格仍明确地指出电影的观赏不等同于做梦,或者称之为“客观化的梦”。这是因为情感在电影中所发挥的作用与梦境有所不同。就创作上来讲,电影是情感的符号,画面、音乐、声音等手段都围绕着情感,巧妙地安排在一起,保持故事的连续性。如电影镜头的剪辑,有学者在研究香港动作片的剪辑方式时提出“三镜头法”,就是演员在打斗过程中,当身体触碰时一定要完整地呈现在画面,从而保持画面的真实,成功地调动观众的情绪。这自然有利于整部影片的欣赏,如影片《叶问2》中叶问与洪震南的圆桌对决,观众看得目瞪口呆,全身心地投入,并成功地进入故事中,追随故事的发展。在观赏中,审美对象是自主的,观赏者能够意识到情感被左右,苏珊·朗格早于韦尔施关注到情感化效应,只不过她仅仅将电影作为了研究对象。
对于情感化效应的大段阐述,目的是说明影视剧,作为大众的主要娱乐方式,是如何作用于观赏者的。从这一角度而言,我们的影视剧创作,应该是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受众获得心灵的震撼和净化为追求的。通过影视剧的观赏,受众会在审美愉悦的过程中得到情感的感染和向上的力量。而这种效果不是通过理性的方式,而是以满足受众的审美需要的方式产生的。这就需要创作者很好地处理影视剧作品中的艺术性与娱乐性。若作品仅仅追求艺术性,那就曲高和寡,没有收视率或票房,在传播过程中也不会产生效应。若作品以放弃艺术性为代价,一味偏向娱乐,或许赢得收视率或票房,但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自然招来批判。
作品中艺术性与娱乐性二者的平衡,直接关系着美育的发展水平。从社会学上讲,当民众摆脱了过去普遍存在的生存压力后,每个个体便面临着行为抉择,而这时没有选择的模范或规则可依,内心体验便成为选择依据的首要因素。娱乐成分是内心体验的需要,费斯克就指出,“快乐之所以是有快感可言的,只是因为它是由体验到快乐的大众生产出来的,它不是从外部传送给人民的”。[4]优秀的影视剧作品都会顺应观众的需求,满足大众的娱乐欲望。如像《媳妇的美好时代》《幸福来敲门》《喜耕田的故事》,对于普通老百姓家长里短、争风吃醋、油盐酱醋的世俗生活描述,在电视剧《永不磨灭的番号》《亮剑》《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男主人公自身行为霸道、言语粗俗等缺点的展示。然而,这些作品在娱乐观众的同时,或是传递出积极向上、乐观昂扬的生活态度,使欣赏者感受到平淡生活中最朴实真挚的人情美;或是通过塑造的真性情英雄,激发观众自身对国家、对人民的热爱及奉献精神。这些作品中的娱乐,我们不妨看作是艺术欲望,它不是专为观众的消遣而设置,是为了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呈现出生活的多面性,使作品意义更丰富。可见,娱乐性与艺术性的和谐融洽,是影视剧艺术在当下发展的时代特征。
美育作为特殊的教育方式,当然是以人们乐于投入的心情和对愉悦的渴求来进行的。当代的影视剧通过大众传媒的渠道对于绝大多数的人群产生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因而是当代美育最为便捷的、也颇为有效的方式。在于受众本身来说,观赏也许更多的是一种自发的或者是休闲的状态,不同于政治学习和科学研究的理性和自觉的状态,然而唯其如此,观赏活动才能获得最佳的效果;而对于社会性的美育来说,影视剧观赏也成为最为方便、也最为有效的途径。因此,重视影视剧观赏和当代美育的关系,是美育理论的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内容。
[1]张晶.图像的审美价值考察[J].文学评论,2006,(4).
[2][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M].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3][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刘大基,傅志强,周发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480.
[4][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王晓珏,宋伟粟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57.
EmotionandTaste:TheCoreoftheFilmandTVDramaAppreciationForAestheticEducationoftheAudience
MENG li
(School of Literature,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the film and TV drama’s appreciation,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authenticity in images results in a “super-real” appearance, which is to bring people a false sense of what the life is. Therefore, film and TV drama can make a great impact on the audience’s behavior, especially through emotional effects.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realize the influence of the appreciation of film and TV drama. At the same time, we need to make the appreciation an appropriate way for aesthetic education.
watching-appreciation civilization; film and TV drama appreciation; emotional effects; aesthetic education for society
2013-03-29
孟丽(1983-),女,山东曲阜人,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I01
A
1674-2338(2013)04-0092-04
(责任编辑吴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