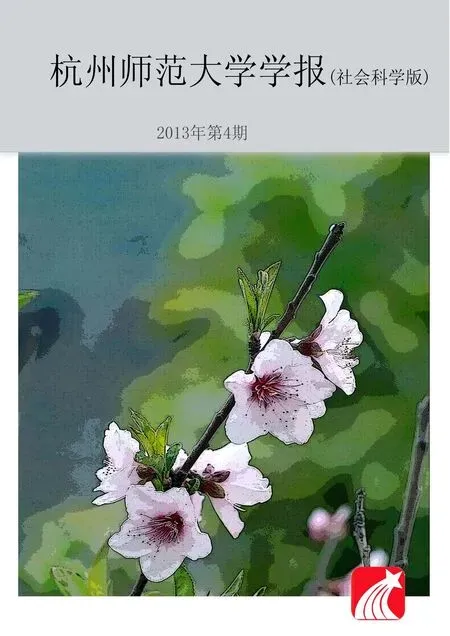从“生活美育”建成“观赏文明”
——如何走向审美化的“文明生态”
2013-04-12刘悦笛
刘悦笛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文艺新论关于“观赏文明与审美教育”的讨论
从“生活美育”建成“观赏文明”
——如何走向审美化的“文明生态”
刘悦笛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21世纪当代中国的新美育,既要理论上回归“生活美学”,倡导一种崭新的“生活美育”,而且也要在践行上走向一种革新的“观赏文明”,最终其整体的目标就是构建一种审美化的“文明生态”。审美不仅是一种“文明素养”,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人权”。“观赏文明”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的感性标志,要从“观赏文明”的建构来走向一种审美化的“文明生态”。“文明生态”不是“生态文明”,前者是基础性自然与人类环境的良好基础,而后者则是以前者为基础的更高的文明性的理想形态。
生活美育;观赏文明;文明生态
21世纪当代中国的新美育,既要理论上回归“生活美学”,倡导一种崭新的“生活美育”,也要在践行上走向一种革新的“观赏文明”,最终其整体的目标就是构建一种审美化的“文明生态”。
一 从21世纪的“生活美育”谈起
简单说来,“生活美育”就是,一切的美育形式最终都要回归到生活当中来得以实现。关于这种崭新的美育观建构,笔者在《走向生活美学的“生活美育”观——21世纪如何建设中国的新美育》[1]一文中已有详细论述,在此恕不赘言。“生活美育”的基本目标,是将大众塑造为“生活艺术家们”,使他们积极地向感性的生活世界开放,善于使用艺术家的技法来应对生活,并将审美观照、审美参与、审美创生综合起来以完善生活经验。
与旧美育观相比,“生活美育”起码具有如下三种新的特征:首先,“生活美育”不仅是艺术教育而是“文化教育”;其次,“生活美育”不再是他人教育而是“自我教育”;再次,“生活美育”不只是短期教育而是“终生教育”。由此看来,蔡元培先生所区分出来的学校美育、家庭美育与社会美育都要回归生活来贯彻实行,这就更涉及到建构中国化的“审美文明”的大问题。
对于中国的普通民众而言,谁不想生活得更美好呢?所谓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起码应该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好的生活,二是美的生活。好的生活是美的生活的现实基础,美的生活则是好的生活的高度升华。好的生活,毫无疑问就是有质量的社会,所谓衣食住行用的各个方面都达到了一定水平,从而满足民众的基本物质需求;而美的生活,则有更高的标准,因为它是有品质的生活,民众在这种生活方式当中要获得更多的精神愉悦。无论是有质量的还是有品质的社会,它们最终都指向了幸福的生活。民众既可以从物质满足当中获得满足感,更可以从文明满足那里获得幸福感。
在中国民众不断有更多机会目睹诸多文化的时候,展览的举办、演出的发生愈加增多,观众源源不断涌入大小剧场、电影院线及博物馆、美术馆欣赏、观看并与艺术品互动,甚至参与到艺术的创作中去,但是,不文明的观赏现象却大量地出现了。这样,从“文明观赏”到“观赏文明”的议题就逐步走入人们的视野。多年以来,大多数人仍将这个议题误解为仅仅停留在文明层面,但恰恰最不应缺失的“审美文明”的视角却被无情地忽视了。
二 从“文明观赏”到“观赏文明”的飞跃
从“文明观赏”到“观赏文明”,这是一个“文明的飞跃”。“观赏文明”绝不仅仅等同于“文明观赏”,而是更高层级的“文明建构”。我们可以浅显地看到,前一个文明的层次较高,后一个文明的层次较低。更纵深地来看,在“观赏文明”更着重于观赏时不越界的文明礼仪(polite)的同时,“观赏文明”将其中的“观赏”定义为一种文化载体,而“文明”则赋予这种文化以一种恒定的价值,“观赏文明”的外延既包含着“文明观赏”,又远远超越了“文明观赏”的内涵。这可追溯到中国作为“礼乐之邦”之时的文明传统,既有“文明观赏”之气度,又秉承“观赏文明”之涵养。我们需要再次继承并振兴中国作为“礼乐之邦”的文明传统,建设一种具有现代化的“观赏文明”。
“文明观赏”主要言说的是,在某位与某些接受者进行文化与艺术欣赏的时候,所需要遵守的基本的“文明礼仪”。这些文明礼仪,恰恰折射出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与“文化状态”。在此,文明并不仅仅是精神的,在中文当中“精神文明”往往是被联用的。其实,精神往往是内在的心灵状态,它需要以外化的形式被展露与表征出来,并不是表面上说出“我很文明”,那么,我的行为就走向文明了。
文明的内在构成是精神的,但还需要通过人们的行为、态度与活动表现出来,如此一来,才能使得全社会的文明得以显露性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由于过于讲求“内心”的修炼,往往忽视了“修身”的外化问题,其实真正理想的“文明状态”恰恰需要在内与外之间达到一种平衡状态。
所以说,我们极力呼吁建设一种中国化的“观赏文明”。我们如今的“文明观赏”的规范基本上是来自西方文明的,但是,我们需要建构一种适合于中国文明的“观赏文明”。
“观赏文明”无疑是个新词语,将观赏与文明组合起来,这也恰恰是中国文化的新的建构。“观赏文明”之“观赏”也是个中国词汇,但在美学中,它是对英文的Appreciation的汉语翻译,同时也可以翻译为“鉴赏”、“欣赏”之类。然而,“观赏”的意蕴却更为丰富与全面,它是“观照”与“欣赏”的合体。一方面,观赏之“观”,乃观照之“观”,它不仅仅是诉诸于视觉的,抑或单单诉诸于听觉的,反而强调的是全方位的参与,也就是对某一文化与审美场景及场域的全方位的参与。另一方面,观赏之“赏”,乃鉴赏之“赏”,它不仅仅是静观式的被动参与,而且还是一种积极的审美品位,“赏”不仅指向了一种“欣赏”的审美,而且指向了一种“赏析”的审美理解。
进入到21世纪的今天,美育与文明的关联之间,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美育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早在1917年,蔡元培就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以美育代宗教说》一文。这个在近代中国产生的著名的“美育代宗教”的观念,从比较文明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看,世界上只有蔡元培先生将美育提升到如此“文明高度”的地位。1985年,整个美国教育界在该年度进行了“全美艺术教育现状”的广泛调研,在此基础上,美国政府在1988年发布了《走向文明:艺术教育报告》,指出今日美国的文明问题就在于“缺乏艺术教育”。
所谓“美育”,顾名思义,就是“育美”,具体来说,就是“育人之美”。美育作为最广义的“感性教育”与“情感教育”,在人类的基本智能当中构成了基本的组成部分。美育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它帮助民众获得发展全部人性的可能,也是人类认识发展中的关键,是人类理解力的基本构成。美育首先发源于创生感情的感性动力,逐渐感知而后形成了对实践活动和文化创新都非常必要的象征系统。因此,一种综合的美育纲领要求发展艺术实践和审美经验,以促进欣赏和理解的能力。
美育的“育人”的基本功能,在西方美育研究者的眼中主要可以归纳为:首先,美育的首要价值在于欣赏艺术美,培养人的情思与意趣;其次,美育培养了人们的审美眼光,由此可以以积极方式改造自身与世界;再次,美育有助于从“人文教育”的角度培养“批判思维”;最后,美育可以提高人们对文化多样选择的尊重与理解。所以,美育可以成为推动人类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有机动力,这无论对于中国还是西方社会而言,都是如此。
总之,审美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文明素养”,因为审美作为人类基本智能的泛化性的成分,可以成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是其中的感性化而非理性化的基本因素。
三 审美既是“文明素养”,也是“文化人权”
审美不仅是一种“文明素养”,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人权”。在这里,文明是与“野蛮”相对而言的,文化则是与“自然”相对而言的。逃离了野蛮,人类才能“走向文明”;告别了自然,人类才能“拥有文化”。
进而,文明与文化还有个重要区别,那就是,“文化”(culture)一词的词源是由其本身的“耕种”意愿所昭示出来的,文化本身应该是“自然生长与生发”出来,并且具有一定的“土著性”。也就是说,某种文化尽管可能最终达到全球化的程度,但最终都是从某个特定时空里面生长与生发出来的。“文明是被构造出来的。它并不需要像树木一样被种植出来。每个人都赞同文明的进步已经变得加速,但是这并不十分有利于文化的生成”,[2](P.61)这也道明了文明与文化之间的发展未必都是同向的,但是如果二者保持基本方向一致,那就会走向更为理想的状态。
在全球化文明得以飞速进展的时代,文化本身仍需要得以保护,当今中国理应倡导一种“公民美育”与“社会美育”来保护文化的成长。
首先,“公民美育”是说,审美能力应该成为公民的基本素质之一,审美本身也是一种人权,属于人的最基本的权力。将文化当作一种“人权”(human right),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1年编辑出版的《自由与文化》当中进行了系统阐述的观点。[2]这种观点的理论基石,就是《世界人权宣言》是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12月10日通过(联合国大会第217号决议,A/RES/217)的一份旨在维护人类基本权利的文献,它也是有组织的国际社会第一次就人权和基本自由作出的“世界性宣言”。
这份《世界人权宣言》里面,集中论述了文化艺术的有两处:一处是总体上的规定(第二十二条),“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这种实现是通过国家努力和国际合作并依照各国的组织和资源情况”;另一处则是具体的言说(第二十七条):“(一)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二)人人由于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
这就说明,无论是接受文化艺术还是创造文化艺术,都应该被纳入到人权的体系当中,并要得以更高层面的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自由与文化》里面,在“文化是一种人权”的总论之下,分别论述了两类权力:一类是从接受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受教育权利”(the right to education)与“获得信息的自由权”;另一类则是从创造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文学与艺术创作、艺术研究所应当获得的权利,其中的重点就是“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问题。
然而,问题在于,关于人权的文化艺术部分,不仅仅要去保护创造者的权利,接受者们的权利也要得到保护,而且,接受者较之创造者而言,无疑占有数量上的大多数。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世界人权宣言》里面就强调了享受艺术与分享社会生活那是“人人有权自由”参与的,由此,审美同样也是一种“文化人权”。但更深层的问题是,即使提供给民众大量丰富的文化艺术作品,却未必能够被人们所接受。这就需要继续进行美育工作,因为没有相应的“审美素质”的人群,即使面对好的文化艺术作品也不能参与其中,这就需要在保证审美作为人人分享的权利的同时,推动民众“审美文明”基本素养的培养。
其次,“社会审美”是说,审美要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感性尺度”,就像保护环境只是个伦理诉求,但是环境是否美化则是更高级的标准那样,审美是社会发展的高级尺度与标杆。
实际上,审美不仅可以成为衡量环境优劣的高级标准,而且,也成为“衡量我们日常生活质量的中心标志”。[3]“让世界更美好”(making the world better),成为当代美学家们内在的基本吁求。然而,当美学家们都承认美学拥有改变世界的能量时,他们的潜台词几乎都是在说:并不是所有的生活都可以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审美化的生活”才能成为改变世界的高级标尺,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美学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就将审美作为“社会进步”的标尺,审美同样也是生活品质的基本标准。在这个意义上,审美也可以成为一种“社会福利”。将文化艺术当作一种社会福利,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由此出发,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更细化的分析。文化与艺术尽管都是社会福利,却不是一样的社会福利。比如说,公共艺术所提供给大众的福利,不是一般的“文化福利”,而应该是“审美福利”(aesthetic welfare)。
究竟什么是“审美福利”呢?“审美”本身怎么就能变成福利?实际上,“审美福利”这个说法最早是由美国分析美学家门罗·比尔兹利(Monroe C. Beardsley)提出的。他在《审美福利、审美公正与教育政策》(Aesthetic Welfare, Aesthetic Justice, and Educational Policy)一文中指出:“在某个处于特定时期的社会当中,审美福利是由特定时期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全部审美经验水平来构成的。”[4]比尔兹利的这篇文章收入到了《公共政策与审美兴趣》(PublicPolicyandtheAestheticInterest)的文集当中,这部文集关注到了审美公共性的政治问题。由此看来,诸如社会上所提供的审美产品理应成为“普遍福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面,因为它会直接同时影响到公众的生活品质的提升抑或降低。所以从这个新的角度来看,这些审美产品作为一种“审美福利”,就要一方面取决于公众的“审美体验”的水平,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公共艺术品本身的“审美价值”,通过审美产品与公众之间的良性循环,才能逐渐累积成为当代社会的“审美财富”(aesthetic wealth),从而为广大的公众所共享与分享,这就是“社会美育”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
从政府职能的实施角度来看,要把社会上的审美供给作为一种“公共文化服务”。从接受的角度来看,这些产品要被视为一种“审美福利”,在这种审美福利的提供者那里,政府就应该充当重要的调控角色。过去我们的社会美育建设,采取了“大政府、小社会”的基本模式,现在应该反过来,采取“大社会、小政府”的崭新模式,社会各个群体与机构理应更多地积极参与美育活动。这也意味着,政府在公共艺术建设中,应在管理方面走向宏观的调控,在服务方面走向微观的提供。
四 总体目标:走向审美化的“文明生态”
“观赏文明”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的感性标志,我们要从“观赏文明”的建构走向一种审美化的“文明生态”。“文明生态”不是“生态文明”。我们要在“生态文明”的基础上来建设一种“文明生态”,前者是自然与人类环境的良好基础,而后者则是以前者为基础的更高的文明性的理想形态。
“生态文明”是一种自然生态和谐的文明,而文明生态则是非自然意义的,主要是对于人类当代文明状态的文化学的规定。当代的生态学概念已经摆脱了生物学的意义,从而成为可以用以理解人类与其文化环境关系的基本概念,这就构成一种新型的“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
由这种视角来反思人类的生活,它的研究视野,就早已超出了传统生物和地理意义上的自然,而更为关注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类生态系统”(human ecosystem)。这样,生态学所强调的有机体依赖于生态系统的基本模式,同样适用于人类有机体,从而可以认定,作为自然存在的人类与自然中的其他部分是处于连续性(continuity)当中的。这无疑是一种更接近东方智慧的观点。由此,“文化生态学”就被赋予了更为广阔的理解,因为它意味着一种包罗万象的“环境语境”,无论是有机的还是无机的要素、社会的还是文化的要素都相互依存、彼此互动,从而形成了一种持续的平衡与平衡的持续。
这种最新的理念,其实来自西方生态学家阿恩·奈斯(Arne Naess)关于“深度生态学”(Deep Ecology)的观念。以往那种强调了生态保护的“生态文明”思想,仅仅是所谓的“浅度生态学”(Shallow Ecology)。由于保护环境,所以浅度生态学就需要改造现有的价值观念与社会体制,如所谓“绿党”就从事类似的实践;然而“深度生态学”则主张要去重建“人类文明的秩序”,从而使文明成为自然整体当中的有机构成部分,而且,其本身就拥有了“文化生态”的基本特质。
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生态学”就成为一种广义的“深度生态学”,而且,理应成为一种“全景生态观”。“全景观生态观,即‘全生态观’,是人文生态、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的统称,是探讨人与人类环境、人与社会环境和人与自然环境三者关系的一种思考框架。这种全景生态视角可作为中国传统‘天地合一’思想的当代转译。所谓‘天、地、人’其实就是‘自然、社会、人类’的简称。”[5]从中国本土思想出发,就可以看到,“全景生态观”恰恰是我们建设具有中国化的“文化生态”的核心,它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社会、他人的和谐关联,强调的也是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联。
[1]刘悦笛.走向生活美学的“生活美育”观——21世纪如何建设中国的新美育[J].美育学刊,2012,(3).
[2]Unesco.FreedomandCulture[M]. London: Wingate,1951.
[3]阿诺德·伯林特.环境美学[M].张敏,周雨译.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06.55.
[4]Monroe C. Beardsley. Aesthetic Welfare, Aesthetic Justice, and Educational Policy[C]//Ralph A. Smith, Ronald Berman.PublicPolicyandtheAestheticInterest.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2.42.
[5]约翰·霍金斯.创意生态[M].林海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1.12.
TheConstructionofWatching-AppreciationCivilizationfromLivingAestheticEducation
LIU Yue-di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00732, Beijing)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new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we need present a new concept of Living Aesthetic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ving Aesthetics in theory.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need to be oriented to constructing a kind of appreciation civilization. In the end, we regard the Ecology of Civilization as our social goal, and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aim of Eco-civilization, while the latter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the former on a new mode of human civilization.
living aesthetic education; watching-appreciation civilization; ecology of civilization
2013-03-29
刘悦笛(1974-),男,辽宁锦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国际美学协会五位总执委之一、中华美学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美学、文化与比较哲学研究。
I01
A
1674-2338(2013)04-0087-05
(责任编辑吴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