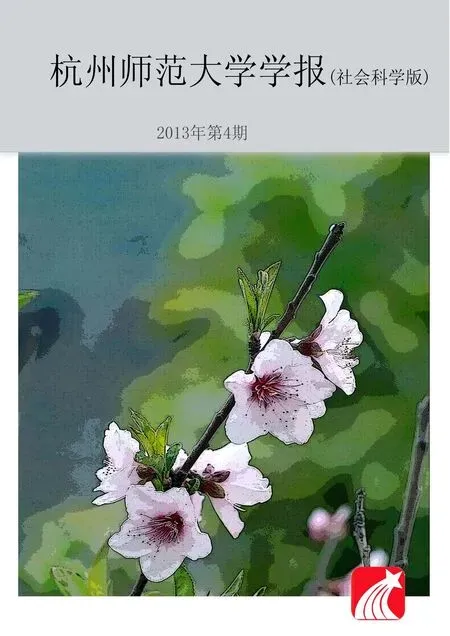人文理性:周作人所倡“科学”的实质内核
2013-04-12黄江苏
黄江苏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文学研究
人文理性:周作人所倡“科学”的实质内核
黄江苏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周作人对“五四”时期的主题话语之一的科学,保持着疏远和警惕的态度,因为那时候他专注于文学的园地,强调人文艺术对人类精神的独特价值。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他内心发生“由情转智”的变化以及与革命文学的论争以后,“科学”成为他最看重的文章主题。他把科学的源头上溯到原始儒家的“疾虚妄”与古典希腊的“爱智慧”精神,实际上是人文理性的立场。这种主张人间生活伦理须以科学知识为本、科学理性又必须合乎人间生活之用的立场,强调“常识”的精神,对于科学工具理性的迷失与当今社会玄虚乱象的匡正,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
周作人;科学;人文理性
一 科学的边界与人文理性的定义
科学是“五四”时代风云里矗立着的两面大纛之一。然而,“五四”时期中国提倡的“科学”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科学”?丹皮尔对“科学”的解释是:“拉丁语词Scientia(Scire,学或知)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是学问或知识的意思。但英语词‘science’却是natural science(自然科学)的简称,虽然最接近的德语对应词Wissenschaft仍然包括一切有系统的学问,不但包括我们所谓的science(科学),而且包括历史,语言学及哲学。”[1]“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像陈独秀、胡适,并非自然科学家,他们坚定地标举自己的“科学”立场,都是取上述的拉丁语词、德语词中那个宽泛的“科学”的含义。陈独秀在1920年写的《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说:“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2]他们对科学有全盘的认识,对于自己的定位也很明确,那就是主要在人文社科领域里下工夫。例如胡适写有《实验主义》《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等文章,提倡在哲学研究、整理国故等学术事业中运用科学方法。在1923年张君劢等人用“人生观”的名义向科学发起挑战时,他们都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分别亮出“唯物的历史观”、“自然主义的人生观”,[3](P.7,23)来捍卫科学在这方面不可动摇的合理性。罗志田认为,五四人“讲‘科学’甚少往‘技术’方向走,讲到西方的物质一面时也往往提高到‘文明’层次”,“五四人更注意的是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在实践层面更首先落实在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以及史学的‘方法’之上”,这跟中国传统“重学轻术”的思想倾向有关。[4]这也是一种很有参考价值的观点。
与陈、胡等人一样,周作人所提倡的科学,其实质内核并非是通常对应的科学——技术理性,而是人文理性。人文理性,简而言之,可以说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的结合形态。它是与一般所称工具理性、历史理性相对的一种说法,对此王岳川教授较早有过论述,他认为工具理性带来的科技力量和历史理性推动的政治操控,都在带来利益的同时带来了巨大伤害,人类急需建立人文理性,它不仅是人文价值、人文关怀,更是理性的思索与反省。[5]还有学者认为,人文理性是认知理性、实践理性、价值理性、交往理性等的总称,是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的中间环节,是人们认知、批判、选择和创造人文价值观的能力。[6]朱德发教授也曾撰文论述现代文学创造中的“人文理性精神与主体人本艺术思维”的关系,[7]并指出早在严复那里,就曾发出过“西人谓一切物性科学之教,皆思理之事,一切美术文章之教,皆感情之事。然而两者往往相入而不可强分。科学之中,大有感情;美术之功,半存思想”的呼声。[8]周作人可以说是严复这一先声的回响,仔细分析周作人所提倡科学的实质内涵,其主张科学不可凌夷文艺,而人文关怀、伦理价值也须得以合乎科学理性为基础的思想,正好高度契合“人文理性”的定义,而且考察其思想发展过程,有一条分明的从偏重人文到转倡理性,再到人文理性的融合的明线。详细阐述周作人这一思想,对于今天的人文精神建设仍然是大有裨益的,故以下分而述之。
二 情理分殊:人文立场对科学霸权的警惕
“五四”乃至20世纪20年代前期,周作人标举“科学”的文字并不算多,比较明确的只有那篇曾归到鲁迅名下的《随感录三十八》。其中说,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9](第2卷,P.73)科学精神的提倡不是这时期他工作的重心,对于热热闹闹的“科玄之争”,他完全置身事外。这个时期,他除了沉迷于新村运动,最主要的工作是致力于文学写作,耕种“自己的园地”。以是之故,在他的心底里,重文学、“防”科学的倾向比较明显。
为什么说“防”科学呢?周作人并不反对科学,这是必然的。胡适曾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3](P.9)胡适的话里已隐然透露出科学掌握着“霸权”的信息。周作人所防备的,就是科学过度的“霸权”,防备科学过度僭越而压制文学的生命。更进一步说,就是警惕理性对情感的压制。他曾说:“我们平常专凭理性,议论各种高上的主义,觉得十分澈底了,但感情不曾改变,便永远只是空言空想,没有实现的时候。真正的文学能够传染人的感情,他固然能将人道主义的思想传给我们,也能将我们的主见思想,从理性移到感情这方面,在我们的心的上面,刻下一个深的印文,为从思想转到事实的枢纽:这是我们对于文学的最大的期望与信托。”[10](《苦雨斋序跋文》,P.16)所以他经常将“科学”与“艺术”并举,声明两者都不可偏废。1924年他在《狗抓地毯》中说:“科学之光与艺术之空气,几时才能侵入青年的心里,造成一种新的两性观念呢?”[10](《雨天的书》,P.100)1927年他在《香园》中又说,“中国人落在礼教与迷信的两重网里,永久跳不出来,如不赶紧加入科学的光与艺术的香去救治一下,极少解脱的希望。”[10](《谈龙集》,P.85)在不可偏废中尤其强调不能用科学的名义取消文学(或者是艺术、情感)的地位。1922年他在《文艺上的异物》中说:“科学思想可以加入文艺里去,使他发生若干变化,却决不能完全占有他,因为科学与艺术的领域是迥异的。”[10](《自己的园地》,P.30)《真的疯人日记》里有一段讽刺那些“用显微镜考察人生的真义”的学者。[10](《谈虎集》,P.377)1923年发表的《镜花缘》,他再次表达了对“用纪限仪显微镜来测看艺术”之人的抗拒,称许P. Colum所说的“对于减缩人们想象力的一切事物——对于凡俗的都市,对于商业的实利,对于从物质组织所发生的文化之严厉的敌视”,并由此称许《镜花缘》和王尔德童话中的“说诳”。[10](《泽泻集》,P.9)在1925年写的《唁辞》中,他甚至为希冀死后生活这样的“迷信”辩护:“我确信这样虚幻的迷信里也自有其美与善的分子存在。……可惜我们不相应地受到了科学的灌洗,既失却先人的可祝福的愚蒙,又没有养成画廊派哲人(Stoics)的超绝的坚忍,其结果是恰如牙根里露出的神经,因了冷风热气随时益增其痛楚。对于幻灭的现代人之遭逢不幸,我们于此更不得不特别表示同情之意。”[10](《雨天的书》,P.22)科学取消文艺及与文艺相关的想象、情感,会造成幻灭的不幸,而避免这一点的出路也只有相对地维护文艺及与文艺相关的这些事物,所以周作人在《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中说:“人间所同具的智与情应该平匀发达才是,否则便是精神的畸形……我相信对于精神的中毒,空想——体会与同情之母——的文学正是一服对症的解药。所以我推举这部《漫游奇境记》给心情没有完全化学化的大人们。”[10](《自己的园地》,P.56)
周作人这样的态度与乃兄鲁迅非常相像。五四时期鲁迅也写过专谈科学的文章,例如《随感录三十三》,但是数量不多,似乎只是时代大合唱中的配合式发声。郜元宝在分析他写于1907年的《科学史教篇》这篇文言论文时,认为“恰恰是这篇专门讨论科学问题的论文,标志着鲁迅的短暂的科学时代的结束,以及他持守一生的文学生涯的开始”,因为在这篇论文里,鲁迅已经超越了肤浅地追求科学的枝叶的阶段,而致力于探求西方科学发达的“深因”、“本根”、“本柢”,也就是科学背后的精神之奋发、心灵之自由等总名之曰“神思”的事物。而鲁迅在编辑《坟》的时候对早期四篇文言论文的编排,更体现出一个完整的思想构造:在《科学史教篇》之后继以《文化偏至论》,指出科学发达的西方到了现代,已经出现“重物质而轻精神”之类的弊端,“立人”——尤其是“立心”,培育人的“内部之生活”已经成了当务之急。接下来便以《摩罗诗力说》阐释了以文艺“涵养神思”的方案,未完成的《破恶声论》更是一次为“迷信”辩护的具体文学实践。[11]参照鲁迅这样的思想历程来看,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及20年代前期对待科学的态度就像是兄长思想的一次迟到的翻版。他的科学与艺术并举的观点就像《科学史教篇》里谈科学兼谈神思,他在《唁辞》里讲科学带来的精神寄托的幻灭就像《文化偏至论》,而《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思路同步于《摩罗诗力说》。周氏兄弟早期思想的一致,尤其是周作人亦步亦趋于鲁迅(去南京,去日本,从事译书等文学运动都受到鲁迅的影响),这又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说起来,鲁迅和周作人都是学“科学”出身,鲁迅从水师学堂转到矿路学堂,到日本又进医学院,周作人则从江南水师学堂被公派到日本学建筑。他们求学和最初成名的年代,都是科学在中国日益得势终至于在知识界建立“霸权”的时候,可是他们在这时却表现出对科学的知识霸权的警惕,在中国的知识界显得非常超前。这跟他们都敏锐而全面地接触了世界思潮有关。正如鲁迅在《随感录五十四》中说的,“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各个不同时期的思潮,“都摩肩挨背的存在”。[12]他们一方面接受了西方的生物学、化学等科学教育,一方面同时接触了西方的浪漫主义等针对科学、理性而出现的反拨性的思潮(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提到拜伦、雪莱等人,还有他钟爱的尼采都有对理性的批判,周作人早期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显示他对这些人也并不陌生),因而造成了这种现象。对文艺事业的选择,更促进了他们这种对待科学的批判性立场。
三 由情转智:回溯儒家的“疾虚妄”与古希腊的理性精神
事情在1925年周作人宣布文学店关门之后有了变化。前面我已经谈到这时期周作人内心发生了由情转智的变化,发出“现在唯一的欲望是想多求一点知,尽我的微力想多读一点书,多用一点思索,别的事且不要管”[9](第4卷,P.97)的爱智宣言,甚至认同“感情是野蛮人所有,理性则是文明的产物”。[10](《谈虎集》,P.389)从这个时候开始,“科学”在周作人笔下分量越来越重,以前常常并举的“文艺”则有隐居二线的趋势。看起来,周作人似乎与时代潮流倒了过来,在众人齐论科学的时候他很超前地警戒了一番实现科学以后的弊病,等到众人都转入各自不同的行当中去了,他再后退一步来提倡追求科学。
1925年之后的几年里,周作人的文章中还没有很多地体现出读书求知的信息,倒是在1928年开始的革命文学对他的批评中,他比较彻底地意识到空有革命激情而不注重求知务实的弊端。《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中说,要促进青年的思想改革,很重要的“即是科学思想的养成。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科学思想都是不可少的”,“中国近来讲主义与问题的人都不免太浪漫一点,他们做着粉红色的梦,硬不肯承认说帐子外有黑暗。譬如谈革命文学的朋友便最怕的是人生的黑暗”。[10](《永日集》,P.98)他把这种只凭梦想提出主张的行为称为“狂信”,并认为狂信是不可靠的,刚脱了旧的专断便会走进新的专断。要破除这种“狂信”,就要提倡“理知”、“学问”,实际上就是科学。“知与信是不大合得来的”,“这须得先有学问的根据,随后思想才能正确”。[10](《苦茶随笔》,P.68)
在与革命文学的论战之后,他才真正转向“闭户读书”。从他30年代出版的第一本偏于“读书随笔”的集子《夜读抄》来看,他一开始想读的也多半是学术性的、“科学”的而非文学的书:《原野物语》《习俗与神话》《猪鹿狸》是民俗学、神话学著作,《蠕范》《性的心理》《兰学事始》是关于生物学、性心理学、医学的,此外还有《塞耳彭自然史》《金枝上的叶子》等与学术相关的书籍。从这样的选择不难看出他的用意。《兰学事始》中,他比较同时期日本与中国的医学家的研究状况,痛切地说:“中国在学问上求智识的活动上早已经战败了,直在乾嘉时代,不必等到光绪甲午才知道。”[10](《夜读抄》,P.49)如今在新的历史时期,他自然希望能通过提倡,让中国的学术事业、科学事业,能够发达起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随着买书条件的限制等原因,他读书越来越局限于中国古代的笔记。此时他更感到了提倡科学精神的急迫,因为在这些笔记里,充斥着各种乌烟瘴气的思想,让他读来气闷,更加意识到用科学精神救治的急迫性。他同时认为,这科学精神其实也并不是中国古来没有的东西,“这本来是希腊文明的产物,不过至近代而始光大,实在也即是王仲任所谓疾虚妄的精神,也本是儒家所具有者也”。[10](《药堂杂文》,P.40)
由此可见,当周作人意识到必须求助于科学才能医治时代的狂信以及历史的迷信之后,他异常敏锐而明智地将视野扩展到了中西文化的源头上去,将古希腊和所谓的原始儒家提了出来。在《过去的工作》中,他说自己很早就注意到国人谈及西方文化时,大抵只凭工业革命以后的欧美两国的现状以立论,总不免是笼统,所以他提倡为得明了真相起见,对于普遍认为的文明之源的古希腊,非详细考察不可。[10](《过去的工作》,P.82)以是之故,他极力鼓吹希腊的科学精神。《希腊人的好学》中说:“后世各部门的科学几乎无不发源于希腊,而希腊科学精神的发达却实在要靠这些书呆子们。……他们对于学,即知识,很有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态度”,“中国人如能多注意他们,能略学他们好学求知,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学风,未始不是好事,对于国家教育大政方针未必能有补救,在个人正不妨当作寂寞的路试去走走耳”。[10](《瓜豆集》,P.86)一方面他认为中国人应该学习希腊这种纯粹的求知精神,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中国并不是完全不曾有过类似的理性,在《自己所能做的》等好几篇文章中,他就曾说过,“中国民族的思想传统本来并不算坏,他没有宗教的狂信与权威,道儒法三家只是爱智者之分派”。[10](《秉烛后谈》,P.2)这其中又尤其是儒家,他本身的长处即是把古代许多迷信理性化,这是周作人早就指了出来的。[10](《谈虎集》,P.343)但是后来怎么变坏了呢?周作人在1941年的《中国的国民思想》中给出了自己的诊断,他认为一个新的因素把健全的儒家思想搞坏了,那就是考试制度。考试制度造成两大流弊,不说真话和胡说八道,“把真实的学问都阻塞了,因此中国的科学也不能发达了”。[9](第8卷,P.579)检查清楚了这个弊端,就要把坏的部分去掉,中国思想也就能重新屹立无忧,所以他说“中国根本思想是好的,不过是后来变坏了,只要再加上科学文明,就可以把固有的国民性恢复过来”。
这就是周作人对中国应该有的科学态度总的观点。他强调中国古代思想里已有科学精神,只是后来泯灭了,中国应该在固有的儒家思想基础上去发展科学,而这样做的途径又不仅仅是学习现代的西方,还应该注意西方文明源头的希腊思想中的科学精神。
四 常识与生活伦理:人文理性精神的最终落脚点
周作人在1944年写的《文艺复兴之梦》中说,“文艺复兴应是整个而不是局部的。照这样看去,日本的明治时代可以够得上这样说”,“中国近年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有了做起讲之意,却是并不做得完篇,其原因便是这运动偏于局部,只有若干文人出来嚷嚷,别的各方面没有什么动静,完全是孤立偏枯的状态”。[10](《苦口甘口》,P.20)话虽如此,周作人毕竟也还属于这“出来嚷嚷”的文人之一,“别的各方面”,因为他不是亲身参与者,有了动静他也不一定知道,或者秉持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以及“文人不谈武”之类的原则,知道了也不一定多谈。事实上,如果我们查考史书,就可以知道文艺、学术、科技等各方面在那个年代都不是空白的,而是有人筚路蓝缕历尽艰辛地开拓,即以自然科学为例,据说“从1916年起,在中国开始了以发展某种科学为目的的专门研究组织的建立,其中重要的有:中央地质研究所(1916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20年)……”也有竺可桢这样比较重要的科学家,产生过一些世界领先的科学成果。[13]周作人何以对这些罔若无睹,视科学处于“偏枯”呢?从他的许多文章来看,他批评的还是民众生活、思想领域中没有科学精神,他着力强调的最终也只是一些指导普通人生活和思想的科学“常识”,强调这些常识最终指向的又是建立合理的伦理观念。对于真正的自然科学研究的深入,是不在他的考虑范围的。
有三个问题,周作人在好些文章中反复谈到:螟蛉之子,腐草为萤,枭鸱食母。从1933年写的《蠕范》开始,到1934年《厂甸》、1935年《猫头鹰》、1936年《毛氏说诗》《螟蛉与萤火》、1944年《萤火》等等,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周作人反复不停地引用同样的材料,反复指出历史上许多儒生笃信不疑的“螟蛉有子,蜾蠃负之”不是实情,萤火虫也不是腐草化的,猫头鹰并不吃母亲。之所以为这些事情花了这么大的力气,首先是因为他从中看到了中国思想传统中的一大弊病,那就是不求甚解,缺乏求真知的精神。他说,中国人如此“观察不清则实验也等于幻想”,“如此格物,何能致知,科学在中国之不发达盖自有其所以然也”。[10](《苦茶随笔》,P.52)在周作人看来,这种“格物往往等于谈玄”的现象在中国学者中是普遍的,《毛氏说诗》一文中,他认为贵为一代宗师的朱熹,其《诗经集传》格物不精、错讹百出,被毛西河笑骂也是无怪。中国古代读书人这些不求甚解,以讹传讹,以耳为目,笃信前人的做法,其背后是头脑的糊涂与混乱,这是周作人所极力批评的。在其他领域里周作人也常为此而叹惜,例如《修辞学序》中说“文人学士多缺乏分析的头脑,所以中国没有文法,也没有名学,没有修辞学,也没有文学批评”,[10](《看云集》,P.85)《文法之趣味》中则鼓励人从文法书中训练头脑之清晰,理解之明敏。
除此之外,周作人反复地讲这三个问题,还想引出另一个意见,即是在生物学及相关科学上建立起正确的伦理观,这是一条明显的经科学——理性到达精神——人文的路径。《螟蛉与萤火》中他指出中国人拙于观察自然,又往往喜欢去把它和人事连接起来,造成错误的伦理观,例如乌鸦反哺、羔羊跪乳等,助长子女必须偿还父母债务的错误的孝道观。要救治这一点,只能求助于正确的生物学知识。周作人是个极端的生物学“粉丝”。他把中国人的许多思想问题都归结到生物学的原因上去,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在早年的《罗素与国粹》中说,中国人保守,沉迷国粹,都是“因为懒,因为怕用心思,怕改变生活”,[10](《谈虎集》,P.13)20世纪30年代写的《论泄气》进一步说:“中国人许多缺点的原因都是病。如懒惰,浮嚣,狡猾,虚伪,投机,喜刺激麻醉,不负责任,都是因为虚弱之故,没有力气,神经衰弱,为善为恶均力不从心。”[10](《夜读抄》,P.190)这种扎根于生物学的思维方式使得他极力推崇生物学知识,谈到人的生活伦理时必定用生物学比附,极力推崇与生物学相关的书籍。《蠕范》中说“读一本《昆虫记》,胜过一堆圣经贤传远矣,我之称赞生物学为最有益的青年必读书盖以此也”,[10](《夜读抄》,P.40)《百廿虫吟》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这些文章都明确指出他的生物学兴趣,并不完全出于纯粹的研究兴趣,而都是指向人的生活伦理,也即是为他后来总结的“伦理之自然化”服务的。
一方面鼓吹科学精神,希望人们格物真切,头脑清晰,另一方面又用强烈的意愿把科学直接联系到人事上去,这倒是完全符合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所分析的儒家的特点。周作人自命儒家,看来的确不是虚言。李约瑟认为,儒家中有两个根本矛盾的倾向:它的重理性,反对一切迷信,甚至反对宗教中的超自然部分,这是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但是集中注意于人与社会,而忽略其他方面,只对“事”研究而放弃一切对物的研究,又造成了科学发展的阻力。[14]周作人这种过于注重科学与人事的联系,急于从科学过渡到伦理的思想,是否也会阻碍他对科学的深入认识呢?答案是显然的。在《我的杂学》中,周作人坦承“关于生物学我完全只是乱翻书的程度,说得好一点也就是涉猎,据自己估价不过是受普通教育过的学生应有的知识,此外加上多少从杂览来的零碎资料而已”。[10](《苦口甘口》,P.72)尽管不断鼓吹科学,认为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在儒家思想之上再增加些科学精神,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成为任何一门学问里研究精深的专家,而是满足于提倡“常识”。他认为只要持之以恒讲述常识,也会对中国有益处,“我们如依据了这种知识,实心实意地做切切实实的文章……这样弄下去三年五年十年,必有一点成绩可言。说这未必能救国,或者也是的,但是这比较用了三年五年的光阴再去背诵许多新鲜古怪的抽象名词总当好一点,至少我想也不至于会更坏一点吧”。[10](《苦竹杂记》,P.200)
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他反复推重的中国思想史上的三盏明灯,他认为有着“疾虚妄”的科学精神的三个人——王充、李贽、俞正燮,在他笔下,实际上都并没有显现出多少科学精神。除了在《凡人的信仰》中写到王充的无神论思想是偏重从科学精神方面立论之外,在《读初潭集》《关于俞理初》《俞理初的著书》中,他反复称扬李、俞二人“为妇人开脱”、“平等的两性观”,实际上还是偏重于伦理方面。对李贽的“童心说”、“六经皆史”说,对俞正燮的古籍订伪考异的卓然成绩、邻邦边境的深入研究,[15]他都没有提及。在《俞理初的著书》中说:“俞理初可以算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常人了,不客气的驳正俗说,而又多以诙谐的态度出之,这最使我佩服”,其驳正俗说之处,即“能尊重人权,对于两性问题常有超越前人的公论”。[10](《秉烛后谈》,P.32)原本只是悃愊无华的学者俞正燮,被他推崇到中国思想史三灯之一,主要就是这个原因。
不仅仅生物学,其他相关的医学、性心理学以及人类学,周作人并没有把它们当作研究室或书斋里的纯粹科学知识来处理,它们都是作为周作人的“杂学”、常识之一部分,为着他心目中理想的“人的生活”服务的。这阻碍了周作人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可是这种取向却深得人文理性的精髓,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正如海德格尔揭示的那样,自近代以来有一个地球和人完全欧洲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实质就是欧洲近代以来的科学理性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然而作为其成果的技术进步,却损害了一切本质性东西的源泉。[16]周作人早在中国处于西学东渐的风潮之初,就敏锐地从“情理分殊”的立场出发,看到了科学理性不能侵害人文艺术的领地,在战火动乱的年代里又坚持着革命激情不能妨害用理性清醒的头脑去认识社会、认识人生,并进而倡导科学为人生所用、人生以科学为理据的道路,始终牢牢把握着以人为本、建设美好的人间生活的主线,体现了一个卓越的启蒙思想家的本色。这对于今天各种“打通任、督二脉”之类的社会乱象,仍然不失匡正之力。
[1]丹皮尔.科学史[M].李珩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9.
[2]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J].新青年,1920,7(5).
[3]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M].黄山:黄山书社,2008.
[4]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M].北京:中华书局,2009.217.
[5]王岳川.呼唤“人文理性”的跨世纪诗学[J].诗探索,1996,(4).
[6]邓周平.论人文理性[J].社会科学,2003,(9).
[7]朱德发.现代文学创造:人文理性精神与主体人本艺术思维[J].山东社会科学,2003,(4).
[8]严复.严复集:第2册[M].三联书店,1984.279.
[9]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0]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文集[M].止庵校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1]郜元宝.鲁迅精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5-21.
[12]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60.
[13]陈廷湘.中国现代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563.
[14]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16.
[15]俞正燮.俞正燮全集[M].黄山:黄山书社,2005.13,16.
[16]海德格尔.林中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263.
HumanRationality:TheEssenceof“Scientific”WhichZhouZuorenAdvocated
HUANG Jiang-su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Zhou Zuoren kept alienated from and vigilant against “science”, which was an important theme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because at that time he focused on literature, emphasizing the unique value of arts and humanities to human spirit. In the late 1920s, after his change of mind and the controversy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science” became the theme of his most important articles. He traced back to the source of “science”, the original Confucian “disease falseness” and classical Greek spirit of “love of wisdom” which, in fact, is the position of human rationality. The claim that the ethics of human life must be based on scientific knowledge, scientific rationality and must be in line with the position of the life on earth emphasizes the spirit of “common sense” science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lost in today’s mysterious social chaos remed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ain the loss of scientific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get rid of today’s mysterious social chaos.
Zhou Zuoren; science; human rationality
2012-06-19
黄江苏(1983-),男,湖南永州人,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6.6
A
1674-2338(2013)04-0057-06
(责任编辑吴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