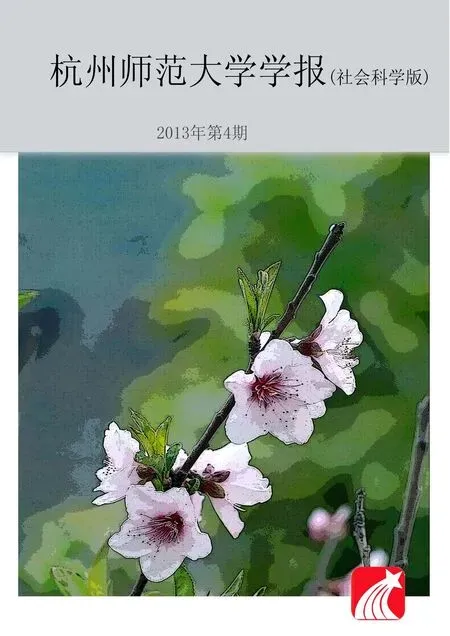著作权与所有权
——以1949-1979年的中国实践为例
2013-04-12彭丽君著张春田译
彭丽君著,张春田译
(1.香港中文大学 文化及宗教研究系,香港 999077;2.华东师范大学 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上海 200241)
学术访谈海外及港台学者访谈之九
著作权与所有权
——以1949-1979年的中国实践为例
彭丽君1著,张春田2译
(1.香港中文大学 文化及宗教研究系,香港 999077;2.华东师范大学 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上海 200241)
在1949-1979年间的中国,作者和作品之间的关系不是根据所有权,而是根据作者作为社会成员的资格来界定的,因此最终的作者是作为集体的人民。这样,作为集体的人民和作为个体的作者不能被截然区分开来。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想象关于文化产品的更加平等主义的实践道路。在这一方面,1949-1979年间中国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经验。
著作权;所有权;延安;社会主义;身份认同
据报道,28岁的中国畅销作家郭敬明的版税已经超过1亿人民币,然而无数职业作家的收入却仅供糊口。[1]中国现在所出现的不平等的文化状况,原因不单只是大众读者对某些明星作者的盲目崇拜,这一直也有;问题更大的,是在这个文化资本经济下,大家把“著作权”等同“所有权”的概念——正因为当中巨大的经济利益左右,作者群中的贫富差别越来越明显。这既是创意经济兴起的结果,也是其原因。创意经济使创造性服从于资本主义机器以产生资本。[2]为了保持文化空间一定程度的自主性,避免市场的侵占,我们必须重新考虑一种不根据所有权来理解的著作权。我们能否这样来确定“作者”的概念:他/她对于其作品没有固有的或专有的权利,他/她不会因为当中的经济利益,而不允许创造性的过程再生,不允许创造性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自然关系从基础出发得以重建?很多关于当代版权的辩论会强调作者和传播者之间的紧张,但把著作权与所有权分离开来的讨论却非常少。
我们可以举关于人身权(moral rights)的辩论作为一个例子。很多今天西方的著作权论者,都褒扬欧陆法系里的著作人人身权(droit d’auteur),认为是更加尊重作者,因为在欧陆传统中,作品是作者个性的延伸,是既在永在的事实,不能更改。相反,在英美普通法系没有这种自然权的概念,著作权更容易通过合同的方式,被授予了作者的雇主或传播者,从而剥夺了作者对于作品的所有权。[3]然而,尽管欧陆实践区别了财产权和人身权,并拒绝把财产权作为版权保护的基础的观点,但保护作者的人身权仍然建基于“所有权”的概念。这样,就妨碍了对作品的公共使用。
在我看来,需要讨论的不是谁拥有何种权利,而是个体作者的占有式本质。当代著作权倾向认定,作者是他所“创造”的作品的所有人。著作权的概念正是建立在这种占有式个人主义的假定之上的。而把创造性作品理解为一种私人财产也是建立在这种假定之上的。 然而,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创意从来不能与复制截然分开,创意的私有化会导致不可避免的阻挡创造性动力的流通。
我曾在拙著《创意及其不满》中提出,今天在后资本主义的运作底下,文艺世界面对的最大的困局之一,就是对作者的迷思,觉得作品就是作者的个人拥有,而作者权/著作权就是此中把文艺变为经济资本的直接工具。更重要的问题是,究竟除了我们熟悉的全球化知识产权外,还有没有其他可能。不同于诉诸诸如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等著作权的另类实践(我认为它们仍然起源于“权利”的概念系统),本文会聚焦于当前著作权讨论中被忽视的1949-1979年间的中国实践。我将论证在这一时期的中国,无需诉诸权利和所有权的概念,作者的身份是如何既被承认又被否认的。在中国集体的领导权(hegemony)决定了最终的作者是人民,而非某个个人。这种意识形态结构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也带来了另一些问题;但它确实能帮助我们认真权衡在著作权和个人主义以外重新把作者概念化的可能性与限度。
著作权与酬报
今天,我们应该开始留意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定位著作权的实践,因为社会主义支持人类产品(既包括物质产品,也包括非物质产品)的集体化。然而,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实际上在法律上以西方国家近似的方式对待著作权。如苏联在1925年通过的社会主义著作权法大部分取自欧陆传统。法律规定,创造性作品一旦被生产出来, 其作者无需登记即拥有权利,并且禁止对一个作者的作品作任何未经授权的修改。[4]尽管这种社会主义著作权强调对于基于财产的著作权法理论的弃绝,但它没有挑战基本的所有权概念。作为1925年法律的修订版,1928年的著作权法案对于著作权的规定在苏联实施了超过30年,并且成为多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主要参考。*在1961年苏联的著作权法中,人身权实际上得到了加强。参见Mira T. Sundara Rajan, Copyright and Creative Freedom: A Study of post-socialist Law Reform,98。
许多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也在很大程度上行使和尊重作者的权利。除了阿尔巴尼亚,所有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前都加入了伯尔尼联盟(Berne Union),而社会主义解放者们也继续承认这个公约,欧洲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发展出关于作者合同的全面的法律系统,以保护作者对作品的权利。[5]在对南斯拉夫著作权法的各种版本的讨论中,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依赖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使用的相同的、关于所有权和个人主义的修辞。[6]作者的人身权在东欧集团(the Eastern Bloc)受到的保护,与在他们的资本主义对手的西方一样多。尽管文化生产中利益驱动的面向被压抑了,但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挑战所有权的基本概念。
著作权上真正的另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第一部现代著作权法是1910年由清政府颁布的,其后经过民国政府的修改和更新以满足国际标准。[7]1949年解放后不久,政府就修订知识产权法以满足新的社会主义治理。1950年,知识产权中的专利权首先得到新中国法律承认,不过,一直到1990年才通过了共和国第一部著作权法。为了替新中国第一部著作权法铺平道路,1957年文化部提出了一个题为“保障出版物、著作权暂行规定(草案)”的方案供公众讨论。“草案”主要参照了苏联1928年著作权法案,但保护的范围大为减少,也没有明确提出作者被赋予的权利。[8](PP.149-150)但即使这个打了折扣的版本也没有被接受。在1958年发起的“大跃进”运动中,私人所有权被完全地废止。著作权法的个人主义面向,明显地与“大跃进”以及此后更激进的“文化大革命”中所提倡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相违背。
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中国从未关注与文化生产相关的经济问题。相对于在法律上对作者权利作出界定,政府聚焦于规范报酬体制。第一个与著作权相关的规定“关于改进和发展出版工作的决议”,是新中国第一次全国出版会议之后,在1950年文化部政策文件上公布的。这份决议清楚地说明,出版社必须尊重作者写作和发表的权利,未经作者同意,出版社不能进行仿制、盗版、变更的相关活动。[8](P.147)但在这份政策文件中,作者实际的权利并没有清晰的规定。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关于作者报酬计算的相对具体的方案。由一套标准决定,包括出版性质(科学类出版物比人文类出版物级别高,原创作品比翻译作品收益高)、质量(被认为有特殊价值的一批精选的出版物将获得更多的报酬)、字数和印数等。[9](PP.264-266)这个方案很快被全国采用。
作者的报酬应该如何计算是一个从那时直到现在都被持久辩论的问题。这些讨论包含了新中国几乎所有关于作者的意识形态讨论,并且一起忽略了著作权概念。关于报酬实践的一个最有争议性的方面与印数有关,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应该根据流行来支付报酬是存在疑问的。在1950年原来的体系里,随着印数的增加,每本付给作者的酬金会相应减少。因此一个作者的收入与销售情况没有直接的比例关系。这是有意要防止写畅销作品的与不那么畅销的作者之间产生重大的经济不平等。在1956年的版本里(这是在政治上更放开的时期颁布的),这一做法被放松了。直到第六次印刷,版税递减才会生效。[10]这个观念是为了鼓励作者写出有广泛影响的作品,畅销写作的作者将必然地获得可观的报酬。很快,当集体主义气氛增强时,这种做法又受到了严厉的批评。1958至1959年的报酬明显减少,每本书所支付的版税与印数之间的反比关系得到更严格的执行。[8]1961年,当“大跃进”正式结束时,重获党内领导权的改革主义者为了推动出版和文艺创作,撤销了1958和1959年的政策。[8]不过,到了1964年,“文化大革命”酝酿前夕,文化部把作者的收入与印数完全分开了,每个作者只会被一次性支付稿酬。[9]
尽管“文化大革命”期间报酬体系并没有正式废除,但支付的标准却进一步降低了,政府甚至鼓励作者不收出版社的报酬。[10]1966年文化部报告中指出,大多数作者、艺术家、科学家已经是政府机构的全职人员,享有基本的月薪,所以无需出版物再带给他们额外的收入。更进一步,普通人应该被鼓励出版,但不应该得到经济上的回报,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有了全职工作。报酬应该给予那些极少数的自由作家和翻译者,他们还需要得到经济支持。[9](P.331)文化生产和经济刺激全然分开了。根据报告,出版者和传播者在与作者的合作中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关心作者的作品和生活,提供给作者必要的信息和反馈,帮助他们把作品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9](P.331)作者和艺术家不是为了物质收益而创作,而是出于他们的抱负和责任,这应该得到人民和国家的感谢,并且在思想上也有益于人民和国家。
个人著作权的概念也被压抑了。相反,集体的著作权得到提倡。那时候创作的大部分文学和艺术作品都归属于一个工作组、政治组织或学习小组。“文化大革命”时期出品的许多电影的原始版本上,甚至连演员都没有列名,观众只有通过口耳相传才知道他们喜欢的女演员的名字。大部分官方的样板表演被归属于是工作组为指定的国家剧团里的项目所创作的。艺术家和文学家更多得以公开署名,不过多数情况也是和他们的工作组连在一起的。当时有一条潜规则:为了鼓励文化民主,只有业余作家才能够署名。职业作家偶尔会因为政治原因而得到擢升。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刘春华在一夜之间获得了荣耀地位。这个艺校学生1967年所画的关于1922年青年毛泽东去安源领导那次重大的工人罢工的油画,被策略性地推出,以批评资深画家侯一民所画的描绘刘少奇的经典油画。这些个体事件与其说是对特别的艺术家的尊重,不如说是由于特殊的政治目的而促生的例外。
尽管中国的社会主义报酬体系是建基于苏联的做法,[10](P.200)并且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也发展出了把一部作品的性质、长度、质量和印数纳入考虑的版税计算方法,但是社会主义中国从未像苏联和许多其他社会主义政府那样将著作权法律化。报酬体系几乎构成了中国著作权体系的全部。在社会主义中国,著作权讨论不是某种关于作者应该具有哪些权利的哲学讨论,他们关注的重心在于给予作者的实际的经济回报,以保证作者的写作和出版。精神生产的经济激励并没有理论化到作者的固有权利的高度。国家聚焦于实际的做法与结果。在1949-1979年间,关于报酬体系的政策变化看上去很激烈,但是讨论从未转移到著作权的本质。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出替代著作权的其他概念,其中之一是文化的“劳动者”,在整个动荡岁月这一概念始终得到推崇。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其1955年报酬规定中清楚地表明,以保障作者群体的整体生活水平为原则,也许不能给那些价值珍贵的原创和翻译作品的作者以公平的报偿,因为那些作品需要长时间的研究和劳动;同时强调了对于这些作品的稿酬,不应该受这些规定的限制的观点。[9](P.281)虽然1955和1956年的做法受到了严厉地批判,稿酬标准继续降低,但到1966年官方文件中仍然清楚地表明,那些极少数在写作作品中付出了极为大量的劳动的文化工作者应该得到比较高的报酬。[9](P.329)基本的稿酬原则是保障基本的生活,这仍然是与文化工作者的劳动,而非作品的固有品质相联系。
尽管苏联的影响是明显的,但社会主义中国从未高扬作者权利,这显示出这两个同样信奉社会主义的国家之间主要的文化差异。在苏联特别是斯大林时期之前,艺术和文学仍然被认为是相对独立于政治的领域。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确立的艺术自由很大程度上受到仍然盛行的现代主义或浪漫主义观念的影响。托洛斯基(Leon Trotsky)把审美当作一种自主的力量的明确信念,对20年代苏联的文化政策和艺术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他批评那些把伟大的文学作品(如但丁的《神曲》)仅仅解读为反映某个特定阶级在某个特定时期的心理状况的历史记录的人,相反,他相信不同时期的读者之间存在直接的美学联系:“我们发现,在中世纪意大利城市发展出来的艺术作品也能够感动我们。这需要什么?一件很小的事:需要这些感情和情绪已经得到如此宽广、强烈和有力的表达,以至于使得它们超越了那些时代生活的限制之上。毫无疑问,但丁是某种社会环境的产物。但是但丁是一个天才,他把他的时代的经验提升到一种惊人的艺术高度。”[11]这里高扬的“天才”话语,可以与玛莎·伍德曼希(Martha Woodmansee)的研究形成共鸣。玛莎·伍德曼希研究著作权话语与把作者视为一个天才、其对人类的特殊贡献必须得到保护的浪漫主义式的观点之间固有的联系。[12]今天著作权制度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关于作者的浪漫主义愿景的扩张,以证成并导致对所有者的越来越广泛的保护。在社会主义中国,天才话语没有听众。文学和艺术必须为人民和为政治服务,作者并没有基于天才身份而赢得一个自主的社会位置。
威廉·爱尔福德(William Alford)把当代中国缺乏著作权意识,追溯到传统中国文化和哲学里个人主义意识的缺席。他认为把原创性理解为创造全然创新立异的东西的想法,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是陌生的,儒家意识形态尊重传统的知识,保护共同资源以供所有未来的作者使用,并未宣扬任何知识产权的体制。[13]爱尔福德的观点正确与否可以讨论,不过我对从文化本质主义的角度看待新中国著作权讨论的缺席没有兴趣。我更想指出的是,共产党是从一个不同的进路来影响文化工作者,使他们与集体相认同。我认为,共产党在某种程度上对作者和艺术家的身份与自我认知非常敏感。然而,共产党不是把何谓作者理论化或对著作权的限制予以清晰表述,而是劝使作者把他们所有的一切交给集体。这才可以解释新中国著作权讨论的缺席。这种做法也决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作者的命运。
作者的身份与身份认同
这种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体制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1936-1945)的文化管理。那时共产党驻扎在延安农村地区,抵抗国民党和日本军队的袭击。对立的两党组成了抗日统一战线后,中共中央在1940年签署了一个由毛泽东执笔的、关于共产党控制地区的具体政策的命令。毛泽东的总体关切是巩固党在这些地区的统治,巩固与国民党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化问题在整个文件中只占一小部分,不过这个指示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文化政策,因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个文件清楚地表明,在整个统一战线政策中文化将扮演宣传的角色,所以文化应该把自己看作是附属于更大的政治任务。最重要的是,文件最首要的关切是“人民”而不是“作品”,这显示出党对于文化工作者的尊重以及隐藏的焦虑。毛泽东提倡接纳所有显示出抗日热情知识分子和学生进入共产党的学校,给予他们短期的训练,然后安排他们去军队、政府或大众机构工作。共产党将大胆地吸纳他们,给他们工作,提拔他们,并且不应该过分谨慎或者害怕反动分子混进来。[14]这个文件指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接受尽可能多的文化工作者(不管是不是共产主义者),不过也提出这些工作者应当首先进入党的文艺学校——鲁迅艺术学院学习。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系统阐述文化观点,是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次会议是党为了回应在逗留于延安的文化工作者之间弥漫的自由放荡(boheimian)文化而召开的。*对于“讲话”,一个更详细的导论参见Bonnie S. McDougall, Mao Zedong’s “Talks at the Yan’an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 A Translation of the 1943 Text with Commentary.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0。毛泽东讨论了文学和艺术的本质。他强调了它们在服务当前需要上所能扮演的政治角色。继承了战时修辞占主导的1940年的文件,“讲话”清楚地提出“文艺为大众”的说法,并且强调了文学和艺术的政治功能。[15]文化工作者再一次被号召接受再教育。民间文化受到尊重,文化工作者需要走到人民中间,向他们学习,同时动员他们。如果说延安“讲话”成为中共此后文化政策的原型,那么“讲话”中传递的理念更像一次寻求文化工作者的身份认同(identification)的宣传声明,而非政策表述。“讲话”中所包含的观念以及这种直接对文化工作者的演说,代表了共产党此后文化治理的特征。
延安“讲话”在中国受到了最广泛的研究,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政策文件。值得注意,这个文件反映了毛泽东及其文化同志在艺术和政治的关系上的哲学思考,这是一种权益的、功利主义的对待文化的进路。“讲话”强调了文化工作者对于人民的从属位置,这是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和战时危急状况的双重结果。这种理论与实践,个人与集体之间的互相决定,没有赋予文化工作者在为人民服务之外的其他责任。
周扬在1945年提出了一份更详细的、紧跟1942年“讲话”的文化政策主张,更加清楚地揭示了共产党如何理解它与文化的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围绕文学的社会角色问题,周扬与主要的左联人物(如鲁迅、胡风)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争。1937年周扬被共产党召到延安,领导新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当周扬到达延安以后,他的文化哲学变得更加的政治化,他极力主张艺术服务于政治。周扬要求作家和艺术家理解党在解放区实施的新政策:
自从(延安)关于文学与艺术的会议以后,文艺创作活动的一个新的显著特点,是其与当前各种革命实际政策的开始结合。这是文艺新方向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艺术应该反映政治,对于解放区来说,这个原则就是通过艺术反映各种政策在人民中实行的过程与结果来实现。……为了反映新时期人民的生活,艺术家需要理解正在实践的各种革命政策,正是这些政策改变了这个时代的面貌。*参见周扬《关于政策与艺术:〈同志,你走错了路〉序言》,缪俊杰、蒋荫安编《周扬序跋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5页。黑体文字为笔者所加。
在周扬看来,艺术家和作家的角色就是追随和理解党所实施的各种新政策,使得这些政策能够在群众中得到传播。周扬并没有使用“文化政策”这个术语来表示党在文化功能上的观点,“文化”和“政策”两个术语是分开使用的,但很明显周扬强调文化为政策服务。
这种服从机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极为公然地利用,那时作家和艺术家是第一批被整肃的。尽管对“文化大革命”从整体上感到愤怒并加以谴责,不过一些作家和艺术家在他们的回忆中承认,他们当时对让他们接受再教育是自愿服从的,他们中的一些人确信知识分子作为一种身份应该消亡。*例如,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和他的妻子在1966年的自杀遗书中说,他们是旧社会的遗留,应该退出历史舞台。这个说法可以有两种解读,或者是作为讽刺,或者是作为一种把红卫兵的指责内化了的看法,我认为两者都有。《傅雷遗书》,http://www.cclawnet.com/fuleijiashu/fl0191.thm.“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关于集体著作权的极端的例子,个人没有什么空间宣称作品是属于自己名下的。
超越个人主义
尽管延安时期文化工作者的服从,是在战时体制和艰难的日常生活条件下启动的,这个机制却在20世纪50年代得到了继续,并且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顶峰。“文化大革命”时期,个人的作者身份必须全然否定,以把著作权再指定给整体人民。作者总是被当作一个临时的范畴,最终将要被取代和消除的。这种历史的重访,让我们从一个社会的和历史的观点,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愿确立著作权的原因,也可以防止我们从一个本质主义的角度对待“中国式”的对著作权的理解。否定给予作者的权利更多是一个政治决定,而非文化必然性。
毛泽东政治哲学的一个主要基础就是个人与集体之间互相决定的辩证关系。党必须依赖于人民的支持,因此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纯粹的列宁主义式的先锋党。然而,在毛泽东的哲学中,人民也始终需要党的引导,因为人民中的每个个人又是幼稚的、容易倒退。如此,文化工作者,或者一般的知识分子既是人民的一部分,又不是人民的一部分:他们的自主性得到承认,因为他们被认为在思想上比一般人民更进步,但他们也为这种身份所苦。他们大部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必须自我否定,以被吸收进人民。从根本上说,文学和艺术产品是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共产主义理想中,所有人都能够自由和充分地写作和参与到文化生产中。在这样一种文化民主的语境中,著作权讨论变得不着边际。所有一切都是公有财产,每个人都无偿地回应、改编甚至复制其他人的作品。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样的状况事实上是存在的。每一个公共场所都有普通市民创作和张贴的大字报、宣传画和连环画,其中一些作品很快被复制和重新散发。这是激进的集体主义时期,正要肃清所有作为资本主义腐化的“私人”的所有权。这也是一个启蒙的乌托邦,所有的人民变得有自主性,不需要知识分子的引导。
这种改造“私人”的实践也带来了几个问题:个人不被允许退出集体,个人自由受到损害,创意不能为任何个人所有。事实上,这种公共的扩张只能在极端政治化的环境中得以维持,在那里,每个人都受到其他人的意识形态检查 。然而,“文化大革命”时期著作权概念的不存在,确实揭示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与现在的情况构成了对比。正是在当前去政治化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著作权和知识产权才得到了热切地提倡。各种权利的概念,既与私人化和个人化的社会是相容的,也是后者所亟需的。但在一个激进政治化的社会里,这些主要集中于保护个人的、关于权利的讨论被集体利益所替代。*一方面,在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在公共领域里几乎不剩下任何东西了。权利是源自个人之间的冲突的产物。而另一方面,在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私人领域整个消失了,所以根本没有必要讨论权利。汉娜·阿伦特把权利理解为个人与公共领域之间协商的结果,可以被看作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找一个中间位置。参见Hanna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London: André,Deustch,1986),301。
本文的核心问题在于是否有可能不以对作品的权利来界定作者。在1949-1979年间的中国,作者和作品之间的关系不是根据所有权,而是根据作者作为社会成员的资格来界定的,反过来是社会拥有作品。最终的作者是作为集体的人民。人民被期待在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主义的经典的指导下写出作品。他们可以创造一大批指向党的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的文本。最重要的,支持党及其意识形态人民本身,在文化和政治之间实现了一种有机结合。*参见Grgorinic和Raden类似的讨论,他们把国家看作是作者。Natalija Grgorinic and Ognjen Raden, “Authors’ Rights as an Instrument of Control: An Overview of the Ideas of Authorship and Authors’ Rights in Socialists Yugoslavia, and How These Ideas Did Not Change to Reflect the Ideas of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Law and Critique 19,no.1,49-50.这样,作为集体的人民和作为个体的作者不能被截然区分开来。通过个人作者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的辩证法,这种集体与个体的互相决定是可能的。今天,即使已经很少有人(即使那些激烈反资本主义的批评家们)愿意致力于社会主义理想主义,但是在我看来,可以在这个理想主义的基础上去想象关于文化产品的、更加平等主义的实践的另类道路。我们不应该让集体著作权全然被个人作者所霸占。关于此,社会主义中国正提供了历史经验;但我们仍然可以探讨如何不以否定个人的方式,而将集体概念化并加以实践?我们紧要的任务,也是当代数字媒体的主要挑战,是去构想一种超越权利话语的著作权的新模式,重新研究个人与集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辩证关系把个人与集体两者都认真对待。
[1]中国文坛贫富悬殊——作家富豪郭敬明登榜首[N].星洲日报,2011-11-22.
[2]Laikwan Pang.CreativityandItsDiscontents:China’sCreativeIndustriesand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Offense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2012.67-85.
[3]Pamela Samuelson. Economic and Constitutional Influences on Copyright Law in the U.S.[C]// Huge Hansen ed.U.S.IntellectualPropertyLawandPolicy.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2006.164-203.
[4]Mira T. Sundara Rajan.CopyrightandCreativeFreedom:AStudyofpost-socialistLawReform[M]. London: Routledge,2006.89-97.
[5]György Boytha. The Berne Convention and the Socialist Countries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Hungary[J].JournalofLaw&theArts11,1986,(73):57-72.
[6]Natalija Grgorinic, Ognjen Raden. Authors’ Rights as an Instrument of Control: An Overview of the Ideas of Authorship and Authors’ Rights in Socialists Yugoslavia, and How These Ideas Did Not Change to Reflect the Ideas of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J].LawandCritique19,2008,(1):35-63.
[7]李明山.中国近代版权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100-127,165-169,174-183.
[8]李雨峰.枪口下的法律:中国版权史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9]周林,李明山.中国版权史研究文献[G].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
[10]郝富强.“十七年”文艺稿酬制度研究[J].江海学刊,2006,(4):201.
[11]Leon Trotsky. Class and Art[M]//Paul N. Siegel.ArtandRevolution:WritingsonLiterature,PoliticsandCulture. New York: Pathfinder,2008.70.
[12]Martha Woodmansee. The Genius and the Copyright: Economic and Legal Conditions of the Emergence of the ‘Author’[J].Eighteenth-CenturyStudies17,1984,(4):425-428.
[13]William Alford.ToStealaBookIsanElegantOffense:IntellectualPropertyLawinChineseCivilization[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1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759-767.
[15]Bonnie S. McDougall.MaoZedong’s“TalksattheYan’anConferenceonLiteratureandArt”:ATranslationofthe1943TextwithCommentary[M].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0.14-17.
AuthorshipversusOwnership:TheCaseofSocialistChina
PANG Lai-kwan1, tr. ZHANG Chun-tian2
(1.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d Religious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 2.Si-mian Instif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uthor and the work is not defined by ownership but by the membership of author as social member between in 1949-1979 China. The final author is the people as the collective. The people as the collective could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author as individual. We can imagine a kind of more equal definition of authorship based on this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1949-1979 China’s practice.
authorship; ownership; Yanan; socialism; identity
2013-05-10
本文翻译自英文原文:Laikwan Pang, “Authorship versus Ownership: The Case of Socialist China,” in Cynthia Chris and David A. Gerstner (eds)MediaAuthorship(New York: Routledge,2013),72-86.
彭丽君,女,中国香港人,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电影史、中国现当代视觉文化、知识产权与创意经济研究;张春田(1981-),男,安徽芜湖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思想史研究。
G12
A
1674-2338(2013)04-0044-06
(责任编辑吴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