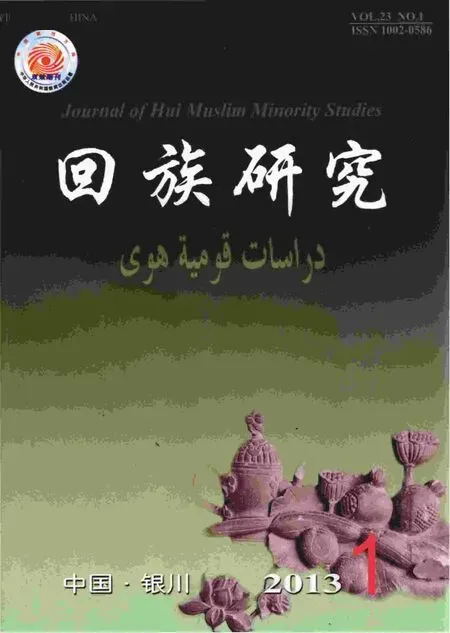从“汉化”到“回化”:泉州回族认同问题再讨论
2013-04-12良警宇
良警宇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081)
一、问题的提出
泉州回族在历史上经历了从先民的穆斯林身份,明朝以后作为穆斯林后裔、汉族身份及其认同,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回族身份及其认同的历史转变过程。什么是推动泉州回族民族身份和认同转变的主要力量?这一问题,不仅是回族学研究中许多学者所关注和探讨的问题,而且成为“了解中国国内族群/民族认同的性质”、考察中国社会“权力关系和社会认同”以及“中国国家及其社会”问题的重要案例。
对于历史上泉州回族“汉化”的原因,特别是陈埭回族“汉化”的原因,基于丰富的史料,学界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众多的研究从历史上宋明理学在闽南地区高度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伊斯兰教育的衰落、回族士绅阶层的出现和宗族的建构、国内国际局势以及人口、通婚因素等多个方面,探讨了泉州回族先民的伊斯兰信仰从社区的日常生活中“退场”,穆斯林认同普遍衰落的原因。
但是,关于已经全面“汉化”的泉州回族在新中国成立后重申回族身份和认同问题的论述,却相对模式化和简化论述,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讨论模式。学界较有影响力的一种观点是关于泉州回族认同及其民族性的“政治性建构”理论。杜磊首先提出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民族识别”过程,是一种“社会命名”的过程,“国家通过对其命名,从法律上规定谁是民族、谁不是民族,然后确定一定族群的人口数量,将他们联结在一起,并赋予一种先前未知的社会生活”。通过这一过程,回族作为一个“民族”被识别出来,并促成了被划定为回族的群体的认同。具体到泉州陈埭丁姓群体对回族身份的诉求,杜磊则认为是两方面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政府干预和政策影响,即“因特殊优惠待遇而发生的族群认同转换”,具体而言,就是政府对少数民族的补助资金和特殊优惠引发了其对回族身份的诉求。但同时,杜磊也强调了不能排斥这一群体的“回族认同的文化持续性”的基础作用,但他认为这一群体对自身祖先身份的文化特质的强调是一种场景性的应用,是祖先认同的文化传统与民族政策、公共政策互动的结果[1]。范可在其《国家政治与泉州回民的穆斯林认同》一文中,也提出了与杜磊相似的观点,他也强调了国家政治对于塑造泉州回族穆斯林认同的影响作用,认为泉州回族的穆斯林认同建构,是在当地政府鼓励下,“通过积累象征资本来为当地获取商机和各种其他资源的行为”[2]。与泉州回族认同及其民族性的“政治建构论”不同的另一种观点则强调了改革开放后,在政府实行了宽松的民族政策和宗教自由政策的背景下,泉州陈埭回族所固守的对穆斯林祖先的文化和认同心理,促使其主动地要求恢复民族身份。换言之,这一观点认为,陈埭回族在“汉化”过程中对伊斯兰文化的特质的保留和固守,是一种共同的民族心理的体现,是一种心灵的守望。在适当的政策环境下,这种守望最终转换成为了一种行动[3][4]。
笔者认为,与关于历史上陈埭回族“汉化”问题的讨论相比较,关于陈埭回族“回化”(本文指“回族化”)的两种讨论,存在将这一过程“简化”论述的倾向。“政治建构论”指出了国家政治和政策的重要影响,并由此将民间的回应定位成工具性和场景性的适应。虽然杜磊也指出了祖先认同的文化基础作用,但他强调的仍然是文化的工具性作用,对于“谁”在具体使用这一“文化工具”并没有进行清楚地辨析,仅仅是统而概之地谈论了祖先的文化认同与国家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影响。同时他也无法解释,20世纪20年代后在外部穆斯林力量的支持下,泉州回族一度开始恢复“祖教”的行动,与70年代后又一次开始恢复“祖教”的行动,在性质上是否存在差异性?如果后者是一种场景性的利用资源获取利益的应对,那么前者又是要应对何种场景,又能从中获取何种优惠和利益呢?而“心灵守望说”则是从穆斯林本位的角度,将民族认同本质化,又过于淡化了国家政治的影响,也无法解释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陈埭回族在政府的促动下,曾不接受转换民族身份的历史事实。因此,两种解释的缺陷都显而易见。
那么如何进一步探讨泉州回族“回化“的问题呢?事实上,关于历史上泉州回族“汉化”问题的讨论,给了我们一种启示。这种启示就是在历史逻辑中探讨民族认同问题的思路。
二、“汉化”与“回化”的概念意涵
在对泉州回族“汉化”和“回化”问题进行讨论之前,笔者需要对文中使用的这两个关键概念进行一个学术性的界定。一些学者在有关历史上泉州地区回族“汉化”问题的研究中,对于“汉化”一词的使用非常谨慎。范可特别对此进行阐述,提出他是在“不同民族在共同生息、交往中所导致的文化趋同现象”这一意义上看待“同化”概念,由此,他将“汉化”定义为“是指在特定条件下,少数民族在文化上趋同于汉族”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并非一定意味着民族消亡”[5](P62)。具体到泉州回族的个案,则是指历史上,泉州回族从穆斯林文化认同和生活方式向汉文化认同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而本文对于“回化”(即“回族化”)概念的使用,则是指泉州回族从汉族身份及其认同向回族身份及其认同的转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包含了这一群体的一部分民众开始恢复伊斯兰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即伊斯兰教信仰及其实践又重新在社区日常生活出现和发展的过程。笔者之所以选择使用“回化”而非“伊斯兰化”或“穆斯林化”这一概念,主要是基于泉州回族群体存在一个被国家和其自身确认为回族身份的过程,对这一过程和相关影响因素的考察正是本文讨论的重点。选择使用“回化”这一概念的另外两个原因:一是因为目前伊斯兰化的生活方式仅仅体现在泉州部分回族的日常生活中,目前大部分泉州回族仍然更多地保持汉文化的风俗习惯;二是“回化”这一概念本身可以包容不同主体对于“回族”这一群体的理解和“想象”,以及由此进行的实践活动。这些理解、“想象”和实践反映在泉州回族在身份确认的过程中及其之后,伊斯兰文化元素的强调及其认同在这一群体中有不断增长的趋势,这种趋势也反映在改革开放后其他地区回族伊斯兰文化复兴的实践中,比如重新强调阿拉伯建筑装饰符号、清真生活方式以及伊斯兰信仰等等。在当今大众社会的日常概念体系中,也往往把回族与伊斯兰生活方式、文化和信仰天然地联系在一起,“回化”这一概念包容了这一认知特点。同样这一概念也包容了目前大部分泉州回族在保持穆斯林祖先认同的同时,仍然更多地保持汉文化的风俗习惯这一现实。
三、泉州回族“汉化”的历史逻辑
关于历史上泉州回族“汉化”的原因,基于丰富的史料,学界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些探讨从不同方面揭示了陈埭回族从先民的穆斯林身份,向汉族身份及其认同转变的历史过程和历史逻辑。所探讨的原因主要包括历史上宋明理学在闽南地区高度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伊斯兰教育的衰落、回族士绅阶层的出现和宗族的建构、国内国际局势以及人口、通婚因素等多个方面。
(一)历史上宋明理学在闽南地区高度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
范可在讨论泉州回族历史上汉化原因的时候,对比张承志、林长宽等学者的研究,提出宋明理学在闽南地区的高度发展,直接导致了泉州回族的全面汉化。这一现象反映了儒家文化强盛与回族汉化程度之间的函数关系,进一步验证了关于回族的汉化程度与儒家文化强盛在地理区域上的分布基本一致的假设[2]。
(二)回族士绅阶层的出现和宗族的建构
回族士绅阶层的出现与儒家教育的普及及其价值观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泉州回族社区中宗族组织和士绅集团的出现,是当地儒家教育普及至回族社区的体现。换言之,回族精英阶层通过接受儒家教育,获得了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士绅阶层“获取功名”的历史事实正是儒家教育和文化影响的必然结果。这一结果的另一表现和直接的结果是标志回族认同转换的宗族建构。许多研究都提到了明朝万历年间,陈埭社区遭受倭寇袭扰后主持社区重建,以儒家之“礼”为准绳,为祭祖定制,从而标志着陈埭社区全面“汉化”这一事件的关键人物丁自申——丁氏家族中一个曾获进士功名、在外地为官,后退归故里的士绅。他之所以能够会集族中耆宿乡绅,并以族务掌管者自居,主持丁姓宗祠的修建,正是基于其在外部社会所获得的功名,而其功名的获得,则正是丁氏族人长期接受和普及儒家教育的直接结果。正如郑振满、范可等学者关于陈埭丁氏族人“汉化”问题研究中所指出的,“儒士化”的丁姓族内的士绅阶层在回族穆斯林认同改变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明中叶后,士绅阶层获得了对宗族事务的支配权,在宗族内部推行儒家传统的纲常礼教,才促成了陈埭丁氏族人的汉化过程[6](P247-257)[2][7]。当然,石奕龙也指出,陈埭丁氏宗教信仰的转变可能经过了一个较长时期的演变过程,正如士绅阶层的出现也必然要经过几代的积累和培育一样,但士绅阶层在其中的推动作用不可否认[8](P197-209)。与此相对照的是,郭姓在倭患之后,社区也出现解体,但却没有如丁姓内部的士绅集团那样有号召力的人出面以儒定制进行社区重建,从而推迟了汉化的进程[2]。
(三)伊斯兰教育与文化传播的衰落
到明朝时期,特别是明朝“嘉靖倭患”,致使海上丝绸之路中断,伊斯兰教的传播陷入低谷,出现“掌教失传”的状况。但在中原地区的知识分子则通过“经堂教育”,南京、苏州等地的回族知识分子通过“以儒诠经”等活动,为伊斯兰教后继人才的培养和伊斯兰文化在上述地区的传播注入新的生机之时,泉州“儒士化”的回族知识分子并没有与以上地区的回族知识分子和穆斯林发生互动,他们在走向仕宦的同时,迅速而全面地转向了儒学认同,并一度发生了“回儒之争”,在内部谴责自己的祖先“不祖其祖,而祖人之祖”,从而对回族的汉化过程,从内部起了催化作用[9](P109-112)。这一过程也可以被看做是伊斯兰教育与文化传播衰落,并使泉州回族的回回认同丧失了核心内容的一个过程。
(四)人口、通婚因素
范可在其研究中指出,明朝时期的两个重要事件导致泉州的穆斯林人口不能再继续快速增长。一是明朝时期东南沿海的“倭患”致使海禁政策实施,并使泉州失去了国际贸易商埠的地位,也中断了海路穆斯林的来源。二是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引发了回回人口的大规模迁徙北上,陆路交通障碍也阻碍了穆斯林或回回人口通过陆路自发大规模迁徙南下[2]。根据明朝时期相关史料对当地回族人口的统计,也可以看出当时泉州回族的规模有限。关于泉州回族主要聚居地之一的百崎地区,“据隆庆四年(1570年)至万历二年(1574年)惠安县知县叶春及的《惠安政书》记载:白崎铺14 村与云头铺2 村均属二十三都,当时共有回汉民147户,1 248 人”[10](P15)。丁氏自一世祖于宋元之际迁居泉州后,是由一人一户逐渐发展到第十世240 人,明末数千人的聚居宗族。泉州城内的回族也屈指可数,根据民国时期张玉光所撰写的《回教入华与泉州回教概况》记载,20世纪30年代时,泉州城内回民只有11 户[11]。此外,许多学者也指出,与汉族通婚不可避免导致大量接受汉文化因素[12](P288-297)[5](P62-63)[13]。由此,人口因素,尤其不再有能带来承载伊斯兰文化的人口因素也成为泉州回族伊斯兰文化衰落的原因。
(五)国内国际局势及其政策
如果进一步扩展对人口学因素的讨论,则这一解释又要延伸到国家政策与世界局势的探讨。海禁政策与朱棣迁都带大批南方回族北上,属于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的范畴,因此可以说东南沿海回族的人口学特征与当时历史条件下国家并非针对回族而专门实施的政治活动和政策有密切关系,这些政策的实施,又与中国当时与周边的紧张关系有密切的联系。
如果把这些导致泉州回族“汉化”的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连接,则会形成一个历史演进的时间上的因果链。在这些影响因素中,可以发现,国内国际局势及其政策也许成为推动泉州回族“汉化”的一个起点。国内国际局势及其政策推行,导致了伊斯兰文化不能持续通过穆斯林的移入这一人口学因素进行传承,经堂教育没在福建兴起也与当时东南地区回族人口学特征有密切关系,当地回族普遍接受儒家教育与经堂教育、“以儒诠经”等民间伊斯兰文化的自救活动未能影响到这一地区的历史过程有密切关系,而儒家教育的普及与宗族的出现和回族入仕并形成士绅阶层有密切关系,士绅阶层的出现则成为宗族构建的必然基础,宗族的构建最终成为陈埭回族认同转换和汉化的最外在的标志。
所以,国际因素、国家政治与政策、人口学因素、宋明理学在闽南地区高度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儒家教育普及、回族士绅形成、宗族构建与泉州回族的最终“汉化”就这样逻辑性地联系在一起,并成为导致历史上泉州回族“汉化”的系列性的过程性原因。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不能说国家政治或者政策直接导致了回族汉化的事实,因为没有中间的因果环节和发展过程,国家政治与回族汉化的逻辑关系也就无法形成。
所以正如许多历史研究中所揭示的,一个社会历史事件或现象的发生从来不是一种因素作用的结果,甚至不是多种因素在同一时间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是一个历史的逻辑过程。历史上的一些“偶然”性事件,则更是参与和作用于了这一过程。比如一些研究提到,元末发生在泉州达10年之久的“亦思巴奚”之乱,导致包括外国穆斯林侨民在内的外国人聚居区不复存在,外国侨民纷纷外逃。也许正是这样的一个事件,使迁移到城郊或远郊地区的“蕃客”的后代感受到生存的压力,并以一种适应性的方式与主流社会接触。类似的“偶然性事件”也可以促成一些标志性事件的发生。例如丁氏士绅阶层的“以礼定制”活动被认为标志着伊斯兰信仰从丁氏日常生活中的全面退场。推动这次社区重建活动的则是丁姓社区于1560年遭受倭寇袭击后日常生活陷入失序这样一个时机。除此之外,自然环境条件也可能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以经济文化类型的分析视角,比较了百崎郭姓回族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全面“汉化”,而不远之处隔海相望的陈埭丁姓社区却在明朝万历年间就已经完成“汉化”过程的差异性原因。认为自然环境条件及在这种条件影响下的生计模式,以及这种模式反过来对每日生活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导致了男性经常外出从事海事活动的百崎回族,没有可能建立和发展起完善的宗族组织,从而使伊斯兰教能在一个理学说教高度发达的区域内坚持了更长的时间[2][14](P298-314)。
四、新中国成立后泉州回族“回化”的历史逻辑
以探讨“汉化”问题的视角来探讨新中国成立后泉州回族的“回化”现象,笔者发现这个逻辑过程如此相似,但各种历史因素交织却是导致泉州回族从“汉化”走向了“回化”。
如前文所述,“政治建构论”和“心灵守望说”都指出了泉州回族“回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分别过于强调一种因素的影响,造成了解释上的逻辑缺陷。笔者认为,这两种解释模式遗漏了一些关键影响因素和因果环节的讨论。比如对照“汉化”过程中士绅阶层的形成和宗族建构的关键因素,关于“回化”问题的探讨,显然忽视了对于主导“回化”的阶层、关键人物和标志性事件的讨论。另外对于国际、国内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关键性影响的讨论也不够深入。在“政治建构论”和“心灵守望说”的讨论中,这些因素或者被概化,或者只是被处理成了一种背景,而没有将其视为一种关键性的影响力量。
(一)政治及其政策影响
“政治建构论”的确是极具洞见地指出了政治因素对泉州回族穆斯林认同的深刻影响。笔者认为,在国内政治影响因素中,有三个政策实施的历史关键期需要分别提出。首先是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国家政府进行政权建设的需要,成为地方政府发掘所辖之地的民族、历史及文化资源的动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民族身份的确认和识别过程中,1957年,百崎的郭姓居民被正式确定为回族,成为地方上民族多样性的一个代表。虽然陈埭丁氏当时拒绝,但仍享受了许多少数民族的待遇,如定期收到民族书刊,民族补助等。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国家恢复和落实民族宗教政策的“拨乱反正”的需要,使陈埭等地的泉州回族又有了一次重申和确认民族身份的机会,并由此最终成功地将民族身份转换为回族。第三次则是“开放”的需要和相关政策实施的影响。“开放”与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急需加强与国际社会联系,吸引外资进行经济建设的需求密切相连。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地方政府有了挖掘当地穆斯林文化遗产,加强与穆斯林世界联系的动力。1991年和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到泉州的参观访问,促成了陈埭清真寺的建成和相关宗教活动的开展。如果没有这些国家政治需要的“契机”,也很难想象“回化”在陈埭以及其他回族地区的继续发展。在这种意义上,政治因素的确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仔细考察这一过程的推动力量,则会发现政治性因素的作用事实上通过关键人物的活动而体现出来,而这些关键人物则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被培养教育起来的。
(二)穆斯林耆老群体及其影响
在改革开放之初,陈埭社区已经存在一个曾经受过伊斯兰教育的穆斯林群体,他们对于陈埭回族“回化”的过程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这段历史必须追溯到19世纪20—40年代在外来穆斯林的努力下所推动的泉州地区的“祖教”恢复活动。这些外来的影响力量涉及时任厦门海关总监,后来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的著名回族人士唐柯三先生,涉及到“中国回教抗日救国会”,涉及到当时培养穆斯林人才的成达师范学校。根据当地的历史资料,1939年至1941年有15 位丁姓子弟,共28 位泉州子弟被送入桂林成达师范学校学习阿拉伯语、伊斯兰教知识。虽然这些泉州的回族子弟毕业后并没有全部回家乡,但却在半个世纪后改革开放的时代,发挥了关键性的影响作用。正如一些研究所揭示的,陈埭回族身份的恢复并非当时政府极力要求的结果,而是有一个从1976—1979年民间反复申请申报的过程。最终被“顺利”认定则是1978年泉州市民政局一笔专门划拨给少数民族的经费需要落实到具体群体的一个“偶然性”契机[15](P29)。但如果没有之前陈埭社区精英的推动,也很难想象这种“偶然性契机”会自动降落在陈埭地区。同样,伊协的成立、清真寺的建成、回族事务委员会的成立等一些关键性事件的发生,也都与社区精英,特别是20世纪20—40年代成达师范学校所培养的一批陈埭回族穆斯林子弟的努力分不开。如果说各级伊斯兰教协会的成立是落实国家政策的一部分,那么清真寺的最终建成则体现了社区既有穆斯林群体的努力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陈埭社区原来没有清真寺,落实民族宗教政策后做礼拜的人不多,20世纪80年代初伊协小组成立后,就开始酝酿成立清真寺,穆斯林耆老通过民间向海内外筹款,募集了清真寺的建设费用,但直到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到泉州参观访问这一国际交流契机的出现,才促成了陈埭清真寺的建成和相关宗教活动的开展,以及后来才可能被政府批准为正式开放的清真寺[15](P30-39)[4]。所以,陈埭丁氏回族身份的转换,伊斯兰教在陈埭地区的复兴,离不开国家政治需要和地方政府对国家政策的落实,同样也与社区精英的努力密切相关。没有社区精英的努力这一环节,国家政治是无法自动建构出一个群体的身份和一种伊斯兰文化的民族认同趋势。如果说“心灵守望说”有一定的道理,应当说也主要体现在这一群体的努力上。
(三)伊斯兰教育及其文化传播
在穆斯林耆老的努力下,1991年开始新一代的年轻人被送出去学习伊斯兰教知识,到2010年,前后大约有60多人被送出学习(包括陈埭和福建其他地方的青年)。一些学习归来的年轻人成为新一代的回族穆斯林,并开始在家乡推广伊斯兰文化。他们成立了联谊会,并凭借泉州地区外贸经济的发展,与国内外穆斯林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网络,他们凭借清真寺的宗教活动与交流,加强了社区的伊斯兰文化氛围和影响[15](P40-49)。可以说,伊斯兰文化在当地新一代年轻人身上的体现,是与政治需要、政策落实、穆斯林耆老的努力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等一系列因素和互动过程密切联系的。这些也必将影响社区的文化内容和文化方向。
(四)穆斯林人口因素
与历史上泉州回族“汉化”过程中承载伊斯兰文化的外来穆斯林减少或消失所形成的影响正好相反,在如今的新时代,外来穆斯林不断涌入,成为影响社区文化走向的重要影响力量。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泉州地区尤其是石狮和晋江制衣、制鞋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地、外国穆斯林通过打工、外贸等方式来到泉州,将伊斯兰文化气息带入陈埭等回族地区。陈埭清真寺是晋江市唯一一座清真寺,每周五聚礼时,会聚集许多外来穆斯林群体。这些人包括来自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外国穆斯林商人和旅游者,也有来自河南、新疆、青海等省区的穆斯林翻译、鞋厂工人、清真餐厅从业者和商贩等长期居住在泉州或晋江地区的国内穆斯林[15](P58-67)[16](P68-85),他们显然成为影响本地伊斯兰文化重建和回族社区文化面貌的重要因素。
总之,将这些因素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泉州回族的“回化”像“汉化”一样,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并非是一种因素主要建构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逻辑过程。民族认同问题也必须被放入历史的脉络中进行具体分析。虽然思维的逻辑需要撇开历史发展的一些细节和偶然因素,以“纯粹”的理论形态对历史进行总结和概括,但逻辑分析必须要以历史发展为基础,思维的逻辑应当反映历史发展过程的内在必然性。在民族认同问题的探讨上也应该如此。
[1]Dru C.Gladney.Ethnic Identity in China:The Making of a Muslim Minority Nationality[M].Orlando.Hardcourt Brace &Company,1998;[美]杜磊.中国的族群认同:一个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制造[M].马海云,周传斌,译.王建民,校.1999年译本.
[2]范可.国家政治与泉州回民的穆斯林认同[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1).
[3]耿喜波.心灵的守护——解读当代福建陈埭回族民族意识的复兴[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5).
[4]马彦虎.陈埭的回族与伊斯兰教[J].中国穆斯林,1993(2).
[5]范可.关于陈埭回民的若干历史问题[A].陈国强.陈埭回族史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62.
[6]郑振满.明代陈江丁氏回族的宗族组织与汉化过程[A].陈国强.陈埭回族史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247—257.
[7]范可.泉州陈埭丁姓回族汉化原因辨析[J].厦门大学学报,1990(3).
[8]石奕龙.陈埭回族宗教信仰演变及其原因探析[A].陈国强.陈埭回族史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197—209.
[9]吴幼雄.百崎郭姓渊源与经堂教育[A].陈国强,陈清发.百崎回族研究[C].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109—112.
[10]陈国强.百崎回族乡的人口与经济的发展[A].陈国强,陈清发.百崎回族研究[C].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15.
[11]张玉光.回教入华与泉州回教概况[A].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市泉州历史研究会.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12]陈自强.泉州回族姓氏婚姻情况分析[A].陈国强.陈埭回族史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298—314.
[13]庄景辉.陈埭丁氏回族婚姻形态的历史考察[J].回族研究,1995(2).
[14]郭志超.陈埭丁与白奇郭汉化的比较研究[A].陈国强.陈埭回族史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298—314.
[15]陈碧.民族、宗教与身份认同——福建陈埭丁氏回族的个案研究[D].硕士论文.福建:厦门大学,2007.
[16]杨阳.国家与国家之外——泉州回族伊斯兰文化重建中的国家与民间[D].硕士论文.福建:厦门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