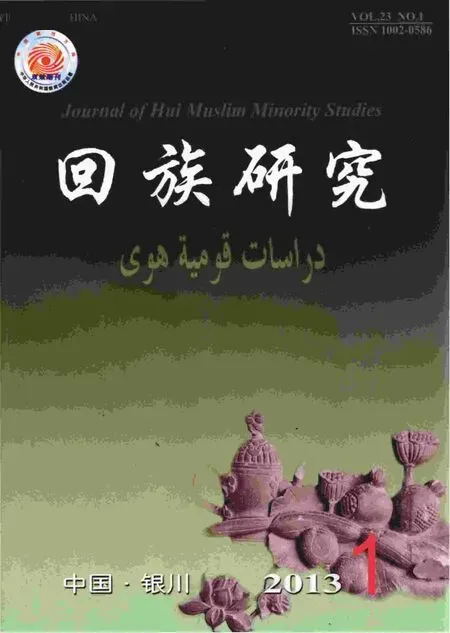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和回族化
2013-04-12白建灵
白建灵
(宁夏大学 人文学院,宁夏 银川750021)
任何一种宗教,当其在异域传播时,必然面临本土化的选择。其是否选择本土化,直接决定它在异域传播的成败;其本土化的程度,也决定了它在异域传播的程度。伊斯兰教作为一种世界性宗教,其世界化的过程,就是在各个异域分别本土化的过程。伊斯兰教传播到中国,也必然面临本土化的问题。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它的这一特征是由三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的:一是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二是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三是伊斯兰教的回族化。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和回族化既有区别,又是一个过程中联系紧密的两个方面,是共同在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展开和完成的。
一、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最初形态可以追溯到黄帝大联盟的建立。其后经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持续努力,建立了一套体制完备的宗法制度。宗法制度有两大核心要素,一是血缘,一是宗教。
就血缘而论,整个天下都具有亲缘关系。这种关系不一定具有历史的真实性,但却具有历史的认同性和传承性。《魏书·序纪》记载:“昔黄帝有子25 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这种“华夷一家”的“大一统”观念在中国各民族中具有相当普遍的认同性,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得以形成的基本观念。
就宗教而论,通过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以神道设教为目的,在宗法制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宗法性国家宗教,完成了国家化的文化建设。宗法性国家宗教,成为夏商周各王朝统治的最高意识形态。
春秋时期,孔子祖述三代,继承以周公为大成者的古代文化,形成了具有人文学术性质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一方面承续宗法性国家宗教,并和宗法性国家宗教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儒家文化和宗法性国家宗教内外一体,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最高意识形态,贯穿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1]。
这一意识形态,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是排外的,而是包容和接纳的。具体而言,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在中原王朝内部对待各种文化的包容态度。谭其骧先生论证指出:“中国在一个国家里,汉族在一个民族里,一贯对待不同文化采取容许共存其荣的态度。”[2]
二是在整个王朝体系内,对待各民族文化的包容态度。《礼制·王制》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3]
综合而论,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环境是:追求国家政治的统一性,以儒家文化和宗法性国家宗教为最高意识形态,允许其他各种文化多元共存其荣。中国社会的这一政治文化环境,是各种外来思想文化、各民族进入中国后落地生根、发展演化的基本前提和有效保障。因此,探讨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和回族化,必须首先明了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环境。
二、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伊斯兰教于唐永徽二年(651年)始传入中国。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方式有两个特点:一是和平的方式;二是民族与宗教结合为一体俱来,具有外来性和内传性特征。依据这两点,探讨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论述。
首先,信仰伊斯兰教的外来民族成员成为中国人。从世界上各种宗教的传播历史来看,一种宗教在异域传播的实现,首先在于异域人民对该宗教的信仰。信仰伊斯兰教的外来民族成员进入中国的主要目的有四:一是贡使;二是经商;三是追求学问;四是因政治、军事的缘故迁徙中国。可以说,信仰伊斯兰教的外来民族成员进入中国的目的,主要不在传教。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形看,它也没有专门从事吸纳中国其他民族成员皈依伊斯兰教的事业。两相结合,说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中国穆斯林自身的需要,走的是内部传播的道路。这是伊斯兰教与佛教及基督教在中国发展不同的地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这种发展,既然没有吸纳中国人皈依伊斯兰教的任务,也就基本不存在中国化的要求和需要。相反,恰恰是盛唐时期中国文化的繁盛,中国文化在当时世界的地位和影响,使其成为各民族慕求的对象,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甚至阿拉伯人也不例外。他们进入中国的目的之一即在追求学问,“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寻求”。就史实而论,这一时期穆斯林的汉文化程度达到相当的水平——其代表人物如李彦昇——这在一定意义上为后来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唐宋时期留居中国的穆斯林,被称为蕃客,他们在中国集中居住的地方被称为蕃坊。唐朝廷对蕃坊的管理方法是“因俗而治”,即“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4]。所谓的“本俗法”,即“一切皆能依《可兰经》、“圣训”及回教习惯行事”[5],所谓“以法律论”,即依中国法律判处。唐宋时期,穆斯林蕃客一方面处在长期不断地往返迁徙之中,另一方面往返迁徙的长期性也使长期定居的现象逐渐增加,其突出事例是“五世蕃客”的出现。但即便如此,他们也依然是蕃客,即外国人,传播伊斯兰教也依然是蕃客的需要。据史料记载:
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贡。……开元初,遣使来朝……。其使谒见,唯平立不拜,宪司欲纠之,中书令张说奏曰:“大食殊俗,慕义远来,不可置罪。”上特许之。……所司屡诘责之,其使遂请依汉法致拜[6]。
这段材料说明,大食贡使因为伊斯兰教的信仰,如同“沙门不敬王者”的佛僧一样,对各国统治者不行跪拜。后来由于唐廷的诘责,最终适应了中国文化跪拜皇帝的礼仪规范。但改从“汉法”跪拜中国皇帝的穆斯林蕃客,在宗教仪式上却不为中国皇帝祈祷,在整个唐宋时期,他们只“为本国君王行祈祷”[7]。对此,中国政府也再没提出要求,这说明伊斯兰教只是蕃客的需要,还没有成为中国人的需要,中国政府自身也还没有产生出要求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需要。
蒙古帝国的建立,一方面打破了各个国家之间原有的界限,一方面使有些国家不复存在,如阿拔斯王朝的覆灭。在这一背景下,元王朝把其治下的各族人民分为四等。四等公民的划分,虽然多了一个等级化的界限,但却少了一个国家化的界限,四等公民都是中国的法定成员。对这一变化,过去学术界多对元王朝民族等级制进行批评和指责,却很少对其打破国家界限的作用进行评述。元王朝打破境内各民族国家化的界限这一事实,对回回人在中国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方面,元王朝于宪宗蒙哥时(1252年)编籍“壬子籍户”中设立“回回户”,又令探马赤军“随军入社,与编民等”。这从法律上使回回人结束了“蕃客”的历史,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人”。明王朝上承元制,下诏:“……色目人既居我土,即吾赤子,有才能者一体擢用。”[8]另一方面,阿拔斯王朝覆灭后,在中国的回回人失去了唐宋时期蕃客“为本国君王行祈祷”的依凭,进而迅速认同于“中国人”。伴随着中国政府和回回人对“回回户”的双向认同,回回人的中国人身份得以完全确立。
其次,回回人成为了中国人,回回人信仰的伊斯兰教随即面临着中国化的选择。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完成,一是表现在社会政治权利方面,二是表现在宗教思想方面。
元代,如何有效治理大批来华回回人是元朝廷政治建设中的大事。元朝廷对回回人进行治理的机构叫做回回哈的司[9]。哈的司的政治职能主要有三:一是“掌教念经”。掌教主持开展各项宗教活动,这是伊斯兰教的本质工作,只要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形态存在,它的这一活动就必须开展,不存在民族和国家的界限。二是为君主“祝寿”和“祈福”。穆斯林在聚礼时为君主祈祷的惯例始于阿拔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时代。唐宋时期,穆斯林蕃客在蕃坊聚礼时为其国王苏丹祈祷。元代东来的回回人乐居中土,“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不复回首故国也”[10]。在宗教仪式上,他们也把为其国王苏丹祈祷变成为元朝皇帝祝寿、祈福,至正八年(1348年)定州《重建礼拜寺记》碑文记载:“有古刹寺一座,堂宇止三间,名为礼拜寺,乃教众朝夕拜天,祝延圣寿之所”[11]。穆斯林祝寿对象由其国王苏丹变为中国皇帝,是与他们中国人的国家身份认同相一致的①。当然,这种转变,不止是穆斯林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统治者的政教需要。元世祖忽必烈说:“我对四大先知(耶稣、穆罕默德、摩西、释迦牟尼)都表示礼敬,恳求他们中间真正在天上的一个尊者给我帮助。”[12]穆斯林也以“祝延圣寿”“为国祈福”相呼应。这种现象,是回回人变为中国人后,国家意识成功转型的重要标志。三是掌回回人“刑名、户婚、钱粮、词讼”,这是伊斯兰教宗教组织社会化的重要表现,或者说是治理回回人社会的政治权力[13]。伊斯兰教的这一政治权力,是其社会化发展的产物。在元代,它的这一政治权力随着元廷中央集权的加强,开始被削弱乃至取消。至大四年(1311年)“罢回回哈的司属”,据《大元通制条格》卷29“词讼”载:“至大四年十月初四日,中书省钦奉圣旨:‘哈的大师每只教他们掌教念经者。回回人应有的刑名、户婚、钱粮、词讼、大小公事,哈的每休问者,教有司官依体例问者。外头设立来的衙门,并委付来的人每,革罢了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至皇庆元年(1312年)十二月,又“敕回回哈的如旧祈福。凡词讼悉归有司,仍拘还先降玺书。”《元史》卷102“刑法志”载:“诸哈的大师止令掌教,回回人应有刑名、户婚、钱粮、词讼并从有司问之。”这一过程几经反复,至明朝最终完成,明廷规定:“回教制度至中国仍不改,领教均有专名。明室以其标奇立异,诏命废止,以后统称掌教者为‘老师傅’。”[14]至此,伊斯兰教“教坊”领教掌管回回人“刑名、户婚、钱粮、词讼”的政务权力被剥夺,仅剩“掌教念经”的教务权力。另外,回回人“祝延圣寿”的宗教仪式获得继续保留,这成为进一步强化回回人国家认同意识的方式,也有效促进了回回人和中国社会的进一步融合。
在宗教思想方面,伊斯兰教遵行“以儒诠经”“附儒以行”。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内地,从唐代迄至明代中叶800年间,伊斯兰教在中国教义不明,教名未定,不见典籍及著作,亦无汉文译著,是个侨民的宗教,或外来民族的宗教[15]。明代中叶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开始出现了中国回族学者自己选用的典籍,以及汉文译著,如胡登洲始兴的经堂教育和王岱舆创始的汉文译著活动。对于这场被称为“中国伊斯兰教的复兴运动”的意义,有学者指出:“自明末清初开始出现的中国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及以后形成的大规模的译著活动,使伊斯兰教在宗教理论上涂上了中国的色彩,而这一宗教理论变化的实质在于:中国的伊斯兰教大量吸收和改造了儒、释、道各家的概念,摄取和运用了儒、释、道各家的思想,从而完成了伊斯兰教在教义学上同中国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思想的结合,并使伊斯兰教的教义得到了丰富和发展。”[16]
经堂教育和汉文译著是有内在联系的。由胡登洲始兴的经堂教育,选定伊斯兰教典籍,创兴经堂语,完成了阿拉伯语适应汉语的转型,为大分散于中国各地的穆斯林起到了教育规范化、体制化的作用。由于中国穆斯林所处的地域及其文化之间的差异,又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大致而言,有陕西学派、山东学派、云南学派、兰州学派、河州学派、东南学派。其中,东南学派,以王岱舆、刘智为代表,用汉文注释、解说伊斯兰教经典。
以王岱舆、刘智等人为代表的译著热潮,确立的原则是融儒学伦理思想和伊斯兰教教义为一体,他们提出:“无论何教,在于以儒律之,近于儒则为正,远于儒则为邪。斯千古不刊之论矣。”[17]明清之际被誉为“学通四教”的王岱舆在其所译的《清真大学》中“会同东西”,把孔圣与穆圣相提并论,“用儒文传西学”,以伊斯兰教教义“与孔孟之言相印证”,提出忠于真主、忠于君、孝于亲是“人生之三大正事”。王岱舆的这种思想,刘智在《天方典礼》中进一步阐述说:“君者,主之影。忠于君即所以忠于主也,”“一时不心于君,即为不贤;一时不合于君,即为不忠。”又说:“王者,代真主以治世者也。王者体主,若影之随形,”故而“念主而忘君,非念主也,念君而忘主非念君也。”在《天方典礼择要解》中,更把儒家的群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等五伦称为“五典”,以此作为中国伊斯兰教的伦理原则,与“五功”并列。王岱舆和刘智通过对伊斯兰教的改造,使伊斯兰文化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环境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并在回族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明清之际形成的门宦制度就带有深刻的中国文化的烙印。在回族民众的思想意识里,甚至中国的统治者(虽然是汉族,非穆斯林)就是真主在中国的代理人②。
经过胡登洲、王岱舆、刘智等伊斯兰学者的通力努力,最终完成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使命,为回回人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并不意味着伊斯兰教的衰落或消亡,而是意味着伊斯兰教在异域文化背景中的新生,即它依然保持了伊斯兰教最本质的思想和教义,保持其独立的品性,使伊斯兰教依然是伊斯兰教。虽然王岱舆、刘智等学者已经把“忠君孝亲”之义完全纳入伊斯兰教教义体系之中,但这种改变,是在首先肯定“认主独一”的基础上进行阐释的。
伊斯兰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不像佛教那样,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曾引起中国政府的“禁教”之举,而是相对比较平和的,正如陈垣先生谓:“明人对于回教,多致好评,政府亦从未有禁止回教之事,与佛教、摩尼教、耶苏教之屡受政府禁止,其历史特异也。”[18]之所以会如此,一方面如前文所讲其传播方式是和平的和民族的特点之外,还有对儒家伦理道德“忠君孝亲”思想的容纳和尊崇,正如王治心先生所说:伊斯兰教“在中国,更有一发皇的原因,就是对儒家思想的容纳与尊崇。……尤其特别是尊敬孔圣人,读儒书应科举,以孔子的伦理道德为最高道德”[19]。
在伊斯兰教以孔子的伦理道德为最高道德的同时,历来汉译经著的作者们,遵循的一个不变的原则是:始终把“认主独一”“忠于真主”等六大信仰作为基本信仰,把“五功”作为最高行为准则去奉行,即所谓“会通诸家而折衷于天方之学”[20],“采精挹萃,辑数经而为一经”[21]。最终形成了以伊斯兰教为核心内容,容纳中国儒、释、道各种文化的新体系。
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过程,以“认主独一”的基本信仰作为最高准则,始终保持着自身的本质属性;以成为中国人的回回人为基本信仰群体,具备了伊斯兰教的传播获得中国民众信仰的基本条件;处在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地与儒家伦理道德文化保持高度的一致,获得了中国统治者和民众的极大认可。三相结合,最终使伊斯兰教实现了中国化,成为了中国化的伊斯兰教。
三、伊斯兰教的回族化
伊斯兰教的回族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伊斯兰教的方式表达回族的特殊性,包括饮食、衣服之制、冠婚丧祭仪式、社会制度等等;二是以国家认同为基础,使以伊斯兰教方式争取民族权利的活动限制在国家政权体系之内。
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是一种社会生活化程度极高的宗教。中国文化对各民族文化、各外来宗教都允许其多元共存,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也因历史的缘由,对其他文化担负有一种教化的使命,这便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用夏变夷”观念。回族的伊斯兰教信仰,虽然在国家文化层面被中国政府待以宽容和扶持,但在社会生活层面,却往往会和汉族发生文化方面的矛盾和冲撞,如回族在饮食、衣服之制、冠婚丧祭之典方面的独特性,遭到了汉族知识分子的猜忌,甚至请求统治者予以取缔,如顾炎武、陈世倌、鲁国华等。顾炎武说:“惟回回自守其国俗,终不肯变。结成党伙,为暴闾阎,以累朝之德化,而不能驯其顽扩之习,所谓食桑葚而怀好音,固难言之矣。”[22]这种来自汉族知识分子的责难,有其历史的惯性。从中国历史来看,但凡进入中国的各民族成员,几乎都遵循了“用夏变夷”的规则,经过中国文明的洗礼而加入到汉族大家庭之中。唯独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人例外。回回人进入中国后长期生活在汉族社会之中,一方面和汉族社会发生着日益紧密的联系,与汉族在思想文化和社会习俗方面有高度的一致(相对于周边各民族)。一方面也和汉族社会产生了日益明显的区别,在思想文化和社会习俗方面保持了自己的独特性(相对于进入中国社会的各民族)。于是,回回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逐渐在内部形成明确的自我意识,并与外部明确别异。
尽管汉族知识分子以“用夏变夷”的观念对回族的社会习俗提出质疑和批评,但这种批评恰恰证明回族习俗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具有民族认同的象征性意义。对此,清朝统治者和回族学者均从民族意义上进行了阐述。雍正皇帝针对鲁国华的奏折指出:“回民之自为一教,乃其先代相沿之土俗,……其来已久矣。历观前代,亦未通行禁约,强其画一也。”[23]清代回族学者金天柱认为:“今子言用夏变夷,恐亦未详所言之宗旨。使吾教之道无君臣,无父子,则当变;无夫妇,无昆弟、朋友,则当变;无贡税,无长幼,无仁义礼智,不待子言,宜变之久矣。今回教于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贡税、长幼何如者?而何变之有?而子乃曰,回教之人未读儒书,流于拘执,何未之思也?尝闻大家祖先,莫不垂有家训,以示子孙。吾教守祖训兢兢。”[24](P34)一方面伊斯兰教是回族的“先代土俗”,和“祖先家训”,一方面回族是“吾教守祖”,这说明伊斯兰教是回族不同于汉族的文化特征,具有回族对内认同和对外别异的象征性价值和意义。
回回人成为中国人后,在其民族尚未形成之际,伴随中国政府中央集权加强的过程,伊斯兰教在唐宋元时期的政教合一组织到元末明初被改造成单纯的宗教组织。单纯的宗教组织,有助于回回人社会习俗的维续,为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保留了星星之火。这种现象持续发展到清代,清政府一方面承认伊斯兰教乃回民“先代相沿之土俗”,对回民“一视同仁”,“要在地方官吏不以回民异视,而以治众者治回民”;一方面在政治上否认其为一个特殊群体,要求“回民者亦不以回民自异,即以习回教者习善教。则赏善罚恶,上之令自无不行;悔过迁善,下之俗自无不厚也。”若回民以特殊群体自诩并演化为具体的社会行为,则“倘自谓别为一教,怙恶行私,则是冥顽无知,甘为异类。宪典俱在,朕岂能宽假乎!”[25]
明中叶以后,回族逐渐形成。在回族形成的过程中,回族的民族意识逐渐升华和强化。在回族民族意识的作用下,胡登洲首先创始了经堂教育,王岱舆继起创兴了汉译经著。经堂教育和汉译经著既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又各自适应了不同的文化环境。在经堂教育和汉译经著的持续发展下,使伊斯兰教和汉文化在回族社会实现了相当的普及,从而提高了回族自身的文化水平,加强了回族内部的联系。随着伊斯兰教苏非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并进一步和回族社会的宗法制结合,于是出现了具有回族特色的门宦制度。
在各门宦相继兴起发展的过程中,门宦间时常出现争教的现象。回族社会的争教活动和清廷的封建集权体系逐渐发生矛盾,并进一步引发冲突,乃至斗争,这便是清代的回民起义。回民起义不同于汉族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一般是以推翻旧政权重建新政权为目的,回民起义则只在争取自己的民族权利,而不欲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权。这是具有国家意识的回民起义的本质特征。在回民起义中,回族一方面争取自己的民族权利,一方面又努力申辩他们是忠于国家的。尤其是1862年的西北回民大起义中,回族反复申明“非敢另有异谋”[26],“回教之来中夏自隋唐始,代为编氓,绝无异念”[24](P152)。“非敢另有异谋”和“绝无异念”的意思是相同的,指没有推翻清廷的统治而建立民族政权之意。由此可见,在回族的意识中,国家认同是首先形成的,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寻求自己民族权利的表现方式和实现途径也是在国家认同的范围内表达和进行的。
四、结 语
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和回族化,是在中国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展开和完成的。中国的政治文化环境,在政治上表现为统一性或一体性,在文化上表现为以儒家文化和宗法性国家宗教为最高的意识形态,且对其他各种文化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允许它们共存其荣。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是宗教与民族一体俱来的。唐宋时期,进入中国的穆斯林被视为蕃客,他们也以蕃客自居,伊斯兰教只是为了满足他们自身的需要,还不存在中国化的需要。
元代,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回回人转变成了中国人,相应地,伊斯兰教为了适应回回人的自身需要,就需要发生转型。这种转型,就是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这一过程经过元明两代,至明末清初经堂教育和汉译经著的系统化出现才告完成。
伊斯兰教在宗教层面发生中国化转变的同时,也面临着民族层面回族化的转变。当然,中国化和回族化不一定是同步的,但一定是有密切联系的。
伊斯兰教的回族化,既有对伊斯兰教社会习俗的保持和强调,也有以伊斯兰教强化回族意识的内在需要和发展。前者具有传承性,表现为先代土俗和祖先家训,后者具有创新性,表现为具有回族特征的门宦制度的形成。
在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是首先发生的,主要表现为国家认同意识;伊斯兰教的回族化是随之发生的,具有回族认同意识。回族认同意识和国家认同意识既有区别,亦有联系。区别在于二者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观念形态,联系在于回族的民族认同意识是以国家认同意识为基础,在国家认同的范围内寻求表达和实现的。
注释:
①这种现象在阿拉伯帝国的历史上,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例如“在麦尔夫,达乌德命令人们在星期五聚礼时诵念他的姓名,突格里勒·贝格则在尼沙浦尔要人们在星期五聚礼时诵念他的姓名”。(德)卡尔·布罗克尔曼著:《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第205 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类似记载,在该书中多处提到。
②小时候,我爷爷对我说:“毛主席是真主派来治理中国,解放回民的”。这一点,跟藏族人认为中国皇帝是“文殊菩萨”的道理是一样的,都是宗教领域国家认同的表现方式。
[1]吕大吉.泛论宗教与文化的关系[A].从哲学到宗教学——吕大吉学术论文选集[C].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803—804.
[2]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A].王元化.释中国:卷3[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633—1635.
[3]礼记·王制第五[Z].
[4]唐律疏议:卷6[A].杨怀中,余振贵.伊斯兰与中国文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594.
[5]苏烈曼游记[A].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C].北京:中华书局,2003:759.
[6]旧唐书:卷198·大食传[M].
[7]周咨见闻录:卷1[M];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C].中华书局,2003:759.
[8]明实录·太祖实录:卷34[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
[9]邱树森.中国回族史[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312.
[10]周密.癸辛杂识·续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1]余振贵,雷晓静.中国回族金石录[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14-15.
[12]张声作.宗教与民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312.
[13]邱树森.中国回族史[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余振贵.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
[14]薛文波.明代与回民之关系[A].李兴华,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参考资料选编(1949—1991)[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15]杨怀中,余振贵.伊斯兰与中国文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132.
[16]曹琦,彭耀.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244.
[17]清真释疑补辑·唐晋微叙[Z].
[18]陈垣.回回教入中国史略[A].李兴华,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参考资料选编(1949—1991)[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19]赵林.儒家伦理对三大外来宗教的同化与拒斥[J].中州学刊,1997(1).
[20]刘智.天方至圣实录·著书述[Z].
[21]刘智.天方性理·袁汝琦序[Z].
[22]顾炎武.日知录·吐蕃回纥条[Z].
[23]清世宗实录:卷94[Z].
[24](清)金天柱.清真释疑[M].海正忠,译注.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34.
[25]清世宗实录:卷80[Z].
[26]平回方略:卷123[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