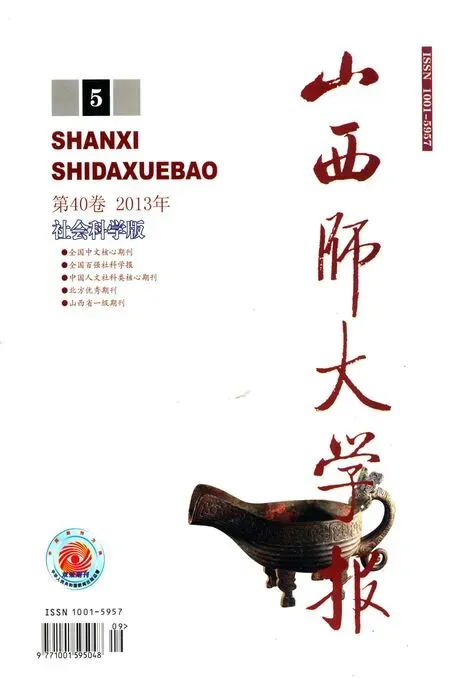人大代表选举相关法律的社会性别分析
2013-04-12张永英
张 永 英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北京 100730)
一、问题的提出
议会女议员的比例是联合国用于衡量各国性别平等情况的主要工具和“性别不平等指数”*根据联合国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性别不平等指数反映了三个维度的性别差距:生育健康、赋权和劳动力市场。生育健康方面的指标包括:孕产妇死亡率、(15- 19岁)青少年生育率;赋权方面的指标包括:接受过中等及以上教育的男女人口、议会议员中的男女比例;劳动力市场方面的指标包括:男女的劳动参与率。的核心指标之一。就中国来说,人大女代表比例不仅是衡量妇女参政水平的核心指标,同时也是反映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标志。与世界女议员比例不断提高的趋势相比,中国人大女代表的比例在近30年来呈现停滞不前的徘徊局面,2013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女代表的比例为23.4%,虽然比上一届提高了2.1个百分点,但也仅比改革开放之初的1983年六届人大(21.2%)提高了2.2个百分点。中国人大女代表的比例在女议员比例的国际排名也不断下降,从1994年的第12位,下降到2013年3月的第54位*数据来源于国际议会联盟网站,http://www.ipu.org/wmn- e/classif.htm,下载于2013年5月20日。,妇女在人大中的参与比例成为关心妇女参政的各界人士关注的焦点议题。
从促进妇女参政的国际趋势来看,在国家法律和政党政策中规定妇女参政比例(即配额制)被公认为是促进妇女参政的最有效途径之一,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配额制的措施促进妇女参政。中国也非常重视妇女参政问题,一直以来也采取各种积极措施促进妇女参政,从《宪法》到《妇女权益保障法》、《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选举法》等,都有对妇女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人大女代表名额问题的规定。这些规定的具体内容如何,近30年来其内容有没有变化,是否能够保障妇女在参与人大中的实质性平等?都是值得学者和行动家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从以往国内的研究来看,虽然对这一问题关注得较多,但研究成果仅有数篇论文涉及人大女代表问题。如2007年浙江省妇联通过对浙江省部分人大女代表的调查和访谈,描述了人大女代表的参政议政状况,但对原因的分析比较简单和主观,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持。[1]66—72缪珍南从修订《四川省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中是否写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时,女代表比例应不低于25%”这一条文的争论入手,论证了规定人大女代表比例的意义和可行性,并提出相关建议,但对现行法律的内容没有进行概括和分析。[2]18—19邓飞的硕士论文分析了人大女代表参政的制度困境,从妇女组织、人大选举过程等分析了限制妇女参与各级人大的诸多障碍。[3]总的来看,这些研究在分析有关人大代表选举法律中的性别内容时不够全面和深入,比如没有将地方法规与国家法律进行比较,较少从历史层面回顾有关法律规定的发展变化。本文拟通过全面梳理有关人大选举法律中有关妇女代表名额的规定及其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演变,并通过与地方法规的内容比较,从性别视角分析这些法律规定中存在的问题,以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二、人大代表选举相关法律中有关妇女代表名额的规定
涉及人大女代表内容的主要相关法律,既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也包括《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及各省根据自身情况进一步具体化的选举法实施细则和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等,同时全国人大关于代表名额问题的决定中也有相关内容。
(一)国家法律中的相关内容。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历次《选举法》的修订,可以看出其中有关妇女代表名额的内容经历了从无到有、重要性逐步上升的过程。1979年、1982年、1986年的《选举法》中没有妇女代表名额的专门规定,只是规定了“使各民族、各地区、各方面都能有适当数量的代表的原则”,性别并没有在其中作为代表名额分配的一个分类标准。1995年和2004年的《选举法》第六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对妇女代表名额问题作了原则性规定。2010年《选举法》相关内容表述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基层代表,特别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这一表述把妇女代表比例问题上升到代表性的高度,正式将性别作为一个重要分类标准。
改革开放以来,在历届人代会换届前一年的人代会上,都会做出关于代表名额分配问题的决定,20世纪80年代,这一文件中没有关于妇女代表名额的内容。1992年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作出的《关于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妇女代表的比例不低于七届的比例。”1997年八届人大五次会议《关于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中相关的表述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妇女代表的比例应高于八届的比例。”2002年九届人大五次会议关于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问题的决定中,有关妇女名额的表述与八届相似。2007年十届人大五次会议做出突破,第一次规定了全国人大女代表的具体比例,即“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妇女代表的比例不低于22%”。2012年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作出的有关规定比2007年有所倒退,又回到了“妇女代表的比例应当高于上届”的原则性规定,对于出现这一变化的原因没有权威的解释,不过与十一届人大女代表比例没有实现22%的要求所引发的争论和质疑不无关系。从历届人大关于代表名额问题的决定的回顾可以看出,有关妇女代表名额问题的规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低于上届”到“高于上届”,再到规定具体比例的过程。
《妇女权益保障法》于1992年颁布施行,2005年作了修正。作为保障妇女权益的一部专门法律,1992年该法即对人大女代表的数量问题作出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第十条第 2款)2005年这一表述变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国家采取措施,逐步提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妇女代表的比例。”(第十一条第2款)这种表述的修改其实质内容并无变化,只是语气更为积极主动。
(二)地方法规中的相关内容。地方法规作为中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充分发挥地方的能动性,使国家法律进一步具体化和可操作化。各省的选举法实施细则和妇女法实施办法对于国家法律中的相关规定作了各种不同的解读,具体包括:没有妇女名额的规定、照搬国家法律(即适当比例)、规定候选人中的妇女比例、规定人大代表中的妇女比例、规定人大常委中的妇女数量等。这些积极或消极的解读,对于保障人大女代表的比例有着不同的影响。
从省级选举法实施细则来看,没有妇女名额内容的省份有甘肃、广东和天津等,安徽、湖北、上海等大部分省份实施细则中在有关妇女代表名额方面照搬了《选举法》的相关表述,基本上为“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但也有部分省份在这方面比国家法律有所突破,比如云南、河北、黑龙江、江苏、江西、新疆等省份规定了人大代表候选人中的妇女比例,这一比例的范围从25%到30%不等,比如《云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2011年修正)》第七条规定:“代表候选人中妇女的比例应当占30%以上,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河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2010年修正)》中规定:“在代表候选人中,妇女所占比例应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并逐步提高比例。”(第九条)而西藏则就妇女代表的比例作了明确规定,2011年修正的选举法实施细则规定:“妇女代表比例不低于20%,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第四条)
从省级妇女法实施办法来看,所有的省级法规都涉及了与妇女代表比例相关的内容。北京、上海、广东、海南、内蒙等省份与《妇女公益保障法》的规定相类似,即规定“适当数量/比例”,比如《海南省妇女权益若干规定》(2008年)第六条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有超过20个省份的妇女法实施办法规定了人大女代表候选人的具体比例,大部分规定了30%的比例,但也有部分规定25%以上,个别地方规定最低到20%,有的省份省、县、乡等不同级别规定的比例有所不同,比如黑龙江省规定:“正式代表候选人中妇女代表候选人的比例省、市两级不低于30%,县、乡两级不低于25%。”(第七条)湖北省规定:“代表候选人中妇女的比例应当占百分之三十以上。”(第八条)辽宁省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妇女代表候选人应当不低于提名人数的28%。”(第五条)《重庆市妇女权益保障条例(2008年修正)》中规定:“市和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在换届选举时,妇女代表候选人比例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在换届选举时,妇女代表候选人比例不低于百分之二十。”(第十二条)还有贵州、吉林、江西、宁夏、西藏等部分省份规定了人大代表中的妇女比例,但相对于候选人中的妇女比例,有关人大代表中的妇女比例规定的数值较低,基本上在22%或20%。比如贵州省的妇女法实施办法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妇女代表的比例应当逐步提高。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中妇女代表的比例一般不低于22%;县级、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女代表的比例一般不低于20%。”(第十条)另外,与省级选举法实施细则不同,一些省份的省级妇女法实施办法还涉及了地方人大常委会中的妇女名额问题,主要有两类规定:一类是原则性规定,比如适当数量、一定数量等,吉林省规定:“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女性。”(第十条)宁夏自治区规定:“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应当有一定数量的妇女。”另一类是具体数量,如黑龙江省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中至少有一名妇女。”(第八条)四川省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成员中应当有一名以上女性。”(第十条)
三、对人大选举相关法律的社会性别分析和对策建议
有关人大选举的法律法规为更多妇女进入各级人大提供了法律保障,但同时这些法律规定还存在有待完善和改进之处。从历史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人大代表中妇女名额规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原则到具体的过程。整个20世纪80年代,相关法律中没有把性别作为人大代表名额分配的一个标准。但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人大代表选举采取差额选举的方式进行,20世纪80年代后期,各级人大女代表的比例在差额选举中明显下滑。因此,如何保障包括人大女代表比例在内的妇女参政比例问题,受到了各方的广泛关注,如20世纪90年初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全国人大有关代表名额问题的决定,包括随后的《选举法》等,都涉及了这一问题,并做出了原则性规定。随着人大女代表比例长期的停滞不前,妇女界的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以及相关部门一直致力于推动人大女代表比例的提高,在这一背景下,2007年全国人大有关代表名额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了人大女代表的具体比例。
但从总体上来看,国家法律对人大代表中妇女名额的规定过于原则。改革开放的30多年间,《选举法》历经多次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也经修改,但有关妇女代表的名额问题,仅仅做出了原则性规定。虽然在最近一次《选举法》修正过程中,妇女运动者极力推动写入人大女代表的具体比例,但最终仍未能成功。只有全国人大有关代表名额问题的决定作了相对具体的规定,比如“不低于上届”、“高于上届”等,并于2007年首次提出了人大女代表的具体比例,但由于这一规定没有相关的配套措施的保障,比如如果没有达到要求,该如何惩罚或者补救等,所以这一规定具有更多的倡导意义。
地方法规对于国家法律的解读积极与消极并存。国家法律规定的原则性,为地方法规的解读留出了更多空间。由于地方的能动性,地方法规可以使国家法律更为具体和可操作,也可能做出比国家法律更为积极的规定。但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各地对国家法律做出了不同的解读,有的更为积极,也有的不够积极。比如大多数省份的选举法实施细则都做出了与《选举法》相似的规定,只有少部分省份做出了更为具体和量化的规定。由此可见,各地应该集合各种力量,推进省级地方法规做出更为积极量化的规定,以弥补国家法律原则性有余、操作性不足的缺陷。
省级的妇女法实施办法比选举法实施细则规定更为积极。从上文的梳理可见,在有关人大女代表名额的问题上,省级妇女法实施办法的规定总体上比选举法实施细则更为具体和量化。选举法实施细则中有几个省缺乏有关妇女代表名额的内容,而妇女法实施办法则全部都写入了相关内容;大部分省的选举法实施细则都是照搬《选举法》中的规定,仅有少部分省份规定了人大代表候选人中的妇女比例,而大部分省的妇女法实施办法都规定了人大代表候选人中的女性比例,仅有少数几个省份做出了原则性规定;仅有西藏自治区的选举法实施细则规定了人大女代表的具体比例,有5个省份的妇女法实施办法规定了人大女代表的具体比例;另外,许多省的妇女法实施办法中还涉及了人大常委会中的妇女数量问题。这说明专门的妇女法律更容易做出积极的规定,但其影响力相对较弱。
虽然有关人大代表选举的相关法律中做出了人大女代表名额的规定,为人大女代表的比例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法律上的平等与现实中的平等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从立法上来说,有关人大选举的法律总体上缺乏性别敏感,是影响妇女参与人大的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没有对选举委员会的性别结构做出规定。选举委员会作为组织人大代表选举的工作机构,在人大代表选举过程的各个环节保证女代表当选,都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现有的性别结构,各级选举委员会中普遍以男性为主体,女性所占比例偏低。这将不利于在选举的各项决策中做出实质上使男女候选人当选机会均等的决策。
其次,人大女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分配不够具体。虽然法律规定了人大代表候选人中的妇女名额或者比例,但并没有对妇女名额具体如何分配做出规定。这将有可能导致在实际操作中不按照法律的要求保障女代表的比例。
再次,现有的选区划分方式不利于女代表的当选。《选举法》规定:“选区可按居住状况划分,也可以按生产单位、事业单位、工作单位划分。”(第二十四条)按生产和工作单位划分容易造成选举中的不平等:因单位有行政领导关系,选举易行政化。人大代表一般由单位的一把手或是二把手担任。而女性在单位中能做到一把手或者二把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女性难以当选人大代表也就不难想象了。[3]31
根据对人大代表法律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对完善人大代表法律,保障妇女与男性平等参与人大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人大选举相关法律中对于妇女代表名额的规定更为具体和量化。建议全国人大有关代表名额问题的决定中规定妇女代表名额的具体比例,比如“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妇女代表的比例不低于23%。”建议修改《选举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时,写入人大女代表的具体比例,比如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妇女代表的比例不低于30%,并逐步提高”。
第二,增强人大选举相关法律的性别敏感。在《选举法》或省级选举法实施细则中规定选举委员会的性别结构,比如“选举委员会成员中,妇女占30%”。在地方选举法实施细则中明确妇女代表名额的分配,可以参考少数民族代表名额的分配机制。探索改革现有的选区划分方式,使得男女候选人具有同等的当选机会。
[1] 浙江省、市人大女代表、政协女委员参政议政现状研究课题组.浙江省、市人大女代表、政协女委员参政议政现状研究[J].资料通讯,2007,(7,8).
[2] 缪珍南.关于地方性法规中规定人大代表女性比例的思考[J].四川省情,2008,(3).
[3] 邓飞.人大女性代表参政困境的制度分析[D].北京:中央党校硕士论文,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