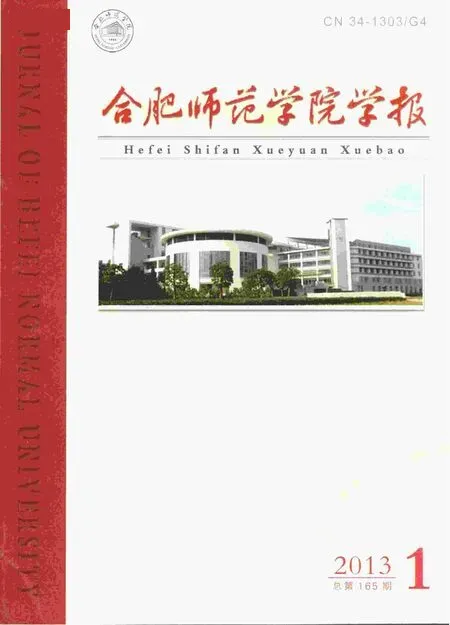学统的转型与道统的延续:转型视野下的《人间词话》
2013-04-12张硕
张 硕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215123)
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谈到王国维的治学影响时,说其“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1]219。《人间词话》正是一部具有这样示范作用的批评著作。学统与道统是古代学术的两大基本要素,由古代向近现代的渐变,必然要在这两要素上有所体现。本文将从这两大要素出发来考察《人间词话》的示范作用,并对其价值与意义做一番探讨。
一、学统与道统
统,既指传统,又指系统。本文学统与道统之“统”侧重于传统。成中英认为:“传统是历史性的存在,尤其具有现实的影响力,构成伽达玛所谓的‘有效历史’。因之,它不必只是历史,而有或多或少的规范权威,但其规范力量不一定来之理性自身的说服力,而是来之人的群体情感与习惯。”[2]当然,传统与系统是密切联系的,“传统可以用来界定系统、发展系统、实现系统,同时也可以包含一定的系统成分”。[2]
学统与道统主要由知识阶层来传承。学统指知识之学的传统。学统根植于本民族的“文化生命”。中国人的“文化生命”里较为缺乏思辨、逻辑的因子,正如王国维所指出的:“而故我中国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析二者皆我国之所 不 长”[3]386,“夫古人之说,固未必悉有条理”[3]391。因此,古代学统以经验为主体,“只停在原始形态(感觉的、实用的),未能发展至‘学之形成’的境地。此即未发展至科学形态也。从认识主体方面说,即‘智’未发展至足以成‘知识之学’之‘知性形态’也。”[4]89王国维也认为:“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3]386
道统是指求“道”的传统。本文的道统不同于起始于韩愈、成熟于朱熹的儒家正统之“道统”,而是站在了一个更加宏观的、更形而上的角度。在古代,儒释道三家各有其“道”,但在知识阶层中占主流的是儒家德性之学,其他两家起辅助作用。但这三家有共同的内在结构,即它们的关注中心是“人”,它们的路数是内在超越,求“道”的过程也就是通过“工夫”达成某种人格的过程。由此可见,道统实质上是一种“生命超越哲学”。牟宗三说:“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所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5]12道统精神与这种中国哲学精神是一致的。从外在看,以儒家为主的道统赋予知识阶层以一种忧国忧民的责任意识和以德性之学改造社会的理想。当然,这与内在部分相比,多因缺乏实际有效的行动而显得无力。
学统与道统是密切相关的。在古代,学统多依附于道统,正所谓“文以载道”,它没有完全的独立性。道统的内在精神往往成为学统的最高价值,冯胜利指出:“‘知人’是国学之本,是传统学术的最高标准、知识的终极境界。”[6]26
二、《人间词话》与学统的转型
在不尚逻辑的学统影响下,中国古代文论多呈现为直觉感悟的形式,本来探讨文艺本质规律的“论”也成了“诗”。例如《二十四诗品》,它用“诗”营造了二十四个意境,即二十四种风格;完全是用“诗”来论“诗”了。只有少数深受佛学浸染的学者,才写出了较有系统的文论,最为突出的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但佛学本身在中国也出现了深刻变化。原始佛教本以思维严谨精湛著称,但它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最终演变成了“不立文字,直指心源”、颇有“诗性思维”的禅宗。这样的学统,难以促使学术系统化、理论化。然而,这种情况在《人间词话》中已发生了显著变化。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他正好处于“古今中西”之间。他的学术活动所采取的方法,其成果所产生的影响,“预示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光辉序幕”[7]。王国维新方法的形成,得意于其对西方逻辑思维的重视与吸收。他曾学习过思辨性极强的康德、叔本华等人的哲学,还直接翻译过耶方斯的逻辑著作《辩学》(全名为《逻辑的基础教程:演绎与归纳》)。在比较中西文化差异的时候,王国维说:“西洋人之特质也,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3]386王国维在其学术著作中自觉地运用了“综括”、“分析”等方法,基本的逻辑思维已经被他消化吸收了。
《人间词话》正是一部体现了王国维的新思路与新方法的批评著作。在《人间词话》里,王国维试图以一种融汇中西的方式重新阐释古典诗学。他虽然延用了中国古典的感发形式,但其将逻辑、思辨之力量注入《人间词话》,使之与传统文论大不同了。这种不同预示了学统的转型,具体表现如下:
(一)整体结构的逻辑化
前面已经指出,学统影响下的中国古代文论侧重于直觉感悟,较为缺乏逻辑。而考察《人间词话》,却能发现它有较为清晰的内在逻辑结构。
首先,《人间词话》在王国维生前有三版:125则的手稿本,64则的《国粹学报》本,31则的《盛京时报》本。手稿本《人间词话》尚停留在随感而发、较为粗糙的阶段,李砾认为:“《人间词话》原手稿结构方式应该就是王国维阅读思考的自然记录。”[8]140在这之后的每次修订都经过了浓缩与重组,这体现了王国维不断追求文本逻辑性、结构性的努力。
其次,以上三个版本中,以64则的《国粹学报》版影响最大。从这个版本自身来看,它可以分为理论、实践、余论三部分。第一至第九则提出“境界”这一范畴,是理论部分;第十至第五十则,以“境界”理论为准的,基本上按时间顺序,对从唐代李白至清代纳兰性德逐一评判,是实践之部分;第五十三之第六十四则涉及了其他结论,可以作为余论部分。总体上看,这是一个“立论——批评”的结构,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批评的基本范式,从而与传统文论拉开了距离。
(二)核心范畴的现代性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境界”与“意境”在艺术审美层次上是互通的,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中往往混用两者。现代视野下的“意境”大都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美学、诗学的核心范畴,它代表了古代美学、诗学最理想的形态,一般有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思与境偕等特征。“境界”范畴的提出,预示着古典“意境”的结束,初步实现了中国古典美学向现代美学的转化。
王国维运用“综括”的方法提炼出“境界”这一核心范畴。在此基础上,他继续分析了如“造境”与“写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客观之诗人”与“主观之诗人”、“隔”与“不隔”、“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情”与“景”等的一系列差异对举的概念。区分的标准主要为 “主观”与“客观”。比如“情”与“景”这组范畴,他“把‘景’说成是‘以描写景物及人生之事实为主’,是‘客观的’、‘知识的’;把‘情’说成是‘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是‘主观的’‘感情的’”[9]。王国维一方面区分“情”与“景”,另一方面又说:“境非独谓景物也,感情亦人心中之境界。故能写直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10]3这样,就把“情”与“景”统一于“境界”了,这正如饶芃子指出的:“王国维意境论的要旨,就是着眼于用主观客观两分又再行结合的方法解决艺术创造的基本问题。”[11]76然而立足于主客二分的“境界”与代表古代、以内在“和谐”为特征的“意境”是不能调和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境界”消解了“意境”。
二元对举、主客二分等逻辑思维方法是现代学术必不可少的,也是现代性的一个标志。尽管这种思维有许多弊端,但采纳它方能从更高的层次超越它。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运用西化的思维方式,一改传统不尚逻辑,不成系统的缺点,做到了“从哲学思辨的高度来反思审美经验和艺术的特征”[12],“特别强调美学研究的现代哲学品格和形而上意义”。[12]当然,《人间词话》并不是完满的,它虽然整体上富有逻辑,但在每一部分仍是沿用了“感悟”的形式,仍具有模糊性。
总之,《人间词话》运用了西化的逻辑思维方法,整篇有较为清晰的内在逻辑,初具系统,体现学统的现代转型。
三、《人间词话》与道统的延续
在西方,人生价值与归宿即“终极意义”问题多交予宗教;与此相比,“淡于宗教”的中国文化把这一问题的解答交给了道统。但王国维所处时代正是传统文化衰败之时,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旧的儒家学说已不能完全担当起为知识阶层提供“终极意义”的责任。道统中的儒家之学逐渐隐退,但道统“生命超越哲学”的信仰结构却深植于知识阶层灵魂之中了,只是每个人寻找的可以替代儒学的对象不同。当然,儒学作为传统仍是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前期的王国维试图于西方哲学中寻找解决“人生问题”的答案,他说到:“人生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3]408同时,作为始终“留着辫子”的王国维,他还是眷恋着传统的。
具体到“学术”上来说,王国维一方面大力倡导超脱功利的“纯粹知识”,主张“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3]214,试图做到“学术之自觉”,这样就与西方独立自觉的、认知主义的学术靠近了。但另一方面,正如叶嘉莹所说,王国维“既关心世变,而却又不能真正涉身世务以求为世用,于是乃退而为学术之研究,以求一己之安慰及对人生困惑之解答;而在一己之学术研究中,却又不能果然忘情于世事,于是乃又对于学术之研究,寄以有裨于世乱的理想”[13]25。其实这就是“为人生”的道统的延续,体现出了道统对学统的深刻影响。作为一部学术著作,《人间词话》鲜明地具有这样的特征,表现如下:
(一)“忧生”与“忧世”之情
“忧生”与“忧世”是《人间词话》里的两个重要概念。《人间词话》第二十五则曰: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聘”,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10]15
“忧生”是对人类生命本身的深切关怀,“忧世”是对当世的忧虑。王国维的这种“忧生”、“忧世”之情怀更多的是延续了道统精神。王国维特别关注“人”的问题,他始终是“忧生”的;面对传统文化式微的境遇,他也是“忧世”的,也因此最终有了“殉文化”的悲剧。杜卫认为“在王国维看来,所谓真理问题实际上也无疑就是人生问题了”[12],“他讲的作为哲学和艺术的目的的‘真理’主要属于生存论范畴,而作为认识论范畴的、西方式的客观真理问题,在王国维的学术独立论当中实际上并不占有核心的地位。了解这一点,正是我们理解王国维的哲学观和美学观的关键所在”[12]。王国维之所以特别钟情于叔本华、尼采的学说,固然出于他的性情与喜好,但中国古代“为人生”的道统无疑构成了王国维一系列阐释的前理解。实际上,叔本华和尼采的学说已经与西方传统哲学大不相同了,他们被称为西方现代人本主义的先驱,因为他们都否定了在传统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上帝,人怎样活着完全靠自己。这样就把关注重心转向了人和现实世界,他们的哲学所要解决问题就是人的生存问题。王国维试图从他们的学说中得到人生的启示,以实现其“生命超越”。
(二)“境界”与人生
《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是“境界”。学界对此范畴的争议颇大,但不论它是根植于中国古典诗学,抑或来自西方理论,“境界”在《人间词话》里不纯粹是个诗学概念,它还是个人生哲学、人生价值问题。《人间词话》第二十六则提出了著名的“三境界”: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当作‘蓦然回首’),那人正(当作‘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10]16
这“三境界”是一个“超离——陶醉——涌现”的结构,具有普遍意义。此处的“三境界”仍可从文学艺术层面来解读,佛雏说:“‘三境说’涉及艺术家修养与创作的阶段性与艰苦性,它把‘顿悟’与‘渐悟’辩证地统一起来,阐明了形象思维中的质的飞跃问题。”[14]248若从“人生境界”的角度理解的话,能从中明显地感受到道统精神的延续。王国维用三句词形象地的描述出追求理想过程中循序渐进的三种状态,也即三种心性修养的境界,实为一种“人生境界美学”。刘锋杰认为:“中国的传统美学其实是一种人生境界美学,立足于个人的修养,讨论如何做人,期望达到人的精神升华与人生境界的提升。中国现代美学继承了这一传统精神,所创造的仍然是人生境界美学。”[15]王国维将“境界”提炼出来,一方面,使其有贯通艺术与人生的特质;另一方面,完成了“人生境界美学”传统与现代的传递。
总之,《人间词话》不仅探讨了文学艺术,更表达了王国维“忧生”、“忧生”之情与对“人生境界美学”的追求,这深刻体现出了道统在王国维身上的内在延续。
四、《人间词话》的启示
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怎样吸纳西学,实现传统文化的新生,是从王国维以来许多代学人共同面临的任务。王国维曾说:“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3]404这充分表达了王国维兼容西学的开放心态和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人间词话》的视角建立在对话的基础上,既是对西学的吸收又是对中国学术的拓展。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所展现出来的融汇中西的新学统与“生命超越”的道统给我们带来许多启示。
实际上,《人间词话》所体现的新学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曹顺庆指出,尽管《人间词话》开创了一种“以中国传统文论话语方式融会西方文论的学术路径”[16],但“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史,我们更多的是走了一条“‘以西释中’、‘以西套中’,甚至‘以西代中’之路”[16]。从美学方面来说,张法认为:“王国维以广大中国资源为基础,融汇西方美学,形成新型美学的方向受到了抑制。”[17]从朱光潜的《谈美》到蔡仪的《新美学》,美学史上占主流的是西方美学的路数。“而王国维以中国资源为主的方向无法进入这一美学原理框架,不知不觉间沦为一种中国古代艺术研究,或者加上一些美的词汇和美学思考,成为中国美学史研究。”[17]中国美学要想真正有自己的特色,取得独立的地位,“其标志应是王国维方向全面进入美学原理,达到中国美学与世界美学的真正结合。这必须深入中西内在精神之中,方可完成”[17]。
表面看来,我们似乎是学到了西方理论,而且能运用自如;但西方理论内在的、最核心的逻辑思维并没有被真正地吸收。因而我们的学术创造力始终处于较低水平,已有的理论不能发展成完整的系统。王富仁曾说:“直至现在,中国文化中的话语形式主要是西方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的混合,现代中国的独立形式极少。我们有西方的哲学,古代的哲学,但没有中国现代的独立哲学体系;我们有西方的文艺学,中国古代的诗学,但没有中国现代人的独立的文艺学…”[18]然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运用综括、分析等逻辑思维方法提出的“境界”理论是晚清以来最本土化、最有活力的美学范畴之一。这一理论在提出后或被继承、或被批判、或启发学者重返其文脉历程,它激活了一片有深刻价值的阐释空间,不断出现在诸如宗白华、朱光潜、叶嘉莹、陈望衡、叶朗等一代代学者的阐释视野之中。这正是原创的魅力。因此,在立足本根的基础上,正视与反思古代学统思辨、逻辑之不足,向西方取长补短,创造出真正属于自己的理论是发展的必然。
同时,成中英认为,传统以“现实性、实践性及心理的依存为主体”[2]。道统所体现的葱郁的“生命超越”之人文精神,始终流淌在王国维为代表的知识阶层的血液之中。这固然有其传统、保守的一面,体现了“心理依存”性;但它有价值的一面不容忽视。一方面,它往往结合“现实性”体现为某种“实践”。高举“人”的旗帜的学者、流派一直是构建中国近现代文艺学、美学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深入研究并继承这一“人”的文学、美学的主题,仍是一项有重要意义的任务。另一方面,道统的以人为本的“生命超越”品质在某些方面也能回应工具理性泛滥、信仰缺失的时代问题,这一点对于“淡于宗教”钡?中国人更为重要。正如成中英所指出的:“人固然不知具体的未来,但人却能就其生命整体的实现在心灵上确定他的终极价值与理想或实际愿望。”[2]
综上所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运用了思辨、逻辑之方法阐释古代诗学,开启了新的学统。另一方面,《人间词话》所体现的“生命超越”精神,仍传承了中国古代的道统。这种“学统之转型”与“道统之延续”的品质代表了中国学术现代化自觉而自信的选择。深入反思《人间词话》的价值,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之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M]//陈寅恪.陈寅恪文集之三·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成中英.新论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中西融合之道[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4,(1).
[3]王国维.王国维论学集[M].傅杰编,校.北京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牟宗三.略论道统、学统、政统[M]//郑家栋.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牟宗三新儒学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5]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6]冯胜利.从人本到逻辑的学术转型——中国学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抉择[M]//学术批评网编.为了学术共同体的尊严.北京:北京奥科德文化传播中心,2006.
[7]夏中义.谒王国维书[J].文艺争鸣,1997,(5).
[8]李砾.《人间词话》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9]朱志荣.王国维美学方法论[J].贵州社会科学,2010,(9).
[10]王国维.人间词话[M].徐调孚,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
[11]饶芃子.中西比较文艺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2]杜卫.王国维与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J].中国社会科学,2004,(1).
[13]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14]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15]刘锋杰.朱光潜与宗白华:美学双峰的并峙性[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4).
[16]曹顺庆.中国文学理论的世纪转折与建构[J].中州学刊,2006,(1).
[17]张法.王国维:以美学接引传统[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03-29(11).
[18]王富仁.完成从选择文化向认知文化的过渡[J].中国文化研究,19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