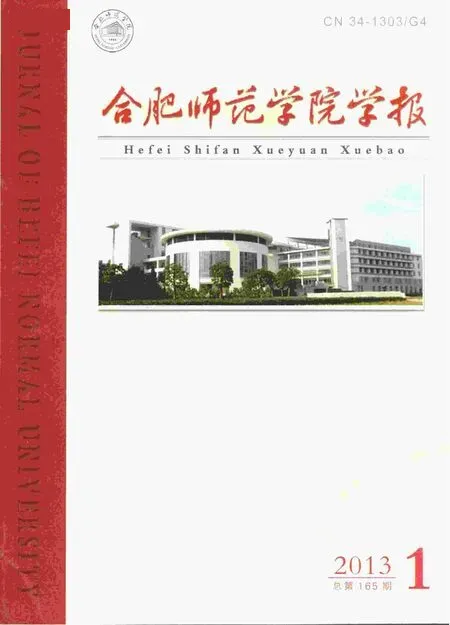试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媒体角色
2013-04-12罗娟丽
罗娟丽
(中国政法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088)
在媒体①从功能上讲,媒体有两大主要功能:信息传播和娱乐大众。本文所说的媒体主要是前者,并且主要关注的是新闻媒体在外交和国际事务上的报道。与政治关系的研究领域,学术界有不少关于媒体对国内事务影响的研究,但是对媒体在外交决策领域所扮演的角色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媒体扮演什么角色?通常研究认为,媒体在对外关系中的主要作用就是为政府提供国际事务的信息渠道,即政策决策过程的信息输入功能。其实,媒体的角色远不止如此。
一、经典媒体角色分析模式
(一)自由多元模式
在外交政策制定的信息沟通过程中,自由多元模式认为,媒体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独立承担重要的政治功能。“主流的新闻媒体能广泛接触到受众,受到他们的信赖,它们能揭露丑行让政客身败名裂,自由民主的法律和文化保障的媒体自由使媒体受到尊敬。”[1]142媒体在水门事件和越南战争的表现是学者们常常用来证明美国媒体自由地位的经典案例,媒体的独立报道对尼克松总统的下台和越南战争的走向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信息在外交政策中是一种权力。”[2]278民主理论认为,这种权力不能完全被政府垄断,公众在决策过程中也可以获得并使用这样的权力。媒体作为独立自由的行为体,它在外交政策领域最基本的职责是用通俗的语言向公众描述他所看见的和发现的,它应该成为公众的眼睛和耳朵。[2]23公众知情权的保障依赖于媒体的这一职能,公众只有在充分了解和掌握信息的基础上才能做出自己关于外交政策正确的判断。从某种意义上人们甚至认为媒体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基本保障,媒体提供的信息越充分越正确,公众做出明智选择的能力就越强。
外交决策者制定的政策需要来自公众的同意和支持,他们希望通过各种途径以满足这类需要。媒体为他们提供了政策解释、试行和信息反馈的途径。但媒体是一种公开的信息途径,政府获得处理问题的有用信息的同时,其他精英和“关注(国际事务)的公众”也可以从中获得所需信息并做出反映,政府对此必须予以回应。媒体为政治行为体提供参与决策所需的信息,并且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对纷繁复杂的信息做出一些解读以利于受众理解和掌握。信息的传播方向可以自上而下,也可以自下而上;媒体可以向民众输出决策中心关于政府政策的信息,也可以向决策中心输入公众舆论和政策的反馈信息。
自由多元模式是最普遍的媒体角色分析模式,政治信息沟通过程中的不同的行为体都倾向于持赞同态度。首先,政府支持媒体独立自由的地位有利于政治权力的合法化。其次,对媒体而言,独立自由赋予了它在政治体系中极其重要的权力,它们“客观和公平”地报道事件、监督政府权力的行使、代表广泛的民意和公共舆论等等。最后,媒体自由、言论自由凸显了人民的权力,公众舆论通过媒体渠道表达,政治决策者必须对它做出反应。
(二)媒体中心模式
相对自由多元模式而言,媒体中心模式更倾向于认为媒体政策制定过程中不仅是自由独立的行为者之一,它还是主要的积极能动的参与者。著名的大众传播理论家麦奎尔(McQuail)认为,媒体“并不仅仅是中立的‘信息传递’网络”,它们“是独立的机构,拥有自己的权力,追求目标和机构动力”[3]70-94。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en)对媒体在决策过程中作用也曾评价,“在人民拥有最高权力的地方,媒体就是国王”[2]33。
作为决策的参与者,媒体不再仅仅是信息的提供者,它常常以民意的代表自居,有时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批评政府或者官员,有时甚至以政策的倡导者或者决策的参与者出现。“在这一角色上,国际新闻的记者是(外交政策制定)过程的参与者,它们试图影响公众和政府官员的观点。”[2]39在媒体政治的研究中,很多学者强调了媒体的“议程设置”作用,在某个问题上,媒体“关注得越多,用更强烈的感情报道,认为政府应该做得更多,媒体似乎已经差不多将这个问题定性为国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了”[4]112。
媒体中心模式支持者强调除了媒体对信息的垄断作用,对公众讨论议题的设定和主导,还有“政府对立者”的角色。虽然外交政策领域不常发生,但在美国人的观念中,媒体的这种角色具有光荣而悠久的历史。“将媒体角色定义为外交政策制定过程的主动参与者,媒体便被看作宪法之外的‘政府第四权力分支’。”[2]31监督政府的所作所为,批判政府的错误行径,有时甚至是制造公共舆论对政府形成层压力,迫使政府采取行动。最著名的美国媒体对外交政策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研究案例是“CNN效应”——生动逼真的现场新闻画面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皮尔斯·罗宾斯(Piers Robinson)在《CNN效应:新闻、外交政策与干预的迷思》一书中具有说服力地表明,冷战后美国在伊拉克、波斯尼亚、索马里、卢旺达、车臣等国际问题上,媒体对危机的现场报道对美国外交活动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如果美国政府不希望被民众认为软弱优柔寡断和无国际人道主义原则的,那它就不得不采取某些行动,就算这些行动是仓促和不符合国家利益的。[5]
(三)被动控制模式
与以上两种模式完全相反,被动控制模式否定了媒体在外交政策中的独立自由与能动性,认为出于各种原因,媒体只是消极被动的参与者。爱德华·赫尔曼(Edward S.Herman)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缔造共识:大众媒体的政治经济学》一书的第一章中认为,主流媒体就是国家政治宣传的延伸,它们根据精英的利益制造、强调或者故意忽视某些事件。新闻基本上有五种因素过滤而形成:专注利润导向的企业所有制;对广告收入的依赖;对政府和商业拥有、资助和处置的信息来源的倚重;右派势力反对媒体的压力以及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操控机制。[6]
首先,新闻的政治正确性。在外交事务中,政府总是有很多不公开信息的理由——影响到外交谈判的进程、危害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等等。虽然媒体在某些情况下并不赞同政府对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定义,但“爱国主义”却是媒体常常必须考虑的因素。与新闻的真实性和政治意义相比,媒体更担心听众给他们贴上“不爱国”的标签。著名媒体政治学者多丽丝·葛拉贝(Doris A.Graber)认为,美国新闻记者在报道国际新闻遵从的原则有:(1)站在美国人的立场;(2)与当前政府的外交政策保持一致;(3)符合公众对世界看法的思维定势。[7]345当媒体的行为被视为与“爱国主义”相关,并且有受到来自政府的双重压力时,媒体对国际事务的报道几乎不会偏离政府意愿的轨道。
其次,外交决策的特点。“外交决策环境的结构将媒体置于不利地位,因此严重削弱了它在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作为独立的观察者和积极参与者的角色。”[8]137政府是 “主要行为者,再加上政治决策是在‘封闭的范围’内被制定出来,这就意味着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媒体和公众舆论只有在政府觉得有必要让他们参与公共辩论的时候,它们才会被政府拉入政治游戏的内环。……处于决策外环的媒体和公众常常缺乏资源,直接接触的途径,以及成为主动参与者的讨价还价的影响力。因此他们参与政治过程常常很大程度上依赖即将出现的政策状况以及决策中心为支持他们的政策选择而达成共识的需要”[8]35。斯科特·卡特利普(Scott M.Cutlip)认为,媒体是政府官员的仆人,它们接受政府的宣传并且不加鉴别地发布。[9]30-57在外交决策中,是政府能够通过精心设计影响到媒体的报道范围和态度倾向;而不是媒体的报道决定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偏向。
最后,媒体的组织特性。用最低的成本追逐最高的利润,美国私有媒体的运作也遵循这一商业原则。由于民众对远离身边的国际事务陌生并且不感兴趣,再加上国际事务的复杂性也一般超过国内问题,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国际新闻必须满足迅速、简短、易理解,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具有轰动效应。对于人们不熟悉的新闻,媒体的报道是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的,因为离他们太远,可能他们根本就不关注这样的信息。“只有貌似可信的信息才是可能被接受的,这些新闻报道必须囿于一个受众相对熟悉的框架……”[10]17就算新闻记者意识到组织因素对客观报道的影响,他们也无意与为改变这种状况做出努力,因为在他们眼中,吸引和讨好读者远比政治意义或民众教育重要。
二、两个不同领域的媒体角色
为了全面理解美国媒体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需要先回答以下的问题:外交事务有什么的特色?如何区别于国内事务?媒体会怎样处理这种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是怎样体现在媒体报道上的?
(一)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区别
国内问题与外交问题的决策是两种不同的机制。在国内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党、国会、政府机构、利益集团、商业团体都会积极参与到激烈的竞争中来讨价还价,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到各个行为体的因素。在公共利益面前,几乎没有人,包括官员和学术界,能给出清晰的定义或划出明确的范围。“与外交政策相比,国内政策明显是麻烦的。总统很难在国内政策制定领域为自己树立一个清晰的形象——高效的强有力的领导者。”[11]18
外交政策的关注点是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与国内事务相比,外交政策决定者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具有较为一致的看法。在国家利益层面,政府和公众比较容易达成共识。美国前国务院政策制定中心主任、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教授(Stephen D.Krasner)认为,国家利益就是美国主要决策制定者的优先目标,这些目标与一般的社会目标相联系,具有一定的持久性和重要性。[12]13尽管分歧存在,但外交政策制定的不同意见并不像国内事务那样导致广泛和持续的利益冲突。在“冲突”内容不存在的情况下,媒体报道只能选择反映“客观事实”和政治精英的看法。
因为国际事务的性质和外交政策的决策程序与国内事务不同,媒体所扮演的角色也有很大的差异。在外交策的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媒体却可以在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这一目标上达成共识,就算是质疑政府的外交政策或者政策的实施方式,美国媒体也很少挑战外交政策的目标。如果说在国内问题和公共政策中,媒体在某些问题上还可以坚持采取与政府不同的立场,那么在国际事务上,媒体在大部分情况下只能与政府保持一致。另外,媒体对政府消息来源的依赖与公众对媒体信息的依赖也导致了媒体可能成为政府误导公众的工具,如果政府有意为之的话。总之,从政治作用来看,无论媒体故意还是无意都充当者政府信息传播的工具。媒体界定公众对外交事务的讨论范畴,改变公众的认知和公共舆论的方向。
(二)美国媒体报道国际新闻的特点
国际新闻远离现实生活,普通民众对其缺乏兴趣;搜集新闻素材的成本(派驻海外记者)高昂,媒体企业考虑其利润;国际事务纷繁复杂、变幻莫测,又增加了民众的理解难度;媒体工作者在爱国主义、国家利益和安全面前表示的忠诚与服从等等因素,都塑造着完全独具特色的国际新闻。
第一,轰动效应。相对于国内事务来说,国际新闻所占的比例决定媒体选择它们时在时间、空间和重要性上要求标准会比国内事务更高。“毫不奇怪大部分的编辑总是将国际新闻尽量消减到最少。”[13]404距离普通民众的生活比较远、报道读者不感兴趣的内容意味着读者的丧失、利润的减少。“编辑、出版商、广播制作人之间有一种共识,即一般的美国民众几乎对国际新闻不感兴趣。因此,在搜集国际新闻上投入大量的资金既没有经济效益也无利可图。”[11]189为了吸进尽可能多的读者,它们必须具有轰动效应。暴力、灾难、离奇事件,或者民众熟悉的人物和状态常常是国际新闻恒定的主题。“国际新闻的报道要求涉及具有更高地位的人物,以及更多的暴力和灾难。”[14]781-795
第二,简单化与片面性。世界上发生的重要事情远比国内发生的事情要多,虽然报纸对国际新闻的报道持续在20-30%左右,①尽管大部分美国人对国外事务不感兴趣,但媒体(包括纸质和电子媒体)对的报道仍然在20%左右,数据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s 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2011state of the news media,2012年6月12日登录 http://stateofthemedia.org/2012/mobile-devices-and-news-consumption-some-good-signsfor-journalism/year-in-2011/。但无疑与国内新闻相比,这样的报道篇幅肯定不能够涵盖世界上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媒体报道的选择性让新闻无可避免的是世界上所发生的事件中很少的一部分,它们是片段的、不系统的、并带有偏见的当前发生的事件。这种内容上的有限性再加上国际新闻的复杂性和及时性,导致了国际新闻的分析和背景原因解释并不充分。在分析这种简化复杂国际新闻的案例中,多丽丝·戈伯认为,比较典型了的就是美国媒体对南海撞击事件的报道,“媒体在2001年中国扣留美国飞机和飞行员事件的报道中,主旋律就是无辜的美国人被独裁的、反美的中国政权扣留作为人质,这显然过分简化当时的复杂状况。中国国内复杂的政治,尤其是军方对事件的影响都没有得到媒体应有的关注,因为这些信息并不符合戏剧化的、吸引大众眼球的国际新闻的标准”[7]332-333。
第三,国际报道的潜规则。“国际新闻的报道和使用常常取决于国家外交,国内治理,军事政策和历史文化传统。”[15]45-50虽然有些美国学者总是认为国内意识形态极化的状况正趋于严重,媒体的立场也比较鲜明,但是在对外政策上,媒体的表现却相当一致。兰斯·班尼特(Lance W.Bennett)认为,媒体对国际新闻报道的特性就是与国家的对外政策保持一致。[16]103媒体对国际新闻的报道倾向于展现一个两极分明的世界:美国处于正常世界的一端,它拥有民主的政治结构,它的人民过着自由的生活;世界的另一端是不正常国家,这些国家的人民陷于专制体制、恐怖主义、贫穷和犯罪的悲惨处境中。这些新闻都以美国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文化为背景,它们与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念以及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相符。对国外所发生的灾难、矛盾冲突和流血战争的关注其实是一种国内政权的一种肯定和宣传。人们对来自骚乱的国外世界的恐惧更加坚定了人们对承诺稳定和秩序的国内政权的支持和期望。
三、美国外交政策中媒体政治
无论是内部事务还是外交政策,没有美国公民的支持,政府将一事无成。民主理论坚信:最终决定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是公民的同意。如何保障公民做出明智的决定以支持或反对政府的政策?一个必要的条件便是,让公民拥有充分的知情权,充分掌握信息的民众可以有效参与到政府政策的制定中。政府、媒体和公众在美国现实政治信息沟通过程中的角色承担是否与民主理论描述的相符?如果不一致,那它们分别有扮演什么角色?
(一)政府——主导而非控制信息沟通过程
首先,总统在外交决策中的绝对权力。“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中,宪法赋予了总统更多的权力,因为制宪者们认识到关系到国家生存的问题需要更迅速和更果断的行动,而这是立法机关做不到的。”[17]277美国前总统里根也曾说:“现代总统的最大优势是六点钟新闻。总统总是能出现在每晚的新闻当中,只要他希望这样——他常常也是这样想的。他们很容易使自己成为重大新闻报道的焦点,因为美国总统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18]279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利用媒体是贯彻政策和增强影响力的有效途径。“新闻报道能够通过塑造公众期待对政策产生连锁反应。尽管认为媒体通过不负责任的报道引起混乱的观点常常听到,但很多外交事务的报道是政策制定者的引导的,他们决定了公众应该期待一些什么。”[19]60-63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肯尼迪总统任内的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曾将决策权力分为三个层次:总统处于权力中心,媒体处于权力第二环,公众舆论处于权力的最外环。[17]277
其次,政府是媒体的主要消息来源。国际新闻报道的内容到底是政府想表达的,还是媒体想说的?一位前美国国务卿评论说,新闻是“记者们所问的问题,而不是总统或国务卿所想说或者拥有内容可以告知的信息。”[2]178为何美国新闻媒体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尤其是外交领域都表现出支持政府决策的态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大量的新闻要么来源于政府部门的新闻发布,要么来源于政府官员的发言、证实或透漏。在国际新闻的收集上,媒体“更加依赖政府提供的关于世界事件的消息来源”[20]364-368。在对外政策制定领域,权力相对集中在白宫和国务院,外交决策程序较国内政治而言也相对封闭。当新闻记者的新闻素材来源于少数的高层领导、政府发言人、对外关系专家时,他们的独立地位客观上受到影响。对媒体消息来源的分析可以发现媒体与政府的密切关系,许多研究都证明政府是媒体的主要消息来源。①Sigal在1973年通过分析《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上的2850条新闻发现,政府的媒体官员和他们各种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占了58%,远远超过了其他的消息来源,Leon V.Sigal,(1973).Reporters and Officials:The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s of Newsmaking,Lexington,MA:D.C.Heath;Hess研究华盛顿的记者也发现,将近有一半的新闻是与政府媒体官员相关的,Stephen Hess,The Washington reports,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如果新闻媒体对政府信息来源过于依赖,政府便很容易在新闻报道的内容选择、报道方式上对媒体具有决定性影响,其它来源的观点也会因此被忽视和过滤掉。
第三,媒体对新闻“客观性”的追求。客观性标准让媒体看起来是独立和自由的,这是民主制度下媒体最引以为豪的地位象征。然而媒体越是倾向于将自己看成中立的信息传送纽带,“它便越容易使用其他的消息来源,尤其是政府官员,媒体将他们看成是主要的消息来源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政府部门中的位置”[2]28。另一些学者还认为,媒体客观性倚重消息来源的影响力,在定义消息的客观性之前,媒体人一般会将消息来源的合法性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因此,媒体会倾向于使用来源于政府或官员们的消息。[21]
(二)媒体——非决定性的重要的决策参与者
媒体在外交中的功能主要有:向公众提供关于外交事务知识的主要渠道;连接政府和关注世界事务的民众;为政策决策者提供观测公众舆论的途径,等等。“如果媒体不能制定外交和防御政策,那么在很多重要的方面媒体都为政策的制定设定了边界。在这个方面,媒体常常是影响政策的制定,而不是决定作用。”[11]2
媒体是重要的信息提供者。卡罗尔·韦斯(Carol H.Weiss)通过对545位各界领袖,包括实业执行官,银行、保险公司、零售业高管,工会主席,国会议员,政党官员,媒体专家,志愿者协会领导等等,访谈研究发现,“对大多数议题,媒体是信息和观点的主要来源,尤其在外交政策、城市问题和文化价值观(涉及到的问题如媒体的自由与质量,青年文化与异化,爱国主义和反共产主义)更是如此”[22]1-22。“那些密切关注外交政策和国际问题的公众的大部分信息直接来自于大众媒体。”[23]229“美国国会议员,尤其是那些与外交事务相关的议员,与政府外交部门的官员都曾做过类似的表述。他们都觉得比起他们的官方消息来源,精英媒体的报道使他们更迅速更充分地了解国际事务。”[7]320“尽管国务院政策制定者周围有很多官方和非官方私人网络以保证他们能充分了解信息,但是他们仍然通过媒体获得他所处的国际政治世界的基本事实的信息……。”[2]209
外交决策者们为什么还要通过正式渠道或私人途径以外的方式获得信息?原因之一在于,媒体作为一种公开的信息渠道不同于内部信息网络,决策者都可以在媒体报道的内容中获取更广泛的消息。其次,报纸有时能提供一种不同于内部消息的独立报道,用另一种角度观察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最后,虽然官员最终依据的仍然是内部的报告或者官方的分析制定政策,但通过报纸获得信息的速度比官方渠道要快,在瞬息万变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外交事务官员更常用媒体作为信息渠道。
媒体是政治过程的参与者,媒体对报道内容和方式有部分决定权。编辑和记者对采用哪些新闻来源,版面如何分布,如何组稿,以什么形式发布等等具有选择和决定的权力。另外,在某些问题上,媒体还可以凭借自己强大的舆论引导功能,在没有其他政治行为体启动议题时,单独设定议题。作为信息传播的渠道,媒体具有向双向的信息收集和发布功能。一是自上而下,媒体接收来自政府的信息,向公民发布;二是自下而上,媒体收集公共舆论和民意,输入到决策中心。另外,一些资深的媒体顾问和公共关系专业人员都有参与到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官员常常会向他们咨询并考虑他们的建议。“当美国总统想要消除盟友的疑虑或者吓唬敌人时,最迅速的途径是通过沃尔夫·布利策(Wolf Blitzer)①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络(CNN)的著名记者,现主持CNN的时事观察室(The Situation Room)栏目。而不是常规的外交途径。”[19]60-63
(三)公众舆论——有限作用但必不可少的支持者
上面论述的结果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几乎掌握在决策精英的手中。罗杰·希尔斯曼的权力分层模式将公众舆论放置最外一环在外交决策程序中是合理的——“关注外交的公众对决策的影响微乎其微的,虽然它们无疑也是因素之一。”[24]284那处于决策权力圈最外围的媒体和公众是不是对外交政策不产生影响?如果是这样,又要如何解释政府的媒体策略以及他们对公共舆论的关注和积极控制的意图?
“在美国,除非媒体为政府行为预备民意支持,否则大部分的国会法案,国外投资,外交活动,重大社会变革都不会成功。”[25]327美国前总统杜鲁门曾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外交政策中的主要决策都是建立在充分知情的公共舆论和绝大部分公众支持的基础之上的。”[26]10但就算所有的外交决策都冠以“公共利益”的名号,公众影响和参与外交政策途径的有限性决定了人们所熟知的民主决策只是一种迷思。“在我们(美国人)能够思考和找出原因之前,我们就被教导相信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国家,而新闻自由是它的主要根基之一。”[16]103对民主体制下媒体自由的认同类似于一种迷思(Myth)深深扎根于人们潜意识中。它不需要人们用实践经验去证明,因为在政治社会化的早期,或者在儿童阶段人们就接受关于这种迷思的教育熏陶。人们在成长过程中,它又受到周围人和事物而巩固加深。在外交政策中,这种认知使公众难以认识到政府与公众之间信息的不平衡关系,也不容易发现政府实质上对外交政策信息的主导权。
公共舆论并不直接作用于外交政策的制定,正如威廉·多尔曼(William A.Dorman)和曼苏尔·法尔汗(Mansour Farhang)所说:“在民主国家具体外交政策的制定上,公众舆论强有力的支持并不是迫切需要的,但必不可少的是没有公众舆论的积极反对。”[11]28由于没有亲身经历,也缺乏相关的知识,美国民众可能并不关注远离它们日常生活的国内和国际事务。对于那些关注国际新闻和外交政策新闻的民众来说,生活距离越远,他们理解的可能性越小,选择相信新闻、根据自己的经验解释新闻的可能性越大。
四、小结
从理论的角度考虑,政府与媒体应该是“天生的对手”。外交决策官员担心媒体的过分参与和提前曝光给外交谈判和决策带来破坏性影响;而媒体和公众则认为,如果媒体不积极参与决策过程,如何保障民主的实施。政府希望媒体服从“国家利益”(大部分时候来源于政府的定义),报道那些能为政府或官员带来利益的消息,而掩盖那些不利的消息。但是媒体则认为,国家利益应该是尽可能曝光政府的行为,完全自由地发布信息,根据媒体人自身的判断决定新闻的价值并且对新闻做出解释。从实践过程来看,媒体与政府从来就不是“势不两立”的敌我关系,媒体也不可能完全实现独立自由、客观中立地报道外交事件。在外交事务方面,政治沟通过程中政府信息的主导地位决定了媒体收集新闻的内容、解释方式以及报道程度。然而,“一位前国务院官员曾感叹:‘在国务院、白宫和五角大楼看来,媒体就像一头危险的不具吸引力的野兽,你可以牵着它走一段路,但是只要它寻着机会,它就会反过头来咬你’”。一名议会下属机构的官员评价说,媒体上20%关于外交政策的新闻是有益的,而80%则是有害的。[2]147这种有益和有害的比例也同时说明美国政府不能直接控制媒体的报道。
认识美国媒体在其外交政策中的作用,能够为分析和理解美国外交提供一个独特而有用的视角。也许媒体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并不像有些记者和学者所认为的那样重要——“媒体能决定外交议程的设置”,但不能否认它对外交具有重要的影响。[27]6在媒体与外交政策的关系研究中,不能孤立或片面地运用某一种模式分析某种角色的作用,简化媒体“新闻报道”的功能。媒体不仅仅是信息的提供者,它还是外交政策的重要参与者,它总是或强或弱、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决策的进程。
[1]Robert A.Hackett.“thepressandforeignpolicydissent:the caseofthegulfwar”,inAbbasMalek,ed.,newsmediaand foreignrelations:amultifacetedperspective,1997[M].New Jersey: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Bernard Cohen.thePressandForeignPolicy,Princeton[M].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
[3]McQuail,D.”Influenceandeffectsofmassmedia”,Inj.Curran,M.Gurevitch,&.j.Woollacott,Eds.,Masscommunicationandsociety.BeverlyHills[M].CA:Sage,1979.
[4]Iyengar,S.& Kinder,D.R.NewsThatMatters:Agenda-SettingandPriminginaTelevisionAge[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5]Piers Robinson.TheCNNEffect:Themythofnews,foreignpolicyandintervention[M].New York,NY:Routledge,2002.
[6]Edward S.Herman&NoamChomsky,Manufacturingconsent:thepoliticaleconomyofthemassmedia[M].New York:Pantheon,1988.
[7]Doris A.Graber.MassMediaandAmericanPolitics,SeventhEdition[M].Washington,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Inc,2006.
[8]Tsan-Kuo Chang.thePressandChinaPolicy:theIllusion ofSino-AmericanRelations,1950-1984[M].New Jersey: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93.
[9]Cutlip,S.M.(1988),“PublicRelationsintheGovernment”,inR.E.Hiebert,Ed.,PrecisionPublicRelations[M].New York:Longman.
[10]Daniel C.Hallin."Hegemony:TheAmericanNewsMedia fromVietnamtoElSalvador:AStudyofIdeological ChangeandItsLimits,"inDavidL.Paletz,ed.Political CommunicationResearch:Approaches,Studies,Assessments,Norwood[M].N.J.:Ablex,1987.
[11]William A.Dorman&MansourFarhang,TheU.S.press andIran,Berkeley,CA[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
[12]Stephen D.Krasner.DefendingtheNationalInterest:Raw MaterialsInvestmentsandU.S.Foreignpolicy,New Jersey:Princeton[M].Princeton University,1978.
[13]Peter M.Sandman,David M.Rubin,andDavidB.Sachsman,media:AnIntroductoryAnalysisofAmericanMass Communications[M].New Jersey:Prentice-Hall,1972.
[14]Pamela J.Shoemaker,Lucig H.Danielian,andNancy Brendlinger."DeviantActs,RiskyBusiness,andU.S.Interests:TheNewsworthinessofWorldEvents," [M].Journalism Quarterly 68(winter 1991).
[15]John A.Lent.“ForeignNewsinAmericanMedia”,JournalofCommunication[M].Winter 1977.
[16]Lance W.Bennett.“TowardaTheoryofPress-StateRelationsintheU.S.”,JournalofCommunication,Vol.40[M].spring 1990.
[17]Roger Hilsman.thePoliticsofPolicyMakinginDefense andForeignAffairs[M].New Jersey:Prentice- Hall,Inc.,1971.
[18]Charles W.Kegley.Americanforeignpolicy:patternand process,4thed[M].NY:St.Martin’s Press,Inc.,1995.
[19]Philip Seib.“PoliticsoftheFourthEstate:theInterplayof MediaandPoliticsinForeignPolicy”[M].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fall 2000.
[20]Lee B.Becker.(1977),Foreignpolicyandpressperformance[J].Journalism Quarterly,54.
[21]Tuchman,G.MakingNews:AStudyintheConstructionof reality[M].New York:Free Press,1978.
[22]Carol H.Weiss.“WhatAmerica’sLeadersRead”[J].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Vol.38,No.1,Spring,1974.
[23]Kegley,C.W.Jr.&Wittkopf,E.R.(1979),American foreignpolicy:Patternandprocess[M].New York:St.Martin’s Press.
[24]Roger Hilsman.thePoliticsofPolicyMakinginDefense andForeignAffairs[M].New Jersey:Prentice- Hall,Inc.,,1971.
[25]Theodore White.theMakingofthePresident,1972[M].New York:Bantam,1973.
[26]Dom D.Bonafede.Presidentsandthepublic[M].Washington,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1990.
[27]Simon Serfaty.themediaandforeignpolicy,1990[M].New York:SL Martin’s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