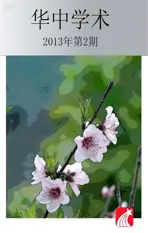拯救“沉沦”:自然与自由
——重读郁达夫的小说《沉沦》
2013-04-12何锡章
何锡章
(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湖北武汉,430070)
九十二年前,郁达夫饱含着血与泪写下了小说《沉沦》。作品一发表,反响热烈,可谓惊世骇俗,既非议四起,又好评者众。随着时间的推移,《沉沦》的意义更为明显,不断被阐释出新的价值。无论是从人性与个性解放的角度,还是从文化心理的视域;不论是对青年心理及其在特殊环境下的“变态”行为的同情性理解,还是从民族、国家立场的思想意义的发明,整体上都得到了相对肯定性的评价。因此,《沉沦》这部小说,经过九十多年的历史沉淀,成为能不断激发读者阅读兴趣、引人深入思索的现代文学经典文本。《沉沦》之所以没有在历史的河流中沉沦和消失,不仅是作者独特的文学表达方式和直面内心、袒露无遗的情感指向,颠覆了中国古代文学过于规避与讳饰的具有某种虚伪脸谱的传统,而且更在于作者写出了特定时代青年的忧郁与苦闷,是一代青年人生命经验在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的真实呈现,其生命、历史、文化的认识价值相当丰厚,即使在今天,人们回望过去、反思历史、反观自我青春之时,这部小说依然是重要的参照。所以,重读《沉沦》,既是学术研究重新理解经典的需要,更是在当下时代提升人的精神自救能力、防止《沉沦》式悲剧再度发生的要求。
一、“他”为什么沉沦?
《沉沦》的主人公是“他”,一个严重的忧郁病患者。这个形象确实有着作家自身生命体验的深刻印记。郁达夫自认为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他坚信一切小说都是作者的自叙传,只有自己的生命、生活,才能在小说中表现得真切,此外的所有都难以企及。从郁达夫小说表现出的基本内容看,都与作家自己的生活经历有着多方面的联系,《沉沦》更不例外。但是,杰出作家笔下的人物,绝不是作家自身生活、情感、行为、命运的简单复制,而是必须超越自身,达到以个体的生命体验揭示更为普遍生命存在状态的深度和广度。《沉沦》就是这样的一部小说,作家塑造的“他”这一形象,既是郁达夫自我生命及其经验的真实传达,更是那个时代众多青年知识者生活状态的普遍性表现,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的一代青年的共同命运:没有真正自由的时代,《沉沦》式的悲剧不可避免。
小说的主人公,其二十余年的生命时光,正处于清末到“五四”前后。一方面,以自由为核心的新的思潮从外部涌进,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科学民主、自由独立,成为时代与社会的理想和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旗帜,成为民族国家自由独立富强繁荣的思想精神动力;另一方面,传统力量依然强大,尤其是专制主义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道德等传统还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更可怕的是,现代观念、思想、精神的拥有者主要集中在社会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其思想和行为得不到多数人的理解和认同。在专制主义及其相适应的种种传统氛围中成长的人,对过去主流的认同意识已深入骨髓,变成了“无意识”的自觉的捍卫者,新的与传统不同的一切,都会被人们视为异端,力图剿杀而后快;因此,新思潮的传播与实践往往处在巨大而深厚的多重的历史传统的包围重压之中,动辄得咎,在这种社会、文化心理下,在没有制度保证人的自由的环境中,非自由造成的悲剧肯定时时而普遍发生。
小说中的主人公“他”就是这普遍性悲剧中的牺牲。在社会思潮和历史变革的影响下,心中潜藏的渴望自由的本能意识开始萌动。辛亥革命爆发时,正值他小学毕业要选择中学,也许是当时的中学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始终没能找到理想的学校。他有自己的求学标准,就是一个人不能按部就班地和其他人一样求学。于是,他不断在一些中学中进行选择,企图找到符合他标准的学校。这些行为,引起了家人的不满,说他心思太活,没有恒性。大概是在家人的干涉下,他在最后还是进了一所中学,不过很快就退学回到了家里。不久进了一所大学的预科,但学校非自由的专制性的管理,引起他强烈不满,不愿服从就范,用小说中的话说,他是一个“爱自由的人”,结果他又选择退学回家在自己小书斋里读书。再后来又去了一所中学,但好景不长,又与教务长闹了一场后和学校“分手”。到最后,他随其长兄到了日本留学,进了一大学的预科。他自己本来选择学习文科,但在长兄的坚持下,改学了医科。“他”的这些经历,自己决定自己的意识,显然是新思想影响的结果;但在最终的意义上,觉醒的自由自我意识及其形成的自我把握命运的力量又是极其脆弱的,根本不能与外在于己的、强大的、与非自由合谋的社会、宗法血缘等力量抗衡,委曲求全,俯首听命就成为普遍的生命事实。正是个人自由意识的萌发及其行动的要求与非自由力量抗争的失败经历,为“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患上“忧郁症”打下了基础;而留学期间所经受的文化歧视,弱国子民在异国感受到的屈辱,不过是引发和加重“忧郁症”的一种条件,而绝不是唯一的条件,真正把主人公逼成“忧郁症”的是不自由的社会。“他”最终走向生命自戕的道路,根本上也是不自由的结果。他渴望异性,渴望爱情,希望自然性情欲得到合理的宣泄;他希望得到家人、中国同学、日本同学的理解与尊重,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得爱。他没有得到,事实上他难以得到。在专制的非自由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情感根本不能达到真正的沟通和理解,自危的恐惧必然形成封闭的自我;只有建立在现代理性基础上的自由的社会,人们才是坦诚的、开放的,人与人、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之间的互信、尊重、理解,才具有真实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所以,小说主人公在自己的国度里不自由,在日本也同样没能感受到自由的快乐。
那么,自由在哪里?在大自然。小说中如此写道:
在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里,在这澄清透明的以太中,他的身体觉得同陶醉似的酥软起来。他好像是睡在慈母怀里的样子。他好像是梦到了桃花源里的样子。他好像是在南欧的海岸,躺在情人膝上,在那里贪午睡的样子。[1]
面对此情此景,主人公心想:
“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轻笑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这晚夏的微风,这初秋的清气,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纯朴的乡间终老了罢。”[2]
然而,大自然并没有使他得救。自然能使人获得某种慰藉,使人能在短暂的时间里获得安宁。但是,社会性的疾病,精神性的人的问题,自然不可能是万用灵丹。所以,主人公没有摆脱忧郁,没有走出苦闷。他选择了沉沦——让生命回归大海,与自然同体。从这个意义讲,他“得救”了,不过是以年轻生命的结束得救的。这种“得救”,当然是与普遍的人性相反动的。
二、用什么“拯救”?
《沉沦》的主人公以其生命的终结,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用什么才能拯救人的精神的“沉沦”?
作家在作品中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人的生命和生活应当是自然自由的,只有自然而自由的实现,才有可能拯救人的精神、思想、心灵、情感的沉沦。主人公“他”的塑造,证明一个原则:个体与国家的生存与强大,自我身心解放和民族的独立自尊,都必须依赖自然与自由的社会环境。
小说的主人公之所以迷恋大自然,视自然为生命的避风港、灵魂的栖息地,是因为自然蕴含着自由。自然的世界是以自在的方式呈现的。所谓自在,就是一种不受外在力量直接控制而是按照自然内在构成方式的存在。因此,自然的存在内含着自在自由的基因。人类来于自然又归于自然,人类和自然有着深刻的联系,人类在天性中就具有自在自由的倾向。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讲,都是自然影响的结果;其精神、思想乃至种种制度规范,最初都是自然的启示。这些都可以从社会现象、社会存在事实中找到经验性的证明。然而,人类社会形成的历史,又是自身逐步摆脱对自然的依赖、简单模仿走向相对独立与社会创造的过程。今天人类不断追求的思想精神的社会性自由,既是自然自在性自由影响的产物,又是人类自身超越自然自在性的结晶。人类的社会性的精神思想的自由,是自在与自为的自觉的自由。这是人类与自然有着深刻联系却又富有独立特点的主要所在。
于是,我们看到,《沉沦》的主人公一方面希望在大自然中得到心灵的解脱,获得治疗孤冷、忧郁、苦闷的爱;另一方面,又希望在人间获得亲人、同学、异性的理解、同情与爱。然而,他失望了。大自然没能使他摆脱种种痛苦,而人间,由于建立在自在自为基础上的自觉的自由没有真正普遍实现,也就没有多少人能理解他内心的愿望,同情、尊重、平等对话沟通当然难以展开。况且,他自身的自觉性自由处在萌生成长阶段,没有成为支撑自我生命的主导,自身占支配地位的还是自然的自在性自由。他渴望异性的肉体,用肉体消费的方式实现自然生理欲望的宣泄,说明他主要还处于自然自在性的自由阶段。当然,这种自由是合理的存在,自本自根的自然性自由是通向人类精神、社会性自由的基础。离开这种基础,任何精神的社会性的自由不过是无本之木。问题是,拯救生命沉沦仅仅用这种方式,在最终意义上是难以完成的。事实正是这样。“他”以自慰的方式、不由自主走进妓院发泄,不过是身体自在性自由的冲动。因此,当实现了这些冲动后,“他”又陷入对这种冲动的道德自我谴责之中。显然,作为自然人的本能冲动与宣泄具有自然的内在合理性,无法简单压制;但是,在信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甚至万恶淫为首的社会里,像主人公式的自我身体的自然性消费是罪恶的、大逆不道的。结果,主人公不可避免地进入了自然自在性自由与外在强制的道德与文化的矛盾痛苦之中。两种力量的较量,胜负不言而喻。作为个体的自然力量远非整体的、占统治地位的正统力量的对手,小说的主人公走向沉沦、走向死亡,有着特定的历史必然性。
自然并没有给主人公带来生命痛苦的解脱,从而他把自己走到今天的沉沦状态归因于祖国的落后和力量的弱小。在主人公自杀前有一段自白:
“可怜你这清影,跟了我二十一年,如今这大海就是你的葬身地了,我的身子,虽然被人家欺辱,我可不该累你也瘦弱到这步田地的。影子呀影子,你饶了我罢!”
他向西面一看,那灯台的光,一霎变了红一霎变了绿的在那里尽它的本职。那绿的光射到海面上的时候,海面就现出一条淡青的路来。再向西天一看,他只见西方青苍苍的天底下,有一颗明星,在那里摇动。
“那一颗摇摇不定的明星的底下,就是我的故国。也就是我的生地。我在那一颗星的底下,也曾送过十八个秋冬,我的乡土啊,我如今再也不能见你的面了。”
他一边走着,一边尽在那里自伤自悼的想这些伤心的哀话。
走了一会,再向那西方的明星看了一眼,他的眼泪便同骤雨似的落下来了。他觉得四边的景物,都模糊起来。把眼泪揩了一下,立住了脚,长叹了一声,他便断断续续的说: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3]
诚然,主人公的痛苦与死亡与民族的落后、国家不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从主人公在异国他乡受到的文化歧视与民族屈辱来说,这种埋怨与不满是真实的;希望祖国的强大从而给他的人民带来尊严与幸福肯定是肺腑之声,是所有中国人的理想。但是,无论是作品中的主人公,还是作家本人,并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一、祖国为什么没能强大?为什么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和中国人成为被他人他国歧视、凌辱的对象?二、祖国真的强大了就能避免被文化歧视和民族歧视吗?就能避免《沉沦》主人公式的悲剧性命运吗?自然身体上的“东亚病夫”可以因祖国的强大而变得茁壮,但精神、文化上就一定能成为真正的“强者”吗?
从作品看,主人公的“忧郁症”并非只是到日本留学时才染上。国内的种种经历早已埋下了忧郁症的根苗,在日本留学时所感受到的文化与民族性歧视不过是引发和加重了“忧郁”。因此,国内的生命经历的种种苦闷才是最初的病因,直接说,就是非自然自由的社会、文化及其制度。整体上讲,几千年的专制主义最大的特征就是非自然自由的思想与制度成为历史和人的命运的主宰,即使人有所“自由”,大体上也还处于自然性的自在阶段,作为人的自在自为的自觉性的自由基本上也还处在被压制甚至被扼杀的状态。这种自在性的“自由”,在维持自然生命的延续和社会的自然性存在方面具有极大的生命力和作用。问题是,由于没能将这种“自由”引导上升到自在而自为的自觉性自由境界,传统中国人就缺乏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意识。在没有自在自为的自由意识的国度和民族里,与此相关的自由创造的能力被严重抑制,最终走向衰落变为任人欺凌的弱国,就是非常可能的,而在中国近代,恰恰就变成了现实。
所以,《沉沦》主人公的滴血的呼吁,作家写作的意义指向,既是希望祖国真的强大起来的理想表现,又是在追寻祖国强大的思想精神动因。这是小说的重要意义所在,显示了郁达夫的某种深刻。一言以蔽之,作家希望国家建立真正的现代自由的社会,并在这种基础上建立强大的祖国,让国民享受自由与尊严,自然自由地生活。这样,才能真正拯救小说主人公式的“沉沦”,防止这种悲剧的再度发生。
注释:
[1]郁达夫:《沉沦》,《短篇小说选》第一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522页。
[2]郁达夫:《沉沦》,《短篇小说选》第一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522页。
[3]郁达夫:《沉沦》,《短篇小说选》第一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553—5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