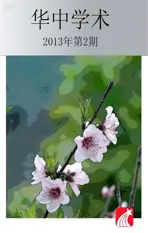重读柔石的《二月》
——兼谈经典重读的原则和方法
2013-04-12王卫平
王卫平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84)
一、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一个明显的倾向:研究课题的选取越来越趋向边缘化和细碎化。翻开本学科的权威刊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你会看到多数文章研究的是边缘性的作家作品、边缘性的文学史问题、边缘性的文献史料考释,以及细碎化的问题。有些作家与作品、现象与问题都是名不见经传的,甚至闻所未闻的。我们虽不能说这些边缘性的问题、细碎化的问题不值得研究,但其价值和意义毕竟是有限的,对于学科整体研究境界的提升,对于教学的促进,对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并不能起到根本性的作用。只有那些支撑本学科大厦的重要作家作品、思潮流派、现象问题的深化研究,特别是经典文本的重读、新论,该学科的学术水准才能登上新高度。有的研究者唯新是举,只要是新问题,以前没有人写过,就自鸣得意地去写,认为这就是创新,而对研究的价值与意义追问得不够。其实,有些问题以往未曾涉足,可能是研究者的忽略,也可能是研究的价值不大。要分清是哪一种情况,多追问几个为什么,不能寻找到一个边缘性的问题、闻所未闻的问题就如获至宝或沾沾自喜。早在2001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生长点研讨会”上,一些资深学者如王嘉良就谈到“老话题”的“新研究”“不唯可能,而且非常必要”[1]。严家炎谈到,“不能一提到生长点就立刻认定是要去重新开辟什么前人未曾涉足的新领域、提出闻所未闻的新话题,其实,已有的、即使哪怕是很熟的研究对象,也仍然是有新的问题可供挖掘、新的意义可供揭示的”[2]。钱理群认为“在那些支撑现代文学大厦重要作家作品上还有‘生长点’有待我们去开发”[3]。赵园则强调指出,“年轻一代应该有勇气对以前一些我们做过的题目进行重做,并对以前那些人们以为不言自明的概念、范畴和理论预设进行更深层次的重新清理”[4]。朱德发认为“经典文本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生长点的源头活水,只有重新解读经典文本,并从中重新发现创意、重新开掘史实、重新评估其意义和价值,才是重写现代文学史之关键所在。而这种经典解读应该是一种‘还原释读’,它既可以拨正过去文本解读中产生的种种误解或制造的不少谎言,又能纠正多年来只热衷宏观考析而忽视微观探索所造成的中国文学研究的粗疏空泛”[5]。今天看来,几位资深学者的看法仍有意义。边缘性、细碎化课题的发掘有意义也是有限度的,应该重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中心,对于支撑该学科大厦的重要作家作品、经典作家作品进行更深层次的重新清理,挖掘其当代价值与意义。正如温儒敏所说:“重新强调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责任,思考如何通过历史研究参与价值重建,是必要而紧迫的。”“和现实对话,参与当代价值重建。”“重新审视现代文学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可能会有助于找回现代文学研究的‘魂’。”[6]
经典重读,用什么标准进行重释和评价?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说到底,现今非常要紧的而又缺少的还是相对认可的某种价值评价标准。”[7]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曾说:“我们在估价某一事物或某一种兴趣的等级时,要参照某种规范,要运用一套标准,要把被估价的事物或兴趣与其他的事物或兴趣加以比较。”在谈到文学评价的标准时,韦勒克·沃伦还说:“我们的标准是具有包容性的,是‘想象的综合’和‘综合材料的总和与多样性’。”[8]韦勒克·沃伦的话提醒我们:文学研究要有规范,要有标准,而且是“一套标准”,这种“标准”具有包容性和综合化的特征。用我们现在的词语概括就是价值标准的多元复合、多元共生。文学的评价尺度不可能是单一的,它一定是包含着多种内涵的系统,这个系统能够涵容多种文学价值观,它一定要克服“一元论”而走向“多元化”。以往,我们走不出“一元论”的思维模式,一会儿强调政治倾向;一会儿强调思想启蒙;一会儿强调社会意义;一会儿强调道德水准;一会儿强调文化含量;一会儿强调审美价值……应该把这些内涵汇集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统一体。不管是什么主义、什么方法、什么理念,只要是好的作品就应该进入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视野。循着这样的思路,我拟从五个维度来重释叙事作品的文学价值,即内涵维度、形象维度、艺术维度、趣味维度和影响维度。由此出发,我们展开对柔石的经典小说《二月》的重释,探寻其文学价值及其构成。
二、重读经典的五个维度及对经典小说《二月》的重读
《二月》是柔石的代表作,也是现代小说中的经典。过去,我们多从政治、革命、知识分子寻找正确道路等角度来看待《二月》和它的主人公萧涧秋,总觉得作者对萧涧秋同情过多,批判不够,对他的软弱性、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的实质揭示得不够,对悲剧产生的社会根源、阶级根源挖掘得不够,甚至认为作品不但没有给人物指出正确的出路,而且所描写的社会环境也缺乏历史的真实性。这不能不影响对该作品的文学评价,导致对《二月》文学价值估计不足。现在,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是在怎样的意义上对作品进行分析的?它有何局限?其实,这只是对作品的政治解读、“革命性”解读和社会意义分析,这种解读和分析又常常脱离了作为虚构的艺术文本,游离了文学性这一核心。作家塑造的是艺术形象,其着眼点是作为整体的人的精神的、性格的揭示和呈现。作家写人不可能像小学的班主任给学生写鉴定那样,清晰地告诉读者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怎样改正,以后怎么做。作家所着眼的是整体的、鲜活的艺术生命,所以,我们不仅要作政治分析,更要作艺术分析。从文学性角度,从艺术形象塑造的角度来看《二月》,我认为它都是成功的作品,过去,我们对它的成就、价值揭示得不够,应该设身处地,给予还原性的释读。
从内涵维度说,《二月》是一部有意蕴的小说,首先是小说中的人道主义和同情心温暖着读者、感染着人们。过去,我们曾经批评《二月》为人道主义唱赞歌,又指出作品揭示了人道主义的失败。其实,这两者兼而有之。萧涧秋同情与救助文嫂,帮助采莲,这不是人道主义的活生生的体现吗?人道主义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应该大力提倡的,尤其是在文学中,它也正是中外文学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因此,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不能用政治学的观点加以排斥,因为它的目的是引导人们向善,这也正是文学的使命之一。当然,文嫂的感恩思想以及为成全萧涧秋和陶岚而自杀是萧涧秋始料不及的,我不认为作者通过文嫂的死就否定了人道主义,它只是体现了人道主义的无力。我们必须把握好分寸感。其次,《二月》还是一曲自我牺牲精神的赞歌。萧涧秋为救助他人,不惜牺牲自己的金钱,还牺牲自己的爱情和婚姻,这在今天看来无异于“道德楷模”、“感动中国的人物”。尽管结果是事与愿违,但这种精神是可贵的。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说柔石总是“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他仍然相信人们是好的。”“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9]这道出了《二月》自我牺牲精神的来源。
从形象维度说,《二月》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成功的、感人的、鲜明的但并不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并不是鲁迅所说的“冲锋的战士”。这一形象不仅体现为鲜活、生动,而且还打上了作家的鲜明印记,是独一无二的,并包含丰富的内涵。当代著名作家莫言说:“一部好小说的标志应该是写出一个让人难以忘记的人物形象。这样的人物形象在过去的小说中没有出现过,生活当中可以有很多类似的人,能在人物身上看到自己的小说,这就是好的小说了。当然还要有好的语言、结构。”[10]《二月》写出了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富有同情心但性格软弱。鲁迅对萧涧秋的简短分析极为中肯,说“他极想有为,怀着热爱”,同时又“有所顾惜,过于矜持”[11],这正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过去,我们总是指责萧涧秋的软弱,认为他脱离群众,不能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其实,是人就有软弱的可能,也有软弱的权利,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去做冲锋的战士,成为革命英雄。对于一个没有缚鸡之力的儒雅书生来说,要求他一定成为革命者、具有坚定的意志,是不现实的。鲁迅曾深刻地指出过“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有知识的人,讲讲柏拉图讲讲苏格拉底是不会有危险的”,“但要他去干危险的事情,那就很费踌躇”[12]。这也正是萧涧秋萍踪浪迹六年,跑遍中国大部分的疆土,但终究不能融于革命的洪流成为弄潮儿的原因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柔石对萧涧秋的塑造是再真实不过了。
从艺术维度和趣味维度说,《二月》是一部精致的作品,是具有艺术的感人性和独创性的作品。它像一首抒情诗,任谁去读它都不能不受到强烈的感染,这感染力来自何方?就来自萧涧秋、陶岚、文嫂、采莲等组成的爱的世界。小说设置了一个基本的爱的三角,增强了作品的趣味性,又不属于或不能等同于一般的三角恋爱小说,其基本的故事和人物格局安排得恰到好处,形象、思想、精神、环境、艺术有机统一,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冲锋的战士,天真的孤儿,年青的寡妇,热情的女人,各有主义的新式公子们,死气沉沉而交头接耳的旧社会,倒也并非如蜘蛛张网,专一在待飞翔的游人,但在寻求安静的青年的眼中,却化为不安的大苦痛”。鲁迅还说《二月》艺术“工妙”“周遭的人物也都生动”[13]。从艺术的独创性来说,《二月》不同于大革命前后文坛中屡见的“革命的罗曼蒂克”式的作品,也没有像张闻天、蒋光慈、洪灵菲、丁玲、华汉包括茅盾、巴金早期的小说所描述的主人公最后走向了工农运动。倒不是说这种描写不应该,而是说这种描写欠真实,有拔高的倾向,使人感到有虚假的一面,尤其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令人难以置信。这在当时的时代和革命氛围下,创作者和接受者可能都浑然不觉,但今天的读者可能一看便知。这说明文学作品既能满足当时的读者又能满足以后的读者的需求,从而保持持续的接受是非常不易的,尤其是处于动荡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我们看到,《二月》中的萧涧秋并没有像当时众多作品中的知识分子那样从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进而投身革命,而是止于个人主义的茫然,这恰恰是作品的独到之处。
从影响维度来说,《二月》是一部有影响的小说,不论在当时还是以后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鲁迅作《二月》小引,是对《二月》的最初评价,奠定了原初接受的基石。20世纪60年代,著名电影导演谢铁骊改编执导了《二月》为故事片《早春二月》,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后因思想僵化和“左”倾错误指导被错误地批判。新时期以后被平反昭雪,拨乱反正,重新上映,同样感染了无数的观众。陈骏涛、杨世伟、王信撰长文《关于〈二月〉的再评价》(发表于《文学评论》1978年第6期)对《二月》和《早春二月》的思想意义予以拨正性的分析、评价。柔石研究的专著和其他论文也相继问世。到了90年代,蓝棣之引入“症候分析批评理论”对《二月》掩藏的症候进行分析阐释,认为“萧涧秋拒绝陶岚的最真实的原因,最深沉的原因,或者说连萧自己也不很清楚的原因,是他对于采莲的感情牵挂”[14]。继而认为,萧涧秋真正爱的既非文嫂,也非陶岚,而是7岁的采莲。这种观点,虽然遭到了质疑,但也别开生面。直到进入新世纪,我们还在重读它、重释它。这也许正是经典的魅力。
三、重读经典的三原则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不仅需要拓展边界,而且应该重读经典,在深度的发掘上下工夫。”[15]重读经典就要遵循一些原则,笔者在这里提出三点:
一是历史意识和当代意识并重的原则。要注重经典的历史价值和当代价值的考量。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曾说:“我们要研究某一艺术作品,就必须能够指出该作品在他自己那个时代的和以后历代的价值。一件艺术品既是‘永恒的’(即永久保持某种特质),又是‘历史的’(即经过有迹可循发展过程)。”这也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要在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中把握作家作品,既要有历史感,又要有当代性。历史感从何体现?就是要把对象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历史语境下设身处地地去考察。作家只能在历史、时代以及个人、家庭给他提供的主客观条件下从事创作,而难以超越这种限制。当代性从何体现?就是要看作品对当代读者的意义,对当代文化建设的意义,挖掘经典文本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从而参与当代价值的重建。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一个作家,无论他过去的贡献如何,最终的评价标准,是他当前的价值。如果一个作家没有目前的实用价值,那么,所有其他的标准都是相对的。”[16]夏志清很看重作家作品的当下价值、今天的意义,这是对的。但他不顾“过去的贡献”显然有失偏颇,需要纠正。
二是克服过度阐释,回归适度阐释的原则。一个时期以来,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经典作品的过度阐释愈演愈烈,甚至完全脱离了文本,不顾作品的特定的语境和作者的原初的意图,加以肆意的主观猜想和推论,把原本简单的问题、单纯的文本复杂化,如对鲁迅《一件小事》的解读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或者引入所谓“新方法”、新概念来套旧作品,这时,经典文本就成了印证新方法的材料,其阐释也就成了表达阐释者新思想、新理念的竞技场。一般说来,经典作品往往具有较大的阐释空间,甚至具有挖掘不尽的潜价值,但任何新的阐释,新的挖掘都必须遵循文本的内在特质,符合文本的实际情形,而不是阐释者的主观臆断和任意肢解。一千个读者,可以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不能有一千个堂吉诃德。经典作品并不都是深不可测的,也并不都是挖掘不完的,因此,要提倡适度阐释,反对过度阐释。适度阐释就是要紧贴作品、接地气,贴着地面前行,而不能在云端舞蹈。
三是创新与还原兼顾的原则。经典重读当然要创新,从经典中发现新内涵、新特质、新意义、新价值。但创新也是有限度的,不能为创新而创新,也不能瞎创新、乱创新。创新是在还原文本、还原释读基础上的创新,这个“新”是来源于文本,是从作品中引申、生发出来的,是要符合作品的实际的。创新是要和还原与坚守兼顾的,要在对经典作品进行还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在创新过程中,要坚守经典作品的主旨、本体、原貌、神韵,回到作家、作品那里去,保持经典的原汁原味。人往往只有在深深地沉浸于历史和传统的时候,才能真正体会到人类生存的艰难和伟大。如果我们能不断地和人类的文化经典、文学经典达到一种还原式的领会和心灵上的交融,我们对当下肯定能多一分体验,多一分理解。
至于经典重读的方法,首先是要直观感受,重返经典,注重细读,去建构自己的阅读体验,这种直观感受和阅读体验会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我们常说,经典是常读常新的。每一次重返经典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体验和理解。要尽量挣脱以往定评、定论对自己阅读的干扰和影响,形成自己对文本的鲜活的感受,因为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文学作品不是一尊纪念碑,而是像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其次是设身处地,把经典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历史语境之内,结合作家的生平、思想、观念把握其经典文本,并联系作家的其他作品以及同时代的作品进行比照和互证,这样得出来的认识才比较确凿。比如,柔石的另一部小说《三姊妹》所写的章先生在断送了莲姑和蕙姑的婚姻幸福以后,抱着聂赫留道夫式的赎罪心理,去救赎莲姑和蕙姑——想娶离婚后衰老、美丽消退的两位姊妹,愿意自己成为一个奴隶。这和《二月》中萧涧秋想娶寡妇文嫂具有类似性、互文性。再次是在前两个方面的基础上进行“明理分析”,开拓思维空间,提升创造境界。温儒敏所提倡的三段式的研究思路,也不失为经典重读的好方法。
本文系2013年度辽宁省社科联重点项目“现代文学价值评估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013LSLKLZDIAN—1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
[1]王嘉良、范越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生长点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
[2]王嘉良、范越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生长点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
[3]王嘉良、范越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生长点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
[4]王嘉良、范越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生长点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
[5]王嘉良、范越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生长点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
[6]余三定:《“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温儒敏访谈》,《文艺报》,2012年12月12日。
[7]温儒敏:《再谈现代文学史写作的“边界”与“价值尺度”》,《学术月刊》,2011年第12期。
[8]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271、279页。
[9]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96—497页。
[10]莫言:《作家应该爱他小说里的所有人物——与马丁·瓦尔泽对话》,《莫言诺贝尔奖典藏文集·碎语文学》,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75页。
[11]鲁迅:《柔石作〈二月〉小引》,《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53—154页。
[12]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25页。
[13]鲁迅:《柔石作〈二月〉小引》,《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53—154页。
[14]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8页。
[15]秦弓:《略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重读》,《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16]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