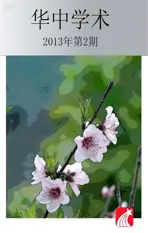论温子升的思想品格与诗歌风格
2013-04-12柏俊才
柏俊才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430079)
温子升是北魏杰出的汉族文学家,与魏收、邢邵并称“北地三才”。他的诗歌成就较高,影响较大。《魏书》本传云:“济阴王晖业尝云:‘江左文人,宋有颜延之、谢灵运,梁有沈约、任昉,我子升足以陵颜轹谢,含任吐沈。’”[1]认为温子升的诗歌成就可以与元嘉三大家之颜延之、谢灵运相媲美,可以与梁代诗人沈约、任昉相并肩。尽管这种说法不乏溢美之辞,但却反映了同时代人对温子升的评价。南朝萧衍曾云:“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恨我辞人,数穷百六。”[2]萧衍将温子升比作曹植与陆机。这说明无论南人或北人,都对温子升的诗歌成就发出了由衷的赞美。的确如此,在南北朝时期,温子升是少有的诗歌名家。
一、温子升的生活时代及其思想
温子升之生年,向来无人考证。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标其生年为公元495年,葛晓音《八代诗史》、钱志熙《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述》、袁行霈《中国文学作品选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陈文新《中国文学编年史》均同。此说值得商榷。今结合所见资料,试辨之。
温子升之生年,史书未载,今所见者唯《魏书·文苑传》中一则资料,“熙平初,中尉、东平王匡博召辞人,以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子升与卢仲宣、孙搴等二十四人为高第。于时预选者争相引决,匡使子升当之,皆受屈而去。搴谓人曰:‘朝来靡旗乱辙者,皆子升逐北。’遂补御史,时年二十二”[3]。《北史·文苑传》与此同。熙平初,中尉、东平王匡征士,温子升补御史,时年22岁。熙平是北魏肃宗孝明皇帝元诩的年号,仅有二年,故“熙平初”很容易让人想到熙平元年(公元516年)。熙平元年,温子升22岁,则其生年为明帝建武二年(公元495年)。这种推理看似无懈可击,事实上有所偏颇,原因是未注意到其他旁证资料。元匡任御史中尉的时间史书未载,但《魏书》有明确记载的是熙平元年、熙平二年元匡为御史中尉。又据《魏书·肃宗纪》载,元匡封东平王的时间在熙平二年(公元517年)二月丁未。如果是熙平元年,元匡仅仅是御史中尉;只有在熙平二年,才可称元匡为中尉、东平王。故中尉、东平王招部曹的时间,只可能是熙平二年。又《魏书·肃宗纪》载中尉、东平王匡招贤之事时云:“(熙平二年正月庚寅)诏‘选曹用人,务在得才,广求栖遁,共康治道。州镇城隍,各令严固。斋会聚集,纠执妖喧。囹圄皆令造屋,桎梏务存轻小。工巧浮迸,不得隐藏。绢布缯彩,长短合式。偷窃军阶,亦悉沙汰。籍贯不实,普使纠案,听自归首,逋违加罪。’诏中尉元匡考定权衡。……(二月)丁未,封御史中尉元匡为东平王。”[4]熙平二年,中尉、东平王匡招贤,温子升以才学拔萃,补御史,年仅22岁,则其生年在明帝建武三年(公元496年)。
温子升之卒年亦有分歧。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钱志熙《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述》、袁行霈《中国文学作品选注》、陈文新《中国文学编年史》、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等书记为公元547年,葛晓音《八代诗史》、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二书记为公元546年。二者的差别仅一年,但这对一个文学家而言,是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故不得不辨。关于温子升之死,《魏书》本传云:“及元瑾、刘思逸、荀济等作乱,文襄疑子升知其谋。方使之作献武王碑文,既成,乃饿诸晋阳狱,食弊襦而死,弃尸路隅,没其家口。”[5]元瑾、刘思逸、荀济等叛乱之事,《北史》记为武定五年(公元547年)八月壬辰,此次叛乱当月就被平定,温子升入晋阳狱及饿死亦当为本年八月之事。故葛晓音《八代诗史》、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二书所记有误,温子升的卒年当在武定五年(公元547年)。
温子升生活的这52年,是北魏后期矛盾尖锐,政变频繁,战乱不断,东西魏对峙,北齐谋篡东魏的时期。这一时期,各种势力膨胀,政权屡易,就温子升生活的北魏后38年,皇帝先后更换了8个。在这样的时代,各种社会思潮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温子升出生之时,正是孝文帝全面推行汉化的时期。在文化政策上,孝文帝采用的是以儒学为主,调和三教的政策。孝文帝去世后,社会遽变,士人们在道家思想中寻求明哲保身,在佛教思想中寻求心灵的慰藉,于是儒学衰微,释、道兴盛。温子升并没有随波逐流,一味地去学释、道,而是以儒学为主,以佛为辅,形成了外儒内佛的思想。
温子升的少年时期是北魏儒学兴盛的太和年间,顺应时代思潮,温子升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儒学教育,“初受学于崔灵恩、刘兰,精勤,以夜继昼,昼夜不倦”[6],有非常好的儒学素养。崔灵恩,清河武城人,是梁代大儒,少笃学,从师遍通“五经”,尤精“三礼”、“三传”。初仕北魏为太常博士,天监十三年(公元514年)南归萧梁,温子升受学于他大约是此年之前,即其19岁前。刘兰是北魏著名的儒学家,“读《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经》。先是张吾贵以聪辨过人,其所解说,不本先儒之旨。唯兰推《经》、《传》之由,本注者之意,参以纬候及先儒旧事,甚为精悉。自后经义审博,皆由于兰”[7]。刘兰是武邑(今属山东)人,30 岁始发奋读书,终成大儒。温子升随其学习,当是刘兰到京城以后的事情。由《魏书》本传来看,刘兰初入京城在永平年间。永平是宣武帝元恪的年号,公元508—公元511年,共4年,温子升从其学大约在此时,是其12岁至15岁之时。自小有名师指点,加以温子升刻苦攻读,故其儒学造诣非同一般。在《舜庙碑》中歌颂舜的丰功伟绩,“受文祖之命,致昭华之玉,班五瑞于群后,禋六宗于上玄,舞干戚而远夷宾,弃金璧而幽灵应。青云浮洛,荣光塞河,符瑞必臻,休祥咸萃”[8],推舜为“帝王之称首”,实则是规劝北魏皇帝以德治理天下,群雄自当归附。在《常山公主碑》中赞扬常山公主的美德,“公主禀灵宸极,资和天地,芬芳有性,温润成质。自然秘远,若上元之隔绛河;直置清高,类姮娥之依桂树。令淑之至,比光明于宵烛;幽闲之盛,匹秾华于桃李。托体宫闱,而执心 顺,婉然左辟,率礼如宾。……立行洁于清冰,抗志高于黄鹄,停轮表信,阖门示礼,终能成其子姓,贻厥孙谋”[9]。常山公主是献文帝元弘之女,下嫁驸马都尉陆昕之为妻,她能践行礼教,孝敬公婆,恪守妇道,温良恭让,具有儒学约束下的传统女性的一切美德。她生三女而无子,主动要求陆昕之纳妾。这样的女子让温子升刮目相看,故撰此文予以褒扬,把她比作冰清玉洁的嫦娥,忠于爱情的娥皇女英。这些作品都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的创作,是在乱世中对儒学的弘扬。
除儒学之外,温子升的思想中还有佛学的因子。目前仅《元魏孝明召释道门人论前后》中涉及温子升与佛教的关系:“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召佛道二宗门人殿前。……太尉丹阳王萧综、太傅李寔、卫尉许伯桃、吏部尚书邢栾、散骑常侍温子升等一百七十人读讫,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更无言说。臣等所议,姜斌罪当惑众。帝加斌极刑,三藏法师菩提流支苦谏乃止,配徙马邑。”[10]这段文字见于《广弘明集》,是对北魏佛道论争的一次记载。在这次论争中,道士刘斌获罪流放,佛教取得胜利,温子升参与其中,而且很明显站在佛教一方。以此来说明温子升受佛学影响未尝不可,但仍显勉强。温子升生活的北魏后期,正是佛学复兴之时。高祖孝文帝元宏在京城建鹿野佛图供僧人居住,亲自度人为僧,并下诏:“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听大州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为常准,著于令。”[11]他以法律的形式要求各州郡定期定额度人为僧。上有所好,下行其效,高祖时佛教发展极为迅速,就京城而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世宗宣武帝元恪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并派遣高僧惠生西行取经,取得经论一百七十部。据日本种智院大学密教研究所张雅静先生所考,北魏的佛教造像大盛于孝文帝元宏之后[12]。在这样的社会风尚之下,温子升不受佛学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从文学创作来看,与佛学有关的作品主要有《大觉寺碑》《寒陵山寺碑》《印山寺碑》《定国寺碑》4篇文章。充斥这4篇作品的是大量与佛教有关的术语,如“缘障”“三乘”“八解”“欲海”“五烛”“天龙”“果报”“因缘”“苦乐之境”“生死之门”等。像这样专业的术语,不是一个对佛学一知半解的人所能运用的。因此,温子升的佛学修养非同一般。
儒学与佛学在温子升的身上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所关联的。南北朝时期,儒学的发展基本上都是援佛入儒,温子升也不例外。儒家注重情理与事理,佛学注重性情。在外在情事上,温子升以儒家精神来规范约束自己,在内在性情上,他以佛学来修身养性,从而形成了外儒内佛的思想特征。这样的思想特点,在其创作中亦可以得到印证。像《大觉寺碑》前半部分有云:“道成树下,光属天上,变化靡穷,神通无及。置须弥于葶苈,纳世界于微尘。辟慈悲之门,开仁寿之路。殛烦恼于三涂,济苦难于五浊。非但化及天龙,被教人鬼,固亦福沾行雁,道洽游鱼。”[13]这纯粹是佛语,与佛教徒的作品无异。然在文末却云:“主上乃据地图,揽天镜;乘六龙,朝万国;牢笼宇宙,禁带江山;道济横流,德昌颓历。四门穆穆,百僚师师,乘法船以径度,驾天轮而高举。神功宝业,既被无边,鸿名懋实,方在不朽。”[14]这里表现的是儒家的“三不朽”精神。全文纳佛于儒,大有以佛治国而达天下一统之意。像《定国寺碑》亦如此,读“惟无上大觉,均悟玄机,应现托生,方便开教,圣灵之至,无复等级,威神之力,不可思议。动三乘之驾,泛八解以,引诸子于火宅,渡群生于海岸。自一音辍响,双树潜神,智慧虽徂,象法犹在,光照金盘,言留石室,遍诸世界,咸用归仰”[15]这些文字,我们似乎在读佛典,然仔细体会,作者用貌似佛学的语言,歌颂了高欢救世平乱的功业,依然是援佛入儒。
二、温子升的人生悲剧及根源
温子升出入于儒、佛的复杂思想,造成了其个人秉性与行为方式的复杂性。同时,他处于政治遽变的历史时期,在某种程度上也对其性格矛盾性与复杂性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温子升的人生悲剧,与其复杂的个性与思想不无关系。
温子升作为北魏的下层文人,经历了胡太后专权、汾阴之变和东西魏对峙等重大历史事件,在乱世中苟延残喘,祈求保全性命,然不幸卷入了政治漩涡,最终饿死在晋阳监狱。对于这样一个饱经战乱的文人,历代评价褒贬不一,大致可分为水火不相容之二途。从时人与后世文人的评价中,我们可尝试窥测其人生悲剧产生的根源。
《魏书》本传云:“子升外恬静,与物无竞,言有准的,不妄毁誉,而内深险。事故之际,好预其间,所以终致祸败。”[16]“好预事故”,这是史学家魏收对温子升的评价。魏收与温子升同列“北地三才”之中,两人相知多年,同朝为官,同掌文诰。因此,魏收的评价应该是可信的。在魏收的眼中,温子升是一个两面派,表面与世无争,内心极为阴险,思虑甚深,好参与朝中大事。隋代大儒王通云:“太原府君曰:‘温子升何人也?’子曰:‘险人也。智小谋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齿焉,则有由也。’”[17]“智小谋大”是说温子升的智慧是有限的,但谋虑极深,终致祸败,实际上与“好预事故”是一致的。南宋叶适云:“史称‘温子升外恬静与物无竞,言有准的,不妄毁誉;而内深险。事故之际,好预其间,所以终致祸败。’尔朱、高欢父子之间,惟子升能有意王室,一时人士,如此比者绝无矣。魏收之言,不亦宜乎?”[18]叶适肯定温子升是捍卫王室的有功之臣,同时也认为魏收的“好预事故”的评价并没有错。
但是,明代的张溥在《温侍读集题辞》中云:“史言温鹏举外静内险,好预事故,终致祸败。今据史魏庄帝杀尔朱荣、元瑾等,背齐文襄作乱,鹏举皆预谋。此二事者,柔顺文明,志存讨贼,设令功成无患,不庶几其先大将军之诛王敦乎?魏书目为深险,佛助何无识也?……元颢之变,策复京师,计之上也。上党即不能为桓文,鹏举之言,管狐许之矣。北人不称其多智,而徒矜斩将搴旗于文墨间,犹皮相也。”[19]张溥把温子升参与杀尔朱荣、元瑾二事看作是“柔顺文明”,认为可以和王导诛王敦相提并论。同时对温子升的谋略大加赞赏,认为魏收不称其多智,是没有真正认识温子升。清代乾隆皇帝在《晓山》诗中云“冰清温子升”[20],把温子升看作冰清玉洁的人。
对温子升之所以产生这两种水火不相容的评价,主要原因在于评论者所持的立场不同。魏收、王通、叶适都是儒学家,但是他们的儒学信仰与温子升不同。魏收、王通、叶适将道家的明哲保身思想融入了儒家思想之中,在大是大非面前不是直面人生,而是讲求退避。他们的这种思想,正是温子升所生活时期的大多数儒学家的立场,能够使得他们在乱世中远离灾祸,保全性命。由这种立场出发来看温子升,他当然是“好预事故”、“智小谋大”的了。温子升就是没有像魏收、王通、叶适那样明哲保身,才导致人生悲剧。张溥和乾隆是从儒家积极进取的角度来评价温子升的。作为明末复社成员的张溥,他反清复明的精神与温子升杀尔朱荣、元瑾,背齐文襄作乱等事件中表现出来的爱国精神是一致的,故大加赞赏,肯定其“多智”;乾隆从帝王的角度看温子升,他积极参与谋略都是为了国家的一统,故称为“冰清”。由此说来,这两种不同的评价都是从儒家的角度出发来探讨温子升人生悲剧的根源。孰对孰错,尚难分辨。如果我们要辨析这些认识,大致要弄清楚三个问题:一是北魏后期、东魏、北齐的几个重大历史事件温子升是不是主谋?二是各种政治力量为什么要选择温子升?三是温子升的有关这些历史事件的文章体现了他怎样的思想认识?
北海王元颢南奔萧梁,萧衍暗中相助,准备反叛北魏,上党王元天穆奉命征讨,温子升为其行台郎中。永安二年(公元529年),元颢攻陷洛阳,北魏朝廷危在旦夕,元天穆问计于温子升:“‘即欲向京师,为随我北渡?’对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狈。元颢新入,人情未安,今往讨之,必有征无战。王若克复京师,奉迎大驾,桓文之举也。舍此北渡,窃为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21]这是史书中对温子升谋略的唯一记载,在当时情境下,温子升劝元天穆入洛阳讨伐元颢,克复都城,迎接庄帝,建立霸业。平心而论,这个策略显示了温子升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可惜未被采纳。除此之外,在其他的历次事件中,温子升只是奉命起草诏书而已,并未参与定计。永安三年(公元530年),庄帝杀尔朱荣和上党王元天穆,“子升预谋,当时赦诏,子升词也”[22]。《魏书》本传的这段话,很容易让人相信温子升参与谋略,实则恐非。据《魏书》载,参与此谋的有义邕、杨侃、李晞、城阳王元徽、李彧、元融和元忻之,这些人要么是皇室成员,要么是庄帝的心腹。温子升当时只是中书舍人,职责是专掌诏诰,恐没有资格参与谋略。《北史》尔朱荣本传有云:“至(九月)十八日,召中书舍人温子升告以杀荣状,并问以杀董卓事。子升具通本……良久,语子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犹须为,况必不死!宁与高贵乡公同日死,不与常道乡公同日生。’”[23]这则材料说明诛杀尔朱荣、元天穆之事不是温子升的谋略。北魏后期,高欢谋夺魏氏天下,随着其势力的日益壮大,他与魏帝的矛盾终于公开化了。永熙三年(公元534年)五月,魏孝武帝元修调集兵力,托名南伐萧梁,实则是对付高欢,高欢抗命,出兵江左,“魏帝知觉其变,乃出神武表,命群官议之,欲止神武诸军。神武乃集在州僚佐,令其博议,还以表闻。……辛未,帝复录在京文武议意以答神武,使舍人温子升草敕。子升逡巡未敢作,帝据胡床,拔剑作色。子升乃为敕曰……”[24]这是高欢与魏帝之间的最后较量,孝武帝元修被逼出奔长安宇文泰,北魏灭亡。温子升在这件事上的态度,《北齐书》用了“逡巡”二字,“逡巡”者,犹豫不决、退避、退让之意也,温子升实在不愿意卷入这样的政治漩涡中去。最后还是替孝武帝草成《孝武帝答高欢敕》。武定五年(公元547年),元瑾、刘思逸、荀济等作乱,“文襄疑子升知其谋。方使之作献武王碑文,既成,乃饿诸晋阳狱,食弊襦而死,弃尸路隅,没其家口”[25]。温子升知元瑾等之谋,背文襄之乱,实在是天大的冤枉!笔者反复阅读《魏书》,试图能找出些蛛丝马迹,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元瑾曾与温子升同为文襄馆客,仅此而已。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交往,本不相知,何能预其谋?文襄对于此事的态度,《魏书》本传用了一个“疑”字,“疑”者本无真凭实据也。一代文人温子升,就在“疑”这样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之下丧命!温子升死后,宋道游为其收葬,文襄云:“子升吾本不杀之,卿葬之何所惮?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26]这当然是惺惺作态,不可信。笔者以为,高澄诛温子升,实欲替其父高欢报仇。在《孝武帝答高欢敕》中,温子升虽温文而婉,但对高欢不臣之心的揭露,路人皆知,引起高澄的极大不满,故借机处死了温子升。
在北魏后期、东魏、北齐的历次重大事件中,温子升只是参与起草诏书,并未参与谋略。那么,各种政治力量为什么会选中温子升?原因是温子升是北魏最杰出的文人。“北地三才”中,邢邵与温子升同时,但其真正崭露头脚是在北齐;魏收晚温子升11岁,文采显露于世在北齐,故在北魏,温子升的才华无人能比。《北史》邢邵本传云“(邢邵)与济阴温子升为文士之冠,世论谓之温、邢。钜鹿魏收虽天才艳发,而年事在二人之后,故子升死后,方称邢、魏焉”[27]。史学家李延寿将“三才”的名次排为温、邢、魏,就是因为温子升出道早、成名早之故。《北史》李德林本传云“魏收尝对高隆之谓其父曰:‘贤子文笔,终当继温子升’”[28],魏收是很推崇温子升的;《魏书》本传云:“建义初,为南主客郎中,修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党王天穆时录尚书事,将加捶挞,子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庄帝曰:‘当世才子不过数人,岂容为此,便相放黜。’”[29]在魏孝武帝的眼中,温子升为“当世才子”;“会并州定国寺新成,神武谓陈元康、温子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时称妙绝,今《定国寺碑》当使谁作词也?’”[30]高欢称温子升《芒山寺碑》“时称妙绝”;“阳夏太守傅标使吐谷浑,见其国主床头有书数卷,乃是子升文也”[31],温子升的文章远播西北。温子升的才华众人莫比,故在北魏后期各种政治力量选取他撰文,也就不足为奇了。
温子升所撰写的有关北魏后期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品,鲜明地体现了他的外儒内佛思想。前文已经述及,温子升自小追随崔灵恩、刘兰学习儒学之义。崔灵恩、刘兰精通诸经,然最擅长的莫过于《左传》。大约受其影响,温子升对《左传》相当精纯,《左传》那种维护周礼、尚德崇礼、以礼来评判人物的思想,深深浸染着他。在北魏后期、东魏、北齐的许多历史事件中,温子升都是以《左传》这一思想为指引,维护北魏王朝,歌颂为北魏作出贡献的英雄,鞭挞贰臣贼子。正光元年(公元520年)七月,侍中元叉、中侍刘腾发动宫廷政变,逼肃宗于显阳殿,幽胡灵太后于北宫,杀太傅、领太尉、清河王怿,全国震惊,闻之者伤心欲绝。清河王怿系孝文帝第五子,因其貌美,被胡灵太后逼通,终成为胡灵太后淫乱后宫的牺牲品。清河王怿之逝,“致使忠臣烈士,丧气阙庭;亲贤宗戚,愤恨内外”[32]。闻此噩耗,温子升写下了《相国清河王挽歌》,哀悼清河王怿之死,控诉元叉、刘腾的罪恶。武泰元年(公元528年)四月,河阴之变爆发,尔朱荣沉胡灵太后和幼主元钊于河,杀诸王及朝臣二千余人。“时又有朝士百余人后至,仍于堤东被围。遂临以白刃,唱云能为禅文者出,当原其命。时有陇西李神俊、顿丘李谐、太原温子升并当世辞人,皆在围中,耻是从命,俯伏不应。有御史赵元则者,恐不免死,出作禅文。”[33]在这场巨变中,温子升拒作禅文,以死捍卫北魏王朝的尊严,具有高贵的民族气节。永安三年(公元530年)九月,庄帝杀尔朱荣和上党王元天穆,温子升草成《孝庄帝杀尔朱荣大赦诏》,歌颂了尔朱荣孝昌勤王、征葛荣、平元颢之功,声讨其河阴之变的罪行,谴责他“方复托名朝宗,阴图衅逆。睥睨天居,窥觎圣历。乃有裂冠毁冕之心,将为拔本塞源之事”[34]的贰臣之心。十二月,尔朱兆攻陷京城,弑孝庄帝子攸,杀皇子及大臣,高欢率三万军队击溃尔朱兆二十万虎狼之师,扶后废帝元朗继位,温子升写成了《寒陵山寺碑》,歌颂高欢捍卫王室之功,把他比作尊周而能建立霸业的晋文公和齐桓公。永熙三年(公元534年)五月,高欢与魏孝武帝元修交恶,高欢有弑君之心,孝武帝有诛高欢之意,温子升草成《孝武帝答高欢敕》,指斥高欢不臣之心,文末“古语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既亲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笔拊膺,不觉歔欷”,以委婉含蓄之笔,揭穿了高欢企图弑君的狼子野心。我们实在无意过分拔高温子升,认为他是北魏儒学家中鹤立鸡群之人。在历次政治事件中,佛学的修身养性使得他迟疑、犹豫,但最后还是儒家的精神占了上风。这种外儒内佛的思想使得他在任何时候都以国家的利益为重,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从维护北魏国家一统的角度出发的。
经历了北魏后期、东魏、北齐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温子升,并不是出谋划策之人,亦非领兵作战之将,只不过因文士之冠而临危受命起草诏书而已。在这些作品中,表现了温子升拥护北魏王室,怒斥心怀叵测的贰臣贼子的外儒内佛的鲜明思想。故而既不能目之为“好预事故”,又不能看做是“智小谋大”,也不能称为“柔顺文明”,更不能把他当做多智之人。我们只能说,在儒学衰微的南北朝,身罹祸乱的温子升具有独特的个性,他那外儒内佛的思想导致了其人生悲剧。杨遵彦在《文德论》中称“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升彬彬有德素”[35]。“彬彬有德素”大约是对温子升最好的评价,也是其人生悲剧的根源。
三、温子升的诗风及其渊源
温子升是北魏杰出的文学家,《北史·文苑传》云:“《魏书》序袁跃、裴敬宪、卢观、封肃、邢臧、裴伯茂、邢昕、温子升为《文苑传》,今唯取子升,其余并各附其家传。”[36]李延寿取温子升为北魏文学家之首,这个看法是很有见地的。大约在北魏,就文学才能而言,无人能与温子升媲美。
温子升诗歌现存11首,艺术成就在北魏是首屈一指的。关于其诗风,历代以来认识也有不同。周建江先生认为温子升是北魏“宫体香艳诗派”,“风格清丽婉约”[37],郑宾于先生认为北魏诗歌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因袭的,古董式的,‘言多胸臆,彫古酌今’派;一派是创造的,趋新的,表现时代‘兴属清华’派”[38],并说温子升的诗歌风格是属于后一派。葛晓音先生以为温子升“善于模仿南朝诗文,风格清婉”[39]。这三种说法都仅仅看到温子升诗风的一个方面。曹道衡先生以为温子升的诗歌“明显地从南朝诗歌中学习借鉴到不少有益的成分……还有一些诗更能代表北朝诗风”[40],钱志熙先生认为“温诗学南朝,但同时有北朝特色”[41],曹、钱二先生注意到温子升诗歌中的两种风格,但具体是什么,没有明言。因此,这些概括既不准确,也不完善,而且从上述五家的观点来看,很明显他们都只很看重温诗学南朝诗风的特点。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很容易诱人误入歧途。实际上,温诗的主导风格应是北朝诗歌一贯的质朴诗风,而学习南朝诗歌,最终达到南北交融的清婉诗风是其创新。
刚健质朴最直观的层面是选取口语、俚语入诗,语言质朴无华,有别于南方诗歌的华艳。温子升的许多诗作,是在北曲的基础上加工创作的,像《白鼻》来源于魏高阳人乐歌,《安定侯曲》来源于魏南部尚书安定侯邓宗庆乐人歌,《敦煌乐》与《凉州乐歌二首》来源于西凉乐等,这些诗作不可避免地继承了北曲语言俚俗的特点。像《白鼻》的首句“少年多好事”,直如家常口语,“好事”本俗语,但却准确刻画出纨绔子弟精力旺盛、爱出风头、放浪轻浮的性格。又如《结袜子》中“谁能”、“会自”、“终”、“空”;《敦煌乐》中“自有”、“不减”;《凉州乐歌》中的“但事”、“谁道”等词语都是来自民间的口语,温子升把这些词嵌入诗中,贴切自然,赋予俗语以新的生命力。刚健质朴还表现在运用白描等手法,营造出苍凉古朴的意境美。像“少年多好事,揽辔向西都。相逢狭斜路,驻马诣当垆”(《白鼻》)采用白描的手法,运用“揽辔”、“相逢”、“驻马”三个动词,既写出了繁华之地、青楼和酒肆三个场景,又表现出了贵族子弟任侠豪爽的气质。又如“客从远方来,相逢歌且笑。自有敦煌乐,不减安陵调”(《敦煌乐》),语言古朴自然,直如白话,用白描的手法简笔勾勒出游子到敦煌时内心的喜悦之情。敦煌是塞外边镇,在南北朝之际许多人是为了避乱远徙敦煌,景色荒凉,人烟稀少,难免产生思归之情。温子升一返常调,变悲为喜,赋予敦煌以全新的认识。《凉州乐歌二首》连用“武威”、“姑臧”、“玉门关”、“龙城坂”四个地名,不仅有距离的遥远之感,更有一种古朴苍凉的意蕴。《相国清河王挽歌》采用白描的手法描绘出清河王怿被杀前后王府的不同,形成鲜明的对比,表达作者的哀悼之意。对于这类作品后人评价甚高,像王夫之就曾云:“江南省偶既盛,古诗已绝,晋宋风流仅存者,北方一鹏举耳。”[42]他认为其继承汉代古诗的传统,独标高格,无人能比。
温子升诗风还有清婉的一面。“清婉”二字是《魏书》本传用来评价温子升诗风的,此后历代评论家多有述及,表述各异,意思大致相同。《北史·文苑列传》称温子升等人“并自孤寒,郁然特起。咸能综采繁缛,兴属清华”[43],《隋书·文学列传》称温子升等人“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44]等都是就温子升学习南朝诗歌而言的,“综采繁缛”和“缛彩郁于云霞”说明在唐人眼中,温子升依然学的是南朝诗歌华丽的辞藻,实则恐非。温子升学习南朝诗歌,不排除有辞藻华丽的一面,更重要的是他进行了革新,形成了自己清婉的风格。
清婉首先是清新。温子升的诗善于选取典型的意象,寥寥几笔,便能勾勒一幅画面,给人以清新之感。像《春日临池》前四句“光风动春树,丹霞起暮阴。嵯峨映连璧,飘摇下散金”,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春日黄昏美景图。碧绿的树木、红色的晚霞、金色的树叶和青色的倒影相映成趣,色彩斑驳,对比鲜明,水天一体,自然浑成。特别是以嵯峨之山峰比喻映照在水中的晚霞,神来之笔,极为清新。这四句诗辞藻华艳,随着时光的推移,写出了晚霞的升起与消散,境界极为壮观,与南朝诗歌的靡靡之音不可同日而语。又如《咏花蝶》前四句“素蝶向林飞,红花逐风散。花蝶俱不息,红素还相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春日花戏蝶图。素蝶、红花、绿树等意象的选取,很好地表达了如沐春风的骀荡之情。
其次是婉转,主要表现为音调的婉转和表现手法的婉转。南朝齐永明以后,声律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押韵、对仗等技巧渐次被诗人所接纳,诗歌音调婉转和谐。温诗非常注意押韵,现存11诗,已初步形成了偶句押韵的格式,像《凉州乐二首》偶句“城”、“横”押同一韵(其一),“坂”、“远”押同一韵(其二);《春日临池》偶句“阴”、“金”、“琴”、“心”押同一韵;即便是长达20句的《从驾幸金墉城》诗,也是偶句“并”、“景”、“屏”、“影”、“静”、“井”、“冷”、“警”、“幸”、“聘”押同一韵。这种整齐的偶句押韵的方式与唐代律诗相接近,已远远超出南朝新体诗的艺术范式。温诗中的对仗是随处可见,像“嵯峨映连璧,飘摇下散金”(《春日临池》)、“素蝶向林飞,红花逐风散”(《咏花蝶》)、“御沟属清洛,驰道通丹屏”(《从驾幸金墉城》)等对仗极为工整。像其《捣衣诗》好评如潮,多是从声律的角度来评价的,像明代杨慎云:“后魏温子升《捣衣》,第五、六句又作五言。”[45]清代赵翼云:“温子升《捣衣》一首……七言属对,绝似七律,惟篇末杂以五言二句耳。”[46]的确如杨慎与赵翼所言,《捣衣诗》如果五、六句“七夕长河烂,中秋明月光”二句不是五言而是七言的话,那么这首诗就是完美的七言律了。偶句“黄”、“凉”、“光”、“狼”押同一韵,三、四句“香杵纹砧知近远,传声递响何凄凉”对仗工整,平仄也合七律要求,故清人沈德潜评云“直是唐人”[47]。这是后人超越时代,按照律诗的要求来评价这首诗的。如果我们着眼于南北朝来看,这首诗在押韵、对仗、声律方面接近唐律;句式不纯恰恰说明它还没有演进到律诗的阶段,如果三、四句是合律的七言,那它就是唐七言律了。注重押韵与对仗技巧,使得温诗婉转流动。从表现手法来看,温诗有意识地将自己比作“弃妇”、“思妇”,委婉含蓄地表现内心的忧愤之情。如《结袜子》:“谁能访故剑,会自逐前鱼。裁纨终委箧,织素空有余。”这首诗四句连用四个典故:第一句用汉宣帝刘询的典故,汉宣帝即位前曾娶许氏,即位后朝臣议立霍光之女为皇后,汉宣帝求故剑,大臣随奏立许氏为后。“故剑”后来用以指代结发妻子。第二句用龙阳君的典故,龙阳君与魏王一起钓鱼,龙阳君钓得十余条鱼后潸然泪下,说当他钓得第一条鱼时非常高兴,后来得十余条后就想抛弃前面所得之鱼,以此来劝谏魏王不要亲信谗佞。“前鱼”用以比喻失宠之人。第三句用汉班婕妤的典故,以团扇喻自己失宠。第四句用汉乐府民歌《上山采蘼芜》的典故,喻弃妇。温子升在用这四个典故的时候,用“谁”、“终”、“空”三个词使得典故的原意发生了变化,表现了弃妇内心的忧伤之情。这首诗大约创作于温子升追随上党王元天穆讨伐元颢之时,温子升劝元天穆入京城驱逐元颢迎接庄帝,元天穆不但不听,反派遣温子升到洛阳见元颢,被任命为中书舍人。不能抗贼,反而要为宦叛臣,其内心痛苦可想而知。而且从当时情形来看,这件事成为人们的笑柄,“北迁邺,于路见狗,温子升戏曰:‘为是宋鹊?为是韩卢?’神俊曰:‘为逐丞相东走?为共帝女南徂?’”[48]李神俊讥讽温子升就是为此事而言。又如《捣衣》诗写思妇,集中笔墨写了七夕情人节和中秋月圆之时思妇无限凄凉和伤感。这首诗大约写在孝武帝元修被高欢驱逐之后,诗人以思妇自喻,含蓄委婉地表达了其爱国之情,含蓄蕴藉,余韵袅袅,境界颇为空灵。梁武帝萧衍曾评温子升是北朝的曹植和陆机,曹植后期诗多以弃妇、思妇自喻,温子升大约继承了曹植的这种创作精神。
质朴与清婉不是割裂的,有时一首诗中可兼具这两种诗风。如《安定侯曲》:“封疆在上地,钟鼓自相和。美人当窗舞,妖姬掩扇歌。”《魏书·灵征志下》有太和元年南部尚书安定侯邓宗庆的记载,这是温子升生前21年前的事情,故不可能是写当朝事,而是一首乐府诗,郭茂倩《乐府诗集》将其收在《杂曲歌辞》中。诗歌写安定侯居功自傲、穷奢极欲、歌舞升平的享乐生活。此诗前两句质朴,后二句清婉。《结袜子》亦当如是观。这种情形是温子升在鲜卑族诗歌质朴的基础上,吸取了南朝诗歌有益的成分,而自创的一种新体诗,故影响较大。直到晚唐,段成式还说:“温子升独擅邺下,常见其词,笔亦足称,是远名近得。”[49]这足以证明到晚唐温子升还有一定的影响。
温子升的诗风有其渊源。过去文学史家多认为其质朴的诗风是学习北朝民歌,清婉的诗风是吸收了南朝诗歌,这种说法过于含混。从北朝文学的发展来看,温子升是继承了拓跋鲜卑族文学质朴的风格,同时吸收了南方诗歌清丽的诗风。
温子升刚健质朴的诗风源于北方少数民族文学。《隋书·文学列传》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50]“词义贞刚”、“气质”是北朝诗歌的总体风格,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刚健质朴。这种刚健质朴不是某个作家的风格,而是北朝少数民族共有的风格特征。从久远的北魏民族诗史《真人代歌》到北周的灭亡,北朝的少数民族文学风格一直未变。北魏初期历代帝王既艳羡汉族文化,又惧怕汉族文化,残酷的杀害汉化士人。沙漠汗、猗卢、什翼犍等皇子被杀,崔浩被诛,崔逞获谴,封懿被废,这一切都传递出一个可怕的信息,谁想向高级文明的汉族学习,就得付出生命的代价。在这样的政治文化氛围中,拓跋氏固守自己的民族传统,经济萧条,文化发展滞后。像“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企喻歌辞》第一首)这样朴拙、幼稚、口语化的鲜卑族民歌就是当时文人创作的样板,汉族士人为了保全性命也得向鲜卑族质朴的诗风靠拢。高允能够写出“邑中有好女,姓秦字罗敷。巧笑美回盼,鬓发复凝肤。脚著花文履,耳穿明月珠。头作堕马髻,倒枕象牙梳。姌姌善趋步,襜襜曳长裾。王侯为之顾,驷马自踟蹰”(《罗敷行》)这样接近南朝诗风的作品,但是大量的是像《答宗钦诗》、《咏贞妇彭城刘氏诗》那样稚嫩的四言诗。孝文帝全面推行汉化以后,学习南朝民歌成为时尚,但拓跋鲜卑族这种质朴的诗风并没有被抛弃。元勰《问松林》诗云:“问松林,松林经几冬?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据说此诗是奉孝文帝之命而作,而且还得到孝文帝的赞誉。这首诗有南朝诗歌的成风不假,但其风格刚健,很明显是鲜卑族质朴诗风的遗存。此外如“权去生道促,忧来死路长。怀恨出国门,含悲入鬼乡。隧门一时闭,幽庭岂复光。思鸟吟青松,哀风吹白杨。昔来闻死苦。何言身自当”(元子攸《临终诗》)、“朱门久可患,紫极非情玩。颠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换。时运正如此,惟有修真观”(元恭《诗》)等诗质朴苍凉,都是鲜卑族诗风的延续。生活在这样氛围中的温子升,当然会向鲜卑族学习,这是其一;其二,温子升多年为官,职责多为掌诏诰,如果不按照鲜卑族的文风去写作,很难得到皇帝的赏识;其三,从上举诗例中可以看出,孝庄帝元子攸、节闵帝元恭都喜好质朴的诗风,这势必也会影响到温子升。
南北对峙之时,南朝作家北漂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些南籍作家带去了南朝华丽的诗风,给北朝诗坛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汉化的全面实施,学习南朝诗歌成为风尚。北朝人不仅要学习南朝诗风,而且还想超过南朝人。《魏书·祖莹列传》云:“尚书令王肃曾于省中咏《悲平城诗》,云……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肃更咏,乃失语云:‘王公吟咏情性,声律殊佳,可更为诵《悲彭城诗》。’肃因戏勰云:‘何意《悲平城》为《悲彭城》也?’勰有惭色。莹在座,即云:‘所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见耳。’肃云:‘可为诵之。’莹应声云:……肃甚嗟赏之。勰亦大悦,退谓莹曰:‘即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几为吴子所屈。’”[51]祖莹以诗才胜过了初入北魏的南朝人王肃,得到元勰的赞赏。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南朝诗风传播得很快,温子升自然而然也就接受了南朝诗风。
温诗清婉的风格源于南朝清丽的诗风。“清”本是中国古代诗学的范畴,自先秦就有之。到了南朝,文人似乎更喜欢追求这种审美规范。刘义庆《世说新语》中《赏誉》《品藻》两篇就有31个“清”,构成了“清婉”、“清远”、“清通”等词;钟嵘《诗品》中有17个“清”,构成了“清润”、“清怨”、“清刚”等词。“清”的审美趣味与南朝士人追求的“丽”结合,便形成了“清丽”。刘勰在《文心雕龙·定势》中云:“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竹紫,随势各配。……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52]刘勰首次对诗赋提出“清丽”的要求,由这里的“宫商竹紫,随势各配”、“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来看,刘勰对“清丽”既有声律的要求,又有辞彩的要求。齐代永明年间,重视诗歌声律的永明体新诗融入了沈约的“三易说”(易见事、易识字、易读诵)、谢朓的“圆美流转”理论,“清丽”便有了婉转之意。温子升学习南朝清丽的诗风,摒弃了华丽的辞藻,吸取了婉转的因素,便形成了自己清婉的诗风。
本文为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批准号:12BZW02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76页。
[2]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76页。
[3]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75页。
[4]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5页。
[5]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77页。
[6]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75页。
[7]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51页。
[8]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766页。
[9]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766页。
[10]释道宣:《广弘明集》,《四部丛刊》本,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第11页。
[11]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39页。
[12]张雅静:《北魏豫北佛教造像碑的样式特征与风格演变》,《华侨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2006年第3期。
[13]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767页。
[14]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767页。
[15]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767页。
[16]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77页。
[17]王通:《文中子中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页。
[18]叶适:《习见记言序目》,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08页。
[19]殷孟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280页。
[20]于敏中:《御制诗集(三集)》《文渊阁四库全书》(11),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44页。
[21]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76页。
[22]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76页。
[23]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61页。
[24]李百药:《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4页。
[25]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77页。
[26]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74页。
[27]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92页。
[28]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04页。
[29]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76页。
[30]李百药:《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515页。
[31]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76页。
[32]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03页。
[33]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54页。
[34]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763页。
[35]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76—1877页。
[36]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82—2783页。
[37]周建江:《北朝文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99—200页。
[38]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第95页。
[39]葛晓音:《八代诗史》,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0页。
[40]曹道衡:《南北朝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355—356页。
[41]钱志熙:《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7页。
[42]王夫之:《古诗评选》,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第29页。
[43]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82页。
[44]魏征:《隋书》卷七十六《文学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730页。
[45]杨慎:《升菴诗话》,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49页。
[46]赵翼:《陔余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456页。
[47]沈德潜:《古诗源》,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39页。
[48]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29页。
[49]段成式:《酉阳杂俎》,《唐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47页。
[50]魏徵:《隋书》卷七十六《文学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730页。
[51]魏徵:《隋书》卷七十六《文学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799页。
[5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5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