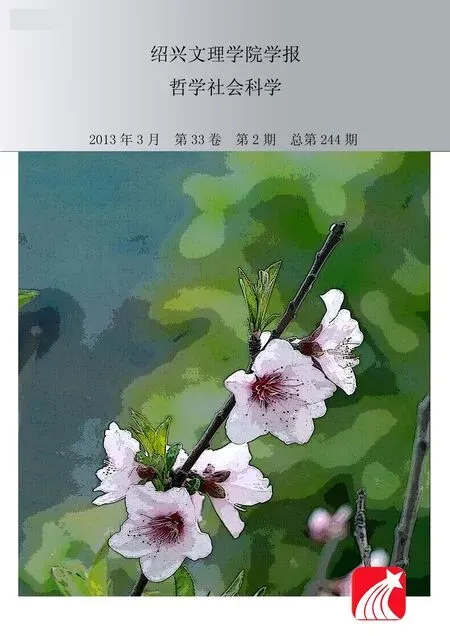魏晋六朝用典论及沈约“三易”说的批评史意义
2013-04-11李翰
李 翰
(上海大学 中文系,上海200444)
经史典籍既是文人的知识资源,也是其情感之寄托,故文人制作隶事用典,自属难免。魏晋六朝,智识主义风气弥漫,文学创作“竞须新事……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更是“浸以成俗”(《诗品序》)。关于用典之讨论、争议,亦随之蜂起。其中,沈约“三易”说所谓“易见事”,非简单肯定或否定用典,而是提出用典从易的见解,体现了沈约调和折中的文论思想。且沈约又是著名诗人,有创作经验、教训可供比考,故具有重要的批评史意义。①本文拟通过考察魏晋六朝用典论,从而更为直观地抉发沈约用典观及其实践的重要价值。
一
南朝隶事成风,时人多以博识多闻相炫,在史传中有很多记载。如《南齐书·陆澄传》:“俭自以博闻多识,读书过澄。澄曰:‘仆年少来无事,唯以读书为业。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务,虽复一览便谙,然见卷轴未必多仆。’俭集学士何宪等盛自商略,澄待俭语毕,然后谈所遗漏数百千条,皆俭所未睹,俭乃叹服。俭在尚书省,出巾箱机案杂服饰,令学士隶事,事多者与之,人人各得一两物,澄后来,更出诸人所不知事复各数条,并夺物将去。”王俭以博闻多识自负,但却折给了陆澄。到了梁代,隶事之风只增不减,《南史·刘峻传》载:“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时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帝乃悦,加其赏赉。会策锦被事,咸言已罄,帝试呼问峻,峻时贫悴冗散,忽请纸笔,疏十余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自是恶之,不复引见。及峻撰《类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之,竟不见用。……”又是一则炫博佚事,刘峻不加收敛,风头太盛,在隶事上盖过了皇帝,而梁武帝气量有限,遭到贬斥自不可避免。不过,这也更加说明了时人对博闻多识的重视。《南史·王僧儒传》:“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时重其富博”,《陈书·姚察传》:“每有制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见,咸重其博”,不但用典,而且要“人所未见”。炫博之风,流衍于文体,一般文人对于隶事用典,视为当然乃至必然。
文人制作用典,起因大要不过三端,一是思想上之宗经;二是写作取源之需要,三是写作艺术之要求。宗经思想古已有之,扬雄《法言·吾子》云:“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以《五经》为济道之舟航;《寡见》篇认为《五经》代表了各类文体的最高成就,“惟《五经》为辩。说天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师范《五经》之意溢乎文外。王充《论衡·佚文》则径云:“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已明言当以《五经》为写作楷式。其后刘勰不过是继承他们的观点,括而论之。如《文心雕龙·原道》云:“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序志》更云后世文章,皆经典之枝条,并立《征圣》《宗经》专章,谓“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并标示“文能宗经,体有六义”,集宗经论之大成。综合宗经论主要着眼点来看,一在于道,要求“依经立义”;一在于文,要求“修辞宗经”。虽然这些并不必然联系着用典,且诗文用典也非仅指儒家经典,但以宗经为指导原则,极易培养依傍经史典籍的写作思维,形成引经据典的写作风尚。
一般皆以为隶事用典之风起自南朝,“颜延、谢庄,尤为繁密”(《诗品序》),被钟嵘点名批评。张戒即谓“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岁寒堂诗话》卷上),语本钟嵘,却有所曲解。按钟嵘谓颜延之、谢庄“尤为繁密”,着一“尤”字,已阐明其非始作俑者。②实则南朝隶事之风,当导源于依傍经典的写作思维,早在两汉即已滥觞。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云:“贾谊《鵩赋》,始用《鶡冠》之说,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书……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记传……”也许,这还只是一般引用。但我们看张衡《归田赋》:“徒临川以羡鱼”“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追渔父以同嬉”,等等。就是很正宗的用典了。在张衡的写作意识里,“感老氏之遗戒”“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前辈典籍皆是模尊礼拜之对象,这使写作客体即便是纯美之大自然,作家仍不免要假灵于先哲前修。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曾谓“汉代之文几无一篇不采录成语者,观二《汉书》可见”[1],根源或即与经学时代所孕育的依经傍典的写作思维有关。这一思维,汉魏以下更为普遍,乃至形成写作之风气。《南齐书·文学传论》就将南齐时代“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的文学风气联系到前代的“傅咸五经,应璩指事”。傅咸是西晋时期著名的儒家学者,其《七经诗》以儒家经典为题材,集其中成句为诗,体现了强烈的宗经思想,并开后代集句诗之风。应璩,汉魏间人,应玚胞弟。钟嵘在《诗品》中说他“善为古语,指事殷勤”,如其《杂诗》(细微可不慎),纯用古事,意在讽谏;《文选》所录《百一诗》,也引用不少典故,历来多认为是为讽劝时任大将军的曹爽所作。这两位都有着浓厚的儒家思想,且秉持诗人之义,写作的功利色彩强烈。孙宝先生在《傅咸家风与魏晋文风流变》一文中说:“集句既是一种文学体式,又是一种创作心态,晋代集句文体的出现与崇尚儒家经典、拘守成句的复古思潮密切相关,它以作者娴熟掌握经典出处并充分融会贯通为前提,体现的是以文学形式展现儒学素养的雅癖。”[2]虽然只提到傅咸,其实像应璩那样的“指事”,体现的也是同一创作心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敏锐地将南朝用典之风与傅、应二人联系起来比较,说明他注意到南朝用典之滥觞,与汉魏以来在宗经观念下形成的写作思维有密切关系。南朝诗人不一定都仅用儒典,也不一定都有意存讽劝的诗人之义,但这一“以文学形式展现儒学素养的雅癖”算是养成了,只不过不限于“儒学”而已。
当依傍经典从思想上“依经立义”到文学上的“修辞使事”,经典即成为一种写作资源。陆机《文赋》云“咏世德之骏烈,颂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即将前辈文章以及记载先人功德的典籍当成写作的重要资源,与大自然之节序流易同观,谓其皆能令作者感慨而援笔。③而实际上,西晋以来模拟风气浓厚,并不仅仅将前代典籍看成创作冲动之诱因,而是径直拿来使用,或以之为写作范本,或以之为抒情说理之素材。此即陆机《文赋》所谓“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其所拟之乐府、《古诗十九首》,及前述傅咸《七经诗》、应璩《杂诗》《百一诗》等,将前代典籍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均此类也。至“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诗品序》),不过延其脉络之极端情形。对这一类作者而言,用典与写作须臾不离,是写作取源之所自。
用典作为写作艺术上之要求,是其修辞学之意义。一般认为《文心雕龙·事类》篇讨论的是用典问题,但该篇所论“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的事类,多是指论事说理之引言论证,故屡次强调要恰当:“事得其要,虽小成绩,譬寸辖制轮,尺枢运关也。或微言美事,置于闲散,是缀金翠于足胫,靓粉黛于胸臆也。”这与我们所理解的修辞上的用典可能还是有一定区别。用典的修辞意义在于通过典故所蕴涵的大量历史信息,取得言约义丰的表达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心雕龙·事类》在谈到用事要恰当的同时,还提出要做到“不啻自其口出”,即能与文章融为一体,所谈则属于用典的修辞意义。不过,就一般情形而言,六朝时文大多尚未达到如此高度,于是就出现了“殆同书抄”的弊端,而这恰好授反对者以口实。
在诸多批评家的眼中,“句无虚语,语无虚字”的隶事之风并不皆具正面意义,其反对之直接原因,便是当时因用典而造成的种种诗文病累,然具体情形又各有不同。钟嵘《诗品序》云:“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晚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将文学色彩较强的诗文与一般应用文区别对待,而其之所以不主张诗文用典,乃基于对诗文之本质在于“吟咏情性”的认识。在钟嵘的意识里,“吟咏情性”与经国道德两途分殊,正与征圣宗经相对立。从钟嵘的论述还能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即南朝以来,那些“殆同书抄”的诗文,并不含有对经典的敬畏,不过炫博逞才而已。因此,那些站在尊经的立场上,即便并不反对用典,面对此类仅因炫博逞才而用典的情形,同样也会提出强烈的批评。比如裴子野《雕虫论》:“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曹,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及风云。”裴氏并不是泛泛批评用典,而是批评所用非儒家经典,即所谓“淫文破典”;其次,时人使用这些典故,只是为了“吟咏情性”,而非关乎礼义。反对当时逞才炫博的用典,裴、钟态度基本一致,只是裴认为用典妨碍礼乐道义,而钟嵘则认为妨碍吟咏情性;裴反对的是淫文破典,钟则笼统反对诗文用典。
由上述可以发现,在很多情形下,用典论总是与宗经与否联系在一起的。一般说来,宗经派不会简单否定用典,而是强调用典的雅正与恰当;且其倡扬之用典,所指大多还不是诗文等文学作品。如前述刘勰《文心雕龙·隶事》所谓“缘古证今”“据事类义”,大多皆为论说类理论文章。其实就这一点而言,钟嵘与刘勰并没有多大区别,钟氏亦云“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因此,在吟咏情性的诗文之中,究竟是否应该用典,用典与吟咏情性知否构成矛盾?才是南朝用典论争执之焦点。
从这个角度来说,批评家确实很少正面对诗文用典做出积极评论的。裴子野、钟嵘等从不同的立场批评时人隶事之风自不必论,即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以专章论隶事,但涉及的大多并非诗文。而对于吟咏情性之诗文,要么反对用典,要么强调须用儒典,使其义归于正,透示着浓厚的尊经意识。作家以自己的实践,表达了对诗文用典的肯定,而在批评家那里,却以否定者居多。批评家与作家的龃龉,使得南朝用典论破多而立少,缺乏建设意义。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虽对用典之方法、技术提出一定的建设性意见,但一是其并不以诗文为重点,二因刘勰本人并不创作,故所论还是未免隔阂。在这一背景下,兼有作家与批评家双重身份的沈约,其与创作实践相联系的用典思想,就尤其值得重视了。
二
沈约关于用典的谈论并不多,较值得注意的有三处,一见于《宋书·谢灵运传论》:“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臆,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二见于《颜氏家训·文章篇》,颜之推训示子侄云:“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诵读,三也。’”以及同书所引邢邵语“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三见于《宋书·周朗传论》:“慕古饰情,义非侧席,文士因斯,各存炫藻。……文词之为累,一至乎此。”
《谢灵运传论》的“直举胸臆,非傍诗史”,其中“直举胸臆”同于第二例中邢邵“若胸臆语”,不同的是,一者是因“非傍诗史”而“直举胸臆”,一者则是因“用事不使人觉”而“若胸臆语”。沈约认为曹植、王粲等人“直举胸臆,非傍诗史”,却能够做到“讽高历赏”,是由于“音律调韵,取高前式”。显然,对沈约来说,“非傍诗史”能使诗文取得较高艺术成就,一般情况下是不可思议的,而曹植等人的某些作品能够做到,是以音律之美进行了弥补。这固然从正面说明了音律的重要性,却也从侧面说明了在通常情况下,用典对于诗文实乃不可或缺。
那么,该如何用典呢?《颜氏家训》所引两段话很有意思,一曰“易见事”,一曰“用事不使人觉”,“用事不觉”,则所用之事当是“不易见”的了,如何理解?二者有所龃龉,还是同一种意思的不同表达?第三例则颇同前述钟嵘、裴子野之论,批评时人炫耀文藻,致使文词为累。综合三处来看,“若胸臆语”最为关键,当是沈约眼中诗文审美之核心特质。“非傍诗史”能做到“直举胸臆”固然不错,而用事如能使人不觉,也同样可以达到“若出胸臆”的审美效果。要达到这一效果,就要做到既“易见事”,又“不使人觉”。二者一指典故之选择,当以熟典、常典为主;一指融化无迹的典故运用艺术。后者以前者为条件,若所用之事过偏,一则导致文意艰涩,二则喧宾夺主;只有恰切的常典,才能平易地融入文章,经过妙手剪裁,达到不使人觉的效果,最终使文章“若胸臆语”。故“易见事”与“用事不觉”非但不矛盾,而且关系紧密,互为依持,实谓用事之手法、典故之选择,虽出机杼,而最终当融化无迹,泯于自然。
南朝诗文用典遭人诟病之处,即在于因炫才逞博而使事忘义,故有“淫文破典”之弊;而有人因这一弊端,便认为抒情性诗文不贵于用事,从而反对用典,又未免矫枉过正。从沈约对用典的态度中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是要求能在直寻与隶事、性情与才学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点。这样,用典对抒情就会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个平衡点简单地说就是人工与自然的统一,虽出机杼,而泯于自然。
这实际上是沈约一以贯之的文学思想。无论声律还是用典,为天地间自然之物,虽有偶然得之之妙手,而大多皆出于匠心,然待其见于诗文,却又要泯灭匠作痕迹。《答徐勉书》云:“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律顿舛”,可见在沈约看来,声律实根源于性情,是情感灵性的自然表露。《宋书·谢灵运传论》谓以往一些“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闇与理合,非由思至”,想来当是这些诗人天机灵动,于无意之中得天成之妙声。但对于一般人来说,更多的可能还是要经过精心的揣摩。《报王筠书》谓王筠诗“声和被纸,光影盈字;夔牙接响,顾有余惭,孔翠群翔,岂不多愧”,而王氏“一至乎此”的艺术成就,乃是“思力所该”,这就是“由思而至”,终出以“天成”的代表。其主张诗文用典,却又强调“不使人觉”,皆出以同一文论思想。
除上引文字外,这一思想在沈约文章其他地方还有过多次表述。如《谢齐竟陵王示永明乐歌启》中,他称颂萧子良诗歌“凤彩鸾章,霞鲜锦缛。觌宝河宗,未必比丽;观乐帝所,远有惭德”,这是指其人工雕饰之靡丽;而另一方面,又云萧诗如“日月在天”“徘徊光景不能自息”,形影相随,则是在强调其根于本性的自然美的表露。《与范述曾论齐竟陵王赋书》云:“夫渺泛沧流,则不识涯涘;杂陈钟石,则莫辨宫商。虽复吟诵环回,编离字灭,终无所辨。”这是在赞美萧子良作赋,宫商音律极美,却又令人感觉不到雕琢之痕迹。又如《报博士刘香书》,谓刘氏所作二赞,“辞采研富,事义毕举。句韵之间,光影相照。便觉此地,自然十倍。故知丽辞之益,其事宏多。”事义与宫商的结合,就不仅仅是合于自然,而是可以巧夺天工,胜于自然了。
对于沈约来说,声律与用典都是提高诗文艺术性的重要手段,二者具一,便能使诗文增色。在《谢灵运传论》中,他认为曹植等人没有用典却能取得较高艺术成就,是以声律作了弥补。如果两者皆备,当然更是锦上添花了。不过,无论声律还是用典,最后达到的效果应该是“不觉”“不辨”“自然”等等,而不能留下人工的痕迹。
三
沈约关于用典主要思想如此,但其本身的创作,却经过了一个摸索乃至反复的过程。胡应麟曾谓沈约诗歌思想理论,如声律说等,允谓作者之圣,而其“自运乃无一篇”(《诗薮·外编》卷二)。话虽偏激,但却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沈约知行不一的情形。其前期作品对于典故的处理,不少并未能摆脱当时炫博逞才的艰涩之风。如《文选》收录的其早期作品《钟山诗应西阳王教》,其中很多典故就需要专门笺解,如“灵山纪地德”的出典,“终南表秦观”的“秦观”之由来;再如以“翠凤翔淮海”喻宋之兴,略“翠凤旗”之“旗”,以及最后一节的“五药”“三芝”等略语,因顾及音韵、句读而割略语典,导致诗意晦涩。后期作品,艺术水准有很大提高,出现了不少名篇,用典臻于浑然无迹,但存在不足的也不少,瑕瑜互见。
沈约晚期诗歌创作,以东阳太守任上成就最为显著。齐郁林王隆昌元年(494),沈约受齐王室权争牵连,外放东阳太守。政治上的失意,却使其诗文达到艺术上的高峰,创作出了《早发定山》《游新安江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同好》《八咏诗》等堪为代表性的作品。就用典而言,此期诗作驱遣皆为熟典,且用典多从表达诗意实际出发,而非矜才恃博,故读之平易亲切,不少皆能达到其所提出的“易见事”“不使人觉”的艺术要求。比如《八咏诗》第一、二首之班姬、飞燕、明君、山林苑、淇川、高唐诸典,第三首化用屈辞《离骚》意象、词汇,等等,都是根据文意及情感抒发需要,选择常用典故。即便像第一首中的“三爵台”“九华殿”可能稍僻,但都能知道是指为豪华气派之所,并不妨碍读者理解诗文。不过,《八咏诗》不足之处也很明显,驱使典故过多,且以名词形式排列铺陈,又稍显堆砌板滞。比较起来,其赴任途中所作的《早发定山》《游新安江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同好》,才算是既用典平易,又妥帖圆融。先看《早发定山》:
夙龄爱远壑,晚莅见奇山。标峰彩虹外,置岭白云间。倾壁忽斜竖,绝顶复孤圆。归海流漫漫,出浦水溅溅。野棠开未落,山樱发欲然。忘归属兰杜,怀禄寄芳荃。眷言采三秀,徘徊望九仙。(《早发定山》)
从题材上看,这是一首典型的山水诗,写景层次清晰,色彩丰富,语言清浅如话,描摹生动。而实际上,不少词句皆有来历。如“标峰彩虹外,置岭白云间”,写山之高峻,实化自《穆天子传》“白云在天,丘陵自出”,但自然妥帖,浑然无迹。自“忘归属兰杜”以下,触景生情,抒写拳拳忠爱之情怀。“兰杜”“芳荃”“三秀”等语汇,皆出自屈辞。融楚辞意象入诗,屡见于沈约此期诗歌,前述《八咏诗》中就有不少,而下面这首《游新安江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同好》,则更为突出:
眷言访舟客,兹川信可珍。洞澈随清浅,皎镜无冬春。千仞写乔树,百丈见游鳞。沧浪有时浊,清济涸无津。岂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纷吾隔嚣滓,宁假濯衣巾。愿以潺湲水,沾君缨上尘。
诗前半写景,后半则化用《楚辞·渔父》之典故,抒发其优游自得、无往不适的情怀。由于诗中所写清水游鳞之水景,与《楚辞》中的沧浪之咏景象类似,即便将沧浪之水看成是本诗中所写的新安江水,也无不可;再加上情绪、心境的契合无间,故本处所用典故,对于阅读本诗并不构成丝毫障碍。明了者知其为用典,不明了者无妨视其为写实。典故融化于诗句之中,浑然一体,可谓是“用事不觉”,而对于诗意的理解来说,其用事之平易,又可谓是“易见事”矣。
用典或声律,有一项运用巧妙,便能为诗文增色,前述《谢灵运传论》所云曹植、王粲等“非傍诗史”,盖能以音律取胜,反之,当声律有瑕疵,诗史典故运用巧妙,也不失为佳作。如其最为人称道的《别范安城》,从形式上看,当为新体诗,然按永明声律论,不少地方却未能避免声病: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
如“日”“暮”同声,犯鹤膝,“离”“时”同声,犯小韵,等等,虽然沈约自诩为妙解声律第一人,而轮到自己创作,却出现胡应麟所批评的拙于“自运”的现象。然本诗仍不失为经典,乃至堪称沈约诗的代表作,在其情感深挚、意味隽永之外,便因本诗之用典,实堪称模范。“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据《文选》李善注,乃用《韩非子》所述故事,战国时张敏和高惠是好友,后来两人分开,张敏对高惠极为思念,以致做梦去寻找高惠,但行至中途却迷失了道路。诗人用这一典故,抒发对友人浓重的情谊,与整个诗境融化无迹,令人浑然不觉其用典。确如后人所评:“一片真气浮动,无一毫境事碎琐参错”“字字幽,字字厚,字字远,字字真。”(钟惺、谭元春《古诗归》)本诗用典之浑然无迹,差不多能代表南朝诗文用典艺术的最高水平。
在这些诗歌中,典故能够化入诗意,不再是外在于诗歌的用事,而是与诗歌成为一浑融的整体,从而达到“用事不觉”的效果。从上述几首诗来看,沈约能够做到这一点,一是用典灵活,能够创造性使用典故,通过联想发挥,借助典故拓展意境、情感。比如《早发定山》中的“标峰彩虹外,置岭白云间”,李善引《穆天子传》“白云在天,丘陵自出”为注,两者在意象、比喻方式上确实呈现相似性,但这又不同于普通的用典。沈诗在前人句意的启发下,将喻象作了进一步的扩展发挥,以高出彩虹,矗立云间来形容山之高峻,比《穆天子传》中比喻更显形象、生动。这一手法,类似于江西诗派的点化之论,窃古人意而再铸新词。二是重视典故内在的思想,与之作深层的精神交流。如上引几首以屈辞词句、意境入诗,在作者而言,是精神意趣相通,情同此心,心同此理。在这里,典故之具体事实较虚泛,而情绪感慨与本诗契合无间。上述两点,一是在写作技术层面,如何灵活处理、丰富典故的艺术表现;一是在思想内容层面,构建与古人莫逆于心的精神空间。无论哪一点,都消解了典故本身的独立性。这种消解,可以如盐入水,如《别范安城》之属,即所谓“用事不觉”;也可以如影随形,如《游新安江》之属,既“易见事”,又与本诗血肉相连,融为一体。
黄春贵先生说:“大约用典之佳者,贵能推陈出新,无异于出自一己之创作,譬如水中煮盐,运化无迹,不使人觉。……故原本古事成辞,用典时却须重加铸造,别出心裁。……夫善纫者无隙缝,工绘者无渍痕,用典若斯,紧著题意,融化而不涩,用事而不为事使,则面目精神,方能一新。”[3]沈约虽未就用典作进一步发挥,然在其后期诗作中出现的一些作品,却在某种程度上将用典艺术推向这一高度。
注释:
①“三易说”并不见于沈约文集,而是出自《颜氏家训·文章篇》,乃颜之推引沈约语训示子侄:“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诵读,三也。’”该说虽非全关用典,但为沈约文学思想之核要,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对于用典的态度。
②曹旭《诗品集注》校异“尤为繁密”条下:“‘尤’,退翁、《对雨楼》《择是居》诸本作‘犹’。张锡瑜《诗平》:尤,疑当作‘先’。”见该书第1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按,即便作“犹”,亦无“先”、“始”之训;张锡瑜疑当作“先”,疑而无据,或即受张戒误导欤?
③注家多谓“咏世德”“颂先人”乃指写作内容为颂扬先人功德,恐受庾信《哀江南赋序》“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之影响。士衡固有《祖德赋》《述先赋》等歌咏先人,但与此处“咏世德”颂先人”并不相混。视本节末句“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可知前述皆引发创作冲动之基础,故此处“咏世德”“颂先人”云云,实指因咏颂记载先辈功德之文字而深受感染,与陆氏作赋自陈世德绝不相类。
参考文献:
[1]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88.
[2]孙宝.傅咸家风与魏晋文风流变[J].兰州学刊,2008,1:199-203.
[3]詹瑛.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