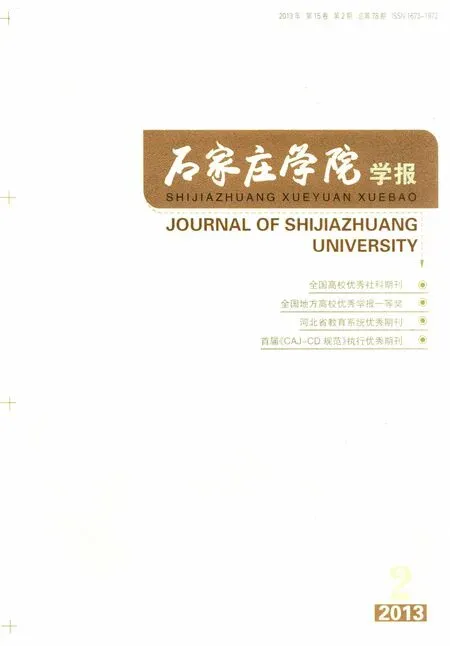个体灵魂的自我拯救——试论“过客”行走的终极意义
2013-04-11孙海军
孙海军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一
《野草·过客》引起笔者注意的并非其所谓“反抗绝望”的主题,而是过客的一种基于本能的行动。“走”,“从我还记得的时候起,我在就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我单记得走了这许多路,现在来到这里了。我接着就要走向那边去,(西指,)前面!”[1]195“走”对于鲁迅而言,就是生命存活的表现,更是生命存在的价值,所以他不能停下来。与其说“走”表现出一种“反抗绝望”的主题,不如说他借助“走”这一生命样式,更本真、更深层地在与自我展开对话,审视并反观自己,也就是说,这里过客所要解决的并非自己与外界(“坟”)的关系,而是自身与自身的关系。在远离人群的乡间小路独自走下去,特别是在意识到前面有一个叫做“坟”的终点的情况下,最为本己的内心世界才会对自身敞开,即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说的“向死而生”,过客正是在此意义上意识到了自己存在这样一个看似毋庸置疑的本真事实。而这一认识的获取,往往发生在对自我能力、身份认同乃至存在价值发生动摇、犹疑的情况下,所以过客的“走”这一最为原始的生命样式在某种程度上是鲁迅对于自身存在价值、自己所投身的启蒙事业本身的质疑的一种呈现形式,深刻彰显了他彼时极为严峻的对于自身的信任危机。
这一危机在十天后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中得到了进一步证实,他一方面谦虚地说自己的确没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另一方面又对许广平说,自己不会像墨翟或是阮籍那样“恸哭而返”,而是“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上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以走的路再走”,“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中姑且走走”[2]15-16。可见,“走”这一生命样式对于鲁迅而言绝不仅仅意味着一个简单的生理动作,更是他在意识到危机的情形下迎难而上、主动出击的一次生命行动。只有冲破了笼罩在“歧路”面前的魅影,只有迎着“穷途”知难而上,人生的旅途才不至于戛然而止。这在某种程度上与鲁迅一贯主张的“韧”的战斗精神有着共通之处。但更为重要的还是在走下去的过程中,随着自我心态的调整与外部环境的变更,生发出无限多样的可能。正是在此意义上,说裴多菲(Sandor Petofi)的那句诗孕育了“过客”精神,或者说“过客”精神正是在那句诗的鼓舞下实践起来的一种行动精神。
过客的本质在于“走”,在于行动。而当时鲁迅依然沉浸在1923年以来的平静中,“我的心分外的寂寞,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没有颜色和声音”[1]181。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只能一方面“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1]181,一方面选择一条姑且似乎可以走的路走下去。笔者觉得这是鲁迅当时最为真实的心态,他正走在人生的“歧路”上,除了确信前面有一处叫做的“坟”的地方外,似乎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就在写作《过客》的前几天,鲁迅几乎重复了《狂人日记》的故事,虽然李大钊读后感慨地说:“鲁迅先生发表《长明灯》,这是他继续《狂人日记》的精神,已经挺身出来了。”[3]178但是,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第一声“呐喊”的《狂人日记》而言,《长明灯》只是更加真实地暴露出鲁迅当时的自我危机这一事实。一方面是他感慨于世界的沉寂,害怕自己在这样平静而安详的环境中沉沦下去,于是拿起了笔;另一方面,或许在他而言,的确有李大钊所说的那种冲破寂寞继续战斗的意思。然而,历史的车轮已经驶过了五四运动的高潮期,他不仅丧失了《狂人日记》当年爆发式的力度,更仿佛一个遗老似的在诉说着当年的风光,并试图借此来击退这死一般沉寂的世界。可以想像,这种心理落差对鲁迅而言是多么巨大。尽管他一再声称自己对于当年的新文化运动并不怎样热心,但在经历了更多的挫折之后,他想起的还是《新青年》所开展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与青年的通信中,他禁不住说:“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句话,虽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4]23对鲁迅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份痛苦的自白,何况又身处那样一个军阀混战、政府更替极为频繁的年代,“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5]468。然而,他终于没有因此而真的颓唐下去,又重新提起了笔,这力量的来源就是“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5]468。
二
当老翁问过客,你这样走下去,到底是要走向哪里,过客回答说不知道,他只知道前面有个声音在呼唤他,他歇不下。过客的这一举动,初看上去有些盲目,因为作为有着独立意志的个体,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连目的地都没搞清楚就这么盲目地走下去的,除非他是一个“被了诅咒”的人,就像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提到的那个叫做Ahasvar的人一样。亦或者如加缪(AlbertCamus)笔下的西绪福斯,整天只知道从山脚往山上搬运石头,而石头又会因为自身的重量自行滑落,他只好下到山脚再次将它们搬上山去,因此他也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他们三个都在不停歇地走着,运动着,但三者之间又有着截然不同的哲学意味。Ahasvar之所以停不下来是因为他触犯了圣子,不让其在屋檐下休息,所以耶稣才诅咒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时候。这本是一个宗教传说,可鲁迅却接着发挥道:“他何以不安息呢?虽说背着诅咒,可是大约总该是觉得走比安息还适意,所以始终狂走的罢。”[6]170这难免就有些借题发挥了,但或许就是在这里孕育了后来的“过客”精神。但是,Ahasvar的“走”是为了赎罪,是一种基督教原罪宿命论的思想,宗教色彩更为强烈。而西绪福斯不停地搬运石头,似乎也是一种命定的必然,而且他的这一举动也是一种惩罚,只不过是披着一件神话的外衣。但是,加缪却从中感受到了现代式的荒谬,而这份荒谬的由来则是因为西绪福斯看似不停歇的运动实际上只是一种毫无差异的重复,而个体的精力、生命也就在这些重复运动中消耗掉了。最为关键的是,这种自我消耗、自我牺牲是无谓的,因为它根本就从未触及到世界的本源意义,于是,西绪福斯相比于Ahasvar更多出了一份世俗的悲剧意味。
“过客”的形象相对于前两者而言,宗教和神话色彩都要淡些,他只是活在人间,行走在自我生命征途上的一个没有名姓的旅者,更像一则寓言。值得追问的是,这则寓言的寓意到底是什么,鲁迅借助这个不断行走的形象想要表达怎样一层意思,说得更加直白一点,过客坚持走下去到底是要走向哪里,会是人生的终点“坟”吗?——这是确然的,我们每个人都逃不过这一终局。鲁迅因为从青年时代起就目睹、经历过多次死亡,诸如政治斗争中屡见不鲜的暗杀,借着革命的名义正大光明的枪杀,以及军阀政客架起机枪屠杀请愿的青年学生,还有,也许更为重要的还是范爱农之类抑郁者的“自沉”,所以他对于死亡的确有着较之常人更为直接、更为深切的体悟。也正因此,他的作品中常常写到死,以至于有论者说“鲁迅是一个善于描写死的丑恶的能手”[7]373。
死亡的确是鲁迅一向倾心的主题,但《过客》所要表达的绝不应该是这样一个主题。这一点鲁迅自己说得很明白:“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6]300这段话很明确地说明了《过客》所要表达的也与鲁迅执着于现在的追求相关。换句话说,他借助过客这一形象所思考的并非那个无须我们着急的终点,而是怎样去走这一段路,是现世的幸福。所以,张梦阳才称“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是鲁迅思想的一个原点[8]。由此我们来反观《过客》的寓意,也就可以说,鲁迅所着力的并非“过客”明知前面是“坟”而坚持向之走去这层所谓的“反抗绝望”的意思;与其说他看中的是这层意思,不如说他更加看重“走”这一行动本身。
那么,“走”这个动词的指向到底是什么呢?笔者觉得不应该是坟,也不应该是现实中诸多困厄的拟人化,而就是他自身。也就是说,鲁迅创作《过客》的真正初衷是要更真实、更直接地走近自己、逼视自己,即汪晖所说的“自审”。“在鲁迅对陀氏的阐释中,我们发现了一种把自己当作道德法则进行审判的‘罪’的自觉。这种以‘自审’为其特征的精神现象贯穿于鲁迅的一生,又是其人格哲学的主要内容。”[9]107这种“自审”意识在“彷徨”“野草”时期表现得尤为充分。具体到《过客》而言,过客义无反顾的“走”固然流露出鲁迅自我身份和信仰的危机,但更为重要的还在于,鲁迅试图借助“自审”而重建新的价值认同和精神追求。像鲁迅许多小说一样,《过客》中出现的三个人物,也可以理解成鲁迅精神上的三个极点,其中形象最不明确、寓意也似乎浅淡些的小女孩可以看做是鲁迅对自己短暂童年的“抵抗式”记忆,这一段是他所不乐意回味的,所以小女孩的形象才这般模糊,仿佛是要表现出她的天真、纯粹,但整篇文章的艰涩、深沉又成功“消解”了这一印象。老翁的形象也有些模糊,但相对于小女孩的不明确,还是多了一份过来人的沧桑,比如他说年轻时也曾听到过一个声音召唤他,但他没有理睬,渐渐地也就听不到了。有人据此认为鲁迅这里借着老翁的形象所讥刺的是那些从历次革命运动的洪流中不断退缩下来的人,但在笔者看来,老翁形象更多的却是鲁迅对于自己的一种警醒。在《希望》中,鲁迅第一次发现自己老了,“我大概老了。我的头发已经苍白,不是很明白的事么?我的手颤抖着,不是很明白的事么?”老翁的形象可以说是这个意思的延续,而紧接着这句话,鲁迅感慨地写到,“这以前,我的心也曾经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1]181。可以说,从《希望》开始,鲁迅已经在有意识地审视并反省自己了,他特别害怕自己在这样寂寞而平安的环境中枯萎下去,于是一再呼唤着“真的暗夜”的到来。《过客》中的老翁形象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换句话说,直到写作《过客》,鲁迅依然没能解决自己内心的犹疑、不安和焦虑,他依然有在寂寞而平安的假象中沉静下去的危险。然而,这是他所不希望看到的,他更为倾心的还是“过客”那样的行动者,所以“过客”的形象才会那样刚毅而决绝。鲁迅当时所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韧性的、战斗的形象,可以说,鲁迅通过创作《过客》进一步认清了自己,初步建立起了自我身份和信仰的新认同。
三
《过客》是《野草》中鲁迅第一次将自己的内心世界挖得很深的作品,这一方面说明鲁迅在与自己的对话中逐渐把握到了竹内好 (Takeuchi Yoshimi)称之为“自觉”的某种东西,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鲁迅此时内心世界的低沉、阴暗。这就如同一个比喻说的那样,树长得越高,它的根须扎进土地也就越深,而越是向深里扎去,光亮的东西也就越少,代之的必将是更多的黑暗因子。鲁迅对此有过很深刻的体验,比如那篇《影的告别》,在充满了紧张和悖论的文字间透漏出鲁迅思想的黑暗甚至危机,这种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会连自己也不在乎,就像他自己说的,“我很憎恶我自己”[2]452,“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2]453,又说,“做事的时候……有时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2]81。无疑,这种思想是很阴沉的,但它又是个体生命发生“自觉”的某种前提。“过客”永不停息的行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思想的形象化表述。只是,“过客”的处境并不比那个告别了一切的“影子”好多少,“影子”不愿上天堂,又不愿去地狱,也不相信将来的“黄金世界”,想要“沉没在黑暗里,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所以最终只能“彷徨于无地”。[1]169“过客”看似走在一条通向坟茔的小路上,其实那地方的名字叫做“坟”毋宁叫做“无地”更为恰当。事实上,“影子”和“过客”无论怎样周旋怎样抉择,他们的命运终将逃不出“彷徨于无地”的终局,因为创作他们的主体正在这般“无地”彷徨着,禁不住颓唐了,然而又不甘于这样的颓唐;发现自己老了,也不肯承认。可在杂文中又不经意间流露出喜好回忆的倾向,并自我解嘲道:“我不知怎的,近来很有‘怀古’的倾向。”[4]66
步入中年的鲁迅的确走在那任谁都知道终点的路上,他不比“呐喊”时期那般激越昂扬了,加之当时政治环境的压迫、言论氛围的紧张,鲁迅难免会更为敏感、多疑,甚至悲观、颓唐,同时也积淀下更多的苦闷,但最终过客勇于行走的实践精神激励了他。因为就“过客”而言,只有不停地走下去,在行走的过程中不断地审视自己,拷问自己,以此来抵挡孤独以及那些不断涌现出来的劝他回转去的声音,似乎只有这样,他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走”对他而言不仅是解决自身危机的一种充满着悖论的选择,同时也是唯一有效的自我拯救的路径,正如李欧梵(Leo Lee)所指出的那样:“‘走’成为在‘无意义’威胁下的唯一
[1]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李何林.鲁迅年谱:第二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4]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鲁迅全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夏济安.鲁迅的复杂意识[M]//乐黛云.国外鲁迅研究论集.有意义的行动。”[10]116“过客”深知这一点,所以在“走”下去的路上他只能背对历史,面向未来;只有真正解决了自身与自身的问题,才能最终成为面对“无物之阵”、面对太平的宣告而义无反顾地举起了投枪的“这样的战士”。也只有到那时,鲁迅才能真正解决自己内心的苦闷、疑惑,重新建立起对于自己战士身份和生命价值的崭新认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8]张梦阳.“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本原思想探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8):81-89.
[9]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10][美]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1999.
(责任编辑 周亚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