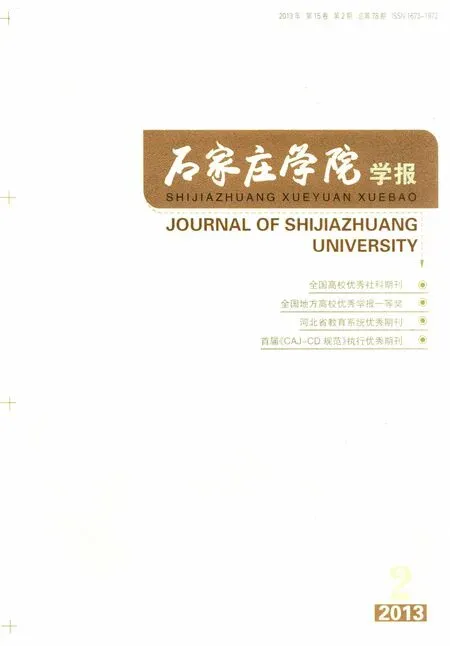“吟叹曲”与吟叹乐府诗
2013-04-11梁海燕
梁海燕
(韩国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学部,韩国 首尔 130-791)
与“相和曲”一样,“吟叹曲”也是汉乐府的一个歌诗类别。但“相和曲”及“相和歌辞”在乐府艺术系统中声名显赫,历来受到关注。至于“吟叹曲”,却鲜有专门的研究。究其原因,主要是汉乐府“吟叹曲”的歌辞及艺术形态在早期乐录文献中缺乏清晰明确的记载。笔者不揣浅陋,悉心检索相关文献,钩沉稽微,述其流衍,同时结合文人的同类乐府诗创作,拟从乐府艺术的系统中审视“吟叹曲”对于后世诗学的影响。
一、“吟叹曲”流传情形考
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将“吟叹曲”著录在“相和歌辞”类目之下,而实际上,“吟叹曲”与“相和曲”本是两类不同的表演艺术,二者应为并列而非从属关系。根据《乐府诗集》卷二十九“吟叹曲”序引南朝陈释智匠《古今乐录》的文字,可知吟叹曲“古有八曲”, 分别为:《大雅吟》《王昭君》《楚妃叹》《王子乔》《小雅吟》《蜀琴头》《楚王吟》《东武吟》。
上述八曲之中,惟《王子乔》尚存古辞,于魏晋乐府中继续使用。除此之外,郭茂倩并未对汉乐府吟叹曲辞的使用情况给出具体说明,显然他所依据的南朝乐书《古今乐录》对汉乐府“吟叹曲”的演奏情况已不甚清楚。
不过,在《乐府诗集》卷四十一“楚调曲”题序中又引述了《古今乐录》的另一段文字,内容为:
王僧虔《技录》:楚调曲有《白头吟行》《泰山吟行》《梁甫吟行》《东武琵琶吟行》《怨诗行》。其器有笙、笛弄、节、琴、筝、琵琶、瑟七种。[1]599
《技录》一书全称《大明三年宴乐技录》,为南齐王僧虔所著。上述引文值得注意的是,所列举的《白头吟行》《泰山吟行》《梁甫吟行》《东武琵琶吟行》四曲题名中,以“吟”“行”两字连称作为后缀。而在《乐府诗集》转引《技录》所载“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众多曲名中,并未出现过“吟”“行”连称作为题名后缀的情况。也就是说,“吟”“行”两字并称作为题名后缀,只是“楚调曲”乐府诗题特有的现象。那么,这些“楚调曲”与“吟叹曲”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呢?笔者经考察之后认为,这些楚调曲的题名当中本来并无“行”字,曲名称“行”,正是随着魏晋“相和诸调歌诗”艺术之兴起,这些本属“吟叹曲”的乐歌被演绎、转化为“相和诸调”中“楚调曲”曲目的结果。理由如下:
其一,郭茂倩虽在题解中引王僧虔《技录》曰“楚调曲有《白头吟行》”,但著录歌辞时仍以《白头吟》《泰山吟》《梁甫吟》称之,并不以“行”作为题名后缀。如此著录歌辞,极可能是据其本名而为。
其二,这些歌辞本有广泛的民间咏唱背景,在别处作为民间歌谣的身份出现时,也不称“行”。如《宋书·乐志》曰:“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白头吟》之属是也。”[2]549《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也说:“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甫)吟》。 ”[3]911然而,从《乐府诗集》著录的晋乐府所奏《白头吟》的曲辞看,已经具有“五解”规模的表演体制,演奏乐器也与当时流行的相和“三调歌诗”基本相同。显然,晋乐府中的楚调曲《白头吟行》,歌词虽源自汉乐府《白头吟》,却具有新的表演体制,题名中增添的“行”字正是一个重要提示。换言之,从汉乐府《白头吟》到晋乐府《白头吟行》的演变,正是汉乐府古辞传至魏晋时代所经历的重要变革的一个缩影。
其三,《古今乐录》说“吟叹曲”有《东武吟》一曲,而“楚调曲”恰有《东武琵琶吟行》。《古今乐录》叙“古吟叹八曲”中有《东武吟》,但说此曲已阙。今按《文选》李善注嵇康《琴赋》“东武太山”句曰:“魏武帝乐府有《东武吟》,曹植有《太山梁甫吟》。左思《齐都赋》注曰:‘《东武》、《太山》,皆齐之土风,谣歌讴吟之曲名也。 ’”[4]258可知,《东武吟》《太山吟》都是产生年代较早的以“谣歌讴吟”为演奏特色的乐府歌辞。鲍照《代东武吟》首句也说“主人且勿喧,贱子歌一言”[5]71,则《东武吟》曲调至少在刘宋年间并未失传。王僧虔《技录》所说楚调曲《东武琵琶吟行》当是汉乐府吟叹曲《东武吟》之后裔,可能此曲以琵琶作为主要演奏乐器,故又称“东武琵琶吟”。
从吟叹曲《东武吟》演变为楚调曲《东武琵琶吟行》的实例可以证明,汉乐府中产生较早的吟叹歌诗至少有一部分被分化、融入到了“相和诸调”中的“楚调曲”当中,如 《白头吟》《泰山吟》《梁甫吟》《东武吟》,这一变化应该是与“相和曲”演变为“三调歌诗艺术”同步发生的。除此之外,仍有一部分歌辞继续保留着独曲演奏形式,如《王子乔》,在魏晋宫廷乐府中仍是吟叹曲的保留曲目。但从整体上看,随着楚声艺术的衰落,“吟叹曲”在宫廷乐部中的地位日有所降,古曲曲辞逐渐散亡,至晋代,乐府仅传四曲。《乐府诗集》“吟叹曲”序曰:
《古今乐录》曰:张永《元嘉技录》有吟叹四曲:一曰《大雅吟》,二曰《王明君》,三曰《楚妃叹》,四曰《王子乔》。 《大雅吟》《王明君》《楚妃叹》,并石崇辞。《王子乔》,古辞。《王明君》一曲,今有歌。《大雅吟》《楚妃叹》二曲,今无能歌者。古有八曲,其《小雅吟》《蜀琴头》《楚王吟》《东武吟》四曲阙。[1]424
综上所述,汉乐府中的“吟叹曲”本来自成一类,曲目是很丰富的。《古今乐录》所说“古有八曲”,应该是汉乐府“吟叹曲”被分入相和歌“楚调曲”之后仍然保持独立演奏形态的吟叹曲辞的曲目。东晋以后,宫廷乐部中不复有“吟叹曲”类目,其演奏艺术主要被“楚调曲”继承了。不过,汉魏两晋乐府中吟叹曲辞的表演艺术及音乐风格对于文人进行同类乐府文体的创作仍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吟叹曲”的音乐形态与艺术风格
《宋书·乐志》曰:“汉、魏之世,歌咏杂兴,而诗之流乃有八名:曰行,曰引,曰歌,曰谣,曰吟,曰咏,曰怨,曰叹,皆诗人六义之馀也。至其协声律,播金石,而总谓之曲。”①所列举的八类诗题名称,其实是由八类各具特色的歌咏方式产生的文体区别。这些不同的徒歌咏唱方式直接影响到“散之律吕”后乐府歌诗的音乐形态与艺术功能。吟叹曲源于民间的 “吟”“叹”歌诗艺术,基本演奏形态为丝竹乐器伴奏下歌唱主体的悲吟怨叹。从部分“吟叹曲”至魏晋被分入“楚调曲”的经历看,不少吟叹曲辞的演奏具有楚歌的凄怨风格。同时,与相和歌辞的散歌叙事不同,吟叹曲辞主要表现为自叙悲情的抒情艺术。
(一)悲吟寄情与吟叹曲辞的悲怨风格
许慎《说文解字》:“吟,呻也。 ”[6]34又释“叹”:“吞叹也。一曰太息也。”[6]34太息,即叹息。“叹”字古有两形:一曰嘆(从口),二曰歎(从欠)。两字大多情况下可以通用,但情感表达有别。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歎(从欠)近于喜,嘆(从口)近于哀。 ”[7]60“吟叹曲”以悲吟怨叹作为寄情方式,曲辞及演奏风格呈现悲怨哀伤的情感基调,这从《王子乔》古辞的演奏也能得到证明。辞曰:
王子乔,参驾白鹿云中遨。参驾白鹿云中遨,下游来,王子乔。参驾白鹿上至云,戏游遨。上建逋阴广里践近高。结仙宫,过谒三台,东游四海五岳,上过蓬莱紫云台。三王五帝不足令,令我圣明应太平。养民若子事父明,当究天禄永康宁。玉女罗坐吹笛箫,嗟行圣人游八极,鸣吐衔福翔殿侧。圣主享万年,悲吟皇帝延寿命。[1]437
此篇虽说是汉乐府流传的旧辞,但在魏晋乐府演奏时应该进行过艺术加工。篇章题旨与曹操《气出倡》“驾六龙乘风而行”、《陌上桑》“驾虹霓”似乎较接近,都涉及游仙、宴饮、祝寿情节。然而细读之下,二者的艺术风格却有不小区别。曹操乐府诗描述了欢宴场景,友朋满座,歌乐喧天,人人尽情享受生命的欢乐,如歌中所唱:“吹我洞箫鼓瑟琴,何訚訚。酒与歌戏,今日相乐诚为乐。”[1]383《陌上桑》也以“景未移,行数千,寿如南山不忘愆”[1]412收尾,欢宴将终,齐向主人祝寿。而吟叹曲《王子乔》篇末却说“悲吟皇帝延寿命”,歌者有感于圣人王子乔游遨八极,世人却不能同去,前面的仙游场景瞬时皆成无望之想,顿时令人嗟叹生悲。“悲吟”两字,正是该曲演唱风格的重要提示。不过,从郭茂倩题解引述刘向《列仙传》述王子乔仙去故事本身,可知王子乔成仙的故事并没有令人特别哀伤的情节。那么,魏晋乐府中《王子乔》的演奏过程出现“悲吟”情景,显然是吟叹曲的演奏方式及其音乐风格导致的。
有些曲目尽管未见古辞,根据其他文献的引述,也能大致推测其乐奏风格。晋潘岳《笙赋》曰:“荆王喟其长吟,楚妃叹而增悲。”[8]1988鲍照《代白纻舞歌诗》也说:“荆王流叹楚妃泣。”[5]99由此可知,《楚王吟》以展现楚王喟然长叹为主要题材,《楚妃叹》以楚妃之怨叹为创调的原始。陆机《吴趋行》也说:“楚妃且勿叹。”[1]934夏侯湛《夜听笳赋》曰:“来楚妃之绝叹。”[9]796。《王昭君》的怀归思乡主题,同样决定了此曲不能不为悲音。石崇《王昭君》序也说:“其造新曲,多哀怨之声。”[4]1291就是后来进入相和楚调曲的《白头吟》《泰山吟》《梁甫吟》,也具有悲吟歌唱的艺术传统。东汉蔡邕《琴赋》已述及“《梁甫》悲吟”的演奏风格。晋陆机《梁甫吟》也说:“哀吟梁甫巅,慷慨独抚膺。”[1]606郭茂倩又于解题中指出《泰山吟》《梁甫吟》源出丧葬挽歌,“亦《薤露》《蒿里》之类也”[1]605。其音乐形态皆为悲吟长叹无疑。
(二)代言体歌唱与吟叹曲辞的自叙悲情艺术
“吟”“叹”形式的歌咏,以行为主体排遣忧思、抒发积郁为多。因此,演奏“吟叹曲”时,往往需要表演者以剧中主人公的身份、口吻直接抒情。这种代言体歌唱方式对于提升歌辞文本的语言艺术具有积极作用。兹举吟叹曲中的经典乐章《王昭君》为例。在《琴操》之前,西汉焦赣《焦氏易林》及东汉班固《汉书·元帝纪》都述及昭君和亲的历史事件,皆着眼于和亲的政治效果,并未涉及昭君在胡地的生活。至汉末蔡邕《琴操》,始正式确立王昭君的悲剧人物形象,同时记载了王昭君在胡地所作的《怨旷思惟歌》。晋乐府“吟叹曲”所奏石崇《王明君辞》,在继承怨旷怀归主题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昭君自我申诉的范围,使歌辞的悲情艺术达到极致。其歌辞为:
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辞诀未及终,前驱已抗旌。仆御涕流离,辕马悲且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沾朱缨。行行日已远,遂造匈奴城。延我于穹庐,加我阏氏名。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父子见凌辱,对之惭且惊。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愿假飞鸿翼,乘之以遐征。飞鸿不我顾,伫立以屏营。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朝华不足嘉,甘与秋草并。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1]426
全篇由演唱者以第一人称口吻抒怀言事。石崇新辞在“怀归”主题外,又增加了“辞诀”“远行”“见辱”“传语”等情节。通过“我”的悲唳申诉,将昭君的异域怀归之痛扩大为所有远嫁异域的汉族女性的人生悲剧。歌辞中四次强调“我”的存在,折射出主人公内心莫大的激愤。篇末哀呼“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
正与首句所强调的“我本汉家子”相呼应。歌辞细腻的心理描写、循序渐进的情绪变化、呼之欲出的言语表达,都与其代言体歌唱的角色设置直接相关。鲍照
《代东武吟》的创作明显受到此歌影响,同样开篇自报家门,曰“仆本寒乡士,出身蒙汉恩”;中叙“时事一朝异,弧绩谁复论”“少壮辞家去,穷老还入门”,征战一生却功名无果,至老被弃。[5]71其“昔如鞲上鹰,今似槛中猿”的命运,直似昭君“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的哀呼。这首辞无论篇章结构,还是自叙身世的语体风格,明显见出鲍照有意学习石崇《王昭君》的痕迹。而这种诗法的自觉传承,与二诗同为“吟”类歌曲不无关系。
三、吟叹曲辞的风格传承——以唐代吟叹题乐府诗为例
后世文人对于“吟”“叹”题乐府诗的深度抒情性能有着一致看法。如元代郝经《续后汉书·文艺传·文章总叙·诗部》释“吟”曰:“吟亦歌类也,歌者,发扬其声而咏其辞也。吟者,掩抑其声而味其言也。歌浅而吟深。 ”[10]卷66上上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曰:“吁嗟慨歌,悲忧深思,以呻其郁者曰‘吟’……感而发言曰‘叹’。”[11]104此例甚多,不烦多举。总之,汉魏晋乐府音乐演奏体系中吟叹曲辞的悲情艺术表达对于南朝以来的吟叹乐府拟辞创作,以及以“吟”“叹”为题的乐府新辞写作,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文体要求。下面仅以《乐府诗集》著录的唐人“吟”“叹”题乐府诗为例,探索其与古乐府系统中吟叹曲辞的诗学关联。
(一)作旧题吟叹乐府,赋咏古题中的悲情因素,寄托心志
东晋以后,吟叹曲《楚妃叹》已经不传,但在琴曲艺术中有所保留,或名曰《楚妃怨》。《乐府诗集·吟叹曲》在《楚妃叹》题名下收录张籍诗二篇,一曰《楚妃叹》,二曰《楚妃怨》。且唐代文人拟作此题者,惟张籍一人。张籍《楚妃叹》曰:
湘云初起江沉沉,君王遥在云梦林。江南雨多旌旗暗,台下朝朝春水深。章华殿前朝万国,君心独自无终极。楚兵满地能逐禽,谁用一身骋筋力?西江若翻云梦中,麋鹿死尽应还宫。[1]436
今按《文选》卷二十八陆机《吴趋行》李善注引《歌录》曰:“石崇《楚妃叹》曰:‘歌辞《楚妃叹》,莫知其所由。楚之贤妃能立德著勋,垂名于后,唯樊姬焉。故今叹咏之声,永世不绝。’”[4]1308晋乐府所采用的石崇《楚妃叹》歌辞,内容便是颂咏樊姬贤德,据此可推测,演奏时乐人必作咏叹赞美之声。唐初文献中,李善注《文选》、徐坚《初学记》都引用了晋石崇《楚妃叹》的序文,把歌颂樊姬贤德作为《楚妃叹》的本事。复观张籍《楚妃叹》,虽然也提到了樊姬谏猎——“楚兵满地能逐禽,谁用一身骋筋力”,但重心却在怨叹“君心独自无终极”、久游不归。显然,张籍并未完全延续石崇的题解,将题名中的“叹”字理解为“叹咏之声”,而是让楚妃作为愁叹行为的主体,从樊姬忧叹楚王穷奢极欲、耽于游猎、不理朝政等方面写其内心的忧思深虑。据李善注《文选》张华《女史箴》“樊姬感庄,不食鲜禽”条,《列女传》曰:“楚庄樊姬者,楚庄王之夫人。庄王初即位,好狩猎毕弋,樊姬谏不止,乃不食禽兽之肉,三年王改。”[4]2404试想,当“樊姬谏不止,乃不食禽兽之肉”时,心中必然忧愁烦闷。张籍将《楚妃叹》视为悲怨诗题,着力发掘楚妃本事故事中的忧怨情绪,正是对石崇颂美型《楚妃叹》的主题反拨。南朝以来,在琴曲艺术《楚妃叹》《楚妃怨》传承了宫怨主题、吟叹曲《楚妃叹》的本事几乎被人遗忘之时,张籍仍能从历来相传的楚妃故事出发,重为制辞,融入忧虑讽谏思想,不愧于时人“尤工乐府诗”[12]2之赞誉。
乐府以“吟”“叹”命题者,多为忧思之叹,张籍对此深有体会。其《白头吟》写弃妇之哀,篇末慨叹“人心回互自无穷,眼前好恶那能定。君恩已去若再返,菖蒲花生月长满”[13]4299。集中另一篇《古钗叹》,讲述了一枚堕入深井的古钗,被人打捞上来后,却因不合时俗审美观被弃之匣中不用,其遭遇令人叹惋。“虽离井底入匣中,不用还与坠时同。”[13]4294张籍明为古钗而悲,实为自己以及当时众多恪守古道、不附流俗的贫困士人悲哀感叹。这种乐府诗,完全是诗人寄托心志之作。
(二)作杂题吟叹乐府,自吟其情或吟叹史事,抒写悲怨
孟郊有二十余篇以吟、叹为题的作品,《乐府诗集》卷六十七“杂曲歌辞”著录其《游子吟》。郭茂倩题解云:“汉苏武诗曰:‘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怀。请为《游子吟》,泠泠一何悲。’又有《游子移》,亦类此也。”[1]971但南朝宋刘义恭的《游子移》,写游荡子趁青春年少四处游宴、及时行乐,与《游子吟》绝不相类。《游子吟》写游子含悲,储光羲《升天行贻卢六健》也说“恻恻《苦哉行》,呱呱《游子吟》”[13]1386。孟郊诗当自古诗中的悲情《游子吟》而来。诗人其时为官溧阳,仕途非常不得意,经历生活磨难,尝尽世态炎凉,故对于亲人的思念愈发强烈。千载之下,诗人悲感、思亲之情如在目前。
《乐府诗集·杂曲歌辞》还著录了一组以张华《壮士篇》为首题的乐府诗,贾岛《壮士吟》居其下。郭茂倩解题曰:“燕荆轲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壮士篇》盖出于此。”[1]973不过从张华《壮士篇》内容看,不一定与荆轲赴秦史事有关,作者用铺排手法塑造了一位恐“年时俯仰过”,急于立功边漠的英雄形象。同时载录的刘禹锡《壮士行》却以昂扬的笔调歌颂了杀虎斩蛟的历史人物周处。施肩吾《壮士行》则写“一斗之胆撑脏腑,如磥之筋碍臂骨”的无名壮士,空怀一身本领,却因“当今四海无烟尘,胸襟被压不得伸”。[1]974应该说,真正符合郭茂倩对《壮士篇》本事注释的只有贾岛的《壮士吟》与鲍溶的《壮士行》。鲍溶《壮士行》写荆轲提剑赴秦时的心理状态:宁为知己者死,羞于碌碌无为老病而终。对于功名节义的追求,甚至淡化了 “横剑别妻子”[1]974时的生离死别之痛。此诗延续了张华《壮士篇》对“壮士”形象的塑造与歌颂主题。正是在这一点上,贾岛的《壮士吟》显得与众不同。其辞曰:
壮士不曾悲,悲即无回期。如何易水上,未歌先泪垂。[1]973
此诗既无张华《壮士篇》华丽铺排的语言,也无刘禹锡《壮士行》慷慨激昂的格调,仅以诗人自述的口吻感叹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剧命运。前两句从荆轲的角度言壮士不悲,表露视死如归的心理;后两句写众人易水送别,闻荆轲之歌不禁垂泪涕泣。贾岛此诗表面写“壮士不悲”,实写“壮士之悲”,其所吟咏的是一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英雄。虽然郭茂倩将张华《壮士篇》、刘禹锡《壮士行》、贾岛《壮士吟》著录在一起,但仔细比较的话,由于“吟”与“篇”“行”这些乐府题名在乐府学体系内各自继承了不同的艺术风格,贾岛的《壮士吟》也由之具有了独特的悲情色彩。
再如,《乐府诗集·杂曲歌辞》载录的一组以“春游”为题的乐府诗,包括李华《春游吟》①《乐府诗集》本作“李章”,依《全唐诗》卷一五三当做“李华”。一首、施肩吾《春游乐》一首、李端《春游乐》一首以及张仲素《春游曲》三首。诸篇均写游春之乐,惟《春游吟》写伤春心绪,春光虽然大好,无奈形单影支,引人感叹伤怀:“所思杳何处,宛在吴江曲。可怜不得共芳菲,日暮归来泪满衣。”[1]1087
总之,从孟郊《游子吟》与刘义恭《游子移》、贾岛《壮士吟》与刘禹锡《壮士行》,以及李华《春游吟》与其余诗人《春游乐》《春游曲》的对比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唐代诗人对于吟叹乐府诗抒写悲情艺术的把握与认同。而张籍、孟郊、贾岛等人由于其独特的人生体验,所以对吟叹题名的乐府诗特别垂爱,往往结合其身世之感,使作品蒙上了更深的悲情色彩。
(三)作新题吟叹乐府诗,传承吟叹曲辞的自叙悲情艺术
中晚唐贫士诗人的吟叹题新乐府诗创作,肇始于元结。元结《系乐府》组诗中有三篇吟叹乐府,《陇上叹》叹息戎狄地区缺少礼仪教化,《古遗叹》叹息古之遗贤,《贱士吟》写贫士自说其愁。其《贱士吟》曰:
南风发天和,和气天下流。能使万物荣,不能变羁愁。为愁亦何尔,自请说此由。谄竞实多路,苟邪皆共求。常闻古君子,指以为深羞。正方终莫可,江海有沧洲。[1]1340
自叙悲愁、独抒胸臆的表达方式,与古乐府中的吟叹曲辞并无二致。
《乐府诗集·新乐府辞》所载张籍《节妇吟》,是一篇广为传诵的乐府名篇。关于此诗的创作本旨以及篇中的“节妇”形象,自宋代以来就聚讼纷纭。大多数人认为,此诗整体上采用比兴手法,借节妇之“事夫誓拟同生死”[1]1327寓意诗人效忠朝廷、不事二主的决心。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阐释,主要是宋代以来不少典籍载录本诗时,常于诗题“节妇吟”后附注“寄东平李司空”,如姚铉《唐文粹》、计有功《唐诗纪事》。王铚《四六话》记其事曰:“唐张籍用裴晋公荐为国子博士,而东平帅李师道辟为从事,籍赋《节妇吟》见志以辞之。”[14]卷上但是,这种解释总觉与诗中“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以及“还君明珠双泪垂,何不相逢未嫁时”[1]1327的遗恨之情不相谐和,故而引发争论。笔者以为,如果从吟叹题乐府诗的自叙悲情文体特点出发,或许有助于解读此诗。
抛开“寄东平李司空”的可能性背景,《节妇吟》当是一篇吟叹题乐府新辞。据研究,认为张籍此诗有具体寄赠对象的观点,目前并无来自唐代文献资料的支持。[15]从吟叹乐府诗的自叙悲情艺术来看,这正是一篇“节妇”自我悲叹的作品,是“节妇”内心世界悲哀的流露,而不是对“节妇”的歌颂。诗曰: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何不相逢未嫁时。[1]1327
主人公是一位有夫之妇。其家既富且贵,良人在朝为官。其中的“夸夫”情节显然受到汉乐府《陌上桑》影响。但《陌上桑》里的罗敷夸夫是多方面的,其对“夫婿”热情的夸赞流露出她对“夫婿”的依恋。这里的“妾”只是说“良人执戟明光里”,丝毫感受不到她对“良人”的情感态度;反倒是对赠己双明珠的“君”,既感其“缠绵意”,复叹恨“何不相逢未嫁时”。这一连串的反应表明,这位嫁在显贵家的妇人,生活虽然富有,但情感世界异常苍白。就在此时,一位“用心如日月”的男子向她表白爱意。少妇始而惊喜,将对方所赠之明珠珍重地“系在红罗襦”。但是,多年来所受的礼教节义告诫她,绝不能有违纲训,她最终选择了放弃。从她的哀叹声中,我们深深感受到少妇对于这份“有缘无份”的感情多么无奈。作者用“节妇”自我吟叹的口吻,将这份悲哀表现得淋漓尽致、委曲动人。
综上所述,中晚唐时期的贫士诗人倾心于吟叹题名的乐府创作,既与他们的性情及创作方式有关,也是困顿不遇的人生经历培育出他们忧郁感伤的心灵意绪的结果。从维护古乐府的文体风格角度看,这些作品对于汉魏两晋吟叹曲辞艺术风格的传承具有积极作用。这些贫士诗人,以他们敏感多思的情性,将其抑郁苦闷的人生境遇苦吟入歌,准确地诠释了吟叹乐府诗沉郁悲怨的艺术风格。据此可见,后世文人以吟、叹为题的乐府诗创作深受汉魏两晋吟叹曲辞的影响,在乐府学的体系内,吟叹题乐府诗表现出自叙悲情的独特艺术风格。
[1]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萧统.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鲍照.鲍参军集注[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6]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7]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8]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9]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0]郝经.续后汉书[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2]白居易.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3]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
[14]王铚.四六话[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刘明华.张籍《节妇吟》的本事及异文[J].文献季刊,2010,(2):160-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