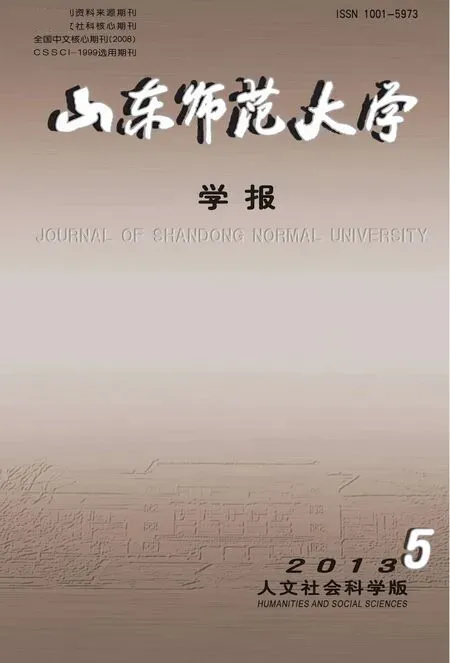试论汉晋子书之兼容趋向*
2013-04-11王琳
王 琳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一、先秦至西汉各种思想间的排斥与吸纳
早在战国时期,某些学者在著述中为了标榜自家学说,或攻乎异端,非议其他学派的思想家,如《墨子》在《非儒》、《公孟》、《耕柱》等篇激烈地攻击儒家学说。《孟子》则激烈抨击杨朱、墨翟,宣称要“距杨、墨,放淫辞,正人心,熄邪说”。《荀子·非十二子》及《成相》、《解蔽》、《儒效》诸篇多抨击其他思想家。汉代初期的某些儒家学者,往往站在儒家思想的立场上,自以为是,而以他家为非,甚至将儒家以外的某些学说斥责为“饰邪说,文奸言,以乱天下”。如韩婴《韩诗外传》卷四云:“夫当世之愚,饰邪说,文奸言,以乱天下,欺惑众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则是范雎、魏牟、田文、庄周、慎到、田骈、墨翟、宋钘、邓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顺非泽,闻见杂博,然而不师上古,不法先王,按往旧造说,务自为工,道无所遇,而人相从,故曰十子者之工说,说皆不足合大道、美风俗、治纲纪。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众愚,交乱朴鄙,则是十子之罪也……仁人将何务哉?上法舜禹之制,下则仲尼之义,以务息十子之说。如是者,仁人之事毕矣,天下之害除矣,圣人之迹著矣。”②[汉]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50-151页。汉武帝时群臣之对策、奏议中亦往往对儒家以外的思想学说持贬斥态度。如董仲舒在对策中宣扬:“《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③[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23页。到西汉后期,朝廷重用儒生,儒家经学受到空前的尊崇,某些人物往往将儒家之外的其他学说视为异端,予以斥责,著名文士扬雄和权臣王凤可谓代表。
扬雄站在崇孔尊经的立场上,步孟子之后尘,好攻乎异端,对战国诸子尤其是法家、纵横家,往往表现出轻视或反感的态度,如其《法言·学行》云:“视日月而知众星之蔑也,仰圣人而知众说(按指儒家之外的各家学说)之小也。”《法言·吾子》云:“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或问:‘公孙龙诡辞数万以为法,法欤?’曰:‘断木为棋,捖革为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观书者譬诸观山及水,升东岳而知众山之逦迆也,况介丘乎?浮沧海而知江河之恶沱也,况枯泽乎?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弃常珍而嗜乎异馔者,恶睹其识味也;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法言·五百》云:“庄、杨荡而不法,墨、晏俭而废礼,申、韩险而无化,邹衍迂而不信。”《法言·问道》云:“申、韩之术,不仁之至矣。”因此,他要像孟子那样,辟邪说,维护经学的权威并保持儒家思想的纯洁性,故唐刘知几《史通·自叙》概括《法言》写作缘起云:“盖仲尼既殁,微言不行;史公著书,是非多谬。由是百家诸子,诡说异辞,务为小辨,破彼大道,故扬雄《法言》生焉。”①[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1页。
在西汉后期空前浓重的尊经观念弥漫之时,子书的传播受到抑制。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事例为东平王刘宇上疏求阅诸子书而被朝廷所拒绝。《汉书》卷八十《东平思王刘宇传》记述云:
(宇)后年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臣闻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礼不言。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不许之辞宜曰:‘《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王审乐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讲诵,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辩破义,小道不通,致远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诸益于经术者,不爱于王。’”对奏,天子如凤言,遂不与。②[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324-3325页。
《汉书》卷一百《叙传》也有类似的记载,谓其时诸子之书藏于秘府,非皇帝亲近,不能与目,或欲辗转借阅,亦难以遂愿。
另一方面,战国至西汉子书诸学派,较明显地呈现相互吸纳或兼容的趋势。如《墨子》之《修身》、《亲士》、《所染》等篇,观念与儒家同;其《经上下》、《大小取》、《经说上下》则同乎名家言;《备城门》诸篇,则为兵家言。《管子》杂糅诸家思想,其中《任法》、《明法》、《正世》等篇为法家言;《牧民》、《形势》等篇杂糅道家、法家学说;《君臣上下》多道家、法家言,杂糅儒家言;《兵法》、《地图》、《参患》、《制分》多兵家言;《霸言》杂糅纵横家言;《四时》、《五行》为阴阳家言;《地员》、《轻重》则多为农家言。《荀子》的思想,虽以儒家为主导,但已融入不少法家观念,具有较浓的以儒统法的特征。汉初陆贾《新语》在高扬儒家德教仁政思想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有选择地吸收了其他学派的思想,尤其是黄老道家贵柔及清静无为的思想。如:“故怀刚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长,躁疾者为速厥,迟重者为常存,尚勇者为悔近,温厚者行宽舒,怀急促者必有所亏,柔懦者制刚强。”(《新语·辅政》)“夫刑重者则心烦,事众者则身劳;心烦者则刑罚纵横而无所立,身劳者则百端回邪而无所就。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新语·至德》)“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舜治天下也,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新语·无为》)这种思想适应了休养生息、安定社会、发展经济的时代要求。其后的贾谊等远承荀况学说,在治国思想上,主张以儒家礼乐教化为主,兼采百家之学,如叔孙通制订朝仪以尊君卑臣,贾谊主张众建诸侯以少其力,黄老之学中的政略治术和法家思想得以结合;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同时吸收韩非等法家人物的尊君卑臣思想。
相对而言,对诸子学说态度尤为宽容,议论较为通达的是某些黄老道家思想浓重的人士。刘安堪称代表。《淮南子·俶真训》:“百家异说,各有所出。若夫墨、杨、申、商之于治道,犹盖之无一橑而轮之无一辐,有之可以备数,无之未有害于用也。己自以为独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此为通达之论,对各家思想自以为是而排斥异己的狭隘观念有所批评,《淮南子》博采兼容百家学说,便是对此种“自以为独擅之”的狭隘观念的自觉矫正。又《淮南子·氾论训》云:“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淮南子·齐俗训》谓诸子百家思想观念虽有差异,但皆与大道相合,犹如丝竹金石虽有不同的曲调,但皆不失为音乐:“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也。譬若丝竹金石之会乐同也,其曲家异而不失于体。”此种思想对葛洪《抱朴子》等魏晋著述有较深刻的影响。《淮南子》一书以黄老道家的思想较为浓重,此外也杂糅儒家、名家、法家、兵家等诸家思想。《原道训》、《俶真训》、《览冥训》、《精神训》、《本经训》、《道应训》、《诠言训》等篇多为道家言,《主术训》、《缪称训》、《氾论训》、《修务训》等篇多杂糅法家、儒家思想,《兵略训》则富于兵家言。《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述六家要旨,其述道家云:“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此道家已非先秦的道家,而是汉代杂家化了的道家,《淮南子》正属这种性质的著述,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将《淮南子》列于“采儒墨,合名法”之杂家类。汉武帝刘彻乃深谋远虑、雄图大略之君,他虽推重儒术,但同时也能兼容百家之学。《史记·龟策列传》太史公曰:“至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技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武帝所延揽之士,包括熟悉道家、法家、纵横家、杂家及阴阳、五行、术数等各种思想的人才;在他的提倡下进行的图书文献整理中,许多经传诸子著述得到保存,《汉书·艺文志》序云:“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书写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西汉后期刘氏宗室之著名思想家刘向,虽对诸子书难免有不满之词,但其总体上对待诸子的态度较为宽容。他和儿子刘歆在整理诸子群书时,对各家思想之长处和短处进行了较为客观、公允的概括,强调从诸子书中吸取思想营养以充实儒家学说。刘向以为诸子书对于治道各有所益,蕴含符合经义的内容。在此基础上,他对诸子著述予以肯定。其《管子书录》云:“《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晏子书录》云:“晏子博闻强记,通于古今,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列子书录》云:“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申子书录》、《韩子书录》称法家人物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归其本于黄老”;评法家的刑名之术云:“循名以责实,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于六经也”。《战国策书录》评纵横家人物云:“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其《说苑·善说》,不仅引用《鬼谷子》中语,而且颇为认可苏秦、蒯通等纵横家人物的善于言辞,云:“昔子产修其辞而赵武致其敬,王孙满明其言而楚庄以惭,苏秦行其说而六国安,蒯通陈说而身得以全。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刘向父刘德少修黄老之术,有智略,刘向受其影响,故对黄老道家思想有颇为深刻的把握,上引《列子书录》即为显例。据《汉志》著录,刘向撰有《说老子》四篇,是为汉代出现较早的专门研究老子思想的著述。刘向所撰《说苑》二十篇,以《君道》为首,借助历史故事传说,宣扬人君清静无为之旨;其他篇如《政理》亦有强调老子清静无为之治道的内容。刘歆《七略·诸子略》以儒家为首,以下分列道、法等九家,并为十家,主张兼采各家思想之长,以充实完善儒家的治国方略。有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弊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①[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46页。这鲜明地流露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来博采统摄诸子思想精华的开放包容的学术观念。他在解说杂家的产生及其特点时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这里指出了杂家的兼容并包的特质。所谓“兼儒、墨,合名、法”,只是就大概而言,实则杂家还兼容了儒墨名法之外的思想,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的道家思想就相当浓重,还杂糅了兵家、农家及阴阳家的思想。
二、东汉至魏晋士人学派意识的淡化
东汉以来士人对诸子典籍的认同程度,显然超越西汉。这主要表现在西汉尤其是西汉中后期士人对诸子典籍的态度是以儒家统摄诸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吸收诸子的某些思想成分,以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其中渗透了尊崇儒家的学派意识。而东汉的某些子书作者在写作时则往往淡化或缺乏这种尊崇儒家的学派意识,如王充《论衡》就是如此。《论衡》中当然有儒家思想,但王充并未以之为尊,刘知几《史通·自叙》概括《论衡》之创作缘起云:“儒者之书,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华。而流俗鄙夫,贵远贱近,传兹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论衡》生焉。”①[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1页。乃至书中有《问孔》、《刺孟》之篇。书中除儒家思想外,黄老道家、法家及墨家思想也皆有所流露,故《隋书·经籍志》列于杂家,这与王充学术视野开阔,思想上较少拘束,说理不主于一家,而注重博采兼取百家的学术趣味,是密不可分的。东汉中后期作家直接继承了王充的理性色彩和批判精神,作品内容由疾虚妄而转向关注更广泛的社会问题,思想则由杂取众家取代独尊儒术。王符、崔寔、仲长统或被称为汉末三子,他们的生活年代较接近,在思想渊源上,对诸子百家皆持兼容并包的态度,但在《隋书·经籍志》著录中三书却非同类,王符《潜夫论》列于儒家,崔寔《政论》列于法家,仲长统《昌言》列于杂家。原因何在?我以为在于三家书的主导思想有所差异。相对而言,《政论》中流露的法家思想更浓重一些;《昌言》思想较为驳杂,主导倾向不明显;《潜夫论》的儒家思想虽浓重一些,但并非专尊儒术,故清汪继培《〈潜夫论笺〉序》云:“王氏精习经术,而达于当世之务。其言用人行政诸大端,皆按切时势,令今可行,不为卓绝诡激之论。其学折中孔子,而复涉猎于申商刑名、韩子杂说,未为醇儒。”②[汉]王符撰、[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87页。又如王逸《正部论》八卷,梁代书目及后来的《隋书·经籍志》皆列于儒家,但与王符《潜夫论》相似,其书亦杂糅一些法家观念,如:“明刑审法,怜民惠下,生者不怨,死者不恨。谚曰:‘政如冰霜,奸宄消亡;威如雷霆,寇盗不生。’”③[唐]马总撰、王天海校注:《意林校注》,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87页。以博学著称的经师马融,其治学不仅局限于儒家典籍,还涉及《老子》、《淮南子》等。其《长笛赋》描摹音乐形象,善用先秦诸子及其他人士作比拟,其中有“孔、孟之方”、“老、庄之概”、“随、光之介”、“诸、贲之气”、“管、商之制”、“申、韩之察”、“范、蔡之说”、“皙、龙之惠”等,亦可见子书知识系统在马融心目中占据重要地位。
汉魏之际以降,治学不主常师、思想兼收并蓄成为人们更加自觉的追求。广大士人无论在学术领域还是在为人处世方面,对于诸子思想往往持包容的态度,而以会通儒道为其鲜明特色;某些统治者在政略治术上对各家思想的取舍,也表现了不拘一格、随时调整的博采兼容态势。
建安年间佚名《〈中论〉序》述及徐幹的治学态度及学术理想,明确指出其转益多师和博采众家之长的取向,有云:“君子之达也,学无常师。有一业胜己者,便从学焉,必尽其所知而后释之;有一言之美,不令过耳,必心识之。志在总众言之长,统道德之微,耻一物之不知,愧一艺之不克。故日夜亹亹,昃不暇食,夕不解衣,昼则研精经纬,夜则历观列宿。考混元于未形,补圣德之空缺,诞长虑于无穷,旌微言之将坠,何暇讙小学,治浮名,与俗士相弥缝哉!故浮浅寡识之人,适解驱使荣利,岂知大道之根?”④[清]严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360页。这段话的关键词为“学无常师”、“总众言之长”,强调了徐幹在治学旨趣上不为名利驱使,以义理的探究为本,以章句之学为末。此外,刘陶兼治经学、子学,著数十万言,又撰《匡老子》《反韩非》《复孟轲》等,对先秦儒、道、法诸家学说予以评论,显示了学术的会通。高诱不仅注释《孟子》、《孝经》,还注释《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杂家书。三国时期不少学者道家、儒家兼治。《三国志》卷十三《魏书·王肃传》注引《魏略》记载董遇事迹曰:“遇字季直,性质讷而好学……明帝时,入为侍中、大司农。数年,病亡。初,遇善治《老子》,为《老子》作训注。又善《左氏传》,更为作朱墨别异。”卷五十七《吴书·虞翻传》载,虞翻好学,研习五经,并及《老子》。王昶治学注重经世济物,精于儒家的治道以及行军作战的兵家之学。《三国志》卷二十七《魏书·王昶传》载其在魏明帝时期的著述情况云:“昶虽在外任,心存朝廷,以为魏承秦、汉之弊,法制苛碎,不大厘改国典以准先王之风,而望治化复兴,不可得也。乃著《治论》,略依古制而合于时务者二十余篇,又著《兵书》十余篇,言奇正之用,青龙中奏之。”此迥异于汉儒之重视章句训诂的学术路径。在为人处世方面,王昶则显示了非常鲜明的会通儒道的特色,本传载其《诫子侄书》云:
夫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则宗族安之,仁义则乡党重之,此行成于内,名著于外者矣。人若不笃于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华焉,以成朋党焉;浮华则有虚伪之累,朋党则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车滋众,逐末弥甚,皆由惑当时之誉,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贵声名,人情所乐,而君子或得而不处,何也?恶不由其道耳。患人知进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语曰:“如不知足,则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览往事之成败,察将来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厌,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禄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虚为名,欲使汝曹顾名思义,不敢违越也。①[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44-745页。
从中可以看出,魏晋士人遵循的为人处世原则,主要受到儒家和道家的影响,其他诸子学派的影响则难以与儒道二家之学相抗衡,大体上处于陪衬的地位。又《晋书·儒林传》记述儒家学者徐苗的事迹,同时揭示其平生著述行事有浓重的道家气息,可谓儒道兼综的代表人物:“(苗)作《五经同异评》,又依道家著《玄微论》,前后所造数万言。永宁二年卒,遗命濯巾瀚衣,榆棺杂甎,露车载尸,苇席瓦器而已。”此犹西汉道家信徒杨王孙之志也。某些佛教学者在治学上也往往会通儒道。如释惠皎《高僧传》卷六《释慧远传》载,释慧远“博综六经,尤善《庄》、《老》”。
魏晋统治者的执政思想往往具有明显的兼容性质。此以曹操和东晋前期君臣为例。曹操是一个非常清醒而成熟的政治家,他之为政,儒法兼容,刑礼并用,既重才智,也不忽弃德行,贵在适应形势变化有所调整而已。《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及裴注载,建安八年夏,他下令有曰:“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同年秋,他又令曰:“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②[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4页。对荀彧尊崇儒家文教的建议,他有积极的回应,《三国志》卷十《荀彧传》裴松之注引《荀彧别传》载云:
是时,征役草创,制度多所兴复,彧尝言于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庶绩,教化征伐,并时而用……今公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国难方弭,六礼俱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诚仲尼述作之意;显制度于当时,扬名于后世,岂不盛哉!若须武事毕而后制作,以稽治化,于事未敏。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烦重,以一圣真,并隆礼学,渐敦教化,则王道两济。”彧从容与太祖论治道,如此之类甚众,太祖常嘉纳之。③[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7-318页。
晋代人对曹操思想的评价,时见歧异。或强调其推重法家的一面,如为学界经常引用的西晋初傅玄所谓“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的评价。另一方面,关于强调其重视儒学教化方面的评价亦不鲜见,如东晋重臣庾亮在武昌开置学官,颁布教令,在强调礼乐教化之重要性的同时,特意将曹操视为典范人物予以表彰。文云:“自胡夷交侵,殆三十年矣……季路称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为之三年,犹欲行其义方。况今江表晏然,王道隆盛,而不能弘敷礼乐,敦明庠序,其何以训彝伦而来远人乎?魏武帝于驰骛之时,以马上为家,逮于建安之末,风尘未弭,然犹留心远览,大学兴业,所谓颠沛必于是,真通才也。”①[南朝梁]沈约撰:《宋书》卷十四《礼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63-364页。合而观之,可见曹操主持军政事务,并非拘于某家思想,而是根据局势变化,随时调整,不拘一格,多方吸纳。他的某些看似极端的言论,仅是在不同的形势下,或特殊的语境中,不得不有所强调、有所偏重的产物。明乎此,作为后世学理性的评价,当然不可以偏概全。傅玄、庾亮的言论,皆带有在特定的语境下的强调某方面的性质,并非全面之论。
东晋为老庄思想盛行的时代,但也不乏信奉申韩之术的记载。《晋书》卷七十三《庾亮传》载,晋元帝司马睿要求太子司马绍学习申韩之术,并以《韩非子》授太子,庾亮认为“申韩刻薄伤化,不足留圣心”。而庾亮后来在以帝舅身份辅政时,则出现法家的倾向,因此受到某些士族人物的不满。本传云:“先是,王导辅政,以宽和得众;亮任法裁物,颇以此失人心。”其弟庾冰与之近似,同卷附传曰:“是时王导新丧,人情恇然。冰兄亮既固辞不入,众望归冰。既当重任,经纶时务,不舍夙夜,宾礼朝贤,升擢后进。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贤相。初,导辅政,每从宽惠,冰颇任威刑。”
魏晋人的诸子观,学派意识普遍淡化,当时社会思想虽然极其活跃,但已罕见先秦时期各学派间相互争鸣的盛况。有关著述往往扬长避短,求同重于存异,糅合大于排斥,会通多于分化,吸纳胜于抗衡。此即徐幹所谓“总众言之长”,陆云所谓“思乐百氏,博采其珍”。魏晋之际子书重要作家傅玄,今存其子书辑本《傅子·补遗上》有云:“知人之难,莫难于别真伪。设所修出于为道者,则言自然而贵玄虚;所修出于为儒者,则言分制而贵公正;所修出于为纵横者,则言权宜而贵变常。九家殊务,各有其长,非所为难也。”“见虎一毛,不知其斑。道家笑儒者之拘,儒者嗤道家之放,皆不见本也。”②[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737-1740页。指出道、儒、纵横诸家或“言自然而贵玄虚”,或“言分制而贵公正”,或“言权宜而贵变常”,皆有其所注重的话语体系,皆有所优长。在此基础上,傅玄对拘于某家、自以为是、各执一偏的狭隘观念表示了不满,这可谓当时子书博采会通之著述趋向的明确表白。
东晋人的诸子观,袁宏有一定的代表性,其《后汉纪》卷十二《章帝纪》论曰: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诸子之言纷然散乱,太史公谈判而定之以为六家,班固演其说而明九流。观其所由,皆圣王之道也。支流区别,各成一家之说。夫物必有宗,事必有主,虽治道弥纶,所明殊方,举其纲契,必有所归。寻史谈之言,以道家为统,班固之论,以儒家为高。二家之说,未知所辩。
尝试论之曰:夫百司而可以总百司,非君道如何情动,动而非已也。虚无以应其变,变而非为也。夫以天下之事而为以一人,即精神内竭,祸乱外作。故明者为之视,聪者为之听,能者为之使。惟三者为之虑,不行而可以至,不为而可以治,精神平粹,万物自得。斯道家之大旨,而人君自处之术也。
夫爱之者,非徒美其车服,厚其滋味;必将导之训典,辅其正性,纳之义方,闲其邪物。故仁而欲其通,爱而欲其济,仁爱之至,于是兼善也。然则百司弘宣,在于通物之方,则儒家之算,先王教化之道,居极则玄默之以司契,运通则仁爱之以教化。故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其可知也矣。
夫大道行则仁爱直达而无伤,及其不足则抑参差而并陈。患万物之多惑,故推四时以顺,此明阴阳家之所生也。惧天下扰扰,竟故辩加位以归真,此名家之所起。畏众寡之相犯,故立法制以止杀,此法家之所兴也。虑有国之奢弊,故明节俭以示人,此墨家之所因也。斯乃随时之迹,总而为治者也。后之言者,各演一家之理以为天下法,儒、道且犹纷然,而况四家者乎?③[汉]荀悦、[晋]袁宏撰,张烈点校:《两汉纪》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31-232页。
袁宏认同司马谈、刘向、刘歆及班固对于诸子百家予以“支流区别”,进行学术归宗的方式,并对司马谈与班固不同的学术旨趣予以辨析,指出司马谈“以道家为统”,班固“以儒家为高”。他对司马谈和班固的观念皆有所吸收,既推崇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人君南面之术及政治理念,也重视儒家思想在政治实践运作中的效用,故以“道明其本,儒言其用”来概括儒道关系,其思想具有儒道合流的特征。儒、道二家之外,袁宏还论及阴阳、名、法、墨四家,但他不同于前人之关注对各家长短得失的较量,而是揭示各家产生的原因,认为四家之所以产生,皆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以此而推,阴阳、名、法、墨诸家,虽思想内容有异,但皆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理由。在此基础上,袁宏对仅看重某家,并欲推演某家之理以为天下法者,颇不以为然。其中流露的观念甚为弘通,显示了不拘执于一端的开放的学术胸襟。
这种观念明显地表现在晋代子书创作上,兹以学界较少关注的晋代两部道家子书为例。先秦道家典籍《老子》和《庄子》,排斥儒、法诸家的观念显而易见,但晋代道家子书,则往往异于是。如孙绰《孙子》(或称《孙绰子》),《隋志》著录十二卷,列于道家。其书今存少量佚文,其中流露的思想,包括道家的无为、儒家的仁义、名家的循名责实、法家的法治等,可见孙绰《孙子》以道家为主而融合诸家的性质。苏彦《苏子》,原有七卷,《隋志》列于道家,已佚。佚文略见于唐马总《意林》、宋李昉《太平御览》等书,其思想或有同于《庄子》者,如宣扬无用获全、有用获残之理,蔑视世俗的荣华富贵观念;或抨击周、秦之管叔、蔡叔、赵高,斥其覆国残家、禽兽不如,与《庄子》的愤世嫉俗也有相通之处。但也有与先秦道家大异其趣的,如先秦道家轻儒斥法,而此书则肯定儒、法典籍:“立君臣,设尊卑,杜将渐,防未萌,莫过乎《礼》;哀王道,伤时政,莫过乎《诗》;导阴阳,示悔吝,莫过乎《易》;明善恶,著废兴,吐辞令,莫过乎《春秋》;量远近,赋九州,莫过乎《尚书》;和人情,动风俗,莫过乎《乐》;治刑名,审法术,莫过乎《商》、《韩》。”①[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六百零八,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737页。可见与孙绰《孙子》相似,苏彦《苏子》认同道家思想,但并不排斥他家思想,具有明显的兼容性。其根源在于作者学派意识的淡化。
三、博涉为贵的士林风尚与子书内容的兼容
东汉以来,士林中盛行博涉群籍的风气。东汉前期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为王充。《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传》载,王充年轻时“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王充后来在写作中高度评价博览群籍并能独立思考而著述子书者。《论衡·别通篇》有云:“颜渊曰:‘博我以文。’才智高者,能为博矣。颜渊之曰博者,岂徒一经哉?不能通五经,又不能博众事,守信一学,不好广观,无温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览之暗,其谓一经是者,其宜也。”“人不博览者,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儒生不博览,犹为闭暗。”《论衡·超奇篇》:“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在王充心目中,最轻视那些不好博览而仅能因循师传解说一经的儒生,最推重那些博学通览且善于独立思考而能撰作子书的人物。东汉后期郑玄,谈论及著述既博且通。《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传》载其自青州到冀州,“时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遣使要玄,大会宾客,玄最后至,乃延升上座。身长八尺,饮酒一斛,秀眉明目,容仪温伟。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若非平时博涉群籍,对有关知识了然于胸,何能在宴会上即兴论辩,应对自如?另一著名学者应劭的知识构成颇为驳杂,《后汉书》卷四十八《应劭传》称劭“博览多闻……撰《风俗通》,以辩物类名号,释时俗嫌疑。文虽不典,后世服其洽闻”。其他士人博涉通览的嗜好,《后汉书》亦多有记载,如卷二十八上《桓谭传》载,桓谭“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卷三十上《苏竟传》载,苏竟善图律,能通百家之言。卷四十上《班彪传附子固传》载,班固“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卷五十二《崔骃传》载,崔骃“年十三能通《诗》、《易》、《春秋》,博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善属文”。卷六十下《蔡邕传》载,蔡邕“少博学,师事太傅胡广。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卷六十二《荀爽传》载,荀爽父荀淑“少有高行,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而州里称其知人”。卷六十四《延笃传》载,延笃“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师”。
魏晋社会思想更为活跃,人们的治学视野进一步拓展,“博学而不好章句”成为士林中较普遍的治学趋向。他们对于传统的章句训诂之学,已不似前代儒生那样热衷而趋之若鹜,而转为崇尚博通,注重义理的阐发。此种治学兴趣及学术动向,建安文人徐幹在《中论·治学篇》有明确的表白,云:“故君子……言不苟出,必以博闻……圣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学者所以总群道也。群道统乎己心,群言一乎己口,唯所用之……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然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务于训诂,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此无异乎女史诵诗、内竖传令也。”①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62-263页。其他的有关记述中,“六经”、“百氏”往往并列,成为时人博学广览的代称。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述及汉魏之际荆州地区学术兴盛一时,学人云集,学术研讨范围广泛:“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遂训六经,讲礼物,谐八音,协律吕,修纪历,理刑法,六略咸秩,百氏备矣。”②[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93页。曹丕《与吴质书》忆及他与建安诸子在一起的学术和娱乐活动:“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碁间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三国志》卷二《文帝纪》注引王沈《魏书》称曹丕:“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曹丕《典论》内容富赡,集中体现他崇尚博通的治学追求。曹植学识广博,才艺超群,极受时人赞赏。《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裴注引《魏略》载,邯郸淳依附曹操后,因博学多才,颇受敬异。操遣淳侍奉曹植,植得淳甚喜,“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才,谓之‘天人’”。邯郸淳赞叹曹植,既在于他潇洒的谈吐风度,更在于他异常广博的学识。其他博涉通览或擅长著述的人物,也多见于魏晋史籍记载。如《三国志》卷三十八《蜀书·秦宓传》载,李权明确提出“君子以博识为弘”的观念:“先是,李权从宓借《战国策》,宓曰:‘战国从横,用之何为?’权曰:‘仲尼、严平,会聚众书,以成《春秋》、《指归》之文,故海以合流为大,君子以博识为弘。’”卷五十三《吴书·薛综传附薛莹传》载华覈上书,言及对博览群籍且擅长撰作之士的重视:“莹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僚之中,莹为冠首。今者见吏,虽多经学,记述之才,如莹者少。”会稽虞翻以博学著称,且善于辞令,有纵横家风神。《三国志》卷五十七《吴书·虞翻传》注引《江表传》载,孙策创业时期,曾遣虞翻游说豫章太守华歆,翻游说成功。孙策敬重虞翻的重要原因在于虞翻具有“博学洽闻”的高超素质,并希望他到中原之许都一展风采,以反击、破除某些中原人士所谓江南士人“学问不博”的成见。
《晋书》也多有士人博涉而好著述的记载。如卷三十三《郑冲传》载,郑冲“起自寒微,卓尔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经史,遂博究儒术及百家之言”。卷三十四《羊祜传》载,羊祜博学能属文,善谈论,撰有《老子注》。卷五十一《皇甫谧传》载,皇甫谧贫而好学,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以著书为务,自号玄晏先生。同卷《挚虞传》载,挚虞“少事皇甫谧,才学通博,著述不倦”。又同卷《束皙传》载,束皙才学博通,所著《三魏人士传》、《七代通记》、《晋书》纪志,遇乱亡失;其《五经通论》、《发蒙记》、《补亡诗》、文集数十篇,行于世。卷七十五《范汪传》载,范汪博学多通,善谈名理。卷八十二《习凿齿传》载,习凿齿“少有志气,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同卷《徐广传》载,徐广家世好学,“至广尤为精纯,百家数术无不研览”。卷九十一《杜夷传》载,杜夷“少而恬泊,操尚贞素……博览经籍百家之书,算历图纬靡不毕究”。皆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晋人以博涉为贵的治学取向。
博览是学术兴趣、学术视野的拓展,同时也预示着学术方向,所涉博通经史百家之言的魏晋人物,往往撰有子书。他们之博通经史百家之言,不仅为其子书写作积累了素材,而且直接决定了其子书的内容。魏晋子书作家学派意识较为淡薄,其著述富于兼容性,在很大程度上缘自推重博通的时代风尚。如袁宏所言,诸子百家之言,其思想不免差异,但宗旨皆在于“为治”,皆有其不朽的社会价值,因而不可推演一家之理以为平治天下的法则,故探讨政略治术,须不拘一格,博采百家思想。博采的前提是博览,博览的前提是对知识和学术的敬畏。晋代子家巨擘葛洪博学洽闻,对知识和学术满怀敬畏,对不学无术深恶痛绝,其《抱朴子外篇·疾谬》抨击汉末以来中原社会失礼放诞、不学无术的不良现象,其中对不学无术之人的虚伪情状有入木三分的揭露,“若问”一节,尤写得淋漓酣畅、栩栩如生。有云:
若问以《坟》、《索》之微言,鬼神之情状,万物之变化,殊方之奇怪,朝廷宗庙之大礼,郊祀禘祫之仪品,三正四始之原本,阴阳律历之道度,军国社稷之典式,古今因革之异同,则恍悸自失,喑呜俛仰,蒙蒙焉,莫莫焉,虽心觉面墙之困,而外护其短乏之病,不肎谧已,强张大谈曰:“杂碎故事,盖是穷巷诸生,章句之士,吟咏而向枯简,匍匐以守黄卷者所宜识,不足以问吾徒也。”①[晋]葛洪撰、杨明照校笺:《抱朴子外篇校笺》上,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635页。
葛洪所胪述的知识范围很广,既含政略治术、军事谋画,也有礼仪制度、天文历数,还有地理博物、鬼神情状等等,已远远超越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知识领域,而显示出一种鲜明的博涉化、知识化的价值评判态度和立场。《抱朴子内外篇》内容之富赡,作为子书前所罕见,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作者空前自觉的博涉群籍而兼容并蓄的治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