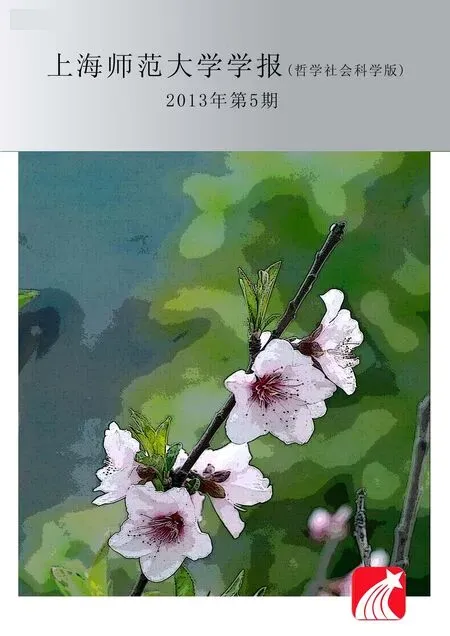近代日本视野下的孔教运动
2013-04-11朱忆天
朱忆天
(华东理工大学 人文科学研究院,上海 200237)
辛亥革命的爆发、清王朝的崩溃,令康有为的“保皇”理想化为泡影。1912年秋,康有为联系美国留学归来的弟子陈焕章 ,在上海成立孔教会,并在全国各地展开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而是否在宪法中明文规定孔教为国教,则成为民国初年政治生活的一大焦点。
康有为积极推动孔教运动,显然是受到了日本明治维新宗教改革的启发和影响。康有为认为,民国初年中国面对的国家分裂、民心涣散等难题,明治维新前夜的日本有识之士也曾同样经历过。明治指导者在文明开化的旗帜下,一方面通过神佛分离令、废法毁释等手段,对古代、中世纪以来的自发信仰予以毁灭性打击;另一方面,则围绕天皇的存在,进行复古性设计,有意识地培植国家神道,重点建构“万世一系”的“传统”,在确立天皇神权性的基础之上,确立天皇政治支配的正当性。
康有为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明治维新确立了天皇的神圣性,并以皇室祭祀为中心再编神道,通过国家的祭祀来统合人心,这是日本近代天皇制国家成功创出的关键要素。因此,康有为也希望模仿这种做法,通过推动孔教运动,确保“举国一致”,创出中国的近代国家新体制。正因为如此,康有为特别看重明治天皇祭天和誓文发表等的重要象征意义。日本学者子安宣邦认为,这种构想,明显可以看出祭祀的近代天皇制国家日本的影子。康有为主导的孔教运动,是对于近代国家日本的回应。①
显然,民国初年孔教运动的原初构思,其相当部分源于明治日本的经验,这种东亚地区思想的连锁互动,自然也吸引了有贺长雄、服部宇之吉和内藤湖南等既具有深厚儒学功底、又十分关注中国发展的日本思想家的注意。在近代日本的视角之下,他们究竟是如何观察、理解和评价中国的这场孔教运动呢?有必要对此作进一步的梳理分析。
一、有贺长雄的视角
对孔教运动予以肯定评价的同时代日本思想家,首推有贺长雄。有贺长雄(1860—1921)曾留学德、奥,精通国际法。在甲午战争中,有贺担任日本陆军大将、陆军大臣兼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伯爵的国际法顾问官,并全程参与了北洋舰队投降的谈判。②1913年3月,有贺被袁世凯聘为中华民国的法制顾问,以此为平台积极涉足中国内政。
有贺对议会政体抱有明显的疑虑,他认为中国这样具有君主制传统的国家,不宜马上实行共和制,至少应该把君主制与共和制融合起来。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保持秩序和进步”,才能“使新旧两种势力协调”。为此,他到北京后,第一个建议就是要求恢复祭天典礼。③
有贺依托明治维新创造“国民国家”的经验,进一步思考用何种方法助推作为“国民国家”的中华民国的构建。有贺强调:日本民族团结奋进的核心要素,是因为其拥有绵延悠长的皇统;而中国民族团结奋进的关键原因,则是其四千年同一文明的延续。④有贺虽然在此使用了“文明”一词,但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孔子之说。由此,有贺将中国的文明(孔教)和日本的皇室等量齐观,看作是国家存续、发展、繁荣之基础。
有贺高度颂扬孔教在支配国民精神、维系社会绵延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孔教)尊祖祀天,不言神秘甚密之义。而于人伦则至纤至悉,郑重周详,是故伦理者乃中国文明之精华,为西汉以来二千年间政教之基础,其浸润于国民意识甚深,其支配国民精神之力极大。”⑤这种观点,显然与康有为的构想极为合拍,康有为曾用“中国之魂”来高度颂扬孔教,在《孔教会杂志》的发刊词《孔教会序一》中,他这样写道:
今中国人所自以为中国者,岂徒谓禹域之山川、羲、轩之遗胄哉,岂非以中国有数千年之文明教化,有无量数之圣哲精英,孕之育之,可歌可泣,可乐可观,此乃中国之魂,而令人缠绵爱慕于中国者哉。有此缠绵爱慕之心,而后与中国结不解之缘,而后与中国死生存亡焉。⑥
用如此美丽词藻描绘的“中国之魂”,是对过去遗产的赞美,以及基于这点之上的民族同一性的强调。在康有为看来,这无疑是孔教的精髓。有贺和康有为均立足于挖掘传统资源,寻觅维系国家延续之纽带,可谓殊途同归。
不仅如此,有贺还非常看重孔教运动与“国家权力”的结合。他说:“居今而言保守,不但须将通国之中所有被服儒术,崇奉孔教者总为一团体,由国家公认而保护之,且于宪法特著明文,以此为国家风教大本。”⑦具体而言:第一,国家设立学校,以孔教为伦理教育之基础;第二,国家公认孔教学位(进士、举人、秀才等),作为选举及被选举之资格;第三,以国家公款维持孔教学校;第四,对孔子后裔表示特别之优遇。⑧
日本学者岛田虔次曾指出,民国初年的孔教运动,与“国家权力”密不可分:“从上而下通过孔教的统一,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官僚国家构想的产物,宗教在这里,从理念上而言,并不是与国家、政治不同单元的东西,而是深深植根于政府或行政的框架之中。民国以后,孔教运动很快就显示出顽固地与国家权力结合的倾向。”⑨
有贺对康有为诉诸政治、借助政权确立孔教国教地位的做法颇为赞赏。也正因为如此,康有为对有贺亦不吝赞美之辞:“日本博士有贺长雄之为宪法也,郑重发明中国与孔教之关系,以为不尊孔教则中国亡。乃吾国人而必反孔教也,何其识之出于有贺长雄下也!”⑩
有贺对推动中国的孔教运动不遗余力,但其目的绝非康有为赞誉的那般“纯粹”,他的出发点,无非是要将中国的改革进程纳入其构想的框架中,通过在中国打造日本式“国民国家”之翻版,为“神圣”天皇制背书,进而以这种方式进一步确立日本在东亚的主导地位。
与有贺的“力挺”相对照,服部宇之吉(1867—1939)、内藤湖南(1866—1934)等则对孔教运动持严厉的批判立场。
二、内藤湖南的视角
创设京都帝国大学“支那学”的内藤湖南,具有深厚的汉学修养和对现实中国的关切情怀。1909年,内藤就任京都大学东洋史专业教授,他汲取清代考据学之优点,侧重中国本位之学,其独特的时代划分方法影响甚大,被称为“内藤史学”。内藤一生曾9次到访中国, 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名流、著名学者如罗振玉、王国维、严复、郑孝胥、张元济等有过密切交流。
内藤对民国初年的孔教运动抱有浓厚的兴趣。1915年,内藤写下《支那论》,全面阐述了他对孔教运动的一些独特看法。内藤对支持和反对孔教运动的两大阵营了如指掌,他指出:“一时间孔教是否适合共和国的争论叠出,甚至还出现了废除孔教的极端议论。这种局面的出现,是针对近来要求孔教国教化、要将其载入宪法,并在政治会议咨询案中提出祭天、祀孔的一种反拨。”
不仅如此,内藤还以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为参照系,剖析了维新当时日本近代思想的发展历程:
维新当时的日本,热衷于汲取西洋文明的新知识、新思想,如星火燎原般破坏一切旧事物。这种局面维持约20年,之后出现了对抗局面,日本主义、保存国粹的呼声高涨,在教育方面带来的影响,便是推出了可以被认为是东洋伦理思想复活的教育敕语,家族制度、敬神爱国之说喧嚣至上。
内藤敏锐地捕捉到社会激烈转型时期“国粹”思想复活的不可避免性,并得出结论:在中国即便爆发了共和革命,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但短期内出现孔教的一时蠢动,也是一种历史之必然。
具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造诣的内藤,对孔教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充分肯定:“儒教令支那陷入今日衰弱之议论,从某种角度来说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是,尽管有那么一些弊病,儒教在长时间内维持了支那之道德,这是其必然之原因。如果从一开始儒教对支那的社会组织内部或对外没有一定的功效的话,那么,它断无延续至今日的道理。”内藤进一步指出:
孔教毫无疑问是中国伦理之根底,今日将其立为国教之议论,实在是没有必要。中国的其他宗教,譬如很早就流传下来的、与国民性融合的佛教,或者是与汉民族没有多大关系的回教、从中国人较低信仰中发展起来的道教,以及近代流入的天主教等,它们渐进推广自身而均未采取抵触儒教精神的对策。因此,今日即便没有将孔教正式树为国教,因为孔教的精神已经被公认为中国伦理的基础,虽然一时的革命对其产生一些疑问,孔教的尊严受到一点损伤,但其精神绝对不可能从中国国民的心目中消逝。
内藤要强调的是:孔教早已浸透于中国国民意识的根底深处,在中国,以孔教为基础的伦理本身,就是无所不在的普遍的东西。在这一视点之下,内藤对康有为推动孔教运动的手法,提出了严厉批评。
内藤如此突出这一点,也反映出他的一种忧虑:内藤对当时中国某些政客利用孔教,打着孔教复兴的幌子行“复辟”之举,抱有强烈的警戒心理。内藤曾这样点评袁世凯的“尊孔”举动:“袁世凯模仿皇帝,做出与共和国总统身份不相符的祭天虚礼,其真意是要利用孔子,实际上是在给孔子添乱。”从中也显示出内藤对中国现状的清醒认识。
三、服部宇之吉的视角
服部宇之吉是日本近代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曾担任东京帝国大学支那学讲座的主任教授,他曾三度前往中国。在中国的长期停留,对他的学问和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其健在的时候,服部就被誉为“现代的孔夫子”。服部本人也毫不掩饰对孔子教的倾心,公然“以孔子之徒自任”。
服部在1917年刊行的《孔子及孔子教》中,曾这样提到:“本书收录的10多篇论文,或者是阐述孔子人格的伟大,或者是探究中国人误解孔子教义的原因等,均是围绕阐明孔子教的真意而展开。”在《谈谈孔夫子》一书的结语中,服部又说:“作为孔子之徒,深入了解孔夫子人格与德教的精神与根本,以之修己之身,进而感化统领天下之人,乃当然之务。”
很显然,服部以“给予儒教以新生命而树立它在新时代的权威”为己任,他的研究具有针对性。他这样提到:
可以想像,儒教的真髓是孔子之教。可是,中国国内的这种真精神湮没已久,到现代,要么被误认为是三民主义而不得发扬,要么是被过激的欧化思想抹杀殆尽。相反,孔子之教在日本被很好地保存普及,成为日本国民建设卓越文化的力量。
正因为中国儒教的“真精神”早已埋没,所以服部要擎起复兴、弘扬孔子之教的大旗, 阐释对孔子之教的坚定信仰和儒教伦理的现代意义,从而走上了布道“日本孔教”的新征程。
基于此,服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孔子之教辨诬。服部断言,将孔子视为救世主的主张,本身就是一个诬妄,孔教绝非纯然的宗教。服部在《支那的孔子尊崇》中指出,中国参拜孔子庙的民众虽然不少,但看不到有香火供奉,以祈求现世和来世的幸福;从中可以发现,中国人面对神佛与面对孔子,采取的是截然迥异的态度。儒教基本上不会为现世利益而祈祷,中国人尊崇的是孔子的“伟大崇高的人格”,这种崇拜绝非宗教性的。
其次,服部严厉批评所谓“民主共和”之孔教及视孔子为革命主义者的孔教。在服部看来,从孔子的言行中,根本找不到有关民主共和的片言碎语。相反,无论从哪个方面观察,孔子在政治上均属君主政体的积极主张者,孔教与君主政体有着天然密切的关系。如果天真地向孔教求民主共和之根据,就如同缘木求鱼,不值一驳。
第三,服部对康有为提倡孔教的出发点提出异议。服部认为,清末中国社会的民心统一、国家的基本平稳,靠的就是孔子之教。如果没有这种重要的精神支撑,中国早已不可收拾。因此,服部强调:“中国之所以能够统一,乃是由于有孔子之教。”康有为提倡孔教国教化的主张,在服部看来完全是本末倒置。在这一点上,服部的看法和内藤湖南颇为一致。
服部强烈反对廉价利用孔子之教,反复表明维护其“纯洁”的迫切愿望:“中国是否存在孔子之教与吾人无关,唯假存之名而恣意牵强付会则为吾人所不能许,非鸣鼓以问诬圣人之罪不罢休。”
服部再三强调,他主张的“孔子教”,虽然与“孔教”只是一字之差,但日本的“孔子教”,在精神实质上与中国的“孔教”有着巨大差别:“孔教会的信徒主张:如果不能确立作为宗教家的孔子,那么就无法发现孔子的伟大……吾等虽然认为孔子教是建立在宗教信念之上,但其绝非宗教。在这一点上的见解与孔教会的信徒截然不同。”
四、日本的“天职”与“天命”
面对民国初年的孔教运动,无论是持赞同立场的有贺长雄,还是持反对意见的内藤湖南、服部宇之吉,尽管他们解读的路径有所不同,但所持的价值取向可谓惊人地相似。他们一致主张,日本在崭新的高度上综合了东西文明,孔子之教已融入日本的国体之中,成为日本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自豪地宣称:东亚文明的中心已经从中国转向日本,儒教的振兴是日本学者责无旁贷的崇高使命。
有贺虽然支持中国的孔教运动,但他并不认为这场运动纯粹源自中国内部,它需要外力的强势推动;而这种外力,无非就是日本的“国民体验”。当有贺以此为标杆衡量中国改革的成功与否时,注定了他是站在“指导者”的立场之上,自上而下地指点中国的发展进程,在他的潜意识深处,已深深植入了“日本新文明”与“中华旧文明”的两极对立;当有贺拿出日本的“范本”,要求中国在这一框架之下推动变革,以所谓进取的新文明来警醒落后的旧文明时,他实际上已成为“一支地道的保证日本对华政策实施的‘海外特殊部队’的一员,扮演着为帝国的‘亚洲雄飞’效犬马之劳的角色”。
有贺在推销“日本经验”方面不遗余力,但他没有公开宣布“日本新文明”替代“中华旧文明”的时间表,在这方面内藤与服部走得更远。
内藤在《东洋文化史研究》中,以“文化中心移动说”立论,公然宣称:“正如文化中心从黄河流域迁移到江南一样,在现代,文化中心移到了日本,故应将以日本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作为新的中国文化加以酝酿。”在此基础之上,内藤阐述了著名的“日本的天职说”:
日本的天职就是日本的天职,它不在于中介西洋文明,传之于支那,使其在东洋弘广,也不在于保全支那的旧物,售之于西洋,而在于使我日本的文明,日本的趣味,风靡天下,光被坤舆。我国为东洋之国,而东洋诸国以支那为最大,故欲为之,不得不以支那为主。
1894年11月,在中日甲午战争激战正酣之际,内藤又发表了《日本的天职与学者》一文,进一步论述“文化中心移动说”的相关理论及“日本的天职”、“学者的使命”。内藤强调,日本文化曾经依托于中国,但发展至今日,是咀嚼、消化、吸收西欧及外来文化,站在新的高度而集大成。值此战事大进之时, 值此日本的“ 威力” 、“ 国民之意气”空前勃兴之今日,日本将“成就东方之新极致,以取代欧洲而兴起,新的坤舆文明(世界文明)之中心,岂不在反掌之间耳”。在内藤看来,致力于打造与“坤舆文明”相匹配的新学术,便成为日本的“天职”和日本学者的“使命”。
与内藤的“天职”说如出一辙的,是服部倡导的“天命”说。服部认为,孔子一生的经历,乃是本于对天命的自信;孔子从事社会活动的原动力,归结于知天命畏天命。他强调,现代西洋哲学家关于精神生活的种种所谓新说,都不出孔子的天命信念之外,不出论语之外,了无新意,只不过是用语不同而已。那么,这个“天命”又是什么呢?在服部看来,它不是苍茫不测的天穹,而是一种现实的意志力量。对日本来说,所谓的“天命”,便是亘古不变的皇统意志。
服部对孔子知“天命”的解说,目的是为了激发“日本的天命”意识,并引申出自身对日本所肩负的特殊“天命”的自信。服部认为,中国儒教的衰败,是一种文化的宿命,但同时也是一种机遇,它赋予了日本一种神圣的“天命”。服部表示:“日本用东西文明融会的新文明使东洋的天地打成一片,进而横扫世界,让世界人类都沐浴这种新文明的恩泽。”
孔子的“知天命”如何导引出日本的“天命”意识,服部并未给出答案。如果说,康有为提倡孔教是为了整合国民精神,那么,服部倡导的“孔子教”则是为了赋予日本一种神圣的文化使命。为此,子安宣邦认为,如果说,康有为的孔教国教论是对近代国家日本的回应,那么,服部的孔子教论则是近代天皇制国家日本对于中国孔教论的再回应。
五、结论
无论是支持孔教运动的有贺长雄,还是持反对意见的内藤湖南、服部宇之吉,他们均对中国有着直接的感性认识,并近距离地体验过孔教运动的盛况,在以下几个方面,他们的立场是基本一致的:
第一,高度认可孔教在中国国民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有贺支持孔教运动,是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孔教思想是国家团结、统合的坚实基础,这种文明必须通过孔教运动予以继承、光大。而反对孔教运动的内藤、服部,则从贯穿中国历史的孔子尊崇的风潮中,捕捉到儒教确保中国一统这一基本事实,因此,他们主张,孔教已经潜移默化地浸透到中国民众的思想深处,早已成为中国社会传统伦理的基底,没有必要进一步国教化。双方殊途同归,共同将孔教与国家统合之命运紧密相联。
第二,与第一点相关联,是对康有为提倡孔教的动机均表现出一定的理解。岛田虔次曾这样分析康有为提倡孔教的动机:“康有为是希望在中华民国推行孔教,强化精神的纽带,促进精神的振兴,进而将一盘散沙的民众汇聚在一起,形成国民的强固统一。”在康有为看来,只有立孔教为国教,才能保存和发扬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重铸民族精神。对于康有为利用政治手段推动孔教运动的做法,这些思想家的评价有所不同,但对康有为仿效明治日本的宗教改革经验、积极推动“国民国家”建设这一基本思路,总体上还是予以肯定的。
第三,近代日本的崛起,令日本近代思想家的自信心空前膨胀,要摆脱长期以来中国儒学及近代西学对日本的“文化殖民”,确立“兴亚抗欧”的话语系统,实现“文化自主自立”。但这种崛起的话语系统,也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一方面,中国作为“落伍”的亚洲代表,必然成为日本排斥的主要对象;但另一方面,中国又是日本自我身份认知的重要一环,是其难以排斥的依赖对象。由此,在日本的近代化自我想像之中,中国永远是一个难解的死结。
近代日本思想家只能在“中华旧文明”的背景之下,寻觅其表述“当代”的思想材料,并在“重新阐释”这些思想材料的过程中,重新创造自身的“历史”。在他们充满霸气、自负的话语系统中,我们既可以感受到其渴望创造“历史”的冲动,又可感受到其力不从心的焦灼感。
虽然这些思想家对中国的孔教运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他们的最终着眼点,是要为近代日本的崛起寻求合法性依据,寻求话语主导权。因此,他们眼中的孔子之教,已经不再是中国专有的儒家核心价值,而是变成了日本主导之下东亚国际秩序核心理念的代名词。以日本精神同化中华文明,重新打造作为人类导师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孔子像,并令之开出远远超越本土的绚丽花朵,最终实现文化中心向日本的转移——正是这份优越意识和自负心,令他们带着居高临下的姿态,毫无顾忌地点评中国的思想变迁及内政。这种研究取向,也注定了他们难以进入中国近代思想的深层,理解和把握风云变幻时期中国知识阶层特有的思想苦闷和彷徨。
注释:
①子安宣邦:《近代中国、日本和孔子教——孔教国教化问题与中国认识》(《近代中国と日本と孔子教─孔教国教化問題と中国認識》),《环》(总第12号),东京:藤原书店, 2003年1月,第460-477页。
②刘恩格、于时化译:《日清战争实记选译》,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8册),中华书局,1994年,第270-277页。
③李宗一:《袁世凯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第266页。
④有贺长雄:《文学论》(1885年前后),有贺长雄:《支那正观》,东京:外交时报社,1918年,第2页。
⑤有贺长雄:《宪法须规定明文以孔教为国家风教大本》,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0辑(498),台北:文海出版社,第5094页。
⑥康有为:《孔教会序其一》,《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2号),1912年,第2-3页。
⑦有贺长雄:《宪法须规定明文以孔教为国家风教大本》,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0辑(498),第5094页。
⑧同上,第5098页。
⑨岛田虔次:《辛亥革命时期的孔子问题》(《辛亥革命期の孔子問題》),小野川秀美、岛田虔次编:《辛亥革命的研究》(《辛亥革命の研究》),东京:筑摩书房,1978年,第11页。
⑩康有为:《乱后罪言》(1913年11月),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全二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9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