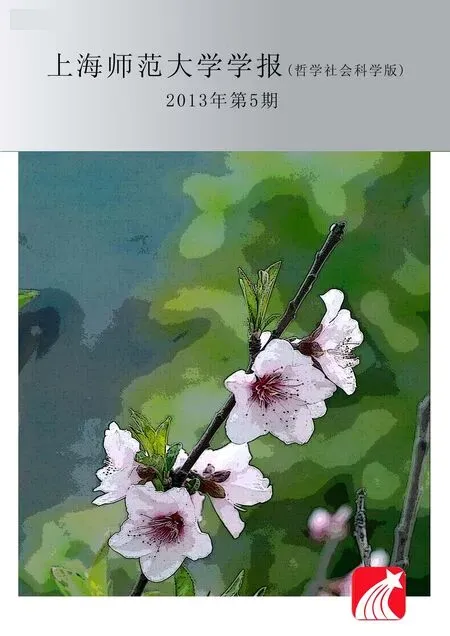繁兴与畸变:清末民初古文小说发展论略
2013-04-11庄逸云
庄逸云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一
古文小说是中国文言小说的一个重要门类,肇始于唐代的古文运动。此后,古文小说的发展或隐或显,但其延绵之势一直持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关于这一颇为特殊的小说文体,已有不少学者予以关注。如蒋凡在《韩愈柳宗元的古文“小说”观》一文中,专论韩、柳的古文小说观及其创作实践。[1](P57~63)陈平原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里,辟有一节专门探讨清末民初的古文小说与骈文小说。[2](P175~184)不过,这些学者在谈及古文小说的概念时,仍有语焉不详之嫌。古文小说的内涵及外延,仍是较为模糊的。
那么,什么是古文小说呢?古文小说,简言之,就是以古文写成的小说。古文小说除了在语言上具备奇句单行、不事骈偶的特点之外,还得渗透古文的意趣与笔法,如小说的内容与道统相关、艺术上留意于“规模、繁简、提挈顿挫”等法度。在古文小说的判定上,有几点必须厘清:其一,古文虽与骈文相对,但并非所有奇句单行的文字都可称之为古文。同理,也不是只要用了散体文言写成的小说都可归为古文小说。语言上的奇句单行只是构成古文小说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其二,并不是只要采用了古文笔法的小说就是古文小说。中国的文言小说本身就与史传文学有纠缠不清的关系,小说受正统文学的影响势所难免。譬如《聊斋志异》,多处化用古文笔法,冯镇峦甚至将其视为古文的范本,与《左传》相提并论。[3](P541)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聊斋》即是古文小说。古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秉承了“文以传道”的古文道统观,在题材内容方面虽不至于“本经术而依事物之理”,却几乎不会专门描写爱情及神怪故事。其三,古文小说的产生,是在小说文体臻于成熟之时。文人在创作古文小说时,对小说及古文两种文体皆有较明确的认识。唐以前的诸子及史传散文不乏小说的因子,但并不能将《史记》里的《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篇目等同为古文小说。其四,古文小说虽带上了古文的烙印,但其核心仍是“小说”。它并不排斥幻设为文的艺术虚构,且常于细节描写及氛围铺陈处,施之以藻绘与点染,注入小说家的想像力。在结构的安排上,古文小说也往往矜尚新异。
中唐韩愈、柳宗元行以古文笔法写成的《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童区寄传》、《李赤传》等文,堪称小说史上的第一批古文小说。其后,一直有文人出入于古文与小说之间,写作了不少古文小说。苏轼的《万石君罗文传》、《方山子传》等可谓古文小说的佳作,其《僧圆泽传》更是直接以古文笔法改写唐传奇名篇而成。古文小说发展至清初,掀起了一波小高潮。彼时小说繁兴,受其影响,不少作家好以小说为古文辞。魏禧的《大铁椎传》、侯方域的《马伶传》、王猷定的《汤琵琶传》等文,乃斯时古文小说的代表作。不过,自唐迄清,古文小说的发展虽脉络不断,但它常被目为野狐歪道,几乎每一次的集中出现,皆会招致抨击或引发争议。到了清末民初,世易时移,社会及文化环境大变,因获得了正面的倡导,古文小说的发展竟蔚为大观,成为当时小说界的重要现象。可以说,清末民初既是古文小说发展的最后一期,也是最为繁盛的一期。
二
古文小说在清末民初的发展大致以1912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12年之前,古文小说的创作尚未形成气候。此时期的古文小说以翻译小说为主,其代表作家当首推林纾。林纾在翻译西方小说时,“遣词缀句,胎息史汉”,使“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样大的成绩”。[4](P215)林纾翻译的社会小说与政治小说如《黑奴吁天录》、《爱国二童子传》等,皆可视为古文小说。1912年至1917年是古文小说在清末民初发展的第二阶段。1912年4月,《小说月报》从第三卷起改由恽铁樵担任主编,自此,古文小说获得了最重要的发表阵地,其发展呈现出空前的繁盛之姿。《小说月报》、《中华小说界》等刊物推出了恽铁樵、钱基博、江山渊、王梅癯、程善之等古文小说家及大量创作类的古文小说。小说界的巨擘林纾在辛亥革命后亦投入到古文小说的创作,出版了《剑腥录》、《金陵秋》、《巾帼阳秋》等长篇小说及《践卓翁小说》、《铁笛亭琐记》、《林琴南笔记》等小说集。
古文小说之所以在清末民初时期繁兴,原因是多方面的。古文小说是古文与小说交互渗透的产物。古文小说每一次的集中出现,皆与小说的兴起或繁盛有关。清末民初,小说大盛,且一度被梁启超鼓吹为“文学之最上乘”。不过,真正能认同此观念的人不算太多,大家充其量承认小说在改变世道人心方面,有“不可思议之力”,可用以启迪青年或愚氓,若就审美层面而言,小说依然未能与传统的雅文学等量齐观。在此情形下,古文小说获得不少文人的青睐,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小说文体与传统的雅文学最为接近。写作古文小说,既可满足人们眷念雅文学的心理,又可迎合市场对于小说的旺盛需求。还有一种情况是,有部分文人虽不至于认为小说是“文学之最上乘”,但也视小说为文学之一种,所谓“欧人以小说与文学并为一谈,故小说家颇为社会所注意”。[5](P530)基于此,他们好将古文嫁接在小说的枝干上,以此来赋予小说的雅文学色彩,从而提升小说的地位,实现启蒙社会的目的。除了这两种情形,古文小说在清末民初的兴盛,还离不开两个更为具体和重要的因素。
1.国粹思潮的影响
林纾在1901年还劝告读者不要对西方小说抱有成见:“有志西学者,勿遽贬西书,谓其文境不如中国也。”[6](P43)这说明直至此时,虽然遭受了政治、军事上的多次重创,但国人至少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传统文化还是颇具信心的。但很快,这种信心开始消退,一种对西方文化的“艳羡心理”、一种趋新尚西的风气逐渐在社会蔓延。知识阶层对此深表忧虑,基于反思现状与建构文化的需要,知识阶层开始倡导保存国粹。自1905年国粹学派创立《国粹学报》开始,保存国粹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尤其是在进入民国后的最初几年里,在官方推行的文化复古政策的裹挟下,保存国粹的号召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所拥护,“国粹”一词几乎成为流行语。小说界亦受到这一风潮的影响,不少作家纷纷视保护国粹为己任。如上海进步书局的主笔蒋景缄在其小说《身外身》中哀叹时人“忘固有之国粹”,声称政体和科技等都可以向西方借鉴,“唯论及文艺,则断不能舍长从短,受人转移”。[7](P75)亚东破佛创作小说《闺中剑》,亦自称“将藉为开发民智,挽救时弊,保存国粹之具”。[8]
包括古文在内的文言文学作为国粹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在保存和保护之列。为了实现弘扬国文的目的,文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了与古文关系密切的小说。小说这一文体在当时虽还未跻身于雅文学之列,但它的影响毕竟在日益扩大,已成为市民读者最喜欢的文体,这一点毋庸置疑。既然小说与古文中的“传”、“记”之文不无相通之处,那么通过流行的小说来提高国文的影响力亦是合理可行的事情。吴曾祺就认为可以借小说来窥探古文的奥妙,所谓“余窃以窥古文之秘者,莫此为近”,所以他择取说部诸书,编选了一部《旧小说》,“将以是为学文之助云尔”。[9]持有类似观点且进行大力鼓吹的还有恽铁樵,他提出:“今之小说,责以通俗教育,诚谦让未遑;若谓初学借小说以通文理,则为世所公认。故小说可谓作文辅助教科书。”[10](P534)总之,以古文写小说,原本符合文人的积习和审美心理,在国粹思潮的影响下,创作古文小说竟至上升为部分文人的自觉意识和社会责任,这极大地促进了古文小说的发展。
2.骈文小说的刺激
在清末民初尤其是民初的小说界,骈文小说大受欢迎。如《玉梨魂》一书,“出版两年以还,行销达两万以上”,[11]堪称民国时期最为畅销的小说之一。1914年,骈文小说专门的发表阵地《小说丛报》、《小说新报》、《民权素》纷纷创刊,此时骈文小说的繁盛达到顶点。对于骈文小说的风行,以恽铁樵为代表的古文小说作者颇为不满,屡屡提出批评。他们从多个角度论证了骈文虽为“中国文学上之一部分国粹,然断不可施之小说”。首先,骈文小说“多用风云月露花鸟绮罗等字样,须知此种字样有时而穷”,“何况僻典非小说所宜,雅言不能状琐屑事物”。其次,文章应以意胜,骈文小说“不言其理,徒讲藻饰,此与搬弄新名词者何异?宜其味同嚼蜡也”。他还引用了当时流行的进化论来推断骈文小说的命运:“若夫词章之专以雕琢为工,而连篇累牍无甚命意者,吾敢昌言曰:就适者生存之公例言之,必归淘汰;且淘汰而后,于中国文学上丝毫无损。”[12](P520~521)古文小说的作者又从理论上揄扬古文小说的价值:“修辞学之原则有三:曰理,曰力,曰美。头头是道,有条不紊,是之谓理,吾国古文家所谓提挈剪裁近之。……理为第一步,力为第二步,美为第三步。有其一无其二与三,不过程度问题;舍其一用其二与三,则皮之不存,毛将安附?此固非言小说,然小说不能离文学独立,宁得背修辞之公例?”[10](P533)据此观点,古文成了实现小说之审美价值的重要前提,至于八股家与辞章家,皆与修辞公例背道而驰,甚至“普通一般苟中八股、辞章之毒,终身不能文可也”。[10](P534)配合这种理论上的攻势,恽铁樵将《小说月报》发展成了刊载古文小说的重要阵地,他甚至针对骈文小说一味炮制哀情的现象,提出了“言情小说撰不如译”的口号,拒绝在《小说月报》里刊载写情小说。
骈文小说的确流弊甚多,但它在民初拥有十分广大的读者市场,这是不争的事实。正是骈文小说这种浩大的发展声势,激发了古文小说家们的危机意识,使得他们在理论和创作上都愈发倡导古文小说。
三
清末民初的古文小说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走向,产生了两类风貌迥异的作品:一类作品在题材、主题或叙事模式上趋向新变;一类作品则在意趣及写法上秉承了传统。这两类作品皆不乏佳篇杰作,共同为小说的现代转型作出了贡献。
1.趋向新变的作品
在叙事模式上进行一些翻新尝试,这是清末民初小说的常态,古文小说也不例外。例如林纾的《金陵秋》以对话开篇,形成一起之突兀的效果,就有异于传统的纪传体例。当然,正如茅盾所批评的那样,许多小说只是“采取西洋短篇小说里显而易见的一点特别布局法而已”。[13](P230)不过,当时也有少数作品在题材、主题及叙事模式上均能打破常规,体现出强烈的开创性。在这一点上,古文小说走在了骈文小说的前面。可以说,清末民初时期最具实验性、先锋性的小说正是由古文小说所奉献的。其中,恽铁樵的《村老妪》、《工人小史》、鲁迅的《怀旧》、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等堪称佼佼者。
《村老妪》(《小说月报》第3卷第10号)通过写一乡村老妇人的生活片断,来反映民初“民主政治”的推行状况,即所谓的民主选举既已为别有用心者所利用而发生变质,民主举措本身所蕴涵的精神更是远未为普通民众理解。《怀旧》(《小说月报》第4卷第1号)则写一乡村幼童的生活点滴,作品重点刻画了在疑似“长毛”造反的传闻中,乡村各色人等的反应。数十个难民涌入“何墟”,众人以为是又一次“长毛”造反,遂陷入了慌乱中。尤其是乡绅、塾师等惶惶不安,纷纷计划逃亡。对于那些一穷二白的普通乡民而言,他们也回忆起了曾经发生过的“长毛”叛乱,不过在他们眼里,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仅仅成了饭余茶后的谈资,革命留下的仅仅是惊险曲折的故事而已。《工人小史》(《小说月报》第4卷第7号)算得上是表现产业工人的生存境遇的开山之作,小说并无完整和连贯的情节,通篇由上海某厂工人韩蘖人的工作和生活琐事构成。小说为产业工人的生活提供了一幅真实的写生画卷,控诉了阶级压迫与社会不公。这几篇小说通过如实描述普通人的生活,深刻地反省着社会的发展方向,作品呈现出“普遍与真挚”的基调,可谓周作人所倡导的“平民文学”的先声。《断鸿零雁记》虽为写情小说,但并非专门描写爱情的作品,它以第一人称自叙的口吻,细致地展现了一个方外之人的情感世界;又以极细腻的笔墨刻画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孤独者形象,主人公具有强烈的被遗弃感和悲剧性的存在意识。“这种对存在的悲剧性感受——在旧的文学中发展很不充分,甚至完全没有——实际上是现代艺术的一个突出的特征。”[14](P2~3)
上述小说在写法上完全突破了古文中“记”、“传”之文的体例,在精神内核上则颇具现代小说的色彩。不过,这些作品仍保留了“古文”的风貌:首先,小说所体现出的关注社会与现实人生的意识与文以载道的古文传统不无相通之处。其次,就语言风格而言,这些作品秉承了古文家法,学古之迹清晰可辨。恽铁樵和鲁迅宗法魏晋文章,文字略显古奥奇崛;苏曼殊虽被钱基博列为魏晋文家,但其小说清新流畅,颇得宋人散文之壸奥。
2.秉承传统的作品
所谓“秉承传统”,指在叙事体例上严格遵循古文叙事惯用的纪传体或纪事本末体,在审美风格上亦唯传统的古文宗派或古文家是尚。据其宗法对象的不同及由此带来的题材、风格上的差异,秉承传统的古文小说又出现了两大类别:一类以左、马、班、韩的史传文为典范,为义士或奇人立传,追求“惊异”、“传奇”的审美效果,代表作家有江山渊、林纾等。另一类则有赖于归有光散文的直接影响,着重叙写家庭琐事或婚姻生活,多以朴实平淡为美。
江山渊对司马迁的《史记》推崇备至,谓“《史记》一书,为史家正宗,而龙门文笔亦敻绝千载,言古文者多宗之”。[15]其小说深受《史记》的影响,风格沉雄壮丽,颇具阳刚之美。他多写忠臣、义士、孝子、畸人,这些人物往往儒而侠,颇具狂狷气质;对于环境及关键的细节、场景,他不惜以浓墨敷衍,不复保持史家的克制。如他的《王延善》(《小说月报》第6卷第1号)一文,写王延善父子四人,起兵抗清,不屈不挠,在王延善被俘后,其子余恪、余严欲以身殉父,于是一路跋涉,远赴燕都。作者于路上的情景有颇多的渲染。他的另一篇作品《死荣生哀》(《小说月报》第8卷第3号)则通过写蜑户出身的“陈某”的戏剧性一生,表达了个人被历史的偶然因素摆布所带来的荒谬感和悲剧感,作者在环境描写上铺陈了大量的笔墨。林纾是古文大家,在小说创作中会有意识地贯彻古文笔法。其小说集《技击余闻》就被钱基博评价为“叙事简劲,有似承祚《三国》”。[16]在《畏庐漫录》、《林琴南笔记》、《铁笛亭琐记》里,也收录了多篇古文小说。如《巢香》、《崔影》两篇皆以辛亥革命风潮为背景,前者写为满清殉难的旗人女子,后者写为推翻满清而牺牲的一对青年男女。作者表彰节、义的思想渗透于字里行间,笔法则兼得古文与小说两者之趣。又如《余渊》一文,是为在甲午海战中殉难的平民英雄立传。作者十分讲究结构布局之“章法”,开篇伊始便写余渊预知甲午海事“必败”,接下来写战争过程则聚焦于清军用人不当、设备不全及军队不和、缺乏沟通,处处皆以“必败”为内核。全篇的叙事夭矫曲折而条贯分明。同时作者又在开篇大肆铺陈余渊奔赴战场前与妻子的离别情景,用笔细腻而深情,呈现出鲜明的小说意味。江山渊、林纾的这类作品既注重表彰忠孝节义等传统道德,又追求“惊异”、“传奇”的审美效果,实则构成了传奇小说的一种变格,即古文体传奇。以唐传奇为代表的传奇自然是传奇小说的正格,它们书写爱情、豪侠或神怪等无关宏旨的浪漫人生,注重想像与虚构,叙述婉曲,文辞华艳,有研究者称这类传奇为“辞章化传奇”。[17](P183)古文体传奇则仍以“载道”、“劝谕”为根本,所写之人大都是有裨于风教的历史英雄、先贤、耆旧、孝子、高士、烈女。叙事虽亦委曲,文辞则不尚“华艳”。
在归有光的散文中,有较多描写家庭生活、回忆家人的作品,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思子亭记》、《女如兰圹志》、《女二二圹志》、《寒花葬志》等。清末民初有不少文人奉归有光的散文为圭臬,如赵绂章谈到:“往读震川《思子亭记》,俯仰夷犹,惋怆欲绝。虽由文诣之高,亦缘至性为文,语语有血泪在。与作意矜饰者,固自有别。盖文章之极轨,固未有不本于诚者也”。[18]受归有光散文的影响,清末民初出现了不少叙写家庭或婚姻生活的作品,如《尘海因缘史》(《小说月报》第4卷12号)、《眉楼忆语》(《小说月报》第5卷第1号)、《回首》(《小说月报》第6卷第1号)、《浮生四幻》(《小说月报》第6卷第5号)、《兄弟孔怀》(《小说月报》第7卷第3号)等。这些作品既脱胎于归有光的散文,又吸收了一些新鲜元素。因为它们大都本以个体的真实生活,且采用第一人称,所以算得上是较早的一批自叙传小说。署名为浪子的两篇作品《回首》与《兄弟孔怀》,前者追忆年少时的家庭生活,包括父母龃龉乃至反目、家庭经济困顿、母亲轧棉为生等;后者则是作者回忆其兄长们的生前事迹,尤为详细地叙述了长兄为求生而辗转流离,最后不幸死于匪乱的凄凉一生。作品采用白描,不事雕琢,风格极为朴素自然,与归有光散文近似。不同的是,作品表现的是下层人士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的命运,并无归氏散文特有的宁静优雅的格调。此外,作品多在闲漫纤碎之处动色而陈,体现出明显的小说特质,异于归氏散文的高洁。以下是《回首》中作者陪同母亲清晨出门购买棉花的一段描写,据此可管窥作品的面貌:
鸡初鸣,母已起。以惜油故,不燃灯,暗中摸索梳头毕,始呼余起,“新、新,起来”,余陡从梦中惊觉。新者,余小字也。顾余虽醒,犹恋恋床褥不遽起,母屡趋之始起。母乃自往厨下烧汤,顷之,汤热,余衣已着毕。母及余盥洗已,余方出室门,而余之犬已立前扑余身,忽左忽右,忽前忽后,时或吮余之手,若甚欢迎主人早起者。余不胜其嬲,则叱去之。母又隔窗呼姐起,曰:“吾等将往西关买棉,汝其速起关门者。”于是吾姐亦起,摒挡既毕,母及余拔关出,姊从内阖之。门既阖,母复呼姐曰:“天尚早,汝宜更眠片时,养息精神,俾日中好轧棉也。”姊从门内应之曰:“诺。”[19]
上述两类小说,皆以仿效古文经典为旨归,并不追求叙事模式上的翻新,因而透露出较为浓郁的复古气息。但前一类小说(古文体传奇)着意于谋篇布局和语言的打磨,所以不少作品的文字奕奕有生气,相较于一些刻意求新、急就章式的小说,反倒更具艺术的魅力。后一类小说初步呈显了自叙传小说的特质,它们大都以个体的真实生活为原型,抒发的是一种真诚的忏悔意识或怀旧情绪,格调迥异于民初那些矫情做作的写情小说,为小说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20](P150~153)
四
自民国三年(1914)开始,古文小说的发展出现了一种新的倾向:即小说逐渐向古文靠拢,最后小说的文体特征竟至模糊,所谓的“小说”变得完全趋同于古文。1914年至1916年是骈文小说大行其道的时候,而这几年间的《小说月报》(即第5卷、6卷、7卷)所载的不少古文小说已与古文无甚差异。如第5卷第1号刊载了卧园原著、铁樵校订的《罂花碧血记》,作品写民国成立之初,禁烟令虽下达,但某些官吏为自身利益,鼓动乡民种烟之事。作者在篇首提出:“事属身经,语皆纪实,特无涂泽无附会,微嫌视时下流行小说,体裁不类。然吾闻之,小说者所以补史乘之缺,供参考昭鉴戒者也。训道不纯,愚民陷焉,得是篇为之讼冤,肉食者安所辞。”这种对纪实和载道的双重强调其实与人们对古文的要求并无二致。又如第6卷第11号载有江子厚的《方孝娥》,该文写一贞洁、孝烈的女子,备受虐待而毫无怨尤;文章旨在训诫,叙事直质、不事敷衍,与正史里的“节妇传”无异。同一期里一厂所撰的《记刘傅两节妇事》亦复如此。除了江子厚、一厂,这几卷的《小说月报》还发表了程善之、王梅癯的文字多篇,这些作品皆意存劝诫、粗陈梗概,绝不在细节处刻意摹写,实在算不上是小说。
这种现象的产生首先与古文小说的文体特质和作者的身份认同有关。古文的意趣与笔法是古文小说的重要构成要素,所以古文小说与古文天然地存在着纠缠不清的关系,两者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在中唐与清初,写作古文小说的几乎都是古文家,到了清末民初,写古文小说者虽活跃于小说界,但他们仍兼有古文家的身份,甚至他们更愿意首先以古文家自居。这种身份认同使得他们在创作小说时,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古文倾斜,从而强化古文小说的“古文”特质。
这种现象的产生也与恽铁樵的有意倡导不无关系。恽铁樵本人创作过质量上乘的小说,也翻译过西方小说如《豆蔻葩》、《波痕荑因》等,他对小说的文体性质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曾提出:“小说之为物,不出幻想。若记事实,即是别裁。然虽幻想,而作用弥大,盖能现世界于一粟,不徒造楼阁于空中。”[5](P530)既认识到小说的特质在于幻想,又强调以幻想来观照、反映现实,这无疑是一种相当成熟的小说观。但与此同时,对于“记事实”这种小说“别裁”性质的文类,恽铁樵却越来越偏爱,自第5卷起,《小说月报》所发表的趋同于古文的作品日渐增多,刊物的栏目分类标准和称谓也一直在进行调整。自第8卷第1号起,《小说月报》的栏目分类调整为寓言、记事、文苑、杂俎等,恽铁樵在《编辑余谈》中申述了他的分类标准及最近的小说观:“凡记琐事之一则,无论其事属里巷与闺阁廊庙或宫闱,要之,非正面发挥政治学术之大者,皆小说也……兹于向所谓长短篇小说者名曰寓言,明此为设事惩劝,非可据为典实者也。向之名掌故瀛谈者,统言之曰记事,明此为有本而言,非信口雌黄、淆乱黑白者也。此全卷之正文页,犹未足以尽小说之范围。另辟一栏曰杂俎,凡关夫小说考据,与夫零缣断素之小品文属之。”[21]恽铁樵将“非可据为典实”的虚构之文、“有本而言”的记事之文及零缣断素的小品文皆视为小说,并再次重申小说与古文并无明确的界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恽氏之前将“记事实”的文字视为小说之“别裁”,此时则不再提“别裁”这一说法,而是将“有本而言”的记事之文列入“全卷之正文页”,与虚构之文同等。
并非不明白小说为何物的恽铁樵持有这种看似保守甚至“倒退”的小说观,不过是欲藉此与当时风行的骈文小说分庭抗礼而已。骈文小说在1914年后大盛,对此,恽铁樵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提倡小说的纪实和载道功能、强化《小说月报》的古文化色彩,诸种举措皆是针对骈文小说以情言绮语饷食青年的现象。不过,恽铁樵显然有些矫枉过正了,他本应该倡导如《工人小史》、《村老妪》、《怀旧》那样的写实小说,而不是“有本而言”的记事之文。对古文传统的过度眷念使恽铁樵等人在小说与古文两者之间游移时,最终仍然偏向了古文,这也使得古文小说的发展走向了死胡同。以古文的创作标准来观照小说,并非全然不合理,某些古文义法的确可资小说借鉴,但过犹不及,若过分强调小说向古文靠拢甚至泯灭两者的界限,自然不利于小说的正常发展。
[1] 蒋凡.韩愈、柳宗元的古文“小说”观[J].学术月刊,1993,(12).
[2]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3] 冯镇峦.读聊斋杂说[A].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4]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A].胡适.胡适文集(3)[C].欧阳哲生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 恽铁樵.作者七人序[A].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6] 林纾.黑奴吁天录例言[A].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7] 蒋景缄.身外身[M].上海:上海进步书局,1916.
[8] 儒冠和尚.读闺中剑书后[A].亚东破佛.闺中剑[C].上海:破佛发行、小说林代印及分售,1907.
[9] 吴曾祺.旧小说叙[A].吴曾祺.旧小说(甲集)[C].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
[10] 恽铁樵.论言情小说撰不如译[A].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1] 徐枕亚.枕亚启事[J].小说丛报,1915,(16).
[12] 恽铁樵.答刘幼新论言情小说书[A].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3] 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A].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4] 普实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15] 江山渊.省保斋文话[J].小说新报,1915,1(1).
[16] 钱基博.技击余闻补[J].小说月报,1914,5(1).
[17] 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18] 赵绂章.浮生四幻[J].小说月报,1915,6(5).
[19] 浪子.回首[J].小说月报,1915,6(1).
[20] 庄逸云.清末民初的自叙传小说[J].当代文坛,2008,(4).
[21] 恽铁樵.编辑余谈[J].小说月报,1917,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