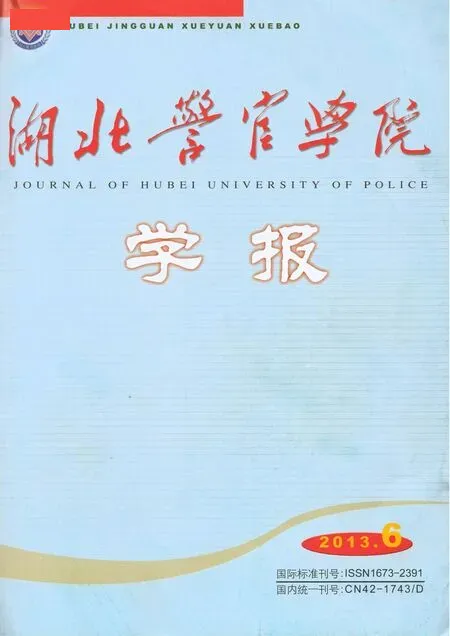人寿保险合同自杀条款研究
2013-04-11邬学成
邬学成
(上海大学 法学院,上海200444)
一、自杀条款的定义及其产生的理论基础
(一)自杀条款的定义
现代意义上的自杀条款一般都出现在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中,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后的一定时期内自杀,保险人将不承担保险责任。
各国人寿保险契约立法中都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规范“被保险人自杀致死”和“保险人给付义务”的关系?其原因在于,人寿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生命健康为标的的保险,自杀是导致被保险人死亡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一般传统观点认为自杀行为是被保险人可以控制的。矛盾因此而产生。
(二)自杀免责条款产生的理论基础
18世纪的欧洲受宗教影响,“自杀即是犯罪”的观念笼罩着整个社会。这种观念相当于法律,或者说各个国家以此观念制定了相关的禁止自杀法,在规定了自杀是犯罪行为的同时,还宣布了对自杀人尊严的冒渎、财产的没收之类诸多刑罚规范。
到了19世纪,“自杀即是犯罪”的观念虽然被肃清,但继而又引发了“危险发生不确定性”的理论争论。简言之,自杀是行为人自己可以控制的,而保险技术性却要求保险事故是因偶然性事件所致且在被保险人可控能力之外的,因此,保险人对于自杀导致死亡的情形还是绝对地免责的。
直到20世纪,有美国学者提出了“基于人寿保险的目的,应将自杀列入可保范围”的观点,即“目的说”。这种观点认为,基于公序良俗的角度,保护被保险人死亡时遗留的、缺乏生活保障的受扶养家属是人寿保险契约的基本目的。基于此,认为自杀是完全可保的。同时,美国学者在实务中发现,保险公司人寿保险保险费率的计算,所依据的死亡率的计算是将自杀导致的死亡因素完全包含进去的。
“危险发生不确定性”和“目的说”两种理论各具充分的的理由支持各自观点,这两种观点的冲突实质上反映了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利益就成为了焦点。在20世纪后半叶美国法院审理的“里特诉美国人寿保险公司(Ritter v.Mutual Life Insurance U.S)案”中找到了“折中点”。案中提到的“法律或保险单得规定自杀发生于保险契约生效经过一定期间后,始在承保范围内,以示抑制。”就是平衡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利益的“折中点”,是自杀免责条款的理论基础来源及自杀免责期间制度的雏形。
二、自杀免责期间适用的合理性
根据我国《保险法》第44条第1款的规定,自杀免责期间为2年。那么,本文所讨论的自杀免责期间适用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哪方面?在我国,认为人寿合同复效之后重新计算被保险人2年的自杀免责期间是否合理?
我国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第44条增补了所谓“从复效之日起重新开始起算”之规定:“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成立之日起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满2年后,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该法条规定的理论依据是基于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例如,某人认为已买的人寿保险合同只有在死亡时才能得到保险金,实在是没有多大意思,遂停止支付保费,导致保险合同效力中止。后由于各种因素而产生轻生的念头,此时,想到年迈的父母养大自己实属不易,于是想以自杀换取保险金以安慰父母,于是便复效合同。在该案例中,如果复效之后不重新计算2年的免责期间,会加强自杀者自杀的冲动,反之,能减缓其自杀的行为。有学者也指出,复效之后重新计算免责期间旨在于预防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的效力停止期间,萌生自杀的想法,而在交清保费使保险合同恢复效力之后再采取自杀行为。这样的结果不但造成被保险人的逆向选择,更可能成为自杀行为的催化剂,违背了保险合同的初衷。
复效合同本就是原合同的继续,从法条所使用“暂停”效力二字即可看出。既然是原合同的继续,为何要重新计算两年期间?另外,保险人的免责期间是平衡保险人与被保险之间的利益而产生的“折中点”。那么,期间的长短即表示了立法者倾向于保护保险人还是被保险人。保险免责期间为1到2年为合理的程度,如果将原来合同成立后经过的2年加上复效之后重新计算的2年,那么我国保险人的免责期间就变成了4年。这显然已超出了合理的限度,更加倾向于保护保险人的利益,故该条规定是否合理有待进一步论证。
三、自杀条款的具体适用及完善建议
我国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第44条规定: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2年内,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由此可知,在2年的免责期间内,保险人只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杀的情形不免责,其他一律免责。这样的规定是否合理,值得商榷。我们对民事行为能力的划分主要是按照行为主体的辨认能力作出的,而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显然不能等同,自由意思决定能力包含了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所以,法条的规定是狭隘的,在具体案件的适用上会产生不公平。
例如,比较容易产生自杀想法并实施自杀行为的抑郁症患者可归类于“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患者,但不可将其归类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通常能够辨认自己的行为,但因病不能控制自己自杀的行为,当然不属于保险人免责意义上的自杀。这种自杀应属于死亡的正常风险,不具有以自杀骗取保险金的意图,保险人应当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65条“自杀”含义的请示的答复》中提到,被保险人在投保后两年内因患精神病,在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情况下溺水身亡,不属于主动剥夺自己生命的行为,亦不具有骗取保险金的目的,故保险人应按合同约定承担保险责任。
另外,关于醉酒之后自杀的问题属不属于保险人免责意义上的自杀,关键还需判断行为人在醉酒之后有没有控制能力以及控制能力大小。如果没有控制能力则还需进一步考察行为人对于醉酒有无过错。比如,明知自己喝醉酒之后会有轻生行为仍然放任发生的,则认为有过错,保险人可以在被保险人过错范围内免责。
当然,法条上规定以被保险人自杀时的行为能力为标准是有一定道理的。该标准因其客观性而易于判断,但对于精神病之类的判断在操作上比较困难,易导致弄虚作假的情形出现,更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但是,不能为了便捷规避风险而牺牲实体公正。
2009年修订后的《保险法》对于自杀条款规定的进步是巨大的,但在实际适用中大都只起到一个总则的指导作用。目前的法律还存在着一些疏漏,导致保险公司在人寿保险合同中直接规定排除因病自杀之类情形承担责任的条款,使被保险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建议我国未来修法时可借鉴《德国保险契约法》第169条之立法例:“若其行为出于病理失常状态,以致不能自由决定其意思时,保险人仍须负责。”同时,用列举式并增加兜底条款来完善被保险人在免责期间自杀不承担责任的情形,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不断完善保险人免责期间不应免责的情形。
[1]樊启荣.人寿保险合同之自杀条款研究——以200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44条为分析对象[J].法商研究,2 009(5).
[2]刘树峰.建议安乐死与寿险理赔[J].中国保险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3).
[3]王泽鉴.民法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4]江朝国.保险法基本理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5]潘令仪,王祖承.中国自杀研究的现状[A].第四届泛亚太地区心理卫生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集[C].2005.
[6]于涛.被保险人自杀索赔问题的中美法律比较——解析新《保险法》第四十四条[J].保险研究,2009(3).
[7]袁美范.保险犯罪事件(下册)[M].台北:台湾广场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7:108.
[8][美]肯尼思·布莱克,哈罗德·斯基珀.人寿保险(上册)[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9,154,150,151.
[9]GarySchuman.Suicide and TheLifeInsurance Contract:Was The Insured Sane or Insane?That is The Question-or Is It?[J].Tort&Insurance Law Journal,Summer 1993.
[10]Ritter v.Mutual Life Insurance U.S,169 U.S.139,18 S.Ct.300,42 L.Ed.693,189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