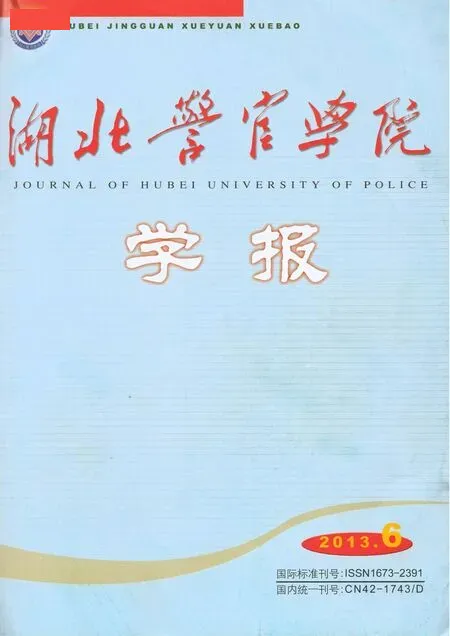美国医疗知情同意原则对我国的启示
2013-04-11竺伟东
冯 玲,竺伟东
(浙江工商大学 法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一、美国知情同意原则
(一)知情同意的历史渊源
英国的Slater案确立了实施手术前获取患者的同意是“外科医生之惯例和法则”,这是医疗行为中第一次出现同意的判例。美国承认了该判例,在1914年的Schloendor v.Society of New York Hospital[211 N.Y.125,105 N.E.92,(1914)]中,卡多佐法官指出:“每一个精神正常的成年人有权决定别人可对他的身体做什么。”该经典论断认为医生未经病患同意而实施医疗行为是一种暴行及伤害(Assault and Battery),体现了对患者“自主权”与“自我决定权”的尊重,但仅仅局限于外科手术。195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上诉法院在Salgo v.Leland Stanford Jr.UniversityBoard OfTrustees[154Cal.App.2d 560,317P.2d 170.(1957)]中认为,“医生若不完全告知患者作出决定的全部信息构成对患者信息披露义务的违反,需承担过失责任”,由此确立了“知情同意”的概念。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在Cobbs v.Grant案中明确把知情同意原则归入过失侵权法领域。至此,知情同意基于暴行和伤害的法理基础转向了疏忽责任。
(二)信息披露的判断标准
美国关于信息披露的判断标准有两种,一为“医师标准”(physician oriented standard),二为“患者标准”(patientorientedstandard)。美国堪萨斯州最高法院Schroeder法官在Natansonv.Kline[350P.2d1093(1960)]案中认为,“医师的披露义务限于一位合理医师在相同或相似情境下意欲披露的程度”。该案确立了“医师标准”。[1]美国宾夕法尼亚州Jones v.Chidester案确立了“两种流派”原则,并对行业内的认同度作了数量(“相当数量”)和质量(“相当质量”,即医师经认可的和受尊敬的程度)上的限定。该判例实质上是对“医师标准”的严格限制。不同于“医师标准”,Canterbury v.Spenc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Dist rict of Columbia Circuit[1972 464 F.2d 772]案开创了“患者标准”的先河,即以患者为取向的信息披露标准。
(三)信息披露的内容
美国法上的“患者标准”要求信息披露的内容为“实质性”信息。在Smith v.Shannon案中,华盛顿最高法院认为,医师应披露一个合理患者认为对其决定有实质性影响的风险。在美国法上,一个非常遥远的风险不具有实质性,美国司法只要求披露具有严重性质(serious nature)的风险。Moore v.Regents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upreme Court of California[1990,51 Cal.3d 120,271 Cal.Rptr.146,793 P.2d 479]案在美国医疗侵权上具有重大意义,确定了医师应当告知患者的组织体是否用于研究利益和经济利益。德克萨斯州最高法院的Duke vs.Migill of the UniversityofTexas案是关于医师告知研究利益最有名的判例。若医师未能披露上述利益,患者可以基于违反知情同意对医师提起诉讼。[2]Johnsonv.Kokemoor案的判决肯定了医生对患者披露职业资格与经验。D.A.B.v.Brown案认为医生应当向患者披露是否收取药品回扣的信息。对于患者而言,“实质性”信息的鉴定标准为:若医师披露相关决定性作用的信息,患者将选择替代方案。
(四)表意能力的判断
表意能力的判断主要包括民事行为能力说、识别说和英美法系的个案认定。个案认定需要综合患者“做出选择”、“理解相关信息”、“认知其处境和后果”、“合理处理信息的能力”等。此外,美国学术界还有所谓的“流动判准法”,即表意能力的判定标准依决定的复杂、重要程度和决定对患者健康的危险程度而定。笔者认为民事行为能力说过于笼统,不能适应每一个表意行为人;而识别说又具有极强的主观色彩,实务操作性不强;适当借鉴美国的个案判断方法,并结合民事行为能力说,具有可采性。
(五)知情同意的例外
美国法的知情同意的例外包括六种情形:一为紧急情形。Cardozo法官一方面认为“外科医师在实施手术前应征得患者的同意”,另一方面也认识到存在“患者意识不清和同意获取前有必要进行手术的紧急情形”两种例外。如一个病人在实行手术时被麻醉了,外科医生在实行手术的过程中发现必须实行另外一个手术才能保命,于是在来不及征求同意的情形下擅自进行了手术。该情形便是为挽救生命未经同意可以免责的紧急情形。[3]耶和华见证人输血的教义遵循的就是医疗正义。生命至上的价值伦理与尊重信仰发生冲突时如何权衡,医师是否可以基于生命至上而实行医疗行为,是值得具体案例加以探讨的。二为医疗特权。Bray法官认为,医生在履行告知义务时应当遵循“患者最佳利益标准”,考量患者的心理和情感状态对诊疗的影响。因此,医师基于完全告知信息将对患者诊疗产生不利而未完全披露信息是被允许的。三为权利放弃。Holtv.Nelson[523 P.2d 211,219(1974)]案的判决——“当患者要求不被告知危险时,医生不需要向其披露治疗危险”可以佐证。四为Goss v.Oklahoma Blood Institute案确立的有关已知风险例外。五为Reiserv.Lohner案确立的不可预测风险的例外。六为医疗强制措施的例外。
(六)预先指示制度
预先指示是患者在医疗干预和代理人问题上事先表达的一种意愿,是患者对医疗行为行使控制权的表现。美国1990年《联邦病人自我决定法》要求每一个接受医疗保障计划的医疗照护提供者应尽告知患者关于预先指示的法律的义务。预先指示的类型有代理型指示与指令型指示,后者包括积极与消极两种情形,而实践中往往是代理与指令并行。[4]预先指示制度是为了维护被代理人的权益,决策代理人的行为应当遵循替代判断。俄勒冈和明尼苏达州对精神患者的立法规定可供借鉴。
二、对我国的启示
(一)我国立法现状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七章规定了医务人员的告知义务。第55条规定,医务人员违反告知义务或者未经患者同意擅自实施医疗行为造成患者损害的,以侵权论,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第56条规定,在紧急情况下,未经患者或者其近亲属同意的,经医疗机构或者授权负责人批准,医务人员便可以实施相应的医疗行为。第57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我国现行立法存在三大优势:(1)明确了医务人员违反告知义务由医疗机构承担侵权责任,结束了以往患者仅仅依靠行政手段寻求救济的局面;(2)坚持了国际化的立法趋势,将告知义务与诊疗义务区分开来;(3)规定了知情同意的例外,即紧急情况。
(二)美国法对我国立法的启示
1.确立知情同意的两大原则
知情同意的两大原则为患者的“自主决定权”和保护“患者最佳利益”,法理基础是尊重患者的“自主权”与“自我决定权”,而非简单的生命健康利益。[5]美国的信仰宗教的孕妇拒绝输血而死亡的判例就是医院尊重患者自主决定权的有利佐证。在具体案例中,如何考量紧急情况、医疗特权等例外规定需遵循“患者最佳利益”原则。我国《侵权责任法》对医疗责任的规定必须严格遵循以上两大原则。
2.确立信息披露的判断标准
美国的信息披露标准从“医师标准”转向了“患者标准”。其中,“医师标准”是“父权主义”的代表,在Canterbury案后,“患者标准”在美国各个州被采纳,同时也受到了加拿大最高法院[Reibl v.Hughes(1980)2 SCR 880,(1980)114 D.L.R.(3d)1(S.C.C.)]、澳大利亚最高法院[Rogers v Whitaker(1992)175C.L.R.479(HCA)]、新西兰患者权利立法Health and Disability Commissioner(Code of Health and Disability Services Consumers'Rights Regulation 1996,Schedule,Right 6)的垂青。我国目前有关知情同意的立法规定就文义解释而言还不能确定信息披露的标准。因此,确立信息披露标准可以弥补立法缺陷,也可以为医务人员告知具体内容确立指导方向。我国应采“患者标准”,当下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也要求立法向弱势患者倾斜。
3.规定实质性风险的告知内容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88条解释了诊疗活动与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涵义。但何谓“实质性”风险,我国立法还未作出明确规定。我国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的“Roger两翼”判断标准,作为告知内容的原则性规定,“两翼”为“客观之翼”(医务人员的“主动型告知义务”)与“主观之翼”(“应对型告知义务”,有赖于患者诸如主动询问激活)。我国宜遵循“信息”与“实质性”区分的做法,医务人员应当告知其基于医疗专业人员所应告知的信息,告知信息的实质性应当以患者主观上意欲知道的内容为准。Chappellv.Hart案的判决可为佐证:在类似违反风险告知义务的案件中,只要原告能证明如果他被适当告知,他就不会选择某一手术,因果关系便成立,哪怕原告以后会选择同样的手术而面临同样的危险。
4.规范知情同意的例外情形
Cardozo法官在肯定患者具有身体处分权的同时,也指出存在“患者意识不清和同意前有必要进行手术的紧急情形”。[6]医疗知情同意的例外有四种,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6条明确规定了紧急情况的例外。此外,第55条规定的“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可以被理解为是关于医疗特权的立法,但立法需作出更明确的规定。基于患者主动放弃亦应当作出充分的解释。患者主动放弃是尊重患者自我决定权的表现。当患者的“自我决定权”与“患者的最佳利益”冲突时,将何者置于首位值得立法斟酌。我国目前的强制医疗立法大多为原则性的宣誓,应当进一步完善对传染病、精神病人等特殊群体的规范。[7]
5.确定表意能力的判断标准
我国关于表意人的行为能力实际上遵循的是民事行为能力说。民事行为能力说具有规范统一化的优点,但在实际生活中,表意人的表意能力往往参差不齐,鉴定医疗决策主体的资格在实务操作中一直是一个难题。《侵权责任法》承认和强化了患者知情同意的权利,但具有一定理解能力的限制行为能力人是否完全被排除独立行使知情同意权值得商榷。我国可以在适当肯定民事行为能力说的前提下,借鉴美国表意能力个案认定的方法,根据具体案例,考量患者的理解能力、年龄、精神状况、决定的复杂程度、决定对患者生命健康的影响等方面,同时适当降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判定标准,以医学上的判断(即有能力完全理解治疗的后果、可能的副作用以及不治疗的预期后果等)确定患者的表意能力,并遵循“患者最佳利益”原则。
6.建立预先指示制度
预先指示的关键问题在于,在表意人同意能力欠缺时,如何最大限度地保障其自主决定权。就我国目前立法而言,关于医疗领域患者家属同意的规定仅限于《侵权责任法》第55条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医疗特权以及第56条紧急情况的知情同意例外情形。我国针对医疗专业领域的预先指示制度尚未建立,应仿效美国,建立预先指示制度。
三、结语
我国在医患矛盾凸显的当下,借鉴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实务操作性强的知情同意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对于特殊群体的表意能力问题、家属代签手术同意书问题、急诊中的知情同意问题、医疗服务合同的性质问题、医生告知与患者交流问题等,均需立法作出进一步的解释。
[1]赵西巨,王瑛.论美国法中的知情同意原则及我国的立法思考[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4(3).
[2]赵西巨.从美国Moore案看对人体组织提供者的法律保护[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8(1).
[3][美]伊曼纽尔.侵权法(影印本)[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61.
[4]赵西巨,韩新民.论精神疾病患者的“预先指示权”[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5]赵西巨.我国侵权责任法知情同意条款评析[J].中国卫生法制,20 10(3).
[6]赵西巨.医事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79.
[7]陈洁蕾.论医患关系中的知情同意——以意大利法和中国法的比较为视角[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