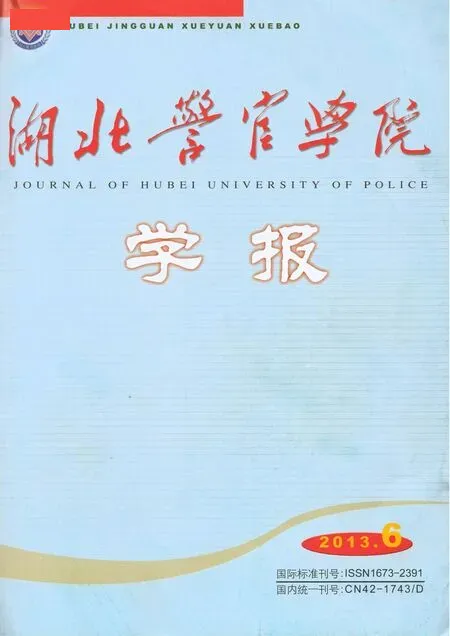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定性分析
2013-04-11杨新元
杨新元
(广西民族大学,广西 南宁530006)
近些年来,我国交通事故层出不穷,疲劳驾驶、酒后驾车、超载、违章等是其主因。同时,发生事故后因恐惧、害怕受到处罚等心理的作用而逃逸的现象屡屡出现,这是造成受害人死亡的一个重要因素。刑法第133条规定:“交通肇事是指违反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对交通肇事逃逸,尤其是产生致人死亡严重后果的逃逸行为有必要进行定性分析。
一、逃逸行为的含义
关于逃逸行为的含义,主要有两种观点:(1)行为人在交通肇事的当场以及与当场紧密联系的时空的逃逸,从而延误了被害人得到救助的宝贵时间;(2)逃避法律的制裁,即逃逸行为不限于交通肇事的当场,只要是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而逃逸的,即使行为人把被害人送到医院后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而逃走的,也构成逃逸行为。
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法律加大对逃逸行为的处罚力度主要基于我国目前交通肇事频发,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救助而造成残疾或死亡的案件较多,从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出发,只要有利于促进行为人肇事后积极履行救助被害人的义务,就不应当再认定其为逃逸。第二种观点有把逃逸行为扩大化之嫌。立法者的原意是为了让更多的受害者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而不是去追究肇事逃逸者的刑事责任,救人是第一位的,惩罚是第二位的。
二、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分析
关于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含义,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1)“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明知被害人不及时抢救会有生命危险而潜逃,致使被害人延误了抢救时机而死亡,此属于逃逸在刑法上的狭义解释;(2)“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在逃逸过程中致使他人死亡,即发生了第二次交通事故。这两种看法都是可取的。立法者的本意是更好地保护受害者,这两种观点体现了这一点。有些学者认为第二种情形应为另一个交通肇事罪,笔者不敢苟同,对于第二种情形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盲目地认定为第二个交通肇事罪。若将逃逸致人死亡中的‘人’只限于交通肇事中的被害人,这将导致刑法所保护的范围缩小,这是违背立法者的本意的。
三、交通肇事罪的现状与局限
我国目前在交通肇事逃逸这一块的刑事处罚尚处在一片空白的尴尬境地。出现一般的肇事案件,现有罪名还能应付得过去,但若出现严重或恶性的交通事故,现行的交通肇事罪的局限性就凸显出来了,显得无能为力。而此时司法机关往往会借鉴其他罪名,这就会在发生交通肇事后不能定交通肇事罪的尴尬局面,致使交通肇事罪在有些情况下有被架空之势,这是违背立法者的本意的。
当前我国刑法把“逃逸”与其他特别恶劣情节放在一起作为加重法定刑的情节(情节加重犯是指在基本犯罪的基础上,由于具有一定的加重情节,适用较之基本犯罪更为严厉的法定刑),这种设置导致了解释上的混乱。首先,从实际情况来看,发生交通肇事逃逸时,肇事行为和逃逸行为可以明确分为一前一后两个阶段。在肇事行为已经独立构成犯罪的情况下,犯罪后逃逸与否并不影响对前一个行为的评价,这有违刑法设置加重情节的通常做法。若按我国现行刑法的理解,也有“牵强附会”之嫌,有违法理。针对上述情况,我国可以借鉴一些外国的立法经验。目前很多国家和地区将肇事后逃逸的行为单独作为另一罪处罚,如日本。这种设置的不同,导致在法益保护上形成一定的区别。至少,对逃逸行为另定它罪,产生了一个独立的犯罪构成,可以从一个新的法益视角去综合各种事实行为。但是,如果“逃逸”仍在交通肇事罪中,则在解释时不得不顾及交通肇事罪本来的法益保护视角以及该罪本来的完整性。换句话说,加重情节的“逃逸”较之另成他罪的“逃逸”,前者所保护的法益必然有限一些。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把“逃逸”行为分割开来并入罪是可行的,符合人们对刑法的一般预测,这也能填补我国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伤的法律空白,对完善立法具有促进作用,有助于促进法律的细化,使法律变得更具有操作性和明确性,消除法律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四、肇事逃逸行为的分解
纵观整个逃逸行为,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逃逸行为”是继交通肇事后的又一个独立行为。即交通肇事行为与逃逸行为是相分离的,并独立完成各自的形态。逃逸是肇事后的后继行为,但不是必然的后继行为,逃逸行为具有或然性。当前,我国刑法理论上普遍把肇事行为和逃逸行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仅把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作为交通肇事的加重情节,这有待商榷。
若把交通肇事并逃逸这两个行为分开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交通肇事上当事人主观上是过失的,即肇事者并不希望交通事故的发生,主观上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是抵制的,交通肇事发生时,肇事者的主观态度是可以被确定的。而逃逸行为,从主观上看是有意为之的,即肇事者有逃逸的故意,并积极主动地实施了逃逸行为,其主观上的故意是可以明确的。由此可见,交通肇事行为和逃逸行为在主观心态上是有所区别的。故现行刑法笼统地把两者结合起来,把此行为看做彼行为的加重情形,是不妥当的。这毕竟不同于刑法中的加重或转化情形。加重情形一般是指在一个犯罪故意的范围内,罪犯使用的手段或犯罪情节超出了原刑法规定内容所能容忍的限度,不加重其刑罚将有违罪刑法定精神,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加重对其的处罚;刑法犯罪中的转化情形是在一个犯罪行为中,罪犯的主观故意由此故意到彼故意的转化过程,从而导致定罪处罚的改变。从上面两种情形来看,一般对犯罪进行加重处罚的情况都是发生在同一主观心态的情况下,对超出一种主观心态之外的一般都会给以数罪并罚。而在“交通肇事逃逸”,肇事者在两个不同行为中存在两种不同的主观心态,且没有前一行为,也就无后一行为的存在,即肇事行为是逃逸行为的基础,没有肇事即没有逃逸。故两者在主观状态上是不可能存在转化的情形的。从一个犯罪只有一个主观心态来看,这两者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因此,把交通肇事逃逸前后两个行为区分开来是可行的,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甚至将逃逸行为入罪也未尝不可。
因此,对于“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亦应分两个阶段进行分析。对于交通肇事,如前所述,不再重复。此处着重于“逃逸致人死亡”的分析。“逃逸致人死亡”的逃逸行为在主观上是有意为之的,即是故意的,客观上也造成了被害人生命权的丧失。从主客观相统一的要件来看,逃逸行为致人死亡在形式要件上符合不作为故意杀人的构成要件。因为,肇事行为促使肇事者有救助被害人的义务,该义务是由肇事的先行行为引起的,先行行为的作为义务源于法律的禁止性规范。如果行为人因自己的行为给法律保护的利益造成一定的危险就产生了采取积极行动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即有责任保证这一危险结果不会转变为损害结果发生的现实。且《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明确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员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这表明,肇事者的救助义务不仅仅是由于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更是一种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而逃逸行为违反了该救助义务,即为不作为。从理论上来说,不作为即有放任的故意,即不支持也不反对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由此看来,对“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另定故意杀人罪是完全可以的。旧刑法中有过类似的规定,但当时被认为不合时宜,或者被认为有定罪量刑过重之嫌。况且,国外也没有相关的立法经验。所以,对“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以故意杀人罪定罪一直不能成为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以致现在讨论“故意杀人罪”有绕圈子和倒退之嫌。但事物是变化发展的,彼时不合时宜,现在未必就不合时宜。从社会物质发展的进程来看,以前的交通工具没有现在发达,汽车的数量也没有现在多。就现阶段而言,交通肇事已成为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威胁,加大对交通肇事的处罚力度特别是对逃逸行为的处罚力度已很有必要。只有加大刑法的处罚力度,才能有效防止逃逸事件的发生。对于逃逸事件,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有分清了此行为和彼行为、此罪和彼罪,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刑罚的目的是预防,而预防的目的是有效制止。从现阶段来看,我国各种交通事故频频发生,特别是逃逸致人死亡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而刑法却缺乏足够的控制力。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在立法上存在一定的瑕疵,不能引起肇事者足够的重视,不足以给他们敲响警钟。因而,有必要对逃逸行为单独入罪。只有这样,逃逸者在逃逸之时才会有所顾忌,不敢逃逸。若是这样,预防逃逸的目的就达到了。
五、肇事逃逸致人死定故意杀人罪的可行性
很多学者认为,对逃逸致死行为定故意杀人罪显得过重,理由是肇事者主观恶性并不是很大。笔者不这么认为。首先,交通肇事是行为人违章行驶车辆导致的,即行为人在交通肇事之前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违规行为,也已预料到有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只是轻信能够避免而已。其次,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肇事者不去抢救伤者,反而逃逸导致受害者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从这点看来,肇事者的逃逸行为与其他突发性的临时起意的故意犯罪是很相似的。交通肇事中的肇事属于突发性案件,而逃逸则属于肇事后的临时起意。与其他突发性临时故意犯罪本质上是一样的,主观上的故意毋庸置疑。虽然从这两点看来肇事者的主观恶性并没有一般故意杀人者的主观恶性大,但从危害结果来看,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后果比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更为严重。试想,帮助他人自杀行为都能被定为故意杀人,为何逃逸致人死亡被定故意杀人就说定罪处刑过重呢?两者一比较,孰轻孰重就不言而喻了。因此,对逃逸致人死亡行为定故意杀人罪并不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逃逸致人死亡定故意杀人罪是可行的。
六、并罚机制的引入
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定故意杀人并不是对整个肇事行为的定罪,仅是对逃逸那部分的定罪。因此,对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应数罪并罚。把数罪并罚机制引入,是从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两个行为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得出的结论,并不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
[1]姚诗.交通肇事“逃逸”的规范目的与内涵[J].中国法学,2010(3).
[2]张明楷.刑法学(上)[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33.
[3]杨惠梅,谢沁.析交通肇事罪的“逃逸致人死亡”[J].学术探索,2004(9).
[4]于文湖.析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定罪问题[J].滨州师专学报,2001(3).
[5]高铭暄.刑法学[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2003.
[6]徐跃飞.也谈交通肇事中“逃逸致人死亡”的含义[J].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2).
[7]张亚军.也谈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之界定[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2009(2).
[8]王婧.论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含义[J].法制与经济(下旬刊),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