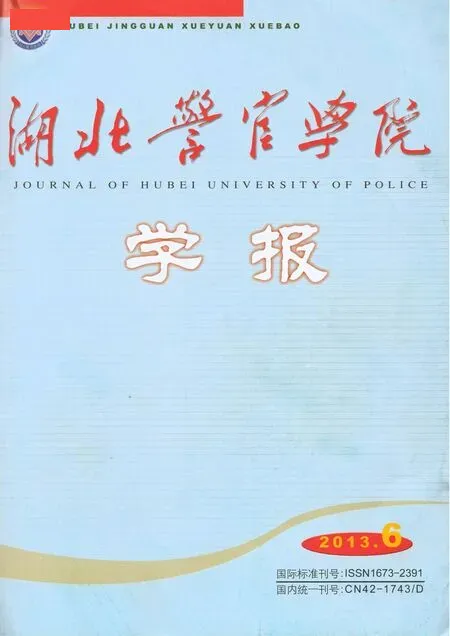走出入宪的迷思
——对迁徙自由的思考
2013-04-11张雷
张 雷
(甘肃政法学院 法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
迁徙自由是学界公认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公民权利,由于我国现行宪法并未像“五四宪法”那样将公民的迁徙自由明确列入文本之中,因此,不断有学者呼吁将该权利重新写入宪法,尤其是近年来,学者就迁徙自由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多,而学界的讨论大多集中于迁徙自由是否以及为何应该重新入宪的问题上。但是,宪法的有效实施需要民主的政治机制、完善的违宪审查制度、合理的宪法诉讼程序以及宽松的新闻舆论环境等配套措施。很显然,在我国当前的现实环境下,将其重新写入宪法对迁徙自由的保护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笔者持怀疑态度。因此,本文试图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即对迁徙自由的讨论应当走出迁徙自由是否该重新入宪的定式思维,如何通过具体的制度保障在社会管理中确保公民迁徙自由的实现才是当下最重要的问题。
一、迁徙自由的释义及其演变
(一)迁徙自由的释义
学界大多根据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以及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来对迁徙自由做出定义。根据这两个国际文件,迁徙自由是指公民在其本国的领土范围内的不同地域之间自由地迁徙并自由地选择住所,以及可以自由地离开他的国家并能够自由地返回其本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还明确列出了可以对迁徙自由做出限制的情形,即在为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需且与该公约所承认的其他权利不抵触的情形下,才能对公民的迁徙自由做出限制。
迁徙自由有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的迁徙自由被认为是公民根据宪法和法律可以在其本国领土范围内的不同地域之间自由旅行并选择居所以及可以自由离开其本国的领土范围并自由回国的权利。而狭义的迁徙自由仅指公民在其本国领土范围内的不同地域之间自由旅行并自由选择住所的权利[1]。本文所称的迁徙自由仅指狭义的迁徙自由。
(二)迁徙自由的演进
世界上最早对迁徙自由作出明文规定的是1215年英国《自由大宪章》的第42条。此后直到1791年的《法国宪法》,公民的迁徙自由才第一次被规定在一国的成文宪法中。19世纪以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对公民的迁徙自由做了直接或间接的规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公民的迁徙自由不仅受到了各国国内法的普遍承认与保护,而且还受到了相关国际公约的保护。
我国法律对公民迁徙自由的保护最早见于1912年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该法第2章第6条规定:“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在此之后,迁徙自由在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和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宪法文件中均有规定,如1921年公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12章第12条、1946年中华民国国民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第2章第10条等;而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的《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亦有迁徙自由的规定。1949年,当时起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及后来的“五四宪法”均对迁徙自由作出了直接的规定。但之后制定的“七五宪法”与“七八宪法”却由于种种原因均取消了对迁徙自由的规定,现行的“八二宪法”亦未恢复。
二、迁徙自由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困境
虽然现行宪法没有规定公民的迁徙自由,但也没有明确反对或限制这项权利,国家对公民的迁徙自由实质上是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但这并不说明我国公民迁徙自由的完全实现。在现实生活中,公民的迁徙自由往往是与我国的户籍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城乡二元结构相连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正处于经济恢复和大规模工业建设时期,但我国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当时经济发展极端困难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国家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成本负担必然就压在了农村和农民的肩头。发展重工业的资金主要靠农业积累,城市的粮食要靠农村生产,发展轻工业的原料要靠农村提供,农业在真正意义上成了国民经济的基础。只有把农民牢牢固定在土地上专心从事农业生产,才能保证这个“基础”的牢固可靠。但是到了1958年,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体制性、技术性问题不断累积,再加上大跃进、大炼钢铁等与经济规律相违背的政策措施的施行,使得农村的物质资源已无法满足农民的生存所需,因而导致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以求解决生计问题。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大批农业劳动力开始转移到工业部门,这也使得城市人口比重相应地提高,国务院为应对人口增长给城市带来的压力以及适应当时生活必需品供给不足的社会经济状况,遂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从此,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被严格地划分成了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农民因户籍身份而被束缚在了农村,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迁徙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此外,即使是城市户口,中央直辖市、省辖市、地级市、县级市的户口也有很大的差别,上一个级别的城市可以向下一个级别的城市调动[2],但反之则不行;再加上单位制所起到的人身控制的特殊功用,这些都使得“五四宪法”所规定的迁徙自由被架空了。
1978年之后,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启动,伴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以及单位制的变迁,国家对公民严格的人身控制开始松动。在农村,农民从严密的组织体系中解脱出来,甚至可以进城打工。近年来,农民工的队伍越来越庞大,逐渐成为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从80年代开始,我国许多省市也在逐步尝试改革户籍制度,例如,198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1986年,安徽滁州市天长县秦栏镇试行“绿卡式户籍制”;1993年,上海施行“蓝印户口制”;1995年,深圳市实行“蓝印户口制”,北京颁布了《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户籍管理规定》,向农民松动了城市户口的铁门;1997年,海南省开始酝酿更深刻的户籍改革,逐步实行人口登记IC卡制代替户籍管理;1998年,国务院转发了公安部《关于解决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对婴儿落户、夫妻分居户口问题、父母投靠子女的户籍问题等作了规定;2001年以来,浙江农村、河北石家庄和广东等地先后推出了新的户籍改革措施,不仅在当地反响强烈,在全国也引起了广泛关注[3]。可以说,这一系列探索卓有成效,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公民的迁徙自由已然有了充分的保障。比如,农民工进城务工,为城市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没有当地户籍,因此,在教育、医疗、住房等福利保障方面依然存在问题,而这些问题恰好是我国公民完全实现迁徙自由的限制性因素。所以,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仍然是我国公民迁徙自由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三、功夫在入宪之外——对迁徙自由的保护
由于“五四宪法”曾对迁徙自由作出过规定,而现行宪法没有恢复相应的条文,因此,学者们争论最多的是迁徙自由重新入宪的问题。但前文已述,在我国目前的法律环境下,是否入宪并非当前最重要的问题。
公民权利有三种:应有权利、法定权利与实有权利。迁徙自由是人的应有权利,但即使将它写入宪法,使之成为公民的法定权利,也并不意味着它马上就可以成为公民的实有权利。而这正是本文所要表达的观点,即迁徙自由重新入宪并不意味着其一定能得到很好的保障。宋代大诗人陆游曾告诫其子,“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对于迁徙自由的保护,笔者也是循此思路,即“功夫在入宪之外”。
如前文所述,自1958年以来,实行多年的城乡二元分割户籍制度依然是我国公民迁徙自由面临的最大障碍,因此,保护公民迁徙自由的最重要措施就在于户籍制度的改革。应彻底打破二元户口界限,消除依附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特定的社会经济利益,让户口成为只是表征公民居住区域的一项证明,只具有人口登记、管理、稽查以及了解人口数量和分布情况的功能,而它本身不反映公民的职业身份。这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也是保障公民迁徙自由权的必然要求。当然,改革户籍制度并不是保障公民迁徙自由的唯一方式,与此相伴随的,还有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改革教育、医疗体制等一系列配套措施。
四、结语
本文强调对公民迁徙自由的保护要走出是否入宪的定式思维,并不是有意轻视宪法的作用或蔑视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崇高地位。恰恰相反,笔者认为,宪法应当成为我们每个人行动的准则。但是按照革命宪法、改革宪法、宪政宪法的分类[4],我国现行宪法显然还属于改革宪法,它与宪政宪法还有一定的距离,在限制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等方面还存在较多不足,这与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执政模式、司法环境不无关系。保护包括迁徙自由在内的公民基本权利,最重要的是限制国家公权力,使权力不能肆意地侵犯权利,而这除了立法的完善外,根本的出路在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在于打破权力垄断、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等一系列使国家朝着现代化方向转型的改革措施。
[1]韩丰收.迁徙自由权在我国的变迁及反思[J].南方论坛,2007(8).
[2][3]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 011:20,37-38.
[4]夏勇.法理讲义:关于法律的道理与学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