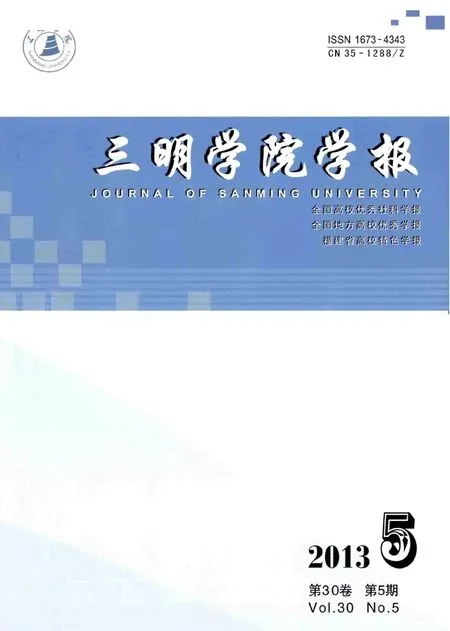20世纪西方语言批评视域下的话语分析
2013-04-11刘惠玲
刘惠玲
(湘南学院外语系,湖南郴州423000)
20世纪西方语言批评视域下的话语分析
刘惠玲
(湘南学院外语系,湖南郴州423000)
随着语言研究与文学理论、文化研究的不断发展与深入,话语分析在20世纪西方文论、文学批评及文化研究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并最终成为当今文学、文化批评和历史解读的最重要的理论武器之一。话语分析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的发展历程与特征,展示了其与20世纪前期西方语言形式批评的关系。自20世纪西方文学研究出现“语言学转向”以来,语言批评经历了一个从前期对“语言形式”的关注转变到后期关注“语言文化”的发展变化过程。
语言文化;话语分析;西方语言形式批评
话语(discourse)①是“现代批评理论中历史相对较短、用法变化最大、使用范围最广、定义繁复多样、意义至关重要”[1](P28)的一个术语。从词源上来说,话语源于拉丁语的discursus,而discursus反过来又源于动词discurrere,意思是“夸夸其谈”。[2](P84)作为概念术语,“话语”并非源于文艺理论领域,而是首先出现在语言学中,指用来交流的语义连贯的语言。[3](P6)发展至今,话语已突破了语言学的界限,具有了社会的、历史的维度,而更多地与许多非语言因素诸如政治、制度、权力、意识形态等相关。
20世纪西方文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语言批评经历了从前期对“语言形式”的关注转变到后期关注“语言文化”的发展变化过程。前期的“语言形式”批评根据语言本身的性质与特点来理解和诠释文学,强调语言对文学的规约性。转向之后的语言批评,由于受后现代主义,尤其是福柯话语理论的影响,则把语言活动与文学的关系作为研究的重点,强调语言与文化、意识形态的关联,以及这种关联对文学的制约性。本文主要梳理、探讨话语分析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的发展历程与特征,期望通过这种梳理以展示其与20世纪前期西方语言形式批评②的关系。
一、话语在现代语言批评中的产生:俄国形式主义和新批评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学的发展变化总是伴随或引起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的产生与发展。受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20世纪初的文学批评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转向了以文本为中心的语言形式批评。
首先把索绪尔的语言结构观运用于文学研究的是俄国形式派。毋容置疑,这与他们既从事语言学研究,又同时从事文学研究密不可分。基于“文学就是文学,与现实无关,文学形式不是别的,就是语言形式,是使文学成其为文学的东西即文学性”的观点,俄国形式主义提出应把语言学与文学紧密地联系起来,借用语言学方法来进行文学研究。“陌生化”和“诗性功能”这两个具有创建性的概念就是俄国形式主义从语言学角度提出来的。什克洛夫斯基明确提出,艺术效果和审美感受的产生来源于艺术家对语言形式的加工,对自动化的不断打破,对机械性的不断摆脱,具体表现为艺术家有意识地对现成材料进行夸大、缩小、拆散及组合等加工改变,使它们在性质、外形、大小、色彩、形状等方面焕然一新,即“陌生化”。[4](P50-65)可以说,“陌生化”就是赋予语言以最大的艺术表现力。
对于“诗性功能”,俄形式派许多理论家如雅可布逊、什克洛夫斯基、托马舍夫斯基、雅库宾斯基、日尔蒙斯基等都有过论述。这里以雅可布逊为例,基于“文学性存在于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中并且是文学作品普遍运用的构造原则和表现手段”的观点,他不断地运用语言学分析方法来分析诗歌。一方面,他以索绪尔语言学为依据,把语句的构成放在选择和组合这两根纵横交错的轴上来说明诗性功能;另一方面,他把诗歌语言放置在语言的交际环境中加以探讨,从语言功能上阐释文学性,寻找发音和意义上对应、语法功能相同的词语,寻找由一行行对称诗句组合而成的诗节,并由此发掘诗的内在结构,说明诗歌语言的特征。通过这种方法,雅可布逊指出,“诗歌的诗性功能越强,语言就越少指向外在现实环境,越偏离实用的目的,而指向自身,指向语言本身的形式因素,如音韵、词语和句法等”[5](P51)。
俄形式主义在将现代语言学的成果应用到文学领域时,虽存在过分夸大艺术形式的作用的局限,但开创了文学领域语言研究的新时代,尤其是关于“陌生化”与“诗性功能”的描述,“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区分,对后来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话语”概念在文论中的提出铺开了道路。
在俄形式主义的影响与启发下,英美新批评率先在文学领域启用“话语”这一概念,并提出“诗歌话语”和“小说话语”,赋予话语以区分不同文学体裁的功能。自此,话语就作为一种具有差异性的语言形式进入读者的视域。
新批评视“诗歌话语”优越于“小说话语”,所以他们的批评主要是对诗歌话语的研究。新批评承继了俄形主义用语言学方法进行文学研究的观点,但更多地从语义学角度出发进行文学研究。如布鲁克斯的“悖论”和“反讽”。悖论,又称诡论,原为一个修辞学术语,意指表面上荒谬而实际上真实的陈述。然而正是这样一种悖论语言,在布鲁克斯看来,是诗人表达真理的理想语言,是诗歌不可避免的语言。并且,布鲁克斯把悖论从语言扩展到结构的使用范围,把它作为体裁的一个差异性特征,使诗歌与其他文体区别开来。除了对悖论的重视外,布鲁克斯也十分注重反讽,但他不把反讽视为一种修辞格,而更愿把它看作是诗歌语言的根本特征,是诗歌的一种结构性原则,是“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4](P205)。布鲁克斯指出,在文学作品中,反讽是由于语词受到语境的压力造成意义扭转而形成的所言与所指之间的对立的语言现象,这也是诗歌语言与科学语言的一个根本性区别。[5](P112)布鲁克斯把悖论和反讽从修辞技巧提升为一种作品的宏观分析,深化了人们对诗歌语言特性的认识,但由于只是从静态的角度来分析双方的矛盾,所以又造成了其理论的不足。
新批评对话语理论的重大贡献是瑞恰慈的语境理论。通过对诗歌语言和科学语言的区分性分析后,瑞恰慈指出,诗歌语言是一种“感情性”(emotive)的语言,而科学语言则是一种“指称性”(referential)的语言。所谓的“感情性”是指诗歌语言具有激发人的感情的特点,语言指称的事物在这里仅起了触发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瑞恰慈认为诗歌语言具有“非指称性”的特点。而要理解、把握这种“非指称性”、虚构性的文学作品的意义,关键问题在于理解语言的功能问题,即语言与实在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传统研究的主要弊病就在于把事物的命名看得过分简单,把一般性的词汇都当作名称来看待,而实际上词汇的意义要复杂得多,语词只有在被人们利用时才具有意义,这就涉及语词、思想和所指客体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如此复杂的意义,瑞恰慈认为,应当通过语境来实现。瑞恰慈对语境概念的理解视野十分开阔,他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角度对仅局限于“某个词、句或段与它们的上下文之间的关系”的传统语境概念作了进一步的拓展。“‘语境’这种熟悉的意义可以进一步扩大到包括任何写出的或说出的话所处的环境;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到包括该单词用来描述那个时期的为人们所知的其他用法,例如莎士比亚剧本中的词;最后还可以扩大到包括那个时期有关的一切事情,或者与我们解释这个词有关的一切事情。”[4](P169)
瑞恰慈还通过对语境与复义之间相互关系的阐述深化他的语境理论。他指出,在文学作品中,语词的意义“有着多重性”,一个词往往会承担几个角色的职责,即它具有多重意义,但由于语境具有“一种节略形式”,因此在文本中,这些角色可以不必再现,这样一来,这个词的意义实际上也就是由它的语境决定的,即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的语境中缺失的部分”[5](P97)。由此,瑞恰慈进一步强化了语境在解读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性。瑞恰慈为新批评派奠定了诗歌语言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他的语境理论对新批评派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难发现,扩展到文学领域的“话语”概念突破了最初语言学层面上的纯粹的描述功能界限,而具有了界定差异的功能。然而,新批评对于这种具有差异性功能的话语进行分析时仍然立足于语言学上的语法分析来对话语的语言现象进行详尽的研究,所以他们提出的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概念,如张力、含混、象征、隐喻等无不出于对隐藏在字词后面的意义的探索,而缺乏从更大范围对话语群进行分析,并且他们对话语差异性的一面也言之过少。尽管瑞恰慈将话语与语境联系起来,拓宽了话语内涵及其研究范畴,但语境还是局限于文本内部或文本之间,故依然是一种语言因素的话语分析。因此,早期的形式主义文学批评和最初启用话语一词的英美新批评最为突出地体现了早期话语分析的语言学特色,但毋容置疑,新批评,尤其是瑞恰慈的语境理论与布鲁克斯的细读法,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文学作品的接受和创作提出的有价值的论述,为话语理论在文学批评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二、话语分析在现代语言批评中的发展: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
随着西方文论的发展,话语理论在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结构主义批评,一方面继承了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所强调的从语言学角度进行文学研究的观点,声称要探索“文字的实际革命的理论”[4](P221),另一方面以“语言整体结构决定语言意义”的观念和认识论,推进了话语理论,这种推进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在结构主义批评家那里,“话语”与文本密切结合起来。不同于英美“新批评”对细读的强调、对单篇作品的关注乃至对单独某句话的分析,结构主义文论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一个由各种因素相互联系而形成的一个封闭式的结构整体,语言符号的意义并不是它们本身的内容所规定的,而是在一个纵横交错的关系网中被语言的整体结构所决定。也就是说,结构主义文论的细读要求将语段的细读与整体参照起来。罗兰·巴尔特如是说:“语言结构含着全部文学创作,差不多就像天空、大地、天地交接线为人类构成了一个熟悉的生态环境一样。与其说它像是一种材料的储存所,不如说像是一条地平线,也就是,既是一个界限又是一块栖止地,简言之,某种机构中的可靠地段。”[6](P67)
第二,话语内涵的扩展,话语与语言区分开来。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分析方法来研究神话时将话语作为语言构造的第三个层面,即超越语言/言语的话语层面。也就是说,话语不再是语言系统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变成了一个独立于语言系统的自主系统。基于这种话语观的结构主义就有了与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不同的话语分析。在托多罗夫和巴尔特看来,叙事即话语。不过他们对叙事话语的具体分析又各有侧重。托多罗夫是法国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与叙述学的重要代表人物。除了关注叙述学的总体理论和具体叙事体裁的研究外,托多罗夫重点研究叙事语法,其核心是叙事作品中人物行为与语法学中的句法间的对应关系,托多罗夫之所以重点研究叙事语法,一是他认为普遍语法决定语言,也决定着叙事学;二是源于他的文学观。托多罗夫的文学观受到20世纪以来语言学研究的影响,他将法国象征派诗人瓦莱里的“文学是而且也只是某些语言属性的扩展和应用”[5](P244)作为知音。正因为此,尽管分析对象是具体的叙事作品,但托多罗夫认为,叙事作品的普遍规律而并非叙事作品构成了叙事学的研究对象,叙述学的目的是去寻求存在于作品之中的抽象的叙事结构(narrative structure)。他对薄伽丘的《十日谈》的分析,就是这一理论的具体实践——他从具体作品概括那些普遍适用的结构规律。
作为法国重要的文论家和批评家,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过渡的关键人物,罗兰·巴尔特认为,叙事具有普遍性,叙事与人类历史本身共同产生,遍及于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任何地方,所以对叙述形式的研究应是结构主义的首要课题。巴尔特对叙事作品的结构分析既不同于19世纪盛行的从作者来研讨作品的思路,也不同于新批评强调作品字词表达特性的方法,而是借用语言学对句子的层次性描述方法,从三个层次对叙事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功能层,研究基本的叙述单位及相互关系;行动层,研究人物的分类;叙述层,研究叙述人、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这三个层次是建立在一个基本原则之上,即:“这三个层次是按照逐渐归并的方式互相连接而来的:一种功能只有当它在一个行动元的全部行为中占有地位时才具有意义;而这一行为本身又因为交给—个自身具有代码的话语,得到叙述才获得最终意义。”[4](P282-283)他的这种从作品的普遍结构上来分析叙事作品的基本要素是运用典型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先是分割,找到系统的最小单位,然后是排列,重建结构,以达到对该系统的理解。
由此可见,结构主义的话语超出了单个句子或句子序列的简单层面而有了更高层次的系统整体综合性,它不仅是一多层次的语言结构,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是一个涉及语言环境和言语主体行为的语言结构,而后一方面是单纯以词句为单位的语言分析所不具有的。无疑,从简单层面的语言到多层次的语言结构和语言外环境的分析,话语有了更丰富的内容和更为重要的社会意义,但由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把文学视为一个系统,以重构结构、结构分析、探寻一个普遍有效的模式为目的,这就不仅把结构变成了静止、封闭、任人宰割的僵尸,而且也泛结构化,把结构分析变成一个神话,把分析始终局限于语言结构之中,话语的功能就在这单个的语言结构之中来建构自身和其他一切主体行为,就连他们所谓的语言外环境和言语主体行为也不过是语言内的一种区分。“在某种意义上,结构主义是另一种形式主义,它有一整套从语言学中借用的关于信息符号与规则的语汇”。[7](P117)
语言结构本身的封闭性所带来的局限很快使结构主义批评受到了内外部的指责而走向解体。走向后结构主义的巴尔特通过消解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理论进一步阐释了话语的概念,把话语的研究扩展到超出了语言学的范围,涉及到了更大的语境范围,从而提出了独特的文本理论与阅读理论。在他看来文本语言的能指与所指并不能构成索绪尔所谓的完整、固定的符号,而是能指的意指活动还未及到达其所指前就转向了其他能指,这样,文本中的语词符号就不再是明确固定的意义实体,而是能指群,它们可以互相指涉、交织、复叠。据此,巴尔特说“文本无所谓构造”与“文本没有任何句式”[5](P299)。由此,巴尔特更进一步指出文本与文本也是互相指涉,从来不存在“原初”文本,每个文本都是由其他文本的碎片编制而成,由此导致文本意义的不断游移、播撒、扩散;文本本身只是开放的无穷无尽的象征活动,任何意义只是这一活动过程中即时的、迅速生成又迅速消失的东西。这样,结构主义的作品意义论就被巴尔特消解了。巴尔特又提出了与文本理论相对应的阅读理论。在他看来,阅读即写作,即批评。他将阅读文本比作一种类似于创造的双重“游戏”:既遵循文本意指活动玩文本“游戏”,不断再生产文本的意义;又把文本当示谱演奏文本,这种演奏不是解释,而是工作、生产,是合作式的创造。[5](P299)由此可见,否定和消解结构主义文论的巴尔特文本理论和阅读理论,看到了文学艺术作为活动的过程性,看到了读者的参与性与创造性,具有独到的价值,但不足之处是他仍未跳出割裂文学与生活的形式主义窠臼。
另外,将解构主义美学推向鼎盛,并将其理论成功运用在文学批评与研究中的美国耶鲁学派的重要代表们尽管各自提出了独特的批评理论,如德曼的修辞学阅读理论,布鲁姆著名的“影响即误读”理论,米勒的的重复理论,哈特曼的文学批评即文学文本,但他们与其他的解构批评家具有共同的话语理论特征:从语言形式本身着手对作品的稳定性、整体性和意义的确定性进行颠覆,否定语言具有最基本的指称的稳定性的一面,强调语言的隐喻性特点,进而强调文学话语的不可读解性。
总之,在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传统的基础上,解构主义文学批评试图把以语言内部为重心的研究向更大空间——文化范畴研究进行外延,但是,解构主义的话语理论并没有完全摆脱结构主义的局限性。虽然把读者的作用考虑了进来,也注重了语境的作用,但将读者与作者对立起来,从语言对读者的限制出发,依赖语言因素而不是读者本身的社会生活经验等非语言因素的语境,因此,他们依然是文本式、语言形式结构的话语分析,只是在解构主义这里,文本话语是开放的,意义是不确定的。所以,实质上,解构主义否定结构主义仍不过是形式主义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而已,并且在强调不确定性和多重性的同时,也走向了意义无解的虚无主义。
从语言学拓展到文学领域的话语有了自己独特的内涵,并在语言形式批评中得到了逐步的丰富和发展。从具有差异性功能的话语推进到超越语言/言语层面的话语层面,从单篇单句的话语分析历经了与语境结合、文本结构整体、文本间的、敞开式的话语分析。由于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和解构主义批评将文学批评的重点放在了文学作品的语义、结构、修辞等“内部规律”的研究上,关注的是话语的语言规则和结构,而忽视话语的非语言因素。这种仅仅关注语言符号形式方面的话语研究的缺陷受到了内外夹击,由此产生了围绕文化、意识形态的话语理论——强调话语与文化、意识形态的关联,以及这种关联对文学活动的制约。这就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等为代表的新的研究路向,即把文学语言的研究重新与社会、历史、政治、伦理等外部因素相结合的话语研究。
注释:
①对于英语discourse一词的翻译,国内目前不一,有翻译成“语篇”的;也有翻译成“话语”的。国内外不同学者对discourse的理解也有差异,本文的话语(discourse)包括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
②主要指从语言内部解读文本的形式结构派,既涵盖了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也包括解构主义。
[1]陈永国.话语[J].外国文学.2002,(3).
[2]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福柯的面孔[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3]Cook,Guy Discours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4]方珊.形式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5]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2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6]陈永国.文学批评中的结构、解构与话语[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
[7]胡铁生.结构与解构:基于文本的悖论与统一[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
Discourse Analysis and Western Linguistic Criticism of the 20th Century
LIU Hui-li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Xiangnan University,Chenzhou 423000,China)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further study of language,literary theory and cultures,discourse analysis has been gett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the 20th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and cultural study.Discourse analysis, consequently,has turned out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eoretical methods to interpret literary,cultural and historical texts.This paper aims to make a survey of how discourse analysis as a literary critical way develops and of how it is characterized,therefore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ourse analysis and western linguistic criticism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However,linguistic criticism has undergone a change from"linguistic form"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o the"linguistic culture"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since"linguistic turn"happened in western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20th century.
linguistic culture;discourse analysis;western linguistic criticism
H0
A
1673-4343(2013)05-0040-05
2013-05-23
湘南学院科研项目(09Z005);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科研项目(1011288A)
刘惠玲,女,湖南衡阳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西方文论与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