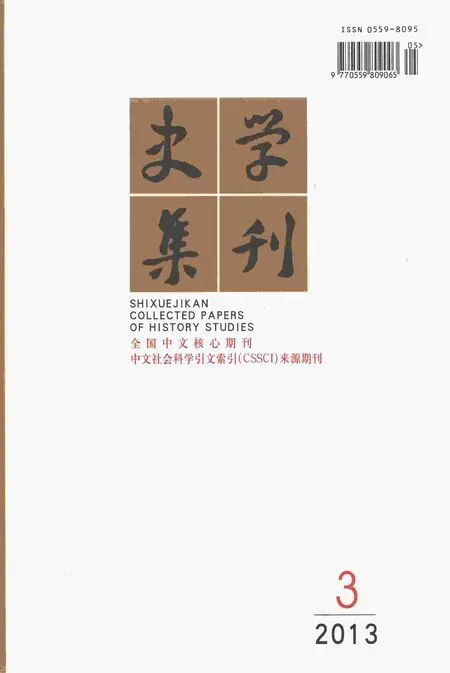晚清收回利权运动新论
2013-04-11朱英
朱 英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9)
利权,主要指经济上的权利以及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权益。利权一般都是相对国家而言,即国家的经济权利与权益,在某种程度上也涉及国家的主权。清末的收回利权运动,是由爱国工商业者积极主导、社会各界 (包括一部分清朝官员)踊跃支持、抵制外国列强对中国利权的疯狂掠夺、采取各种方式从列强手中收回丧失的利权、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一场运动。这场运动不仅具有鲜明的反帝爱国运动性质,同时也兼有一定的反封建色彩,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谱写了值得重视的篇章。关于这场运动的时代特点,有学者曾指出:“与缺乏广厚社会基础的戊戌变法运动不同,清末收回利权运动是从社会中下层喷发而起的民族抗争风潮;与19世纪基于‘华夷之辨’的文化隔膜而形成的反洋教斗争有别,收回利权运动属于20世纪中华民族觉醒和成熟的时代内容。在自然世纪流转的过程中,时代的更新便寓于其中了。”①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1、212页。
20世纪之初的中国,为何会爆发声势浩大的收回利权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的主导者和参与者是哪些社会阶层?运动的作用与影响如何?这些问题史学界虽已有诸多成果进行了考察,但其中仍有需要进一步探讨之处,以下即分别予以论述。
一、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
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首先是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列强加深对中国的政治控制与经济侵略,使中国急剧丧失大量利权,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而结束,清王朝被迫签订了前所未有的卖国条约,不仅向日本支付2亿两白银作为巨额战争赔款,割让台湾全岛,增开商埠,而且允许日本人在通商口岸自由开设工厂,“从事各项工艺制造”,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只交所定进口税,并可在内地设栈寄存。随后,欧美各国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特权,也得以在中国自由开设工厂。于是,诸国列强纷纷争先恐后地在华建立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直接对中国进行疯狂掠夺。
与此同时,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新阶段,垄断资本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取得了支配地位。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特征,是以资本输出取代商品输出成为对外侵略的主要方式。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为帝国主义列强对华输出资本洞开了方便之门。在此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竞相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并通过输出资本而夺取中国的各项利权。
攫取对华铁路的投资和修筑权,是当时各国列强对华输出资本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列强巩固和扩大其在华势力的有力工具。甲午战争后,列强在华争夺铁路投资和修筑权的竞争十分激烈。中国路权几乎丧失殆尽,其危害极为严重。时人即已意识到:“盖自帝国主义发生,世界列强拓土开疆,莫不借铁道以实行其侵略主义。……是故铁道者,通商之后援,而灭国之先导也。”①《滇越铁路赎回之时机及其计划》,《云南杂志》第4号,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杂志选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80页。开矿设厂,是当时各国列强对华输出资本的另一种重要方式,其危害也不仅仅只是涉及经济方面。例如“清末外资在中国开办矿业,其所涉及的问题,至为复杂。矿业并不是一项单纯的经济企业。……一处办有成效的矿区,可以很自然的成为一个独立的社区 (Community),像一处城镇一样。如果此一社区被置于外人的控制之下,加之,外人在华又享有多项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其将发生的后果,自非单纯。所以,外资办矿一事,在实质上,并不仅仅属于投资牟利甚或矿冶技术的范畴,其中实包含有错综复杂的政治意义”。于是,“外资办矿常为各国对华全盘政策中的一个环节,其政治性的意义,远超过于投资本身所具有的经济意义”。②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版,第2、4页。
伴随着利权的大量丧失,还出现了帝国主义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瓜分狂潮,严重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当年的爱国志士,曾满怀愤激忧患之情描述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俄虎、英豹、德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张牙,环伺于四千余年病狮之旁。割要地,租军港,以扼其咽喉;开矿山,筑铁路,以断其筋络;借债索款,推广工商,以脧其膏血;开放门户,划势力圈,搏肥而食,无所顾忌。官吏黜陟,听其指使,政府机关,使司转捩。呜呼!望中国之前途,如风前浊、水中泡耳,几何不随十九世纪之影以俱逝也。”③李书城:《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第3期,“论说”,1903年2月,第1-2页。
显而易见,中国利权的丧失,是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狂潮相辅相成的。时人有言:“比年以来,各国势力范围之划定,实借攘夺铁路矿产为张本。”④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983页。因为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主要目的之一,即是资本输出。例如列强在华攫取铁路修筑权,既是资本输华,又是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另外,利权又是国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利权的大量丧失,后果极为严重,不仅使中国经济利益受到极大损害,也使中国的主权进一步遭受极大破坏,导致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必然会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轰轰烈烈的收回利权运动也随之兴起。
其次,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之后,工商业者经济实力有所增强,思想认识有所提高,组织程度有所发展,这也是促使收回利权运动兴起的重要因素之一。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虽然已经产生,但商办企业为数不多,资本额较小,由官办、官督商办企业居主导地位。甲午战后,随着民间社会中“设厂自救”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情况逐渐发生变化。1895年至1900年间,商办民营企业不仅数量明显增加,而且资本额所占比例显著提高,开始在整个中国的近代企业中居于主导位置。于是,工商业者的经济实力迅速增长。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至1900年中国新设工矿企业共计122家,其中商办107家,占资本总额的83.3%,官办、官督商办15家,占资本总额的16.7%。⑤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 (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又获得进一步发展,其特点同样是商办民营企业的发展更为迅速。这一时期不仅民间开设的工厂数量和投资金额大大增加,而且投资的范围也较前更为广泛。除原有的缫丝业、棉纺织业、火柴业有很大发展外,烟草、肥皂、电灯、玻璃、锅炉、铅笔、化妆品等行业也都有民族资本投资的工厂出现。
民族资本主义虽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获得了发展,但同时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尤其是利权的大量丧失,使民族资本的生存发展举步维艰。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对广大工商业者而言同样也是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在此情况下,工商业者的思想认识也逐渐有所提高,开始将眼光从一己之身家财产移注于国家和民族的存亡,萌发出近代民族主义思想。19世纪末,即有商界人士指出:“爱国非可空言,其要尤在联合,一人之爱国心甚微,合众人之爱国心其力始大。”①陈颐寿:《华商联合报序目》,《华商联合报》,第3期,1909年3月6日。到20世纪初,工商界有识之士更大声疾呼:“凡我商人,宜发爱国之热忱,本爱国之天良。”在1905年由商会联络发起的全国性抵制美货运动中,“伸国权而保商利”也成为颇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口号。当时的工商业者,对利权丧失的严重危害也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例如对铁路修筑权的重要性,江苏商人即曾指出:“路权一失,不啻以全省利权尽归外人掌握,及此不争,将来切肤之痛,不独吾省受之而直接,在商界尤属不堪设想,此万万不可不出死力以抵抗者也。”②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85-786页。
新兴商人团体——商会的诞生,是20世纪初工商业者组织程度明显发展的重要标志。明清时期中国的工商业者虽已成立会馆、公所等具有行会特征的团体,但这些团体主要是为防止竞争、排除异己和垄断市场而建立的一种非常狭隘的组织。公所主要由同行业者联合而成,会馆更兼有同乡会的色彩,由在异乡的同籍者组成。因此,会馆无行业之分,但有地域的限制,公所无地域限制,却有行业帮派之别,均非各业商人或手工业者的统一机关。新成立的商会,则不限籍贯和行业,是联结工商各业的统一组织。商会“登高一呼,众商皆应”,能够将分散在各行业的商人和手工商业者凝聚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与此相适应,商会的活动内容及特点也与公所、会馆大不相同,其宗旨是“联络群情,开通民智,提倡激励与兴利除弊,并调息各业纷争”。③《广东总商会简明章程》,《东方杂志》,第1年,第12期,“商务”,1905年1月30日,第154页。因此,商会诞生之后,工商业者的政治能量与社会形象均大为改观,能够联合起来在收回利权运动中发挥更为突出的作用与影响。有关这方面的影响,以往的论著大多较少提及。
再次,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的改革以及相关政策的变化,对于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也产生了双重复杂影响。
对于清政府在收回利权运动中扮演的角色,过去强调较多的是其出卖利权,受到社会各界反对,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另一方面的作用。实际上,甲午战争的惨败不仅促使民间人士爱国救亡热情急剧高涨,而且也给清朝统治者带来了较大的刺激,迫使其不得不思有所振作,寻求变革。清廷上谕表示:“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加披览,采择施行,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等,如能“实力讲求,必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同时还宣称要“以恤商惠工为本源”。④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631页。与此同时,清朝统治者对利权外溢的严重危害也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出使美、日大臣伍廷芳即曾指出:“中国地大物博,各国环伺,乘间要求,非第利其土地,实亦羡其矿产。我诚定计于先,广为筹办,既可贻我民之乐利,亦可杜他族之觊觎。”⑤“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矿务档》第1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0年版,第42页。朝廷对此也表示关注,认为“马关商约于我华民生计,大有关碍,亟宜设法补救,以保利权”。其具体补救办法就在于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振兴商务,为富强至计,必须讲求工艺,设厂制造,始足以保我利权”。⑥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2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39页。在此之后,清政府开始实施鼓励民营商办企业发展的新政策,具体内容包括颁行有关章程,设立商务局和农工商局,联络工商,创办银行、兴办农工商学等。
20世纪初,清政府又大力推行“新政”改革。经济方面的改革主要是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历代封建王朝奉行不替的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清廷上谕明确阐明:“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亟应变通尽利,加意讲求……总期扫除官习,联络一气,不得有丝毫隔阂,致起弊端。保护维持,尤应不遗余力,庶几商务振兴,蒸蒸日上,阜民财而培邦本。”①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013-5014页。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 (1906年将工部并入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作为执掌农工商路矿事务的中央机构。随后,商部和农工商部陆续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章程法规,包括《商人通例》、《公司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铁路简明章程》、《矿务暂行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等,由此在当时形成了投资兴办实业的热潮。《国风报》第1年第1号刊登的《中国最近五年间实业调查记》一文称:“我国比年鉴于世界大势,渐知实业为富强之本,朝野上下,汲汲以此为务。于是政府立农商专部,编纂商律,立奖励实业宠以爵衔之制,而人民亦群起而应之……不可谓非一时之盛也。”
在保存下来的苏州商会的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苏州商会就成立商办铁路公司一事与商部往来的几封密电,披露其内容,可以发现当时苏州工商界与商部为争取江苏铁路商办而共同进行的努力及其成效。1906年2月,苏州商会致商部“乙密”电云:“苏浙铁路已定商办,浙已开办,苏亦宜办自苏达浙一段,以期交通,路线百里,费约二百余万。绅商现先认定底股三十万元,余再订章招股。乞大部俯赐注册,名曰‘苏省商办苏南铁路有限公司’。”2月27日,商部即回复“感电”称:“路政重要,急宜郑重以图。希即转诸绅商,妥筹改为‘苏省铁路公司’,仍俟公呈到部再行核夺。”3月5日,商部又致苏州商会“镇电”云:“速举总、协理,拟简章,请代奏。”②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第769-770页。根据上述三电,可知江苏工商界在1906年4月左右公开呈请设立商办铁路公司之前,即已暗地就此与商部有过多次磋商,说明当时的商部尽管也害怕开罪列强,但确实对江苏商办铁路运动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之所以采取密电的方式联系,自然是担心英国侵略者过早获悉消息,从中加以阻挠破坏。1906年5月,商办江苏铁路公司也获准成立,王清穆担任总理,张謇、王同愈、许鼎霖为协理,总公司设于上海,在苏州另设驻苏公司。
然而利权的不断丧失,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始终都是一大障碍。因此,清朝统治集团内部越来越多的官员提出应该采取具体措施,维护利权。例如刘坤一、张之洞在联名所上的奏折中指出:外人久已垂涎我矿山铁路,“知我于此等事务,尚无定章,外国情形,未能尽悉,乘机愚我,攘我利权”。“各省利权,将为尽夺,中国无从自振矣”。欲筹措挽救办法,只有“访聘著名律师,采取各国办法,秉公妥订矿路划一章程”。③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762-4763页。当时,朝廷对这道奏折也十分重视,“责成各该督抚等,认真兴办,查照刘坤一、张之洞原奏所陈,各就地方情形,详筹办理”。④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五),第4803页。稍后,会办商约大臣盛宣怀也说明,在商约谈判中各国均欲强占我矿权,中国必须参酌各国矿律,自行妥定章程, “以期主权无碍,利权无损”。⑤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五),第4941页。商部成立之后,更是以维护利权为己任,并向朝廷奏陈:“路矿两端,实为各国富强之根本,事属相因,政宜并重,所有各省矿产,业由臣部酌定表式,并拟妥定章程,奏明请旨办理。……统计三年之内,如查有切实办事,确遵臣部定章,于路务大有起色者,应准由臣部择优奖励。”⑥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415页。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清末收回利权运动兴起之初,清政府各级官员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与支持,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与影响。
复次,公共舆论对于收回利权运动兴起的影响也不应忽略。鉴于利权丧失的诸多危害,20世纪初各种报刊几乎都无一例外地登载了大量呼吁收回利权的言论,形成一种具有相当影响的社会舆论,从而对于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引导与号召作用。过去,史学界对这方面的影响一直较少提及。
19世纪末的维新变法运动期间,是近代中国报纸杂志兴盛的重要阶段,公共舆论的社会影响也随之日益彰显。到20世纪初又在原有基础上获得更进一步发展,不仅各地报纸杂志的数量明显增多,而且往往会对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集中进行报道和评论,所产生的影响也更大,收回利权即是当时诸多报刊的重要论题之一。具体而言,从各种角度揭露利权丧失的严重危害,以警醒国人,激发社会各界对利权问题的高度重视,是当时各种报刊载文谈论最多的话题。有的还上升至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对利权丧失的恶果进行了十分深刻的分析。例如《四川》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即指出:“彼列强各挟其最阴毒最猛辣之手段,层出不穷,以集中我国之经济界,而大饱其鲸吞蚕食之野心。……此不特经济丧失之问题,实国家存亡之问题也。何则?经济为国家之生命,生命之权既操纵于外人之手,彼更进而以开港场,施行政治,侵我主权,以保护路线,屯置军队,缚我手足,一旦势力巩固,由经济界之瓜分,以逮及于国土之瓜分,此亦埃及、印度覆亡之秩序前鉴未远也。”①南溟子:《中国与世界之经济问题》(续第1号),《四川》,第3号,1908年11月,第32-34页。《大公报》发表的一篇山东旅京学界同人公启,也深刻地阐明:列强“昔之灭人国也以兵力,今之灭人国也以利权;昔之灭人国也夺其土地,今之灭人国也攫其铁路。铁路存则国存,铁路亡则国亡,铁路者,固国家存亡之一大关键也”。②《为津镇铁路敬告山东父老文》,《大公报》,1905年10月30日,第2版。如此发聋振聩的大声疾呼,当然会对国人产生极大的警醒作用。不仅如此,当时的报刊舆论还一致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收回丧失的利权,挽救民族危亡。有的强调:“今欲言自立于强权之漩涡中,非先保其路权,以渐复其国家主权不可。”③《山西留学日本学生为同蒲铁路敬告全晋父老书》,《东方杂志》,第3年,第3期,“交通”,1906年2月18日,第7页。有的则发出警世危言,阐明中国若不亟起抗争,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将长为数重之奴隶矣!”④《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3期。转引自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3页。这样的呼吁,对于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自然也会产生比较明显的推动作用。
不仅如此,大众传媒对收回利权运动的发展也不无影响。运动的主导者对此也有所认识,并积极创办相关报刊作为号召和动员民众的工具。例如“川人知道报纸势力,就在争路时代”。⑤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7页。四川保路运动期间,川路公司即曾拨出专款,先后创办《蜀报》、《西顾报》、《白话报》,保路同志会也曾编辑印行《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作为会刊,开辟“报告”、“纪事”、“著录”等栏目,专门登载四川保路运动的消息和评论,受到各界普遍欢迎。《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13号“报告”透露:“本会报告日出万纸,尚不敷分布远甚。今更与印刷公司再三筹商,苦心设法,每日多出五千张。”由此不难看出其受到各界欢迎之程度,其影响也相应可知。湖南保路运动发展过程中,领导者也专门创办发行《湘路新志》,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利权的疯狂掠夺,不仅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随之造成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引起社会各界对利权问题的高度重视。新兴的民族工商业者一方面出于自身生存发展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源于思想认识的提高,对严重的民族危机深表关切,提出了维护利权的强烈要求,并积极投身于收回利权运动。此外,在甲午战争之后处于内忧外患危局中的清王朝,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不得不开始寻求变革。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都推行了鼓励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新举措,在此情况下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不少官员对利权丧失的危害有所认识,并主张维护与收回利权。20世纪初,收回利权的相关论说在各种报刊也屡见不鲜,成为颇有影响的社会舆论。于是,在上述几个方面因素的交相影响与推动之下,清末收回利权运动即因势而起,并不断深化发展,在当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二、收回利权运动的主导者和参与者
早期的相关论著一般都认为收回利权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换言之,即资产阶级是运动的主导者。到20世纪90年代末,有学者对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如果仅仅依据收回利权运动的结果、目标有利于资产阶级或体现资产阶级利益的判断而加以定性的话,那末,这无疑是低估了这一运动的作用。事实上,作为民族抗争的收回利权运动,无论就其斗争目标还是就其结果而言,它体现的是全民族的利益,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民族资产阶级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而是有着具体内涵的可以把握的社会实体力量。收回利权运动究竟是否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应该依据具体史实去考察占据这一斗争中心地位的社会力量的属性和特质。……收回利权运动并非是某一社会阶级 (包括资产阶级)利益和意愿的集中表现,而是全民族面对国权、生存权丧失殆尽而奋起救亡的民族斗争。”至于说在收回利权运动中,究竟是何种社会力量居于发动、组织、指导的中心地位,这位学者指出:“尽管勃兴于各省区的收回利权运动的规模不同,方式有别,进程不一,但作为斗争发起者的社会力量却主要都是由绅士或‘绅商’集团来担负的。”在收回利权运动中,为了更好将各阶层的力量有效地聚集在“民族抗争”的旗帜下,使斗争取得最终胜利,各地都相应地成立了组织领导机构,在这些组织领导机构中居于中心地位的也不是资产阶级,而是绅士阶层。①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第212、216-217页。
还有学者认为,绅商是收回利权运动的中坚力量。“绅与商在晚清社会中进一步相互渗透、合流的结果,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一个与半殖民地半封建过渡社会形态相适应的特殊的绅商阶层。这一新兴社会阶层既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地位,又拥有相当的财力,逐渐取代传统绅士阶层,成为大中城市乃至部分乡镇中最有权势的在野阶层。他们集绅与商的双重身份和双重性格于一身,上通官府,下达工商,构成官与商之间的缓冲与中介,起到既贯彻官府意图,又为工商界请命的‘通官商之邮’的作用。绅商阶层的形成,既是明清以来绅与商长期对流的结果,更是近代社会历史变动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至于绅商的社会阶级属性,不能忽视“近代绅商业已开始从事相当规模的实业投资,同近代经济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开始接触和使用新的资本主义营运方式,其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也开始出现了带有近代趋向的微变”。因此,可以“将近代绅商阶层的社会阶级属性确定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早期形态”。②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205-206页。由此推论,我们也可以说在收回利权运动中居中坚力量的是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绅商’并不具备资本家集团或者资产阶级的典型特征。‘绅商’没有属于自己的雄厚的资本,它只是动员或组织社会资金的主要社会力量。”③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第238页。另外,学界对清末绅商一词的内涵也存在一些争议。具体说来,“绅商”一词究竟是分指绅士与商人,还是单指绅士与商人融合生成的一个新阶层,学界的见解并不完全一致。有学者认为,在清末文献中频繁出现的“绅商”一词,“分指绅士与商人的例证较多”,而“单指性较明显的例证则较少,且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疑点”。④谢放:《“绅商”词义考析》,《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26-127页。但也有学者认为,文献中的“绅商”一词,在多数场合指绅与商的合称,但有时也是对亦绅亦商人物的单称。“所谓绅商,狭隘地讲,就是‘职商’,即上文所说的有职衔和功名的商人;广义地讲,无非是由官僚、士绅、商人相互趋近、结合而形成的一个独特社会群体或阶层”。⑤马敏:《“绅商”词义及其内涵的几点讨论》,《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37页。还有学者以清末广东的情况为例,指出在广东虽然形成了一个人数颇多且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的“亦绅亦商”的群体,“但‘绅’与‘商’远未合流,两者的界限与竞争也是很明显的。总的来看,很可能界限和竞争更是主要的方面”。⑥邱捷:《清末文献中的广东“绅商”》,《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47页。既然对绅商一词的内涵存在这样的争议,那么简单地认定绅商是收回利权运动的主导者或中坚力量,就会存在指向不十分明确的情况,即究竟是指绅士还是指商人,似乎并不能完全确定。
笔者认为,在收回利权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可以说是新兴的工商业者。收回利权运动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的具体内容,一是收回被列强攫取的铁路、矿山利权;二是自行集资修路与开矿,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收回利权运动的组织者与主导者,绝大多数除采取各种方式争取收回利权之外,同时又都积极参与了集资修筑铁路或开采矿山的经营活动,不管他们原来是绅士的身份,或者原本即是商人,抑或是所谓的绅商,在投资参与商办铁路和开矿之后,都可以说是新兴的近代工商业者。
还需要说明的是,1906年以后的“预备立宪”期间,立宪派成为一支十分活跃并具有相当政治号召力和社会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尤其是具有地方议会和自治议会色彩的各省咨议局的成立,使立宪派拥有了一个议决地方应兴应革事件和议决地方财政预算、决算、税法、公债的合法代议机关,立宪派的政治能量和社会影响也随之更为突出。维护利权,发展实业,是绝大多数咨议局一直关注的重点内容。许多地区的收回利权运动中,咨议局都曾议决相关议案,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重要的代议机关。①侯宜杰:《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5页。特别是在保路运动期间,许多咨议局的“中心活动就是保卫路权”,咨议局成为“保路运动的领导核心”。②林增平:《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页。于是,在清末收回利权运动后期,立宪派借助咨议局这个新的代议机关,也成为收回利权运动的另一支重要政治主导力量。有学者强调:“清末的立宪派直接产生于绅商阶层,有的虽服务于学界,但或出身于绅商家庭,或与绅商阶层关系密切,所以他们直接反映着绅商阶层的利益与要求。立宪运动反映他们的政治要求,收回利权运动反映他们的经济要求。立宪派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两个运动的领导者。”除此之外,“立宪派之能够在收回利权运动中起领导和中坚的作用,除了因其掌握舆论,有政治经验和组织能力以外,还因他们有集股的能力。他们有的本身就是富家巨室,有的则以其清望甚高,有稳定的社会地位,令绅商信服”。③耿云志:《收回利权运动、立宪运动与辛亥革命》,《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第75、79页。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收回利权运动中的影响也不能忽视。有关论著在论及收回利权运动时,一般都较少谈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作用与影响,似乎革命派与收回利权运动没有什么关联,实际上并非如此。尽管革命派主要是从事反清革命活动,但在收回利权运动中同样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具体而言,革命派在收回利权运动中的作用与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舆论宣传,革命派创办的诸多报刊都曾阐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与利权丧失的严重危害,大声疾呼收回利权;二是实际参与,福建、广西、云南、山西、浙江、江苏、湖北、湖南等地的革命党人,都曾积极参与了所在省份的收回利权运动。不仅如此,革命派在收回利权运动中的主张与行动往往更为激进,因而有学者称之为收回利权运动中的激进派。④李宗一:《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清末收回利权运动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第3-7页。
收回利权运动之所以能够形成一次颇具规模和影响的爱国运动,除了主导者的作用之外,还在于这场运动具有广泛的社会参与性。换言之,亦即收回利权运动的参与者具有相当的广泛性,涉及诸多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甚至可以说“社会各阶层几已全部卷入”。⑤林增平:《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第215页。这场运动之能够形成这一特点,其原因很简单,因为收回铁路修筑权与矿山开采权在当时是“一个深得民心的运动”。⑥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89页。“收回利权运动并非是某一社会阶级 (包括资产阶级)利益和意愿的集中表现,而是全民族面对国权、生存权丧失殆尽而奋起救亡的民族斗争。她所拥有的社会成员的广泛性是任何旨在为某一阶级奋斗的社会运动所难以比拟的”。另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开始民族觉醒的重要历史阶段,“20世纪属于民族觉醒的世纪”,是收回利权运动的领导者用以呼唤、动员群众的精神武器,“是以国权、生存权为实际内容的民族精神”。因此,“聚集在这面旗帜下的社会力量的广泛性、社会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反抗力量的持久性,都是空前的”。⑦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第213、225页。不过,也有个别学者指出对收回利权运动中“普通民众的参与程度不容高估,光绪三十三年王廷扬致函沈瓞民称:‘如此大风潮,不知者尚多,即知者亦莫名其妙,毫无感觉。以不知他办(指英帝国主义者办路)之害,并未知铁路之利故也。’”(沈瓞民:《浙江拒款保路运动的群众斗争及其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62年,第29页)。见苏全有《对清末利权回收运动的反思——以邮传部收回京汉路为个案》,《历史教学》,2008年第6期。
有学者指出:“近代中国不缺乏投资资金,而是缺乏一种将剩余集中起来转化为投资的机制。……广泛的社会动员是商办铁路集资成败的关键。川路公司、粤路公司、浙路公司成为集资的前三名,得益于广泛的社会动员,多渠道筹集资金”。①尹铁:《晚清商办铁路公司的集资问题》,《浙江学刊》,2007年第4期。事实确实如此。例如在较早兴起的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与集股商办的斗争中,湖南各界都相继积极参与,产生了较大的声势与影响。“城乡广大居民,包括学生、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军营、学校教职员、下级公职人员和一些开明地主分子”,均积极“通过踊跃认股,投入了保路斗争”。②林增平:《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第212页。据《湘路新志》记载,“湘路自去冬咨议局议决后,多方集股,得学界欢迎,去冬周氏女塾各学生向集股会缴入路股二千余元。”修业小学还发起成立成城社,“以劝集路股为目的,联合全体学界,讨论方法……俾湘路早日完成”。数月之后,“即已缴入公司路股洋银四千余元”。商会等团体专门成立了集股分会,负责办理招股、换票、发息,动员广大商人和社会各界踊跃认股,“数日之内,集股已多”。凡属湘籍公职人员、军营、学校还曾以廉薪酌量入股,“各局所、学堂、军营莫不鼓舞从事”,很快即获得廉薪股款近万元。此外,下层民众也激于爱国义愤,节衣缩食争相入股。“农夫、焦煤夫、泥木匠作、红白喜事杠行、洋货担、铣刀磨剪、果粟摊担、舆马帮佣,亦莫不争先入股以为荣”。③详见林增平:《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第212-213页。在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下,湖南出现了集股自办铁路的高潮。
湖北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铁路协会成立时,“农夫演说,洋洋数千言,士兵断指,血淋漓,以及星士解囊,以助协会之用费”。④铸铁:《湘路纪事》,《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48页。在收回粤汉路权、商办铁路日益高涨之际,湖北“军学绅商各界认股者异常踊跃。然上等社会之于公益已见热心。昨有金寿帮土工绅首徐雨亭等会议于六也茶园,拟定办法,除将公款七百余串悉数附股外,其作坊十六家各认十股。该帮艺徒计八百二十一人,每人劝定捐集一股,由各主东在工资项下按月抽提,以便缴纳。今下等社会亦热心公益如此,足见国民程度之进境也”。稍后,该帮又举行大会,议定“由各作坊每家认洋三十元,散工每各认洋一元,合筹现洋一万元,限冬月十五以内缴齐,由徐雨亭呈交公司,认作优先股二千股”。据报载,“当铁路协会开办之初,人人咸抱一路存鄂存、路亡鄂亡之心,所以一时认股如风发潮涌,不数月间已获百万”。⑤参见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94、498页。
四川保路运动中由于川路公司采取独特的“租股”形式筹措股金,⑥川省工商业不发达,川路公司不得不采取独特的招股办法,股本来源有四种,即认购之股、抽租之股、官本之股、公利之股,其中以租股为大宗,涉及广大的自耕农与佃农。因此,川汉铁路集股的社会面广,成效也较为可观。涉及的各阶层民众更为广泛,包括乡村的农民等各个阶层均包括在内,保路运动也随之扩展至更广阔的县镇区域。“无男无女,无老无少,无富贵贫贱,无智愚贤不肖,无客籍西籍,莫不万众一心,心惟一的,惟知合同失利,惟知破约保路,直提出其灵魂于躯壳之外,以赴破约之一的”。⑦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714页。类似社会各界万众一心共同致力于维护路权的情景,无疑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又如筠连县保路同志会成立时,“无论老者、弱者、智者、愚者,咸知川路为吾人生命财产,势必同归于尽。万众一心,誓死进行,连日报名者纷至沓来,争先恐后,吾筠连历年设会,鲜有如此神速者”。成都华阳保路同志会建立,“乡农到会尤多,闻路权尽失,则莫不切齿,异常悲愤”。⑧《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24、16号,转引自鲜于浩:《试论川路租股》,《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第55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积极参与收回利权运动的社会各阶层中,学生界是最为活跃、作用与影响也最为突出的一个阶层。20世纪初的中国,全国各地设立的各种新式学堂已为数众多,学生数量也随之日益增加,从而形成了一个新兴的学生群体。他们的特点是具有新知识和新思想,特别关注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命运,而且眼界开阔,反应敏锐,行动迅速,加之较少既得利益与传统因素的羁绊,其思想和行动也相对比较激进,态度更坚决,具有义无反顾的精神。上述这些特点,使学生界在收回利权运动中的表现显得尤为积极,作用与影响自然也十分令人瞩目。
学生界在收回利权运动中的具体表现与作用,首先是积极采取各种方式向下层民众进行广泛宣传,启发民众的国民意识,号召民众踊跃认股,参与收回利权运动。他们通过集会演说、报刊载文、广发传单,发挥了显著的号召与鼓动作用。例如有的“遍发传单,邀集女界同胞”开会演说,阐明“凡我女界皆属一份子,各宜节省服饰,酌买路股,以尽一份之义务”。有的邀请家长,“特开父兄恳亲会,演说路权丧失,利害切身。各学生及该父兄有顿足咨嗟,泪涔涔下者,于是相继认股”。不少学校的学生还利用假期回到城镇乡村,广泛宣传劝募,如河南河内高小学生担任汴路劝股,计划分途进行,每路正副各4人。“学生皆慷慨争先,全堂遂为一空”。信阳师范学堂学生“亦到处演说,提倡集股”。①详见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其次是踊跃认股,积极筹措股金,支持商办铁路。在江浙两省收回路权运动中,各学堂学生均尽全力带头认股,如上海复旦公学等4校学生共认股29 600元,高等实业学堂学生认1000余股,杭州36个学堂的师生认股合洋230 220元,金华中学和嘉兴府学堂学生各认10 000元和3000元,江宁两江师范学堂认股20 000元。由于自身缺乏经济收入,学生的认股数额并不大,但却体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同学节糕点饼果饵之资及一切无谓之费,共谋公益”。还有学生表示:“我学生入股之法,亦惟有减我一时口腹之供,以保我万世子孙之业而已矣”。②详见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255-256页。
清政府以及一部分官员在收回利权运动中的作用与影响也值得注意。客观地说,在收回利权运动的初期阶段,清政府相关部门以及一部分官员都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起到了促进作用,以收回路权运动为例,清政府于1903年底颁布了《重订铁路简明章程》,规定民间集股设立铁路公司承办铁路为合法,并予以奖励和保护,凡“查明路工实有成效者”,由商部“专折请旨给予奖励”。该章程的颁行,实则为收回路权运动的兴起开了绿灯。紧随其后,许多省份的商人根据这一章程,提出集股自建铁路的要求,绝大部分在起初都受到所在省份督抚和商部的支持,各省京官也都主动联络,内外呼应。从有关记载可以看出,各省工商业者筹建铁路的要求,大多是通过督抚奏请清廷谕允批准,各省的商办铁路公司,也是经商部大力协助上奏清廷谕允成立,至于粤汉、广澳、津镇、京汉等铁路修筑权的赎回,同样是官商共同努力所取得的结果。时论有称:“张之洞、岑春煊首从鄂湘粤三省民意,以美金六百七十万元赎回粤汉铁路,归三省自办。我国收回利权之举,以此为嚆矢”。③凡将:《十年以来中国政治通览·交通篇》,《东方杂志》,第9年,第7期 (纪念增刊),第94页,1913年1月1日。
但是,清政府外务部与商部的态度略有不同,该部因担心收回利权会引发新的中外交涉与冲突,故往往不敢予以支持,甚至有时还对收回利权之举予以阻挠。另外,在收回利权运动后期,清政府一方面屈服于各国列强的压力,另一方面为取得列强的贷款以缓解财政危机,转而主张对外借债修路开矿,并对商办铁路采取高压政策,又严重破坏了收回利权运动的成效与进一步发展。为此,清政府也成为收回利权运动后期社会各界抗争的对象,并使这场运动演变成为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与反抗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相结合的民族民主运动。随后爆发的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甚至还成为了引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三、收回利权运动的影响、作用及相关问题
清末持续数年之久的收回利权运动,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既是维护国家主权,抵制侵略的重大课题,而且具有争取民族解放,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④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册,第482页。在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与影响。
第一,收回利权运动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反对帝国主义掠夺和清朝封建统治者出卖国家主权的民族民主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的开展,使社会各界民众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得到明显增强。“收回利权运动的唯一目的并非要争回绅商对于路矿的经营权,而是要从根本上争回被列强窃取掠夺的国家主权。‘国权’即主权观念,是20世纪民族主义精神的内核,也是收回利权运动的根本要求”。①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第223页。当时的民众,已经普遍意识到利权即国权,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存亡绝续,因而以高涨的爱国热情,态度坚决地积极投入收回利权运动,并使这场运动具备了显著的新时代特征。即如时人所言:“吾所谓利权思想之发达者,不奇于少数之新党志士,而奇于多数素无学识素无意识之众人。犹是矿也,向之引明季故事以为戒,谓巨资掷诸虚牝者,今则公司广设,市井投资,严屏外人之入股矣。犹是路也,向所指为弊政病国病民者,今乃视为利国利民之要举,已入外人之手,以全力争回而自办,各省既同时举行,而投资踊跃,不数月而股数已尽。粤汉尤为先声之夺人,贾竖乡愚亦知权利资本之输,曾不少吝,此固非少数之新党志士,所能随其后而概加以鞭策也。”②匀士:《论中国近日权利思想之发达》,《东方杂志》,第3年,第9期,1906年10月12日。收回利权运动虽然也具有排外色彩,但却并非如同以往盲目落后的仇外运动,而是属于理性的民族民主运动。“各省收回矿权运动,如与同期间内各省进行的收回路权运动,综合起来看,实为一普遍而深入民间的社会运动,具有十分浓厚的排外性。不过,该项排外运动具有正当的目的,也采用适当的手段,既足以表达当时民族自觉的愿望,又不违背现行国际法的原则,与以前中国官绅迭次进行的反外仇外运动,大相迳庭”。③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第367-368页。
第二,收回利权运动的开展,明显促进了20世纪初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例如在收回矿权斗争的刺激下,中国近代的采矿业有了较大发展。在安徽,呈请开办矿务者接踵而起,“一年之间,商人承办者二十余起”。④《皖矿始末通告书》,第2页。转引自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册,第483页。全国各地著名的商办近代煤矿,如山西阳泉保晋煤矿公司、山东中兴煤矿公司、安徽泾铜矿务公司、四川江合公司等,都是在收回矿权运动中集资创办的。收回路权运动不仅一定程度地遏止了帝国主义大肆掠取中国路权的阴谋,而且促进了中国商办铁路的发展。1903年至1911年,全国成立了16个商办铁路公司,集股达5977万元,兴筑铁路422公里。⑤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第1149-1150页。虽然已修铁路仍很有限,但毕竟开创了中国自建铁路的先河,因而具有重要意义。商办铁路还带动了一些与路工有关的民族工业的创办。“从总的方面看,可以说,收回路矿利权斗争带动了路矿的商办,而路矿的商办又促进和引发了其它民族企业的创办,在此意义上讲,1905年至1908年的兴办实业高峰即是收回利权运动的产物”。⑥刘世龙:《略论收回利权运动对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作用》,《历史教学》,1985年第5期,第21页。如为筹备铁路器材,浙路公司等在汉口发起创办了扬子机器制造厂,张謇等人在通州扩建了资生铁厂,苏浙皖赣四省铁路公司在上海合办了桥车厂。收回利权运动在这方面的连带作用与影响,甚至于外人也意识到:在收回利权运动推动之下,“一方面民间有志之士认为,经营企业是收回利权的最好手段,关系国家命运的兴衰,因此大声疾呼:苟有爱国之心,应起而响应股份之招募。看清了利害的中国人民,当然更不计较金钱上的利害,相信能认购一股就等于收回一份权利。于是争相认购股份,引起了全国到处创办起股份、合伙或独资经营的新企业”。⑦根岸佶:《收回利权运动对中国的影响》,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737-738页。当然,中国收回路矿主权也支付了大量赎款,付出了较大的经济代价。⑧有论者指出:时人即已对赎回利权的代价与效果表示怀疑,并进而“开始有人对赎路中的文明排外的手段也产生怀疑”。参见马陵合:《文明排外与赎路情结》,《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330页。另还有学者认为:“在今天看来,不计代价的利权回收运动并不可取,学界一味对之颂肯,是缺乏理性的表现。”参见苏全有:《对清末利权回收运动的反思——以邮传部收回京汉路为个案》,《历史教学》,2008年第6期,第76页。但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一付出既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具有难以估价的政治意义,有效地遏止了帝国主义通过攫取利权而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侵略行径。因此,不能单纯以一时的经济得失,来衡量和评估收回利权运动的长远影响与作用。
第三,收回利权运动对于工商业者的成长,尤其是对工商业者思想认识的提高,也产生了较为突出的影响。首先,工商业者的爱国激情得以高涨。他们深刻地意识到利权即国权,维护利权即维护国权。苏州工商界人士阐明:“国家之权利,莫重于路政,而权利之竞争,亦莫亟于路政。诚以路线所到之处,即国权所植之处,亦即利权所握之处。”基于此种认识,他们特别强调:“自行筹办,则保路权以保国权,亦即以保利权。”①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第772页。由此可见,工商业者维护利权的思想动机,同时也在于维护国家主权,是其高度爱国热情的集中体现;其次,工商业者对利权得失与民族工商业盛衰以及对其切身利益的紧密关联,也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们意识到只有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才能使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因而在收回利权运动中态度坚决,行动积极;再次,通过开展收回利权运动,工商业者的人民自主观念也显著增强。工商界人士曾明确表示:“国家为人民之集合体,人民为国家之一分子,既担一分子义务,应享一分子权利。虽拔一毛其细已甚,而权利所在,亦不能丝毫有所放弃。苟人人有此观念,国家何患不强?从前胶州、广州、威海各口岸之分割,皆不明此义,甘受政府、外人之愚弄所致,甚堪痛惜。今日拒款风潮如此激烈,足见我民气民权发达之一征,于数千年专制政体上放一光明,诚不禁为前途贺。”②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第797页这样的言论,集中反映了收回利权运动促进了工商业者思想认识的提高。
第四,收回利权运动与清末同时开展的其他政治运动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近代中国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例如,“人民权力意识的觉醒是立宪运动与收回利权运动的内在根据,也是两个历史运动同步相联的深层原因”。虽然收回利权运动主要是经济上谋求自立的民族主义运动,立宪运动则是政治上谋求改革的民主主义运动,但两者联系密切,“相互激荡”。一方面,“立宪派的政治勇气提高,直接有利于推展收回利权运动”;另一方面,“收回利权运动的高涨,反过来又明显地促进了立宪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如此,收回利权运动、立宪运动与辛亥革命也存在内在关联性。③详见耿云志:《收回利权运动、立宪运动与辛亥革命》,《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从整个进程看,收回利权运动与立宪运动几乎是“同时发生,同步进展,并彼此呼应,在1911年合为一流”。1911年5月,“皇族内阁”与“铁路国有”相继出台之后,推翻皇族内阁与取消铁路国有令即成为立宪运动与收回路权运动互为关联的任务。“立宪派一面呼吁改组皇族内阁,一面发动保路运动;他们明揭保路旗号,暗行倒阁之实,将保路运动纳入了争取宪政斗争的轨道”。④闵杰:《清末两大社会运动的同步与合流》,《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00页。很显然,保路运动与立宪运动合流之后,声势和影响均更为突出。
第五,随着收回利权运动的发展演变,尤其是“铁路国有”政策出台之后,立宪派以及工商各界对清政府的不满与愤怒也与日俱增,成为武昌起义之后推翻清王朝的重要社会力量。收回利权运动兴起之初,主要斗争目标是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被其攫取的铁路和矿山主权,清朝各级官府包括中央的商部、农工商部和一些地方督抚大员,曾对此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但在收回利权运动不断发展的后期,清政府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转而顽固推行借款卖路的倒行逆施政策,激起立宪派和工商各界的愤怒与反抗。“铁路国有”政策出台后,社会各界更是坚持抵制,并且与清朝统治者的矛盾日益加剧,将斗争锋芒直指清王朝,使收回利权运动发展成为抵制清政府出卖路权和帝国主义奴役性贷款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立宪派和工商各界认识到清王朝的腐败反动本质,对其幻想逐步破灭,不仅坚决反对清王朝的卖国政策,而且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有相当一部分很快转向支持革命,由此成为孤立和推翻清王朝的重要力量。
以上主要从五个方面对清末收回利权运动的作用与影响进行了简要论述,下面再对两个相关问题略作补充说明。首先是清末收回利权运动的斗争范围问题。长期以来,相关著述在论及收回利权运动时都只谈到收回路权与矿权问题,本篇的具体介绍同样也是如此。于是,给人的印象是收回利权运动仅仅只包括收回路权与矿权的斗争范围。实际上,这种印象与历史实际不无偏差。确切而言,清末收回利权运动除了声势浩大的收回路矿主权斗争之外,还包括有收回邮政权、电政权、航运权等方面的交涉与斗争,只是其声势与影响远远不及收回路矿主权,因而容易被人忽略。
晚清的邮政一直附设于海关,而海关又系外人控制,因此邮政权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外人所掌握。19世纪末,国人即意识到应自设邮政专局以收回邮政权,张之洞、刘坤一稍后也曾在联名奏折中论及邮政收回事宜。1906年邮传部设立,以收回邮政权为己任,然而“事历多年,屡议收回自办,皆无结果”。舆论对此不无批评,认为“收回邮政,正旦夕间事”,“虽设有专部,仍不急行收回,授权于外人”。①《论我国推广邮政之所有事》,《盛京时报》,1909年6月18日,第2版。1909年徐世昌继陈璧担任邮传部尚书之后,摄政王载沣曾表示:“邮政为交通要政,现在预备立宪,诸事均须整顿,应将邮政速行设法收回自办,若常属外人,殊与行政有碍。”②《徐尚书预备收回邮政》,《申报》,1909年10月3日,第5版。在各方面因素推动之下,邮传部对收回邮政权更加积极,拟订了接收邮政的具体步骤与方法。但在徐世昌任上,邮政权之收回仍未实现,再次引起了社会舆论与资政院议员的不满。直至“宣统三年春间,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奏请收回邮政,归部直辖,并竭全力争之”,才“决计收回,定于五月初一日起实行”。③苏全有:《清末邮传部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29-330页。随后,邮传部正式设立邮政总局,开始办理邮政事务。在向海关交涉收回邮政权的同时,邮传部还曾采取措施限制和取消列强在华所设邮政业务。1907年,“邮传部议将全国邮政收回自办,所有外洋邮件均归中国邮局传递,而英、美、德、法、俄、日各使亦照会外务部,定期会议邮政办法”。④《外交报》第194期,交涉录要,第13页。转引自苏全有:《清末邮传部研究》,第333页。随后,中日之间先达成协议。“邮传部宣布,凡日俄二国邮件,不许私由铁路递送,应照光绪二十九年三月清日邮件条约第八章一律付寄清国邮局”。⑤《邮部限制日邮》,《中国日报》,1907年11月22日,第2页。至1909年,“凡各国在内地所设邮便局、书信馆,关于华文往来信件报交华人者,不得再由各国代收代递,均归大清邮政局自行收递”。⑥《外交报》,第283期,外交大事记,第15页。转引自苏全有:《清末邮传部研究》,第334页。
电政权主要指的是电话、电报线的修建及其经营使用权。在清末的最后几年间,中国曾与俄国、日本、德国、英国相继交涉收回电政权事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与俄国的交涉主要是北满军线、京恰线派工程师及傅家店违约寄电问题,经多次谈判,俄国允许将东清铁路界外军线电局,交还中国管理;与此同时,中国要求日本也将东清铁路界外之军线撤除,但日方置若罔闻,邮传部“咨行东三省总督,饬知满洲中国各电局,不与日本电局交接”。后通过多次交涉,中国付给一定数额的赎金,与日方议订接收南满洲电线合同,宣统元年 (1909)正月开始接收,“历时三月,始克竣事”。1907年,中德签订青烟沪水线交接办法合同,规定所有德营电话电报线售还中国,具体包括塘沽至津京电报线、塘沽车站至白河口林白格住宅之电话线及天津电话线,1909年交付完毕。与英国的交涉主要是阻止英商在上海租界外擅设电话和无线电报,“以维电政”。此后,清政府反复强调:“无线电报,无论何国何人,均不得在中国境内设立,业经按照各国定章,奏明通行在案。”⑦参见苏全有:《清末邮传部研究》,第335-343页。
航运权是指各国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沿海和内河从事航运的权利。从鸦片战争缔结《南京条约》到20世纪初订立中外通商行船续约,其间清朝政府与各国签订了诸多涉及航运权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不仅丧失了沿海与各商埠的航运主权,而且连非属通商口岸的内河航运权也一并旁落外人之手,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恶劣后果。⑧参见李国华:《近代列强攫取在华沿海和内河航行权的经过》,《史学月刊》,2009年第9期。当时,即有人意识到此种危害,提出收回航运权的主张。宣统元年 (1909)十一月,清朝邮传部为争取利权,制订《各省大小轮船注册给照暂行章程》,规定华商轮船向该部注册获取执照,海关不得径发船牌或执照,其目的是以此接管海关的航运行政权。不过,近代中国航运权的收回,经历了较长的过程,在清末仅仅只是一个发端。
第二个问题,是继清末收回利权运动高潮过后,进入民国时期收回利权思想与行动的长期延续,由此也可看出收回利权运动在近代中国的持久影响。以往的中国近代史论著,谈到收回利权运动都只限于20世纪初期的10年范围,似乎在此之后收回利权已不再为人提及。实际上,收回利权运动在清末经历了发展高潮之后,到民国时期仍然一直是社会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
例如1926年赵祖康发表纵论我国交通权丧失之系列长文,将1912年至1921年划为“利权重创时期”,呼吁国人继续重视利权丧失之严重危害,挽回利权。①赵祖康:《从利权得失观划分中国近世交通史之时期》(收回交通权刍议之四),《南洋季刊》,经济号,1926年第1卷第3期。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仍不断有人提出中国宜振兴土货以挽回利权,“盖土货一兴,即能抵制外来之货,外溢之利,皆可挽回,而利权不失矣”。②顾骏昂:《中国宜振兴土货以挽利权》,《钱业月报》,1927年第7卷第7期。在1928年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上,又有代表提交“振兴国外贸易以兴利权案”,阐明三大具体措施。一是“自开航路”:“中国航业不出国门一步,而欲谋对外贸易者,从何做起?应请财政部发行航业无记名股票二千万元,由财政部负责保息,组织对外航业公司”;二是“请财政部令饬国家银行指定基金,扩充国外押汇,优待押汇事业,以利国际贸易之汇兑”;三是“办国际贸易之检查所,凡运销于国外物品,物质上之是否合乎买主定货单,度量衡之是否准足,非经检查给据,不得起运,以固贸易之信用”。③《振兴国外贸易以挽利权案》,《全国经济会议专刊》,1928,第462-463页。
收回航运权的呼吁与行动,在民国时期甚至呈现出日益高涨的趋势。“吾国海岸线之长,逾七千浬。长江可直航轮船之水道,达一千六百浬,而支流相通之水道,复满布全国,故沿海内河之航权,实为吾人之生命线。此项权利,倘一日不收回,匪特剥夺我资源,制我经济之命脉,抑且影响国防,阻我民族之复兴”。④王洸:《航权收回之前后》,《交通建设》,1943年第1卷第3期。民族资本航运业的呼声尤为强烈,民国《海事》等杂志曾经刊载大量相关的文章和报道,从中可见一斑。航运业阐明“中国各海口及长江引水权,操诸外人,与各种不平等条约,同一危害”,要求政府“速制定法规,将国内引水业务,按国际通例,迅行收回,以保主权”。⑤《船业呈请收回引水权》,《海事》,1931年第4卷第11期。有的还提出收回航运权的具体步骤,定三年期限,分为三期,逐步收回航运权。第一期收回内港航行权,第二期收回江河航行权,第三期收回一切沿岸航行权。与此同时,中国应预先制定船舶国籍法。⑥陈柏青:《关于航权收回之商榷》,《航业月刊》,1930年第1卷第3期。还有人特别指出收回航权之重要意义:“最近收回航权运动,亦随中日改约而起,在此运动期中,吾人不可不细察各国在华享受航业之特权。”各国列强大肆攫取航权,“凡我国沿海内河外航足迹之所到者,均为其间接的投资地,彼等货物之运转畅销,实为我国经济被榨取之一大原因,间接的,则使我国内乱不息,与工商业之不发达,故我国航权收回,实有急不容缓之势”。⑦《航权收回运动应有之认识》,《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1930年第1卷第11期。
交通部也曾表示:“中国航业衰落,实受外航压迫影响,今后当本国际平等原则,收回航权。”⑧《出价收回内河航权》,《海事》,1931年第4卷第8期。其所设想的具体办法为:外商在中国领海内航业公司,出价收回;或由中国出资,暂时合营,但名称及主权,由中国支配,外股定期还清。海军部、交通部以及考选委员会还曾联合拟定引水人考试办法,并创办引水传习所,以此办法培养本国之引水人,改变“外人喧宾夺主之情势”,“期于最短时期能完全收回”。⑨《海交两部积极准备收回引水权》,《工商半月刊》,1931年第3卷第16期。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有关各部召开收回航权会议,商讨实施大纲。1931年7月,交通部设置各地航政局,将海关代办之船舶登记检查丈量等事务,收回自办。“自此以后,我国始略有航政可言”。但是,海关兼办之航路标志、港道工程以及引水管理等事务,仍未能一并收回。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2年10月,国际形势出现新变化,对中国较为有利,交通部又提出收回航权节略,内容包括收回沿岸贸易权、内河航行权、收购英美在华船舶栈埠、收回引水权。随后中国与英美签订包括上述内容在内的新约,终于基本上收回了丧失数十年的航运权。于是,“主权归来,我航界同人,亦一舒往日窒息之气,前途光明,灿烂无穷。”但时人也意识到:“然一念如何振兴之道,百端待理,百事待举,诚非一蹴可几 [就]。”为此需要“加强航政机构”,“储养人才”,“树立造船基础”,“商定发展航业方案”,“准备自办引水管理”。⑩王洸:《航权收回之前后》,《交通建设》,1943年第1卷第3期。
上述情况表明,论及近代中国的收回利权运动,不能仅仅只是关注清末这一运动高潮时期,还需要将研究时段向下延伸,重视对民国时期收回利权运动延续与发展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