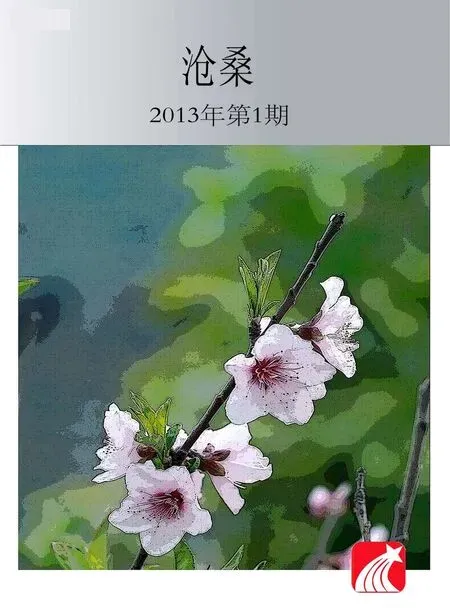秦史误读与汉初礼乐文化的重塑
2013-04-10赵鹏团
赵鹏团
秦史误读与汉初礼乐文化的重塑
赵鹏团
秦朝灭亡后,儒家摆脱了长期受法家压制的处境,迅速振兴。汉初儒生主观上对秦史作了误读,片面地将秦亡的责任归咎于纯任法制。陆贾、叔孙通、贾谊、晁错、辕固生等儒生或受到儒家学说熏陶的士人在汉朝基业草创期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几代帝王产生了较大影响,逐步扶正了儒学在当世学术中的主流地位,确保了儒学取代法学成为当政者推行的主流意识形态,为礼乐文化在汉代的重塑奠定了基础。
秦史误读 汉初儒家 礼乐文化 重塑
秦朝从建国到灭亡,前后仅十五年。因为它是封建井田制度消亡以后建立的第一个专制政权,又因为其存在时间很短,所以秦朝的灭亡原因一直受到后世的关注。汉朝建兴,士人特别是汉儒纷纷将秦朝灭亡归责于苛刑酷法,认为秦廷刻薄寡恩、不行仁政是其迅速灭亡的根本原因。由于在秦亡后,儒家迅速确立了其正统地位,所以汉儒的言论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两千多年时间里,秦朝厉行法制而亡常常成为推崇仁政礼制的重要反证。直到当代,部分研究者也认为秦朝二世而亡是因为它的纯任法制。
但是当我们仔细分辨,不难发现,汉初儒家认为秦朝亡于苛刑酷法的观点,与其说是误判,毋宁说是一种主动误读。其背后反映的,正是儒法两家的激烈争斗。笔者认为,当时朝廷法度由秦朝“以吏为师”向汉朝“独尊儒术”的转变,不仅是统治者的主观选择,也是两个学派势力的此消彼长。
汉初儒家对秦史的误读
秦国由商鞅变法而强,商鞅后来虽然被车裂,但他所创立的法制和他的法制思想却深深扎根在秦国,对秦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秦国始终奉行法家思想、厉行法制,是其能够蚕食六国、统一天下的重要原因。秦朝建立以后,挟大胜之威,更加坚信法家思想的不可替代,废分封而实行郡县制,坚持以法治天下。秦汉时文献中多有对于秦廷苛法很多记述,如《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胜、吴广起义,就曾分析说:“失期,法皆斩。”[1]近年来,云梦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等地下文献的出土,更加印证法家在秦朝的地位。法家地位的盛隆,客观上就是对儒家学派的一个重大打击。秦朝建立后,李斯更是借淳于越等博士议政的机会,提出了“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2]的建议,亲身参与策划了焚坑之事。虽然焚坑之事未必专门针对儒家,但儒家作为当世显学,首当其冲,被祸极深。李斯所要求禁绝的《诗》《书》等,也正是儒家经典。这就进一步激化了儒法两派之间的矛盾,也为秦亡汉兴以后,儒家有意识地攻击法家学说埋下了伏笔。
而儒家对法制的攻击,实际上一直就未停止。那次被李斯作为由头来禁绝诸子学说的博士议政中,淳于越齐人的身份,就决定了他很有可能是儒生,或者说是深受儒家学说影响。他对秦始皇的建议就是:“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3]这是典型的恢复商周封建礼制的言论,深契儒家之道。由此可以推断,在秦朝统治过程中,儒法之争也从未停止,只不过法家始终占据上风。李斯要求禁绝百家语,一方面确实是法家做派;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借机消除来自其他学派、特别是儒家对统治者的影响,以保障自己可以长享富贵。
秦亡以后,法家迅速失势,成为国家灭亡的替罪羊,而儒家也就借势复兴。《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4]陆贾在这时就明确提出秦任法而亡、王者行儒道则兴的理论。
此后,汉朝基业草创,贾谊即系统地提出废苛法、行仁政的儒家学说。在《新书·过秦上》中,他首先提出秦亡的理由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5]接着在《过秦下》中,他系统论述:“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故其亡可立而待也。”[6]在明确法家亡秦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只有行儒家仁义之术才能转危为安:“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7]《过秦下》中,他分析要避免重蹈秦政的危局,只有弃法制而行儒术:“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赈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循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盛德与天下,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唯恐有变。虽有狡害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弭矣。”[8]
汉宣帝即位初期,守廷尉吏路温舒对汉初儒家的这一理论作了系统阐述:“臣闻往者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吏是也。昔秦之时,灭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谓之诽谤,揭过谓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誉谀之声,日满于耳,虚美熏心,实祸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9]至此,法家彻底戴上了亡国的罪名。
从以吏为师到尊崇儒术的转变
汉初儒生对秦朝灭亡史事的分析,与其说是错判,不如说是有意误读。他们虽然也常常提及秦朝施政的暴虐:如贾谊在《过秦下》中提到:“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赋敛无度……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10]刘向在《说苑》中也多次记载秦始皇劳役民力、暴敛无度:“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侈靡。即位三十五年,犹不息。治大驰道……营作朝宫……为复道……又兴骊山之役。”[11]但却始终没有正视秦亡的根本在于征敛无度,总是有意无意地将责任推向法制,将一切的祸根归结于秦朝的纯任法制而仁义不施。他们认为,任法而治必然导致横暴之政,惟有以仁政治天下,才能收取民心,长治久安。汉儒所制造的这种舆论,对于汉代治国方略的逐步形成,无疑具有较大影响。
此前的研究,往往倾向于认为,汉初帝王崇尚黄老学说,以无为治天下。实际上,汉朝建兴之初,身为新兴王朝的统治者,他们往往本能地忌惮与秦亡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法家学说,而容易倾向于与法家明显对立的当世显学——儒学。并且,诚如后来的汉宣帝所言:“汉家自有法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12]宣帝虽然表明了施政决不能纯任儒术,但儒术在明确上下等级、维持尊卑关系、麻痹士人思想等方面,确实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自刘邦开始,儒学就逐步受到重视。厉行儒术,并不是汉武帝时才突然开始的,在此前就已经逐步显现。
笔者注意到,秦亡后,活跃在汉初几位皇帝身边的士人,相当一部分是儒生或者深受儒家学说影响,诸如陆贾、叔孙通、伏生、贾谊、晁错、辕固生等,他们往往受到帝王器重,在汉朝基业草创和巩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汉朝治国方略逐步从秦朝的以吏为师转向尊崇儒术。陆贾对刘邦的影响,上文已具,兹不复述。与其大约同时的叔孙通为汉高帝刘邦制定朝仪,使刘邦感叹:“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13]叔孙通从实用的角度,实实在在地向刘邦展示了以儒术治天下的重要性。
文帝时,对儒学的重视进一步加强:“天下无治尚书者,独闻济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余,老不可征,乃诏太常使人往受之。”[14]后来,太常根据文帝的旨意,派遣晁错前去向伏生学习《尚书》。晁错学习归来,还专门依据儒家学说向文帝上奏施政方略,“还,因上便宜事,以书称说”[15]。晁错作为文、景时的重臣,特别是能受景帝重视,虽然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精通法家学说,但与他师从伏生学儒术的经历,也应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对文帝的“以书称说”,显然也说明晁错受到了儒家学说的影响。那么,在与两代帝王的接触当中,无形当中,晁错也应当加深了文、景二帝对儒学的认可。
略早于晁错的贾谊,更是以儒学著称,并且深受文帝赏识。虽然贾谊本人未能位至公卿,但世人都默认了他,特别是他在《新书》所提出的推行仁政、完备仪礼制度、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等一系列施政方针对汉朝产生深远影响。贾谊的出现,显然对于汉初统治者产生了较大触动,客观上也有力地奠定了儒家学说的主流地位。
景帝时,除了任用晁错外,还对纯儒家出身的辕固生青眼有加。辕固生和黄生关于天命的当庭辩论[16],起码直观之下证明了儒家学说更能维护汉家江山的合法地位。后来,窦太后因为辕固生轻视黄老学说而逼他下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17],这一细节说明景帝对辕固生的格外照顾。后来,景帝拜辕固生为清河王太傅,就更说明他身为统治者,并不排斥兼用儒术治天下。
到了汉武帝时,他继位初年就“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18],并且批准丞相卫绾罢黜“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19]的建议,拉开了儒家学说成为西汉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序幕。
小结
综上所述,秦朝灭亡之后到汉武帝确立儒家主尊地位之前这一段历史时期内,一直充斥着儒法两家的争斗。由于法家与秦王朝的密切关系,客观上导致了汉初统治者对于施行法制的顾虑。儒家趁势而起,利用继起王朝统治者的顾虑,通过对秦史的有意误读,将秦朝灭亡归咎于任用法家学说,从而在两派争夺政治主动权的斗争中始终占据上风。同时,儒学作为当世显学,师从者甚多,汉初几代帝王始终受到身边儒生的直接影响,特别是叔孙通为刘邦制定朝仪、贾谊为汉代奠定治国方略、晁错对文景两代帝王的影响等,以及儒学作为当世显学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力,都促进了汉初帝王对儒学的认可。直到汉武帝时,儒学经过长期的努力和积累,终于正式走上政治舞台。儒学的振兴,确保了礼乐制度在汉初得以重建,中国礼乐文化的正统地位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正式确定。
[1][2][3][4][13][14][15][16][17]司马迁撰.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950,2546,2546,2699,2723,2745,2746, 3122,3123.
[12][18][19]班固.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77,155,156.
[9][11]刘向.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103,516.
[5][6][7][8][10]贾谊.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3,14,14,15,15.
赵鹏团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助理研究员
(责编 陈锦慧)